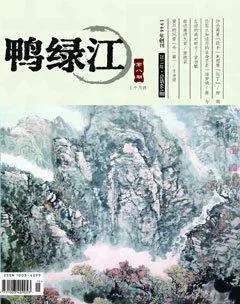老去的村庄
2011-12-31邵卫花
鸭绿江 2011年8期
邵卫花,1974年生,江苏昆山人,笔名玲珑诗芸。昆山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文学界》《翠苑》《教师报》等报刊杂志。
人会老,树会老,万物会老,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会老。就连那沉寂于低洼之处的小溪,也会经不起日月的打磨,渐渐萎缩干涸;孤坐草丛之中的岩石,也抵不过风雨侵蚀,日益松散风化。老,是归宿,是面对时光潇潇洒洒地流逝而无可奈何地放弃。
村子,在形成之前,可能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蛮之地,除了野草外,就是黑褐色的土地;也可能是一片茂密的丛林,枝繁叶茂间,野禽出没;抑或是一片鸟语花香的原始绿洲,郁郁葱葱,姹紫嫣红。它们都是原生态的、自由的、随意的,无所谓繁荣与沧桑,也无关年轻与暮年。在某天,有流浪的人至此, 安营扎寨,生儿育女。缕缕炊烟升起的那刻,村子便诞生了。
人的一生走完了,村子还在。从最初简单困乏,人烟稀少的原始状态,到繁杂富裕,房屋密集的状态,其间经历的虎啸龙吟,风雨沧桑,只有村子自己知道。村子无言,也就无从猜测,更不能枉断。
笼罩村子的光阴里,有生命老去,也有新生命的补充。村子的新陈代谢,让它以自己成长的方式往前迈进。
与外面的世界相比,村子是落后的。外面的路宽,外面的楼高,外面挣的钱多,外面的生活舒适。离开村子的愿望就像瘟疫一样,在空中飘荡着、传递着。“离开这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外面去。”有声音热切地召唤着村子中的男人女人,也使他们抛弃了养育他们的村子。这一走,毅然决绝、义无反顾。那座亲手垒起的院落,那棵亲手栽种的杨柳,那片倾注了汗水的土地……都挽留不住那些躁动不安的心,也牵扯不住那些匆匆离开的脚步。
村子,失去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也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作为生存之根的村子,越来越空虚。倘大的村子,倘多的房子,稀疏的人。在这里,时间失去了意义,空气也仿佛静止了一般,任凭外界风云变幻、斗转星移,村子毫无知觉。失去了流动的人群,它也就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村子,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呆滞、迟钝、僵硬,永远不能回归年轻时的风采。像那些遗留下来的老人。
夜幕降临了,曾经的万家灯火之景不复存在。村子沉浸在一片黑暗中,无声的世界仿佛已经睡去。偶尔闪出的一点灯光,也微弱得犹如风中的蜡烛,转眼就无力地黯淡下去,隐身于无边寂静中。
虽然村子老了,承载不了青年人的梦,但村子却包容着老人,村子需要老人给它以支撑,给它以微弱的呼吸。老人也依恋着村子。老人需要村子的气息,那些即使闭着眼也能准确判断出长短的弄堂,不用数也能知道级数的石桥,不用舔就能尝到的略带湖水湿气的空气……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屋一堂,都是老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他们不愿面对城市中满天都灰蒙着的脸,他们不喜欢嘈杂纷乱的人生乱象,他们也忍受不了儿孙辈们的浮躁。如果让他们离开村子,他们会不知所措,会无所适从。他们宁愿安静地在村子中,在几近停止的时间中消磨所剩无几的人生。
晴天的时候,晒晒老衣,坐在太阳底下,边抚摸手上的玉镯子,边回想儿孙绕膝的情景,想着想着,脸上竟也漾起了笑意。有雨的日子,端个凳子,细数门前雨帘的疏密,静听雨滴落入池塘的声音,似乎要从那错落有致的滴答声中听出一家欢聚的笑声。如若有兴致,也可走进老人活动室,去看不管有没有人看却始终开着的电视。每天的生活,如此缓慢而沉乏。
当然,村子也有热闹的时候。年末岁初,那移居城镇的人,纷纷赶回村子。一辆辆闪亮豪华的车子,穿越了亲情通道,他们要把一年积攒下来的孝心倾倒出来。村子里弥漫着祥和、团圆和美满。安静、沉默已久的村子,突然间沸腾起来。涌动的人流,喧哗的人声,点缀着村子的角角落落。然而,这样的场景是短暂的,当人们散去,感觉就像是个美丽的梦幻。
凝固的村子越来越空洞。孤独的身影徘徊在虚空的村子里,四面八方涌来的是寂静,静得耳朵都能听到那“嗡嗡”的耳鸣声。
村子中的老人,越来越老。到这些老人都故去的那天,村子就失去了那股引导亲情的绳索,在外的游子,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责任编辑 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