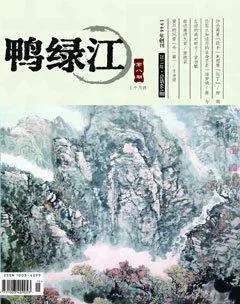半岛手记
2011-12-31盛文强
鸭绿江 2011年8期
盛文强,1984年生于青岛,现居滨州。作品多见于《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读者》《青年作家》《黄河文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西南军事文学》《散文诗》《阳光》《岁月》《散文世界》《文学与人生》《中学生阅读》《微型小说选刊》《小品文选刊》《文学天地》《读者俱乐部》等刊,有作品入选《2010中国散文年度佳作》《学生典藏散文全集》等十余种选本,有长篇散文《黑鱼精的夜晚》。
父亲的茶
父亲上船之前,回家里带了几件衣裳,胡乱塞进网兜里,刚出门又踅回来,到里屋找出一个崭新的搪瓷茶杯,父亲把杯子端在手里,轻轻转动着,在杯壁上看到自己的脸被抻成了麻花似的瘦长条,忍不住笑出声来。谁也没有想到,光滑的杯子暂时充当了一回魔镜的角色,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先照见了父亲以后十几年的畸形生活,而且远比镜像中的变形还要滑稽。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在意,转过山墙,飞身上了车子,通向村口的道路已然在他脚下稳稳地铺开,不远处的海跳跃着,他蹬着车子,也随着海的节奏一起一伏,在他眼前不住地闪现出海鸥、飞速旋转的马达叶片、在船板上扑腾的梭鱼。从那一天起,茶杯正式跟着他上了船,杯子和他的命运重合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用了没几年,搪瓷杯的天蓝色釉子暗了下去,杯沿上有了一大一小两个豁口,露出了里面的黑铁内芯。父亲每次回来,我们都听到杯子响,他的杯子随身带着,装在纺绸的布袋里,绾了几道就挂在车把上,一路叮叮当当,掉瓷的地方,就是和自行车碰了一路。杯底还有一块掉瓷的地方,指头肚大小,杯子倒满水时,它就沉在水底,长年累月,不住投射出充满铁锈的黑烟,一杯清水变得乌云密布,杯底的茶垢丝毫没有盖住它,喝下去呛得咳嗽。搪瓷杯已经老了,它老得太快,当我再次看到搪瓷杯时,它就像一个远行多年的朋友,风尘仆仆回到了我们身边,在异乡寒冷的秋夜里,我想到父亲正双手攥着茶杯取暖,他一个人独坐时,常常含着一口茶水久久不愿咽下,月光照在他高高凸起的双颊,四围是滔天的白浪,那一刻,船如此之轻,二十米的船身如同草芥,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父亲能够握住的,只有这一杯不断消散着的温热。
秋天的夜晚,船在海湾里穿行,一船人裹紧了夹袄,昏昏欲睡,夜渔的寂寞最难熬,很多人熬不住,纷纷上岸了。从那时起,父亲喜欢上了酽茶,不知什么名字的劣质茶叶末,铺满了小半杯,灶上拎下铁壶浇透,一会就能喝了,茶水暗红,冲的次数越多,颜色越重,起初还能看到茶叶末翻转,到后来满杯浊浪滚滚,茶叶末被盖住了,新杯子只需一次就会完全变色。八岁那年,我第一次到船上,端起父亲的茶杯喝了一口,就呛出了眼泪,一股浓烟钻进喉咙里,分明是茶叶末燃烧生出的烟,细小的茶叶末灌了满嘴,纷纷撞在舌头和腮内,急切中咽到了肚里,嘴里的余茶还在,这时才咂出些香味,是烤白薯的焦香,还有开水的灼热,忽觉两耳一炸,再听船外的风浪声,似乎听得更真切了。这时才发觉鬓上沁出汗来,精神也凛然一振,出了船舱见了凉风,才觉出齿间生寒,舌尖上顿时粘满了滑腻的茶香。父亲从我手里接过杯子,一仰而尽,他的喉结一颤,惹得我喉咙痒痒的,我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却是平的。父亲说,他的喉结是喝茶喝出来的,我再也不敢喝他的茶了,就连装茶叶的铁筒也不敢碰一下,生怕长出他那样的喉结来。后来才知道,就算不喝他的茶,也能长出喉结来,很多事情总是难以避免。
夜里,我在舱里睡下了,父亲和他的伙计们还在坐等。此时的海面平静,月亮被雾气盖住了,海水和天都是漆黑一片,小船浮在虚空里,没有人说话,只有茶水下肚的咕咚声。这样的夜晚,不知要喝下多少茶水,才能在寂静的夜里醒着。忽然有人喊道:来了。再看水面上翻起了白花,那是成群结队的银鱼浮出水面觅食。于是下网,“嗨哟哟”的号子声不绝于耳,我在号子声中睡着了。直到喊声停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我才忽然惊醒。父亲只穿着一件背心,臂膀上沁出了汗珠,他正在一杯接一杯地喝茶,壶里的水好像永远倒不干,他喝起来也永远不知疲倦,我忽然想到,他身上的汗珠就是茶水变的。从铁壶长颈里冒出的水柱闪着亮,弯成了绷紧的弓背,看不出它在流动,而它的末端却蹿进茶杯里去,搅得灰尘似的茶叶末飞起来,它们带来的喉咙的阵阵瘙痒,还有忍不住的咳嗽,与此同时,升起的热气把茶香散满了船舱。父亲转过脸来看我,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热茶发出了微弱的亮光,勾出了他的轮廓。他把茶杯交在左手,不住摇晃着右臂,肩膀的关节忽然发出一声闷响,恰似一只弩箭射中了木板做的靶心,震荡出的尾音还在扑棱棱抖颤,总会让围观的人群暗暗地吃了一惊,你知道,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终于,父亲从船上下来,渔网改成了天井上空的天网,茶杯也端回来摆在茶几上,这时,我也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半岛,我们有时间坐到一起喝茶了。午饭过后,院子外的槐树下,两把躺椅,两个茶杯。我小心喝了一口,却并没有当年的苦涩,十几年的时光把它冲淡了。父亲想到了夜渔的困倦,还有海上行船的无聊,那些年他坐在船板上,把鱼从网扣里拽出来,眼前很快就模糊了,眼皮不由自主地合上,无数的银鱼在他眼里变成了一条鱼,就是这一条鱼,怎么抓也抓不到,幸好有一条鱼在他的指间抽搐,这才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他知道,需要来几杯茶了。我讲到了办公室的疲惫,坐在纸堆里也常常眼前发黑,直到手中的笔掉在地上时才会惊醒,父亲说,这太像了,我们相对苦笑。
我们在树下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是谁在这长眠中不经意醒来,听见老式座钟报时的颤巍巍的钟声,大门两侧的石狮低吼,父亲的躺椅空着,桌上的茶缸还在,冒着丝丝热气,舌尖还有丝丝缕缕的茶香,树叶间落下几块斑驳的阳光照在茶杯上面,耀眼的白,杯沿上有几个缺口,我一眼就认出了它。身后的宅院也是似曾相识,石墙的缝隙里抹着水泥,每一条石缝的走向我都了然于胸,好像前生就见到过。
守庙人的黄昏
鱼骨庙是岛上唯一的一座庙,庙中供奉的是东海龙王的三太子,历经元明清三朝,香火不断,是渔家祈求丰收的地方。同行的朋友听着我的介绍,不住地点头。说话间我们转过围墙,来到了南面的山门,几架飞檐横在半空,透过朱红的廊柱,远远望见山门内有三间大殿浮在高坡,在风中摇曳,荒草中蹿出三条土路,长蛇般急匆匆掠过,凌厉的曲线让人心惊,它们是绿色背景上的三条黑线,从山门撒出,分别系在三座大殿的门槛上,整个庙才稳稳地固定住,没有破空飞走。我们从最中间的小路走上去,这时他从偏殿探出身来,只打开半边门,青布褂衬在朱红的铁门上,格外显眼,我们赶紧停下了。他是守庙人,前山的地,后山的果园,都是庙产,需要有专人看护。我给朋友们介绍,朋友点了点头。
守庙人已经降到台阶上,他从高处弯着腰往下看,我们抬头正好和他来个照面,他看见我忽然愣住了,肿胀的眼皮撩开,指着我说:你是不是认得我?我看到他帽檐下露出了额头上的黑痣,也愣住了。我说,认得,如果我没记错,你应该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他冲下台阶,紧紧抓住我的手,全身的重量从台阶高处斜压下来,我倒退了一阶,才有所缓解,他原本高大的身躯弯曲着,现在和我基本持平。我们在此相遇,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十八年前的事情。
十八年前寒冷的冬夜,父亲出海,母亲去邻居家串门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家。他踩着雪来到院里,大声叫着父亲的名字,那时的夜晚安静,他的声音被雪地反射,传出去很远,我听出是他的声音,急忙答应着,他已经推门进了屋,落满雪的毡帽先探进门来。我正在小炕桌上写作业,胸口抵住桌子边,一笔一划写生字,写了十几页,炉火在不知不觉中暗下去,我把炕桌顶在胸前,被子围在身上,他进门一看就笑了。他问我冷不冷,我点点头。他在火炉里加了煤,火炉马上呼呼响起来。你在家里都觉得冷,那你爸在海上冷不冷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扶了扶帽檐,帽子上顶着一层雪,却并不摘下来拍打。父亲曾说他是个秃子,三伏天也不摘帽子,睡觉也戴着帽子,我仔细看过,他毡帽下没有露出鬓角来,他笑着等我回答,我又点了点头。这时火炉旺起来,炉子盖都烧红了,顶棚上照出了环形的光亮。父亲迟迟不回来,他起身要走,出门前对我说,也没什么事,过来看看,他们回来时,不用说我来过。我在玻璃上,看见他踩着雪,走出了院门,他踩着雪咯吱咯吱的声响渐渐远了,像是去了遥远的国度。转过年来,我到外地上学,很少见到他,只记得他在那天晚上给我送来了火炉里的烈焰,由远及近,马蹄般哒哒作响,响彻寒冷的冬夜。
他在海上四十年,闭着眼就能甩出网,网口落水时是光滑整洁的圆形,收回来就是鱼虾满船乱跳。据说他跟龙王结了仇,进鱼骨庙的正殿总被门槛绊倒,一次也不落。他把脚抬高,门槛也跟着长高,躲也躲不掉,有人看见他绊倒在地,帽子也跟着落地,露出了他油亮的秃头。这才是最让他恼火的事,后来他干脆不进正殿,只在偏殿后面的厢房住着,庙里的两个和尚也怕他冲撞了龙王三太子,不让他到正殿来。有一天晚上,他怎么吃都吃不饱,连吃了十个馒头,肚子里还是咕噜噜直叫,能吃的东西却一点也不剩了,他活了这么大年纪,头一次遇上这样的怪事。他走出偏殿,路过正殿时,忽然看见龙王三太子驾前的龟精,肚子高高鼓起来,龟精斜眼睛瞅着他,嘴角掠过一丝冷笑,由于是强忍着的笑,听不到笑声,只看见胡子一翘一翘的。他心里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一定是龟精把十个馒头挪进肚去了,他只能暗气暗憋,回去忍着饿睡下了,睡到半夜,却被胀醒了,撩开被子,眼见着肚子气球一样鼓胀起来,一直胀到了嗓子眼,他扶着床吐了一阵,先前吃进去的十个馒头都吐出来了。他知道,这是龟精想赶他走,几十年来,他捕捉水族无数,龟精这么做还应算是客气的了。
铺盖卷成圆筒,拦腰捆了几道,他坐在床板上点着了烟。一支烟抽完,他想到了生病的老伴,还等着钱看病呢。要在以前,他下海甩上几网,多少都能换回钱来,而如今举笤帚都觉得费力气了,漫长的岁月不光带走了记忆,也把他的力量带走了。他解开了捆扎铺盖的绳扣,一点点铺平,忍怒躺下,怎么也睡不着,唉声叹气到半夜。有时候,龙王三太子半夜里听到他的叹气,从神台上一个空翻跳下来,落地时脚尖先点地,悄无声息,三太子在神坛上坐了一整天,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活动活动,顺便把贡品全都吃光。于是,他在夜里听到咯吱咯吱的声响,那是三太子开启巨口,囫囵吞掉了供桌上的猪头,正在嚼着脆骨,他叹口气接着睡。因为守庙人知道,第二天和尚们看见猪头没了,准会赖到他的头上。第二天早上,他当着和尚的面分辩说,猪头是被三太子吞了的,几个和尚大笑,以为他疯掉了,过了几天,又有猪头消失,他逢人就说,猪头是和尚偷吃的,他看到和尚嘴上油光光的,和尚们听了又是哈哈大笑——和尚是不吃肉的,怎么会吃猪头呢?再说了,以出家人的戒律,怎会偷吃呢?所以,猪头不见了,这事只能是他干的。他说不过这些和尚的。
在山门前,几杆牙旗呼啦啦直响,青石牌楼外,成片的屋顶鱼鳞状排列着,渔村是一条滚动着的大鱼,每每勾起他对海上往事的回忆。再远处就是弧形的海湾,散着几点白帆。他指着远处,回过身来拉住我的手,流着泪说:没想到,一辈子大风大浪,没死在海上,回头来倒要死在这里了。我的眼泪也下来了,这座危险的庙宇,怎么会有他的容身之地呢?
我仿佛看到了虚掩的大殿之门,龙王三太子嚼着脆骨,吐了白花花的一地残骸,龟精的肚子胀到了神坛之外,黑铁的甲胄一片片立起来,嘴角还挂着诡秘的笑。守庙人藏在门外,把这一切都看到了,却又无可奈何。也许三太子和龟精们故意表演给他看,这出戏只有他一个观众,但演员们还是演得津津有味。他只能叹口气,然后回去睡觉。这么多年来,我也常常叹口气,然后回去睡觉。
上岸
我们的船靠了岸,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收获。和我们同时回来的还有十几条船,大家都忙着分拣货物,分别过秤。这些船都是相隔不远的几个村子里出来的,平时走在街上都能遇到那些船上的人,互相点头问个好。所以在船靠岸时,不时有串门的跳过来看看收成,顺便聊上几句。每一个跳上船的人都带来一阵剧烈的摇晃,主船上的人难站稳,不留神会被晃倒在船板上,甚至掉进水里去,我望见有人要跳过来,就提前做好了准备,在他的脚刚落在船板上的时候,我赶紧跳在半空中,把这一阵突然的震颤躲过去。左舷有一位胖老叔早想过来瞧瞧热闹,他看我躲来躲去的样子,再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肚子,也不好意思往这边跳了,我长出一口气。
专门贩卖海货的小贩们早就在等着了,码头上一排探出密匝匝的脑袋,那是一排多么熟悉的脑袋,有几个上年纪的人已经在那里干了一辈子。他们在码头上放下绳子,放到船上来,绳子头上拴着铁钩,我们就把货物勾住,然后高喊一声“起”,圆滚滚的一整包的鱼虾就飞升了。这是个力气活儿,两手交替着往上提,所以在我们看来,货物在空中一顿一顿,在上升的过程中,装货的网兜总要转几圈。父亲手搭凉棚往上看了看,低头对我说,小贩们用的绳子太差劲,动不动就拧了劲儿,我宁愿相信是鱼虾在挣扎,他们细小的腿和身子一起动作,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可惜尼龙绳织成的网兜过于结实,小鱼小虾即便合力也难以挣破,只有艰难地旋转。货物包里不断落下水滴,有的是从海里带上来的海水,还有一些是鱼虾吐出来的水,滚圆的球状水滴坚硬如钢珠,砸在头上嗡嗡作响,遥远的回声在耳鼓回荡。许多年来,我们开始试着躲避落下的水滴,并且学会了在水珠之间穿行——侧着身切进两个水珠之间的空隙,衣襟紧贴着水珠掠过去,稍有不慎就会碰到身上。从远处看,我们的身子晃来晃去,全然没有规律,而且呵欠连天,昏昏欲睡,在外人看来,我们心不在焉的躲闪居然准确无误,足以让他们惊奇,其实我们早已厌倦了这种躲避,几个上了年纪的水手在海上连续航行了几天,手脚已经不听使唤了,许多水滴在这时竖直劈在他们的衣服上,划开了细长的口子。这种水珠含泥沙较多,滴在青布褂上,深色的道子长时间不褪,等送完几批货,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他们红着脸侧过身去。也有些聪明的老水手夹杂在我们中间,他们从舱里找来湿透的布褂套在外面,身上落再多的水点也看不出来。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尚在青壮年的水手衣服上才会滴水不沾。
空中的滴水结束时,我们骤然放松了,三三两两坐下休息,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忙了半天,抬头一看,其他人家都收工了,有的走出了很远,甚至直接走没影了。偌大的码头就剩下我们还在船上,为什么总是我们落后呢?而且往往是上岸越早,收工越晚,这样的落后不止出现一次了,想到这里让人沮丧。
两个月以后,我们又一次回来,这回收获颇丰,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船老大也是笑呵呵的,主动跑出来和我们交谈,我们吃惊地看着他,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他也并不介意。螃蟹和鳝鱼装满了青丝网兜,我们推着手推车,有说有笑,一起回村去。在这热闹的人群里,我猛然想到,这回我们没有落后,热闹的时候容易忽略这个问题,只有在离群时才有巨大的恐慌,回头望,一户落后的船家急急忙忙赶上来,怀里抱着的渔网拖在了地上,他也毫不在意,不久之前,我也像他一样。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