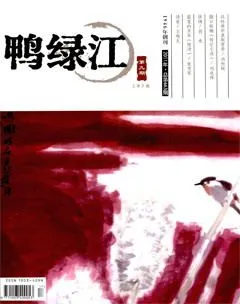幸福的玉米(外一篇)
2011-12-31张福艳
鸭绿江 2011年9期
张福艳,70年12月生,高级农艺师,1991年毕业于辽宁熊岳农业专科学校农学系,2003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专业,现工作于朝阳县农村经济局农业产业化办公室。1998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辽河》《辽宁日报》《辽西文学》《中国文学》《成长》《中学生故事与阅读》《现代家庭教育》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歌百余篇。2009年,歌词《爱的奇迹》获得辽宁省原创计生歌曲一等奖。发表于《辽河》的散文《秋天的滋味》被《读者·乡土人文》2010年12期转载。
无论是质地细腻隐约似玉,还是形状乖巧如玉,尽管它有很多别称,唯有“玉米”这个名字最精致,最值得一品。或白或黄或橙的米粒,色泽半透明,似隐若现,让人容易联想到耳钉、项坠、头饰等小物件,它妙不可言的赋状也曾为它赢得“玉美人”的称呼。玉米原长于美洲,传说七千年前玛雅人已经种植玉米,天文和数学成就令人叹为观止的玛雅人十六世纪从地球上消失,留下了神秘的预言和在地球上生生不息的玉米。玉米传入我国有水陆几条路径,一说在明朝嘉靖年间,由到麦加朝圣的回教徒带来中国。确切的是,在五百年前,玉米还是皇帝的御用美食,那时,它身价高贵,需山珍海味与其搭配。如此说来,来源于美洲野生大绉草的玉米,经过自然选择与人工选育后,虽然称不上血统高贵,总也算得上兼顾中西。玉米的前生今世有这么多的故事铺垫,想来做一株玉米应该是件幸福的事。
我本能地认为,辽西薄土地非常信赖玉米,玉米是能用自己的果实来诠释“我能”的作物,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土地的意志。高粱叶子窄玉米叶子宽,想必是母大子肥的缘故。大豆种子拱土时,随着胚轴的伸长,种皮胀破,仿佛听到“啪”的一声脆响,两片豆瓣用尽全部力气,展成对开的两片子叶。玉米的叶子是从苗心里悄然钻出来的,它不着急,因为它有营养的大后方。玉米种子里不仅有胚,还有双子叶植物没有的胚乳。乳者,生命的浆汁,也是母性独具的标志。玉米喜温喜肥水,除了阳光、雨水和人的精心耕作,玉米不能没有风。风带着一种使命而来,追随着玉米来到一个又一个远方。头顶分生的花蓼,腰系细嫩的丝缨,从植物生理上讲,玉米是两性的。虽然雌雄同株,玉米的天然自交率仅为5%,是风成全了玉米。在风中,它宽宽的、叶缘波浪状的叶子仿佛是正月里扭秧歌的飘带,又仿佛是缠绕田埂的浓郁的乡情。一株玉米通过风之手把花粉洒向其它植株的花丝,又通过风把别的植株的花粉带给自己,彼此共享一段幸福的时光。淡黄色的花粉在时光中飞扬着,味道微微甜,气息有些暖。玉米总是很知足,最先想到的总不是自己,把分享和给予当成约定俗成的事儿,所以就有了幸福的理由。玉米的花丝最初淡淡的,像蓝眼睛少女的金发,花丝的颜色重了,玉米完成了一次生命接力时,就变作了黑头发的辽西乡村妹。对明天的憧憬是从臃肿的腰身里放飞的,虽没有了窈窕淑女的身材,此时的玉米却像个拍着腹部和宝宝说悄悄话的准母亲一样幸福。
土地因玉米而幸福的时候,玉米本身也是幸福的。玉米也像人一样,被需要的时候才凸现价值,才有成就感,才有更多幸福的资本。和邻居张姐唠闲嗑时,猛然发现“被需要”这个词的新理论。含辛茹苦许多年,终于等来儿子大学毕业的这天,这对张姐来说是无限欣慰的事,然而,她却说,每月给儿子寄生活费时是幸福的,不再为儿子付出的时候,心里反倒有种淡淡的失落,因为意味着不被儿子“最需要”。玉米无疑是幸福的,一经传入中国,玉米即被百姓接受,它曾一度成为下层农民的主要裹腹之物,为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口增长做过贡献。从北纬58度的加拿大、俄罗斯到南纬40度的南美诸国,世界上整年每个月都有玉米成熟,感觉玉米像最受欢迎的演艺明星在全球巡回演出,在这里还没有谢幕,在那里又等待隆重登场。
如今的玉米不再是园田里的尤物,不再是奢侈品,它变成了粗粮,甚至饲料。也许我们没有真正读懂神秘的玉米,但我们喜欢玉米,喜欢它平常中给予的一份欣喜,喜欢它宠辱不惊中的那份随缘。玉米不光是它自己幸福,它还让我们从中咀嚼出幸福。玉米虽然是粗粮,但食用价值很高,而且内含一种长寿因子。在墨西哥,人们每年都要祭祀玉米神,国宴上有玉米做的美味佳肴。在我国,吃粗粮也成一种时尚,渐行渐远的玉米又悄悄地回归到我们的生活。昨日回乡下看老爸老妈时,也好好地看了一回久违的玉米。走在玉米青纱帐里,它的叶子正好搭着我的胳膊肘儿,亲亲的,有比肩少年的感觉。邻家大娘管玉米叫棒子,她说今年雨水调和,棒子一点都没耽误长,一个浪头赶着一个浪头,一转眼就“扛腔”了。玉米天生不孤独,它们喜欢以一个绿色的方阵出现,举起长长的裙裾般的叶子,在风中群舞。风过处,掀起层层波浪,玉米涨潮般一下子高了许多。不经意中的言语里,大娘是把玉米地比作一片绿海。“扛腔”是乡下人的“专业术语”,是继玉米拔节后又一个重要状态,此时玉米蓄势待发,它的蓼很快就从“腔”里箭一般蹿出来。多么恰当的表达啊!唯有亲眼看着玉米长大,唯有把玉米看成很有出息的孩子的人,才能说出这样贴切的比喻,才会这么重视玉米生命中的每个细节。玉米在丘陵地上落地生根,也被辽西的土地同化为辽西乡村重要的一部分。
从天上到人间,从高贵到纯朴,从遥远的地方到我们中间,玉米一路随缘地、亲切地走来,它不高高在上,也不低眉俯首,它实实在在,籽粒可食可饲,秸杆可以暖炕。玉米不挑剔,也不张扬,当金子一样的籽粒在田野上晾晒光芒时,那便是玉米呈现给我们的幸福想往。玉米作为大饼子、窝窝头的时代也已经远去,去美食里重读玉米的时候,它五百年来不变的芳香原来就是地道的幸福的味道。
行走的谷子
窗外的世界,先是小柳托起一片淡的绿云,再是老柳系上青的丝绦,尽管我的眼睛无法抵达远方的田野,我知道,春天不会埋没一粒谷子的心事。
谷子是从岁月的深处走过来的,它的年纪也许不止七千五百岁。它应该是天地孕合而成,拥有天地造就的足够的自由和灵性。它最先一定不是长在一条垄里,而是在杂草丛中或是山崖缝里,无论怎样弱小,它都在土里生,朝天空长,和野生的青狗尾草一样,愿意开一串花就开一串花,愿意长穗就结一穗籽。
种子的行走缘于人的行走。当人把自生的谷子驯化得能够裹腹,就把谷子当成神的恩赐,人走到哪儿谷子就走到哪儿了。谷子去皮后就不再行走了,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小米。对于一个民族的哺育,没有谁比小米更资深,几千年之后,谷子也不负哺育作物的美名。也有没去皮也不再行走的谷子,包括谷粒、谷壳、谷穗,它们定格在遗址或墓穴里,碳化成一个标本。再后来,谷子比人走得更远,它搭上火箭飞船,飞去了人类还没有留下脚印的地方。能走到今天的谷子是幸运的,它们浓缩了一个绿色世界,也浓缩了谷子家族生生不息的愿望。
和人同步的行走不是谷子真正的行走。谷子无脚走千里,谷子自己的行走才是真正的行走。谷子经过华丽的转身变成小米后就不需要行走了,那些走着走着就走不动的谷子也没有走到今天。物竞天择,能在大地上行走的谷子是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行走到今天的谷子都是不屈的谷子。每个谷粒都有脐,尽管不容易看到,那是与母体告别时留下的,是谷子共同的胎记。脐上的胚是谷子的精华,它延伸着谷子的命脉,传承着行走大地的意志。真正的生命不染色,能行走的谷子是拥有一个实质所在,它的胚中有生命的呐喊。若将谷粒取出,用温水浸泡使之膨胀,纵分成两半,加入红墨水,胚着色很浅的谷子是能发芽的谷子,有着生命迸发的潜质,而着色的谷胚则失去了活性,不得不退出下一个生命的轮回。
那么多的田垄都在春天里张开,它们先等雨,再等谷子。少雨的日子,我一个劲地在垄里拉滚子,让种子嵌进土地,期待谷子的根在土里跑。最先从胚里伸出的是谷子的根儿,其实它不需要行走太远,也不需要走得太快,但它需要摸索,它要能在黑暗中会区分上下,绕开岩石,往土壤深处扎,让叶子和幼芽钻出土壤,拥抱阳光。谷子在土里的变化,我们看不到,其实那是黑暗中根尖的绝美舞蹈。谷子落地生根,和人一样,将有一个新的开始。可种子比人简单多了,人总是有很多愿望。一些人则更像谷子,比如,我的双目失明的朋友。如果眼睛被挡住了,我的世界缩成漆黑一片,而朋友的世界同样是博大与清明。谷粒能长成一粒能发芽的谷种,可能经过了虫的咬食,雨雪的侵袭,霜冻,或者是先天发育不足就脱落下来。谷子的外形可以有区别,只要得以生命传承的胚没有被着色,它就依然完好,活力无限,小小的胚芽将是一个新的生命体。朋友是遭受过伤害的一粒谷。我甚至不知道他怎样失去眼睛,已经既成的事实,他改变不了的时候,他选择了面对。他的面容是从容的,平和的,他的眼睛是有方向的,专注的,尽管他看不见,因为他知道,生命中实质性的东西没有丢失,那些失去的都不重要。纷繁的色彩远去,黑暗却拓展出无限延展的苍穹,面对广大,世界没有变小,相反它无限延展。作为不缺少生命特质的人或植物,来世间一遭,如果没有绽放过,总是一撼事。拥有生命内涵的谷子,经一段时间的黑暗,重见天日后萌芽、开花、结果。少了虚妄,愿望变很纯粹,专注去做一件事情时,朋友也成了一颗谷粒,一粒浓缩了大自然的美妙和美丽的会发芽的谷粒。
谷子到底走了多远,没人知道,但我却知道,谷子为了行走,由胚衍生出的根,抓紧泥土,远离暄闹,独守宁静。到底有多少谷子的根抱过大地,也没人知道,但谷子在一茬一茬的行走中,让一粒变成一穗谷,一穗谷变成满仓谷。谷子在大地里行走的距离可以与株型无关,与米色无关,但一定与愿意行走的籽粒的多少有关,谷子行得越远,人在岁月里走得越远,越有力。
团起来是一个小粒,展开来是一片葱茏,站起来是一个世界,这对于行走的谷子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