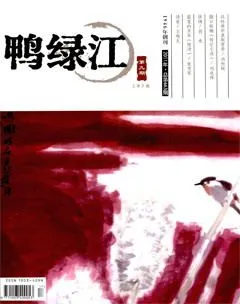铁锈
2011-12-31肖龙
鸭绿江 2011年9期
肖龙,男,蒙古族,原名松布尔。祖籍内蒙喀喇沁旗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文史撰稿员,杂志编辑,公司经理等。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民族文学》《芳草》《草原》《南方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50余万字。其中小说《黑太阳》被《中国文学》选载并译介到国外。曾辍笔下海磨砺十余年,2006年重回小说创作。
1
要出去租房子的念头,是夏荞麦从保安室里出来后产生的,但她憋了半天才把话说出来。
夏荞麦看着走在她前面低头耷拉脑的鲍喜顺,心里又气又难受。夏荞麦把一缕散在脸上的头发往耳后抿抿,像做出什么重大决定似的说,咱们出去租房子吧!鲍喜顺回过神来,摇摇脑袋,这才从愤怒的情绪里清醒过来。耳边有清风擦过去,能听到工厂的高墙外麦田里的流水声和小树林里的蛙鸣雀噪。
鲍喜顺站住脚,回头看着夏荞麦。夏荞麦说,咱得有个自己的窝!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鲍喜顺说,你想想……咱能租得起么!夏荞麦说,咱们从别的地方减省减省!楼房租不起,租间平房也行。大小破烂都不怕,像个家样,有张床有个锅灶能过日子就行!鲍喜顺借着工厂高墙外洒过来的稀薄灯光,看着夏荞麦惊魂未消的脸,既心疼又酸楚。他觉得对不起夏荞麦,连累她跟他受了罪。鲍喜顺想用个拥抱安慰安慰夏荞麦,手臂刚刚张开,又警醒地放下了。
他和夏荞麦结婚没到半年,就从农村出来到城市里打工了。出来打工并不是农村的日子过不下去。鲍喜顺的爹是村里的老木匠,虽不能做出精巧的家具,但庄稼地里的农具还是离不开他的。娘开了家裁缝铺,辛苦是辛苦,可缝缝补补每天都有进项,这在当地就算是富足的家庭了。结婚前他们都在城里打工,鲍喜顺在广州的一家电器厂,夏荞麦在深圳的一家被服厂,回家过年时在火车上认识的,话谈得投机,书信来往了一年,第二年春节回家就结了婚。爹娘拿出积蓄给他们在村子西头盖了新房。房子挺漂亮,双层不锈钢大玻璃窗,把屋子照得亮亮堂堂。炕上叠着双喜字的红绸缎鸳鸯被,墙上贴着抱着鲤鱼的杨柳青娃娃画。爹娘知道他们在外面跑惯了,家再好也留不住他们,只希望他们在家生了孩子再走,趁身体还硬朗帮他们把孩子带大。可没到半年鲍喜顺就受不了了,小时候的玩伴都出去打工了,满村子看不见一个青壮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地里只有老头老太太拖拉着儿子闺女留下的孩子,连咳带喘地干活。鲍喜顺就跟爹娘撒谎说,夏荞麦生育上有问题,乡下的医生治不了,要到城里边打工边看病。这可是传宗接代的大事情,爹娘不敢耽误,就撒手让他们出来了。
因为有家的牵挂,他们没有南下,坐火车来到离家近些的北方城市。这时候已经过了找工作的最佳时机,他们想先落下脚,鲍喜顺暂时找点零活干,夏荞麦先去做保姆,这样骑马找马,以后再慢慢遇机会寻找合适的工作。幸运的是,没跑几天,他们就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而且俩人同在一家工厂里上班。
工厂坐落在城市北部的郊区,高高的青砖院墙上,架着铁丝网,看上去有些森严,一只高炉的烟囱在云端里慢吞吞地吐着黑色的烟雾。这是一家废旧器械处理厂,经营项目是把报废的旧电器和大型机械拆卸零散,能用的器件挑出来去锈刷尘抛光,卖给机械生产厂家,没用的器件就分门别类,填进轧铁车床里轧碎,然后送进高铁炉里熔成铁坨。厂里效益好,机器就像发情公牛似的一天到晚轰鸣不断。上工时黑白两班倒,厂房里人影绰约,来往穿梭。鲍喜顺分在男工班拆卸组里,拆卸报废的机械和旧电器,夏荞麦分在女工班洗尘组里,把选器组选出的机器零件洗尘去污,然后交给上漆组上漆做新。
拆拆卸卸不需要什么技术,谁都能干,有力气就行。鲍喜顺和夏荞麦都是在农村长大,和油污锈铁打交道,脏点累点都不怕,只是厂子里没有单身房,只有集体宿舍,他们只好分居,这让他们感到很别扭!
2
厂子虽然很大,但建筑格局却比较单调,就两个区域,一是生产区,一是生活区。生产区里有拆卸车间和选器做新车间,还有那只庞大的熔铁高炉。生活区是食堂和员工集体宿舍,过去食堂前的广场上曾有个篮球场,但现在早已经荒废了,杂草长到齐腰深。几间职工文化活动室也成了杂物室,仅剩下那只锈迹斑斑的牌子还挂在门框上。西北角员工食堂的侧面是两栋红砖盖起的宿舍,男工宿舍和女工宿舍隔着一个花坛。宿舍都是门和窗台连在一起的集体宿舍,门是铁板焊接的,窗子上装着钢筋打造的防盗栏。每间宿舍里上下两层床铺,八张床住八个人,四张铁皮桌膛里放着八只铝皮的饭盒。再无其他东西。
鲍喜顺和夏荞麦分别住在男女集体宿舍里,只有交接班时才能碰个面。中间半个小时吃饭和休息时间,两个人隔着食堂的餐桌或通红的月季花坛深情地对望一眼,又都匆匆地各走各的路,各干各的事情了。
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却不能相聚,这种咫尺天涯的煎熬要比人隔千里来得更甚。上班的时候还可以,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手拿把攥着沉重的钢钳铁锤,浑身的力气都使出去,用劳累压制想念。最难受的是休息时间,一觉醒来恢复了体力,各种念头死灰复燃,让鲍喜顺坐卧不安。宿舍里没有电视可看,没有书籍可读,每个人就鼓眉瞪眼地躺在狭窄的铁床上,下铺的看着上铺的床板,上铺的看着水泥房顶直勾勾发呆。实在闷得慌,就鼓动山西的老刘念老婆寄给他的家书。山西老刘年纪长些,也无所顾忌,让念就念,让说就说。有些小年轻开始得寸进尺,引诱山西老刘说他和老婆的情史。山西老刘是个结巴,但讲述起家里的老婆却口齿伶俐,流畅得很,不但讲得绘声绘色,还把细微末节讲得透彻逼真。没成家的小年轻,听着山西老刘的讲述,躺在床上想入非非,成了家的人就被山西老刘的话引诱着走进实质的情境里,有了可触可摸的质感……
鲍喜顺在床上躺不住,去趟厕所出来,蹲在锅炉房的水池边,拿眼睛朝远处的洗器车间逡巡。看见夏荞麦出来上厕所,鲍喜顺就跳出来紧紧箍住了夏荞麦的腰。夏荞麦吓了一跳,刚要叫,嘴被鲍喜顺用手捂住。鲍喜顺小声说燕燕你别喊,是我!夏荞麦回过神来,小声呵斥鲍喜顺说,上班呢,你疯了!鲍喜顺说,我想你!
鲍喜顺在后面抱着夏荞麦的腰,喘出的热气烫得夏荞麦浑身酥软。夏荞麦便不挣扎,任鲍喜顺的手在身上游走。这时,黑暗里突然射过几道刺目的手电光亮,把鲍喜顺和夏荞麦死死地罩住,几个巡夜的保安唰唰地跑过来,带着犬牙的橡皮警棍就雨点般落在鲍喜顺的身上。夏荞麦说别打别打,用身体去护鲍喜顺,肩膀上也重重地挨了一下。两个人被灰头土脸地带进保安室。
保安室里灯光雪亮,保安队长是个矮胖子,绿豆大的小眼睛,却射出斗大的光来。保安队长是被保安从老婆的热被窝里叫起来的,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嘴询问着鲍喜顺,眼睛却狗舌头似的在夏荞麦身上舔。夏荞麦臊得低着头,希望地砖闪开条缝钻进去。保安队长说,龟孙子你胆子大呀,敢在厂子里调戏女工!鲍喜顺用手捂着被胶皮警棍打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