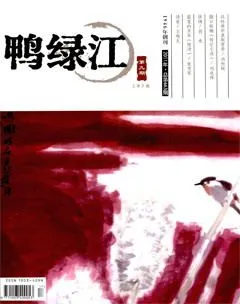城市面孔:乞讨者
2011-12-31刘芬
鸭绿江 2011年9期
刘芬,女,湖北人,七十年代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莞市作家协会理事,东莞市文学艺术院首届签约作家,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九月菊》《花朵在空气中穿行》、报告文学《烽火照东江——蔡子培传》。现任中国作家第一村办公室副主任。
此刻,他正敲打着我的车窗。他挥舞着手中用红色塑料袋特制的扫把,一遍又一遍轻轻地、仓促地敲打着我的车窗。红灯在闪烁,一秒又一秒,时光的流逝清晰可见。他把手中的扫把,一遍又一遍投向过路的陌生车辆。
这是位于樟木头汽车站靠近东深公路处的红绿灯路口,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些行色匆匆的车辆,在短暂的时光里,他们被因缘安排,注定了在此短暂的邂逅、相遇。他们站在时光中,给钱,或者不给钱;开窗,或者不开窗。施舍与被施舍只是在给与接的瞬间,两个看似简单的手势却成为世界的悬念。
我已记不清多少次邂逅这个老人了。他黑,瘦,脏。长长的白色胡须像榕树枝条稀稀疏疏垂了下来。此刻,地表温度已高达三十多度,南方的天气闷热而狂燥。他穿着一件长袖的衣服,袖子因为长时间没有洗涤而泛着一层油光。他的穿着与天气格格不入。看得出来,为了尽最大可能地显示出自己的萎靡、颓废、破败、落魄,他把自己拼命往低处压,压到丧失自我,丧失声音。他的低到尘埃里的姿势,卑微,胆怯,懦弱,他用这种姿势作为生存的武器。
隔着玻璃车窗我打量着他。上了年纪的人,岁月留给他的是一脸的沧桑。他的脸部轮廓并不老实,甚至还带着尖锐的弧度。以我有限的人生阅历来看,通常有这种线条的人并不容易打交道,性格中有很多阴鸷的成分,也就是说,他的长相并不善良。年轻的时候,也许他像一头暴烈的豹子,随时会一跃而起。可是现在,他只是一个被岁月剥夺了锐气的老人。眼神疲惫,姿态突兀,表情荒凉。他在烈日下用厚厚的衣服裹紧自己的身体,为的只是想制造一种让人心酸的效果。他的刻意的装扮更多的只是一种做秀的成分,可是,面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已经被岁月还原成一枚日渐萎缩的坚果,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他的年龄,他的衰老,让我在面对他时曾想起过一些人,一些事。我想起远在家乡的祖父,家中的祖父已经是如他这般年龄的长者了,生命进程已过去大半,还有多少时间能被他们挥霍?我还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同样被生活摧残得弯下腰的中国式的父亲,他们一个生活在画框中,一个生活在生命中,但他们脸上都有一模一样的沧桑。他们额上的皱纹,已成为一种衰老的印记,成为一种年老的象征。
这些与乞讨无关的事无疑在特定的时刻击中过我的内心。所以我冒着伪善的危险,在车来车往的红绿灯路口,一遍又一遍把零钞递到他的手中。这不仅仅是缘于女性性格中脆弱温情的一面,不仅仅是缘于人性中善良的一部分,我想,更多的是他以他的年龄和沧桑做着卑微的事,白发长者的尊严与卑贱的工作冲突着,碰撞着,对人很具视觉冲击力。
在百佳超市入口处的红绿灯处、在汽车站出口处的红绿灯处,甚至在邻镇黄江镇的胜前岗红绿灯路口……我一次次地与他邂逅。他的活动范围只是在本镇与邻镇。他坚守着红绿灯,就像一个辛苦的老农,坚守着他的两分薄地。
在与他相遇的瞬间,我总在暗处看着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重复着相同的语言,他已经麻木了,手和嘴只是机械性地动着,他的脸上已没有任何悲喜。一旦红灯来临,车辆停下,他就迎上前来,挨着顺序敲打着每一辆车。一辆车没开车窗,他不纠缠,而是快速地走向另一辆车,毫秒必争。通常他开口向司机们说的只有一句话,遇上男司机,他就说老板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老板发财。遇上女司机,他就说小妹行行好吧,谢谢小妹。他的口音带着浓厚的河南腔。
一次,在汽车站的红绿灯处,红灯刚启动,他就来到我面前。我打开车窗,递给他五块钱。他探身接过钱,作揖、打拱,一迭声地说多谢小妹,小妹发财之类的恭维话。我告诉他说,老人家,以后不要在红绿灯处要钱了,去别的地方吧,这个地方车多,危险。他似乎深受感动,不停地抱着拳对我说,谢小妹啊,谢小妹,多谢小妹对我关心。说完,他又急匆匆地赶往下一辆车。
小妹。他叫我小妹。以他的年龄,他绝对是我的爷爷辈。可是,他叫我小妹,千真万确。他这么降低自己的身份,原因只有一个,以最卑微的姿势博取众人的同情,让他们对他予以施舍。
可是,又有多少人被他的白发和屈膝所感动呢?我注意到了,在一个红灯时间约为90秒的路口,他能等待大约二三十台车辆,可并不是每一辆车都能给他递过来他期待中的人民币。运气不好的话,他一次也不能得到。人家不开车门,他敲车窗也是枉然。运气好的话,他能得到二到三次的施舍,每次也就是一块钱的样子。通常给钱的,都是女性。这从窗口递钱的那只手可以看出来。
他处在红灯路口,选择的是这样一个危险的区域。给与不给,成为一道难题。这很考验人的道德、良心、同情心,甚至意志。给吧,似乎是纵容了他,让他觉得这个地方肥沃,有油水可捞,不会挪窝去别的地方,而这势必给交通安全造成隐患;不给吧,面对这样一个老人,又于心不忍。他让人们脆弱的同情心饱受煎熬。
时间就在这犹犹豫豫中划过,每天上班都要经过汽车站前的红绿灯,每天都要与他相遇。我有时给,有时不给。
后来有一次我在家门口意外地碰上了他。刚出花园的门,在美宜佳超市的门口,我看到他坐在超市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大口吃着馒头,身边还放着一只矿泉水瓶。我走了过去,在他的工作时间之外,主动给了他五元钱,并与他攀谈起来。我不害怕年老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被岁月挫掉锐气后的无助,一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老去,我对这些老年人都会充满同情。其实也是对自己年老后的一种敬畏。
老人显然认出了我,这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的脸上泛起一种见到熟人后的高兴神情。他主动与我打招呼,称我为好人。在他眼中,世界已被简化,给他钱的他一概统称为好人。
老人告诉我,他是河南周口人,来樟木头已经有些年头了。起先,他是跟着家乡的一班人在工地做泥匠,后来,工头嫌他年纪大,做事不利索,再加上也不是总能接到活干,就与他结了工资让他走人。没办法,他年事已高,又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到处找事,想来想去,只能凭借一张老脸博人同情了。他自嘲地说,也只能这样倚老卖老了。我说,那您儿子知道您在外这么辛苦看人脸色他会怎么想。没想到这一下子戳到了老人的痛处,他瘦弱的身子猛地往下一缩,仿佛遭受到了某种不可言状的痛。他说,小妹,你有所不知呀。你是个好人,我就告诉你我家的事吧。
于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在一个耄耋老人的叙述中清晰地呈现。一个家庭的生存、生活,原本像一条河流,朝着前方不紧不慢地流淌,展开,可是,因为暗礁,或者风浪,河流急速地改变了流向,家庭成员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被改写。这个以乞讨为生的河南老人就是,一场家庭的变故,让他老无所依,成为城市中让人不屑的乞讨者。
老人原本有一个儿子,不幸五年前去世。起因是儿子与儿媳妇发生的一次争吵,儿媳妇拿铁棍打了儿子的后脑勺,儿子当时就晕了过去,约半小时后醒了过来。家人也没太在意。这之后,儿子也没见异常,时不时还喝点小酒。乡下农民,劳累后喝点小酒舒活舒活筋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灾难发生在一个月后。儿子有一天突然倒下,送到医院说是脑出血,大面积的出血,这让人联想到一个月前他后脑勺挨的那一棒子,遭遇暴力,喝酒,这两大因素摧毁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劳力。在医院抢救了一个多月,儿子终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而为了抢救儿子,家里人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不少钱。一共十四万。十四万,对一个年老的老农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老年丧子,欠巨债,老人说他不知那时是怎么过来的,也记不起那段时间他都做了什么。
为了还债,老人被迫背井离乡,与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出来打工。光靠地里的收入,他永远也无法还清那笔债,再加上每天面对着那些借钱给他的亲友,人家就算不催,他也无法交待。就这样,年轻时都没有出来闯世界的老人,在七十岁的古稀之年,毅然决然南下,为了生存、生活。
闯下弥天大祸的儿媳妇没多久便改嫁了,她自己一嫁了之,留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孙子给两个老人家。老人把孙女交给女儿,也就是孩子的大姑,他自己则和老伴一起,带着年幼的孙子来到了南方。
南方哪里是他的立足之地呢?南方哪里能知道他的家事呢?没过多久,他失业了。孙子还小,为了孙子,他决定抛弃尊严,去乞讨。他别无选择。
我在心里为他旁白:他不是堕落,不是懒惰,他只是为了生活。
家里的债还得怎么样了?我问。
他说,这几年也讨了不少钱,家里的债还得差不多了。等把债还完,再讨一些钱,他就带孙子和老伴回家,孙子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他也老得快走不动了。
我的心里一下子像塞满了棉花,无语。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问他,这么大年纪在外乞食,遭受到很多人的白眼,心里一定很难受吧?老人笑了笑说,哪里管得了那么多,有人白眼也是很正常的事,毕竟你是伸手向人要钱啦,人家又不是上辈子欠你的。停了一下他又说,呵呵,世上还是好人多,特别是女娃子,女娃子都特别好,有次有个女娃子见天热还给了我一瓶饮料,红色的,甜得很,我也不知道那是啥饮料。
这段话让我有两个小小的感悟:一、生存是排在尊严前面的,当生活无忧的时候,尊严才会显示它的本性,否则它只能靠边站,它只是生存的附属品;二、女性普遍比男性具有同情心,这也许缘于她们天生的善良与母性。
可是,尊严是个什么东西呢?谁见过尊严?谁能告诉我尊严在哪里?是躲在华丽的衣服背后吗?是藏在装冷酷深沉的墨镜背后吗?
我以为,靠乞讨为生的河南老人是极有尊严的人。他没有选择自杀,他没有放弃孙子,他宽容隐忍地生活,他活着,本身这就是最大的尊严。
在樟木头,在珠三角这个以经济发达著称的小镇里,活跃着很多很多乞讨者。有穿学生装跪在地上的职业乞讨者,有扮孕妇装可怜的乞讨者,有带着小孩死乞白赖着不走的乞讨者……这是一种职业,已成为一种习惯,在它背后,滋生的是人类的寄生性,惰性,不劳而获的价值取向,歪曲的灵魂,它让我们看到的是有手有脚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仿佛尊严只是脸上的面具,他们把它取下来放在一边。尊严与生活脱节了,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
在很多人眼中,很多人肯定以为河南老人也是个以行乞为生的职业骗子,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向每个人诉说他的遭遇,没有人能看到他心里的伤疤和溃疡。可是我相信,那些年老的人,那些以白发和眼泪换取同情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存,从某种意义上来,他们比那些自杀的人要勇敢。因为国家的制度不完善,因为贫富的差异,这些年老的人,老无所依,无所附,无所靠,除了出卖沧桑,这是他们唯一的资本,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再做什么呢?
河南老人,从他的脸上我看到的是沧桑过后的平静。在经过人生的大悲以后,他的表情乐天知命,他的眼神怡然自得,他已经参透了生死,他活着,只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是对家人的一种负责。
他并不是我所遇到的唯一的乞讨者。但绝对是奇特的有尊严的乞讨者。他债务缠身,他已丧失了劳动能力,他没有儿子可以养老,也没有社会力量助他衣食无忧地度过余生。他只能乞讨,别无选择。勿庸置疑,他活着,没有活着的能力,乞讨成为他唯一可以操作的生存方式。但他活得从容,宁静。所以我尊重他,同情他。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乞讨者都能获得我的尊重和同情。城市的乞讨者,大抵分为两类:生活所迫者、自甘堕落者。至于年龄、性别、籍贯,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状态、生存环境,用唯心主义的话来说,或者说是取决于他们的命运、因缘。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他只给两种乞丐钱:老人和孩子。其他的他一概不舍,他认为那是作秀的,表演的。我深以为然。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同情的种子,哪怕自己再没钱,再穷困,再潦倒,遇到比自己生存环境更差的人时,我们的同情心总是在第一时间蹿出来,泛滥成灾。这也正应验了“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格言。
在我们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禁止乞讨行为的存在,这说明乞讨这一谋生的方式和手段,是一片真空的地带。城市的乞讨者,他们只是局限于道德和良心的审判。我国实施了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并没有能使乞丐现象消除或减少,却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公民的尊严和基本权利。
所有的生命都是应该被尊重的。沦为乞丐的人们,不管是因为何种原因,他们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饱受着人类的冷漠和白眼。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体验到世态炎凉的人。
对街上行走的乞讨者,他们的面孔经常在城市的人群中一晃而过。模糊而遥远。他们代表了人类另一种边缘的卑微的生命状态。所以,对这些人我总是远远地,远远地就会充满同情。放下尊严,把自己当成一棵草,或者一片树叶,尊严被无数的脚践踏,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对待乞丐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体现的是社会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程度。有些人在行为上是乞丐,但在精神上他们并不是,比如靠乞讨为生的河南老人,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乞讨者。乞讨也许是他生存的一门技术,正如有些人靠理发有些人靠缝纫一样,都只是一种生存的方式,猪往前拱鸡往后扒,谁又能比谁强一点呢。不过是谋生的方式不同罢了,殊途同归。
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给这群游荡在城市边缘过着边缘化生活的人足够的关心和尊重。我相信,他们一定渴求着温暖,一定向往着光明。他们伸手要钱,是为了让自己,让家人改善生活,这说明他们对未来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这说明他们仍然有一颗向上的心。所以,我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城市的暗处关注他们。
远远地,远远地看着街边那些乞讨者,他们在人群中盲目地穿梭,流动,像一条茫然的鱼。不管有没有施舍他们,我都对他们充满同情。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