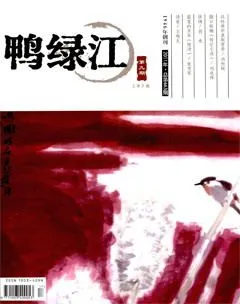从经典中汲取营养
2011-12-31冯积岐
鸭绿江 2011年9期
每一个写作者都面临着文学师承问题,不论你师承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可遵循的规律只有一条:“取法乎上,得之其中”。我相信,大凡在创作中想有所成就的人,都是以经典以大师作为范本和老师的。汲取经典的乳汁是自己体魄健壮的基础。据我所知,我周围的好多作家都是先读莫泊桑、契诃夫、梅里美这些短篇大师的作品而开始短篇小说的写作的。他们用经典的火把来照亮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当然,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文学境况。而近几年,通过读当代的文学期刊也能成名,足以证明文学的“发展”是个硬道理。
我常常给我周围的文学青年说,你们要读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要读卡夫卡、卡尔维洛、乔伊斯,要读马尔克斯、加缪。不是我轻视我们的文学传统(《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三遍),我感慨的是,我们的文学传统,为什么没有按照《山海经》《聊斋志异》《西游记》的路子走下去?我读小学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在故乡的博物馆里目睹过我们那儿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我记住的是青铜器上的纹饰,那些纹饰,大都是夸张变形的,而不是写实的。夸张变形是现代艺术的精髓。也就是说,在两千五六百年前,我们祖先的文化因子中就有了“现代意识”,而发展到如今,这些很有现代意味的艺术品怎么就被主流划到圈外去了?敢问有多少文学期刊接受了荒诞不经的作品?接受了夸张变形的小说?
细细追究,现代主义也不是外国作家的专利。秦腔《游西湖》中的《鬼怨》一场将“鬼”表现得活灵活现。《劈山救母》中,人神完美结合融为一体。《窦娥冤》中,六月炎天,大雪纷飞。这些非现实主义的艺术在我们的舞台上活跃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的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而翻开我们的文学期刊,每年又能刊发几篇像鲁尔福那样写生死两界的荒诞作品,在我们的获奖作品中又有多少篇什具有创新意识——不要说创新了,就是模仿非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没有。
我们的批评界和文艺官员逢会必讲文学创新。究竟什么是新。我想,只要我们全面继承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只要敢于给自己封闭的围墙打开一个豁口,文学创作的气氛就会有所改变,从杂志上学习创作到杂志上发表,然后去某个机构领奖,这种局面就会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会有文学精品产生。假如用国家意识形态规定的一个视角去衡量我们的文学作品,去写遵命文学,我们留给世人的只能是唱颂歌的“宣传品”。艺术毕竟是艺术,好的艺术作品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是具有思想深度的。
我也不止一次地给年轻的作家们说,你们不要一提起笔就写大部头的长篇,应从短篇小说开始练笔。据我的经验,要经营好一个短篇,绝不是易事。短篇是不藏拙的文学样式,一篇好的短篇里蕴藏着作者对这个世界、对人生、对人性深刻的理解,蕴藏着作者的艺术功力和聪明才智。在一部长篇或一部中篇中,作者可以不经意塞进去一把稻草一把棉絮,而短篇中,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填充物。我虽然已经发表了200多个短篇,但依旧对短篇乐此不疲,原因就是,总觉得自己没有达到一个高峰。假如自己运气好,有一天能够写出《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福克纳)、《印第安营地》(海明威)、《墙上的斑点》(伍尔芙)、《大教堂》(卡佛)、《立体几何》(麦克尤恩)这样的短篇,也就心安理得了。
有人担忧,由于种种原因,中短篇小说的气脉欲绝了。我想,没有这种必要。只要人类不朽,不论什么样的艺术就不会绝种。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中短篇小说不会因为种种冲击和读者量的减少而消逝的。艺术作为一种宗教,总会有它的皈依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