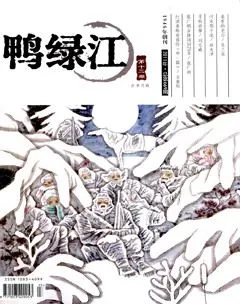魏氏庄园旧事
2011-12-31高维生
鸭绿江 2011年12期
高维生,吉林人,满族。1962年12月26日,生于延边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散文集《季节的心事》《俎豆》《东北家谱》《酒神的夜宴》《午夜功课》。从1988年开始,在《民族文学》《中华散文》《文学界》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诗歌和散文介绍到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并被选入多种选本。
庄园
车子向乡村的腹地行进,越来越接近庄园。天空下,看得见高耸的屋脊,宏伟的城墙和起起伏伏的垛口,这便是闻名遐迩的——魏氏庄园。
庄园前的空场地上,一群人在浇铸水泥停车场,裸膀子的工人,脖子搭着脏污的毛巾,推着装满水泥的独轮车,留下长长的印痕。灰色的水泥倒进捆绑的钢筋骨架上,黄土地覆盖了一层无生命的物体,泥土中的草籽、虫子、蚁窝,被压在阴暗的水泥下,终日得不到阳光和雨露的滋养,被剥夺了自由和生命。
跨过木门坎,走进庄园,镜头对准飞檐和屋脊上的鸟兽,那棵石榴树正是火爆的季节,结着拳头大小的石榴。庄园的过去并不是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高大的院落是地位的象征,它的设计师是从清宫请来的大师,经过许多能工巧匠精心修筑。在这黄河岸边的乡村,庄园主操纵庞大的生意网络,他在华北地区经工商,设银号,开钱庄,立当铺,在魏集经营三千多亩良田。当年魏氏庄园的门前,从住宅大门两侧的上马石,就可以想象,进进出出的人的身份。高挂的红灯笼熄灭了,流淌的烛泪,冷缩成钟乳石的造型,蒙上一层细细的灰尘。岁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如同墙上的工形拴马桩,嵌进了历史之中。
脚下的砖地,经过时间的磨损,砖缝间生长的小草和石阶上的苔藓,使古老的庄院有了朦胧的古典气息。
私塾院
紫藤像梦缠绕多年,我记住这个名字是1990年,在刊物上读到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后花园的墙角那里有一架紫藤,从夏天到秋天,紫藤花一直沉沉地开着。颂莲从她的窗看见那些紫色的絮状花朵在秋风中摇曳,一天天清淡了。”紫色的小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常常想起庄园里的紫藤。
那年我陪客人去惠民县,顺路到了魏氏庄园。初春的天空,阴郁显露不出春的迹象。陈旧的青砖,往外渗出丝丝阴气,庄园一副破败的情景,墙上白石灰写的“禁止烟火”的字样十分醒目,当时庄园还没有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门前的牌子上,写着“魏氏地主庄园”,不像今天改写成“魏氏庄园”。偌大的庄园,只有年老的夫妻看管,我们四处转游,惊叹古老的独具民族色彩的建筑。
走进一座小院,幽静中有一份个性,一棵遒劲的树枝蔓伸展,攀援的架子,遮住了大半个院落。
偏房门敞开,守园的老人坐在马扎上,膝上撂着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京剧,锵锵的锣鼓声给不大的院落,增添了时代感。
“大伯,这是一棵什么树?”
“紫藤呀。”
“紫藤?”
“富贵树,只有富人家才能栽种。”
站在紫藤前,似曾相识却不相识,我深情地观望,抚摸着糙糙的感觉,敲敲,听它发出浑厚的声音。这个季节的紫藤涌积旺盛的活力,经过冬天的休养生息,枝叶将要萌发,等待春风的滋养,紫色的小花依然是梦。
院子里的天空,差不多被紫藤的叶子遮挡住了,椭圆形的叶子,普普通通的,看不出与众不同的娇丽和富贵,找遍整架紫藤,没有苏童笔下的紫色絮状小花。
当年的老伯不见了,偏房的门紧关,挡着一副苇杆编的帘子,隐约可见的铁锁,锈痕斑驳。时间一晃又是几年前的事了,有紫藤的小院子里蝉鸣阵阵,如同当年读书的孩子穿越时空走来,教书先生单薄的身体隐在宽大的衣袍里,一手捋着稀稀的胡髭,倒背的手拿着一本线装书。一边缓缓地踱着,摇晃脑袋,孩子们童稚的声音,在那节奏中朗朗地读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读书声传出很远,越过森严壁垒的大院,融进远处的黄河水中。
摘下一片叶,闻着浓郁的清香味,我夹在采访册中,想留下这点纪念。
书房
这间偏房与别的房子没大的区别,几根涂红漆的木圆柱支撑伸出的房檐,传统的木栅格子窗。庄园主魏肇庆的书房,新粉刷的墙是那种光滑的化学涂料,墙上挂着几幅字,红砖铺地,平平整整,一点没有100多年前的旧迹。
主人常来这地方,泡一壶清茶,坐在宽大的案前,读一卷古书,或铺开宣纸伏案书写,或给远方的亲人、朋友写一封情浓意深的书信。
书房宁静,应该堆满线装书、字画、古玩,表现主人的情趣,读书、思考、体悟在青灯黄卷中,烦心的事会减去很多。
我查阅了魏氏庄园的资料,这座庄园从盛到衰,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庄园留存到今天是一大幸事。尽管主人不是文化名人,也不是彪炳青史的大官僚,但他留下的四合院式的独特建筑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喧闹一天的城市安静了,台灯的光照在纸上,曾经繁荣昌盛的庄园和它的主人,而今全部缩写在薄薄的纸页上。历史就是这样记录、流传下来的吗?读着资料,走进幽深的庄园,我努力地透过纸背,透过时间的烟云,去了解魏氏家族的来龙去脉,然而困难重重。这些资料,大量地介绍庄园的建筑布局,对他的家族是概括性的素描。
第一次走进,我不知道是书房。凸凹不平的泥土地,墙角堆放一堆棉花秸,棚顶黑乎乎的一片阴森可怖。墙上划痕、脏迹、泥点、蛛网,让我觉得这是破烂的仓库。
迎面的墙贴着一张毛主席语录,四周的边缘不规则,贴的报纸依然清楚地看出残存的大黑标题:“切实加强对革命大批判的领导”……版面的字漫漶不清了,发黄的报纸诠释岁月里的经历,其实不过是三十多年的时间,远比建于1890年的庄园年头少得多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成了历史,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一切将尘埃一样飘散。我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一组照片。几年后,写作这些文字时,我在影集里找出照片。
历史发生的事情,人是无法卜而先知的。即便是财大气粗,威震四方八邻的庄园主,他对未来也是难以预料的。城墙的碉堡有一块青石,中间凿成方孔,通过这个方孔,庄园主坐在房中,通过回音的原理,向守园的家丁传达命令。他绝没想到后来的人,站在碉堡上,揿动掌中的手机就能和远方、地球的任何地方通话。庄园走到今天,应该感谢那位不知名的领导,作出的英明决策,把庄园变成粮库。如果不是粮库,那场“文化大革命”,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所谓革命小将“破四旧,立新功”,会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铲成一堆废墟,汇入平原的麦地也未可知,历史偶然也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闺房
闺房: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旧时称女子居住的内室。”
庄园主的女儿,不能随便走出十几平方米的闺房,必须保持与外面隔离的状态。她是在族规家教的繁文缛节中长大的。由于长期封闭,方圆百里的地方,没有一家能和魏氏家族门当户对。历来人们又重男轻女,所以魏肇庆的女儿,终生未嫁,她只活了三十八岁。
讲述这段历史时,女解说员讲解得呆板机械,毫无感情色彩,想必她每天一遍遍地重复着。闺房找不到当年的痕迹,它的每一块砖石都能看到时代的背影,我更看到一出悲剧。心酸的歌唱,低泣的哭声无法敲碎高大的园墙,窜入野地。从黄河刮来的风,带着野性十足的强劲,透过窗吹到她的脸上,飘起的衣裙像幽魂起舞。人静夜深,也许她脱去衣裳,让肌肤感受凉浸的风,生命中涌动的情潮与这犷悍的风媾合了。她不喜欢庄园的静穆,炷香缭绕的几案上,供奉着先祖的牌位。她向往那顶大花轿,金色的锁呐,吹出一曲曲欢乐的调子。一块红盖头,掩住了她幸福的笑容。庄园主可以修建一座城堡,禁锢人的身体,却无能力扼杀泉眼似的情感。
庄园主的女儿,被关进精巧的笼中,饿了有人送饭,渴了有人送水,不必像乡村的劳动者,为了生活四处操劳。她的生命力充沛旺盛,却没有自由走上乡间的辙道,去湾水浣洗衣裳,站在黄河岸边,听艄公的号子,更没有选择人生道路和爱情的权利。闺房帮她躲过生活的飘摇,却逃不出内心苦难的历程。她的生命属于父母,父辈的权威一点不能违背。
她整日坐在床边,做着“女红”。纤细的针、长长的线,缝出“龙飞凤舞”、“石榴”、“梅花”、“兰”……一天又一天,她把对爱情、自由、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一针针流露出来。她常常呆立窗前,一只飞鸟让她感到兴奋,一阵细雨让她伤感,多么想知道庄园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呀。
闺房,每一处角落渗透悲剧的气息,她的灵魂这么多年了,还在叫屈喊冤。威廉·莎士比亚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就写出了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尽管主人公的结局是悲剧,但爱情的理想仍然得胜了。这部剧作为经典在世界各地上演,长久不衰,一代代人在研究着。人们为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为其冲破贵族家庭的隔阂,为了自由和爱情勇敢地斗争,流出晶莹的泪水。今天走进闺房,面对空荡、粉饰过的墙壁,痛苦敲击我的心灵。
磨房
庄园与周围低矮的房屋相比,显现出大家族的气魄。在那个时代庄园是贴近黄河的,几经自然的裂变,河道有了变化,离这越来越远了,水也越来越少了。黄河水宽浪急,船橹摇动,白帆点点的景象,人们只好在老辈人的流传中听到了。
魏氏庄园不似江南园林那样清秀,它的整体风格粗犷,适合黄土地,更能经得住土匪的袭击,狂野的风沙和连年的自然灾害。庄园虽然只有一百多年历史,却像风雨中的小船几经淹没,差一点消失了。
五六十年代,庄园也热闹起来,庄园当初修建时就考虑到水患,所以垫成平台,要比别的地方高出三米。建国后改造成粮库,车来车往,人流不断,打破了沉寂多年的庄园。
庄园的西南角原来是磨房,交公粮时车多碍事,领导一声令下就把它拆掉了,至今能看到残露的房基。庄园被国家批准为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们又在搞旅游开发。文物已很难找到了,他们努力地恢复旧时的原貌,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魏氏家族的资料。
墙上“禁止烟火”的字样被洗净,拆掉山墙吊挂的防火工具。残破的园墙补好,尽可能保持原来的模样。园里的工人在忙碌修整,磨房的位置,摆着一盘石磨,当年的那两盘不知是否存在,即使在的话,深深的槽沟,也已经不起一圈圈的转动。
那两盘新的石磨和碾子,供游人参观时发挥想象。如果在这露天下,放它一百多年,我们的后来人,可能真的以为这就是原物。
倾听城墙
下雨了,街头飘起了雨伞,躲在伞下的人们,匆忙地走在回家的途中。楼前的漏水管滴出的水声,给黄昏带来另一种韵味。
漫无边际的雨声,把人的思绪扯得很远。雨有色彩、有生命,它需要大地,森林、高山、大海与它们碰撞。
几天前,我陪客人去了魏氏庄园。曾经布满辙印、尘土飞扬的土路,铺上了简易的柏油路,两旁杂乱的猪圈、麦秸垛和破旧的土屋拆除了,路面宽畅多了。庄园前修的停车场,停着各种型号的轿车,出现了臂戴红袖标的收费管理员,风抽雨蚀的青砖墙伤痕累累,贮藏时间的流逝。
古老的四合院,院深门高,城垣门是拱券形木制大门包着铁皮,圆钉加固,两个大铁环显示城堡的威严。魏家的人早已离散屋空,家徒四壁,留下的一份家谱,记载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历史的回声。在一间间屋里走过,有几个人面对缭绕的古韵,有着深刻的思考。后人按自己的想象,弄来仿制的箱柜、瓶瓶罐罐装点空荡的屋子,满足游人的“大团圆”心愿。屋中残留的阴森的气息是阳光和风儿吹散不了的。柱头上的雕刻、廊柱、方形的一码三箭直棂窗和屋的角落为灰尘所覆盖,被高大的院墙隔绝于世。
独自走上城墙,墙顶设有内女儿墙,与外砌垛口中间为跑道,可绕城墙一周,方的石制泄水槽伸出墙外,纹理清晰,没雨水流过的迹痕。站在10米高的城墙上居高临下,俯视大院,三进九座的布局,错落有致。鱼鳞似的灰色小布青瓦由远而近,一层层地铺展。在它的遮掩下,躲过了风吹日晒和雪雨,发生的故事很多人淡忘了,很多人消逝了。
我在想一百多年前的雨天,雨落在青瓦上,沿着瓦槽与屋檐落下,淋湿了私塾院中的紫藤花。单调声透着亲切,森严壁垒的大院有了浓郁的人情味。老主人推开窗子,呼吸新鲜的空气,看雨中的庭院。苔藓从门前的石台阶生出,垂花门关闭,阴雨连绵的日子不会有客人来访。这种清代抬式框架的房架,在灰云密布的天空划出漂亮的曲线,体现了古建筑富有的神韵,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难以找到了。
出了庄园思绪纷乱,我沿着墙根走,过去的事情已过去。中华民族发明了造纸,发明了活字印刷,这一切的发明,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历史能记录下来。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那块古老的土地上,对魏氏庄园的文字记载少得可怜。它不是能简单地概括解释清楚的。我观望岁月侵蚀的青砖,坑坑洼洼。城墙是有生命,有思想的,城墙仿佛是一卷翻开的史书,带着霉味扑面而来。
城墙的四周是布局散乱的乡村的民居,大门前拴着的一头黄牛,低头嚼着青草,它的主人蹲在一边抽烟。
庄园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前人留下的一座庄园。里面的门窗、砖石、木柱,并不值得凭吊。没有给后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庄园主只是个武定府的同知,不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名将,或者文化名人,对于古老的土地,对于古老的民族有过贡献。日子一天天过,附近的村民,向往安静的生活。庄园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也就没有自豪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