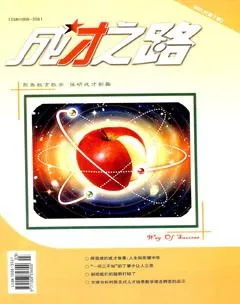凭什么成就卓越
2011-12-29张在军
成才之路 2011年7期
【编者按】张在军,笔名方圆。男,1964年生,特级教师。先后在《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中国教育学刊》等发表文章数百篇。主编过《教师人文教育读本》《中学生魅力阅读》《小学生魅力阅读》《小美文大智慧》《读美文写日记》《阅读作文全优突破》等中小学生读物二百余册,8套丛书获“全国优质教育成果(图书类)”一等奖。他先后获得“香港柏宁顿中国十大杰出教师孺子牛金球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央视“东方之子”栏目对他进行过专访。他对教育的思考探索、感悟,感动了亿万观众。他的事迹,被中组部拍成电教片《时代楷模》,江泽民同志题写片名;中宣部、中组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五部委拍摄的大型党史文献纪录片《使命》中,对他的事迹进行了介绍。
从一个基层教师成长为万众瞩目的东方之子,并多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奖,张在军的从教之路、人生之路,或许能给渴望成功的青年人以启迪。
从本期起,本刊将与四川辞书出版社合作推出张在军的自传体新书《凭什么成就卓越》。全书平实朴素,充满真知灼见,记录了一个乡村教师成长为一名“特级教师”“全国十佳民办教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艰辛而辉煌的心路历程,展现了艰难的生存环境下,乡村教师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对梦想的追求、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全书格调昂扬向上,激情飞扬,展现了奋进者的情怀。
这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的人生奋斗史,更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心灵成长史。
上篇追梦人生
一、桃花源记忆
1.桃花源在每个人的心里
经常收到远方朋友的来信,问我你任教的学校到底什么样子,怎么那么有魅力,可以把你牢牢地吸引在那里。我回信说,这里是实实在在的人间桃花源。
外地的人都知道沂蒙山有著名的72崮,将军诗人陈毅还专门有一首写七十二崮的诗。其实,沂蒙山有大小山头一千多座。
我任教的学校一溜6间瓦房,院子占地5亩多,一棵大柿子树占了大半个院子。学校坐落在纱帽崮的东坡上。自然因崮似纱帽而得名。站在学校院子里,放眼四望,一圈的山崮相连。锥子崮,枕头崮,东汉崮,猪鼻子崮,江家崮……不下十几座。这里距离县城60多里,出山的路只有一条,在往东南20多里的山口上。
学校一开始是五年制完全小学。后来因为高年级要开设实验课,下边的学校教学条件达不到,就把高年级集中到了学区小学。全学区有8个学校,总共二十多个老师,年龄大的五十多岁,年轻的二十来岁,除了学区校长外其余大多是民办教师。
乡镇教育管理的最高机构叫乡镇教委。教委下边是学区,学区下边是村学校。县里有什么新精神新指示,一般或开会或下通知把指示精神传达到乡镇,乡镇再召集学区校长开会传达,学区校长再召集各村学校的组长开会布置下去。
学校就我一名教师,每到去学区开会的时候,就和高年级的班长交代好,让他替我管理。有时候支书王常会也来学校帮我维持秩序。王常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人家的责任田种地瓜玉米,他不种这些,二亩多地全种了辣椒。自己肯定吃不了,就到城里卖,邻居家也让他捎带着卖。渐渐的,三村六庄的都来让他捎带着卖,不知不觉间,竟然成了个小有名气的辣椒贩子专业户。张家李家的邻里乡亲养了十几头牛,没空喂养,就凑些工钱啊草料啊委托他给养着,平时赶到山坡上放一下。没事了就到校园里来和学生一块啦呱、聊天。有时候也到教室里听我讲课。
校园里长着四季不谢的花。学校东边前边是田野,种着成片的庄稼。西边是纱帽崮的山坡。
悠悠的白云底下是群山,山坡上是学校,学校房前种花房后种菜。
这里的一切都是单纯的,平和中洋溢着简单的幸福。孩子们的笑脸像阳光一样,带着诱人的醇香。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读书看报,一起修剪校园里的花花草草。孩子们上课做作业时,我则忙里偷闲趴在讲桌上划拉点小文章寄出去换点补贴生活的费用,找点自我陶醉的理由。
学校南边有一棵软枣树,树长得很茂盛,遮一分多地。软枣树下是一条大路。村人出坡、收工,都爱在树下讲些鸡毛蒜皮的传闻,聊一些捕风捉影的故事,于是便有几十块石头干干净净地摆在软枣树底下等着人们来坐。
教室没有后窗,一到夏天便闷热难捱。早饭后从第二节课开始,我便常把课挪到软枣树下来上。三两个男生抬着黑板,挂到树上,娃们叮叮当当坐好,哇哇的读书声便从软枣树下扩散出去。
每到这时,地里做庄稼的村人便再也不到树下来歇凉。实在累了,就到更远的小树底下吹吹山风,一边用褂子忽闪身上的汗,一边远远听娃们读书唱歌。
读到精彩处,孩子们笑,他们也远远地笑。学生回答不出问题,其他学生着急叹气,他们也远远地着急叹气。
软枣树不远就是山坡,酸枣儿、山里红满坡都是。下课了,口渴的学生便跑回教室喝点水。不渴的书本一放便忽啦啦跑到山坡摘酸枣,摘山草莓,惊惊乍乍的满坡荡漾着喊声、笑声。不上山的,便跑到就近一个场院里滚碌碡。一个站在碌碡上,碌碡咕噜咕噜滚着,上边的学生就敏捷地跳着高。
约莫十几分钟后,我吹吹哨子,四面八方的小娃便跑向软枣树下,有的互相品尝着吃不完的山果,有的放飞着捉来的蝴蝶,一阵疯闹之后,又一节课开始……
村民们对学校都很敬爱。偶尔忘了关校门教室门窗,路过校门口的人总会给你关上。
民办教师家里都有责任田。责任田很零碎,四面山上都有。到学校上课时,估摸放学后到哪块地干活,干什么活,总带上锨啊锄啊农具,放了学和孩子们一块出校门到地里干到天黑。批改作业,备课什么的一般都在晚上。
这里的人收入低,开销也少。青菜、粮食啊自种自给。庄稼上的是土杂肥,污染少。鸡蛋是自养的鸡下的。早晨打开鸡栅栏,把鸡哄出家,鸡们便和邻家的鸡友鸡哥鸡恋人们一起扑棱着翅子飞到山坡上。吃花籽草籽中草药籽,喝山泉水。一边谈恋爱唱歌一边打闹疯叫,天黑了再浩浩荡荡你追我赶回家。
来看我的好多朋友对我说,我们还认为你在这里教书很苦呢。学校房前种花房后种菜,一个教师的学校,简直闲云野鹤啊你。
我笑,朋友也笑。
有时候到城里待几天,和同学朋友聚一聚,一个个都在抱怨累。做生意发家了的有钱朋友说太累,做生意要打点这个伺候那个,要堆着笑脸,有了钱还胆战心惊。没钱的也说自己累,怕下岗怕裁员,怕老人有病没钱住院。
每次听听他们的不如意,我都替他们难受好几天。看看自己的工作环境,想想他们的唉声叹气,更觉得自己生活的舒心。
一个人只要喜欢上了一种自我满足的生活方式,就是难得的宁静和幸福。房前种菜房后种粮,悠悠闲云翩翩野鹤,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境啊。
很多人渴望在海边拥有一所房子,其实这不是房子,而是心,一颗向往宁静的心。正如有位作家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房子,这所房子朝哪里由我们的心情决定。朝东,有海上日出;朝南,有暖阳熏风;朝西,有晚霞余晖;朝北,有昔日之雪。
感谢我从一踏入社会工作开始,命运就把我安排在了祥和宁静芬芳的环境中。
生活中没有桃花源,桃花源在每个人的心里。
2. 娶不到媳妇我认了
1980年8月,我高考落榜了,回到了生我养我的西棋盘村。
“西棋盘,光棍多,缺水缺粮缺老婆。”这句民谣,真实地道出了这里乡亲们的生活境况。
西棋盘七十多户,二百多口人,分散在四个自然村里。自然村都很小,一棵棵的大树把村子抱在怀里。树很古老很高大,几百年的岁月了吧。大树怀抱里的山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云野鹤一般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默默承受着贫困和愚昧的煎熬。
像这样的小山村,在这一带多的是。零零落落的农户就像一枚枚散乱的棋子,稀稀疏疏地撒落在山坡上、山沟里。做饭时炊烟袅袅,你才发觉在这密林深处竟然还藏着几户人家、一个村落呢。
这一年,村学校的那名女民办教师出嫁去了外村,村学校停了课。五十多岁的村支书王常会来到我家对我说,孩子,我知道你是个考大学的料,可眼下咱村的娃娃没人教,你就给他们当老师吧。
当时我正全身心投入复习,准备第二年再参加高考,当民办教师实在没有思想准备。
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别听你常会叔的,好好复习考你的大学吧。你看看周围村学校的这些老师们,头发都白了,转正没指望,家里穷得叮当响,你要干了这个,今辈子打光棍定了,俺可就你这一个儿子。
母亲也对我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这些年俺省吃俭用供你念书,就是指望你能跳出这穷山沟沟,你要在这里当个孩子王,俺的心不白操了?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走出家门。正是伏顶季节,天燥热得厉害,狗们在街头吐着舌头,大柿子树下面,一堆人坐在那里正听村里的民间艺人李秀文说《聊斋》。刚绕过人群走了几步,听到村西边很热闹,就顺着声音走过去,朦胧的月光底下有十几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正在玩“老鹰叼小鸡”的游戏,阵阵玩世不恭的喊叫声惊得夜行鸟扑棱扑棱地乱飞。
再往北走,听见童年的好伙伴坤明家吵吵闹闹,进去一看,几个人正围着桌子喝散装的瓜干白酒,每人面前一大碗,边喝边甩扑克,赌8分钱一盒的“荷花”牌香烟。昏暗的煤油灯下晃动着我同龄伙伴的影子。
这一年正逢沂蒙山区大旱,土地干裂,禾苗枯死。村中的老人们商量着再用那沿袭了几百年的求雨仪式来求得上天的恩赐。几天后,隆重的祈雨仪式要举行了,族长要求一家去一个代表。父亲对我说,我身体不舒服,你16岁了,算是大人了,你去吧。记住,走哪山砍哪柴,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母亲递给我一个勺子一个水瓢说,千万别觉得识了几个字就说三道四的,别给老张家丢了脸。
父母命难违,我走出家门,和各家出来的三三两两的人一起来到村前大柿子树下,老族长简单要求了几句要恭敬要虔诚要善良心诚则灵之类的话,队伍开始往北山崮下行走。一边走,一边念叨着古老的祈雨的话谣。一德高望重者领说,其他众人应和,领说一句应和一句:也有男也有女,一群善人来祈雨,可怜农人庄稼苦,行好洒下透地雨,五谷杂粮都收成,千万善人感谢你。
人们走到山泉边,虔诚地跪在那里。老族长跳进泉里,为每个人的水瓢里象征性地舀进半瓢黄泥水,众人又开始念叨着祈雨谣往村里赶。念叨几句,大家就把水往空中洒一些,雨点落在身上,人们便喊,下雨了下雨了。队伍行进到村里,无论碰到谁,都会把水泼在他身上一些,泼到谁身上,谁都不会烦恼,都会呵呵笑着喊几声下雨了下雨了匆匆跑开。大家行进到村南的石碾前,德高望重的大爷爷空推着石碾,石碾撞击碾台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众人喊着打雷了下雨了,把瓢里的水泼到石碾上。
这样的过程每晚要重复七次,要连续进行七个晚上。如果这几天下了雨,组织祈雨者就成了大功臣,会得到村里人很长时间的尊重。如果七天后没有下雨,那肯定是参加祈雨的人中间有不虔诚者,大家会愤怒地回忆祈雨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谁谁说了什么话,可能是他惹怒了老天爷。
我随着队伍缓缓地走着,没有大人们的虔诚,也没有孩子们的天真。当全村人都跪下来等待长者焚香燃纸的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面对种种令人痛心的情景,我的心被深深地震动了:这么多年父老乡亲为什么一直没有摆脱贫困,是他们懒惰吗?一年365天,他们难得有一个清闲的日子。是他们不俭朴吗?他们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都八十年代了,山里日子为什么还这样苦?他们穷在没有文化。不懂科学,没有文化,难以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难以改变他们陈旧的观念,光凭勤劳和俭朴赶不走贫困,只有靠科技文化才能拔掉穷根。要使山沟从根本上脱贫致富,提高人的素质是当务之急,更是百年大计。今天村里需要我,我怎么能逃避这份责任呢?当教师的决心下定了,我对父亲说,打光棍,娶不到媳妇我认了,这孩子王我干了。
当天深夜,我去敲响了老支书王常会家的门。
学校没有院墙,校舍极其简陋,五间教室多年没有修缮,四面透风,屋顶晴天见太阳,雨天水流淌。老支书和我爬山梁过山谷从荒野里招回拔草的放羊的七大八小的一群三十几个孩子。又从大队粮食加工房扛来一个粉碎机破钢磨头,帮我把它吊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上,这就有了上下课敲的钟。
哐哐哐,西棋盘学校的钟声又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