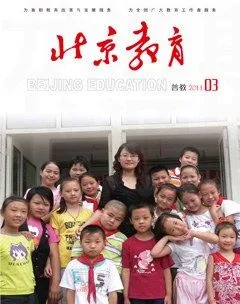回来
2011-12-29朱春蕾
北京教育·普教版 2011年3期
丹丹没去上学,已经在家休息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丹丹整日纠结于上学的痛苦和放弃学业的不甘中,父母更是焦急万分。
除了上课偶尔被老师叫起来发言,其他时间丹丹都不说话,与同学的交往很被动,和家人在一起更是没有兴趣,她心里总是烦烦的。她说,没有人会真心地和她做朋友,都各有自私的想法,付出真心只能换回来失望和伤害,所以还是不要相信别人的好。她认为社会风气也不好,即使上完大学也不见得能有好的未来。她不相信别人,不相信付出就有回报,不相信努力能换来成功,不相信爸爸妈妈是真爱她的……她从见到我的那一刻就开始不停地抱怨。想到过去的那些好时光,她对现在的自己很痛恨,她想要回到过去,却感到无能为力。
两年前的丹丹还非常自信,曾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仅人长得好看,学习好,而且还能跟同学打成一片,多年来一直在班里担任班干部,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她。因她从不以成绩的好坏去划分同学,所以同学对她很信任。同时,上学令她感到自信和有乐趣。无疑,她是优秀的,是能给家庭带来自豪感的好孩子,爸爸妈妈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我耐心地倾听丹丹的叙述,清晰的思路和反思,让我确信她应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子。我给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自我袒露,以便帮助她看到自己的内在情感。我也没有急着扭转她——把她马上送回学校(这是父母给我的咨询目标),而是一步一步地跟着她,看她想要去哪里。我深知我需要给她的是一只像温暖的怀抱一样的容器,接纳和承载着她带来的一切,让她的内心能在这里感到自由。正因如此,她非常信任我。她在咨询室里开始反思:“老师,为何我总看到负面的东西,习惯性地先想到不好的方面?其实我不愿这样。”
我问她:“你希望自己如何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呢?”
丹丹说:“我希望像以前那样轻松自在,不考虑那么多。然而我有那么多朋友,他们伤害了我,渐渐地都离我远了,因此我不愿信任别人。”由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变化的脉络,去探寻丹丹如何由原来的开朗、自信,变成现在这样自闭、忧郁。
丹丹的妈妈是位中学教师,她对丹丹的期望是品学兼优和听话。除了在学习方面盯得紧,在交朋友方面,妈妈也要进行严格盘查。她经常主动向老师了解丹丹在学校的各种情况,还不时通过短信和电话询问,对女儿十分关心。一有让她感觉不对劲的,就马上去纠正,让丹丹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妈妈经常是苦口婆心地摆出很多“严重性”、“危害性”,并以未来的种种发展目标为理由,一定要丹丹与某些同学划清界限。而丹丹身上却有一股“拗劲儿”,是个有主见和个性的孩子。她并不经常给妈妈做“军师”的机会,常常和妈妈辩论、争吵,有时甚至大发脾气,除非妈妈拿出自我伤害的姿态相要挟。有那么几次,她顶撞妈妈的时候,妈妈抽自己的嘴巴,这让丹丹退缩了,再也无法坚持自己,只好妥协。她哭着说:“我不希望妈妈为了我打自己,我必须为了她改变……”
丹丹的妈妈陷入了很多家庭的一个习惯性的悖论:除了孩子自己,别人都知道他是谁,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他是谁。因此丹丹不需要表达就可以“被了解”。妈妈对丹丹的感受和真实想法视而不见。过分担忧和过多干涉,导致丹丹对他人以及对自我评价的混乱,妈妈施加的控制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不自觉地像贴标签一样把同学分类。但她内心也因此混乱了,她也开始关注别人对她的评价和投来的目光。逐渐地她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不确信,不知道该与谁近、与谁远,该信任谁或远离谁。过于关心别人的看法,使得丹丹的人际关系变得敏感,对同学之间的交往渐渐失去了兴趣。从此,她开始有了许多对外界的批判和不满,越发退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丹丹升入高一后,学习更加有压力,身边的朋友却越来越少。丹丹内心感到空虚。曾有几次,她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想到了死。她上网查了很多自杀的方法,比如吃安眠药或者吃一大把各种各样的药,割腕,跳楼,跳河,触电……有时还幻想着自己忽然就融化在空气里消失了。这些念头在她脑海里浮沉,不知道有过多少次。
在咨询中我了解到,丹丹的妈妈来自农村,小时候生活条件很差,因为是女孩儿,在家里没有地位。她靠自己的决心、坚持和努力,考上大学并当了老师。有了女儿,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女儿身上,小时候自己没得到的一切她都要让女儿得到。她希望女儿成为最幸福的孩子。当女儿并不领情,违背她心愿时,她不舍得打女儿,只能恨自己的命运不公,以抽自己嘴巴来解恨。
妈妈伤害自己的举动,使得丹丹感受到这份母爱沉甸甸的,她虽难以理解却充满自责。丹丹压抑自己的情感,尽量按照妈妈的要求一心埋头到学习中,直到有一天,她感觉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对什么也打不起兴趣,经常暗自落泪——丹丹有了抑郁情绪。
在咨询的过程中,我尽量多地让丹丹自己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她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相当强。而在家里,她并没有这样表达的机会,妈妈自以为懂得丹丹所有的心思,总是不等丹丹张口就替她说了。爸爸近几年在外地工作,每月回家两次,对丹丹了解不够,但说起话来如胜券在握,常给她讲很多理性的大道理。我尝试着让丹丹的父母了解到,那样做无疑是让女儿认为自己的想法、判断以及选择是错的。孩子需要倾听,有时提供一双耳朵要比一个嘴巴更能带来好的效果。我让丹丹的父母意识到,他们习惯把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感受投射到孩子身上,以为那就是孩子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做法阻碍了他们去了解孩子真实的感受,也妨碍了孩子建立对自己的认知,甚至依靠从别人那里得到信息反馈来确认自己,导致迷失自我。丹丹就是在迷失的情况下,关闭了自己的内心。
妈妈坚强并固执,她是我们这个心理治疗过程中最艰难的一部分。她最难以面对否定和不认可,因为她的付出的确太多太多。而我也无意批评父母的过错,只是将我看到的呈现给他们。有一次我说:“我发现,你回家后好像还是位老师。”她扑哧一声笑了,说:“是啊,我怎么回家也变不回来啊,我得试着改变了。”还有一次她问我:“朱老师,你直接说吧,到底我们家谁有问题,反正我没问题!”我说:“其实是人就有问题,人人都有,你有,我也有。”她听完看了我一会儿,表情松弛了很多。其实,不要批评父母,他们也需要在理解和支持的情境下做得更好,与孩子一起渡过难关。妈妈在我们的帮助下,不再用自伤的方式表达愤怒,而是要求自己去承载女儿“不听话”时的焦虑,允许女儿有自己的想法和自由。爸爸也更多参与到家庭互动中,放下自己的架子,多听孩子说话。
第一次咨询后丹丹就回学校了,之后断断续续请过几次假,但最终坚持去上学了。我和她约定每周末见一次面,同时,她的父母也接受我的咨询。咨询进行了四个月,至今他们有时遇到问题还会随时来。爸爸妈妈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学习、反思并积极地做出改变。丹丹也在咨询的过程中对自己有了更多了解,重新认识了自己和他人,对自己更加确信,也更容易去相信别人,交往变得轻松了很多,并在父母的一同努力下感受到受尊重的爱,重新树立起信心。
丹丹的父母的确很爱她,她也很爱自己的父母。他们对彼此的期待都没有错,只是父母忽略了个体性的差异,从而少了对个体的尊重。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的抑郁来自于无法做他自己。缺少尊重时,孩子会感到自己不重要,情绪低落或变得喜欢对抗。父母常常以爱的名义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却忽视了孩子内心的情感需求。受到委屈的孩子,很少去反省自己有什么过错,而被感动的人则更容易自省,并且因为感动增加内心的勇气和自信,同时他的自制力也会增强。尊重孩子,是父母必修的功课;放开孩子的手,是父母必经的考验。■
相关链接
友谊医院心理健康之友(简称“友谊心友”)成立于2001年,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科心理门诊柏晓利医生倡导成立,现有来自北京地区各大院校和专科医院的心理治疗师30余人,是由众多热爱心理健康事业的人共同打造的追求心理健康的平台。经过9年的发展,“友谊心友”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理健康促进模式,包括针对疾病人群的个体咨询和团体咨询,以及促进健康人心灵成长的心理课程、发展性咨询、企业内训、课题研究、学术交流等,尤其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与亲子教育。
详情登录:www.youyixinyou.com
心理帮助热线电话:010-63031521,63043023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东经路6号院1号楼2-311室(友谊医院急诊旁)
□栏目编辑 江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