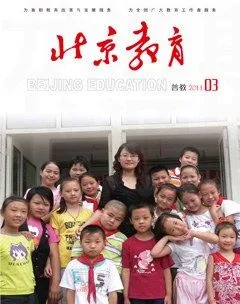有趣味的关联
2011-12-29邰亚臣
北京教育·普教版 2011年3期
学术研究必须注重逻辑的力量和完整的过程,这是学术产生力量的基本要素。但寻找什么样的内容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学术产生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当前中学学术研究缺乏学术基本要素是一个问题,但更为严重的是学术研究内容空洞、单一和虚假,简单地说,中学学术研究缺乏这个研究阶段所应具有的灵活、可爱和温暖。我认为造成如此现状和以下两个问题相关。
学术研究目标的异化。和工作相关的学术研究不能只是让研究者本人高兴,更不能在功利驱使下仅仅完成预设的目标。但扪心自问,今天中学的学术研究如果能出自于研究者本人的浓厚兴趣,即便是自娱自乐已经是很奢侈、珍贵的行为了,更多的是为晋级或者证明自己地位提供一个合理依据,这就是研究目标的异化。我认为,中学学术研究目标中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通过研究帮助孩子们获得智慧、温暖心灵并感受知识带来的快乐。
整体文化观的缺失。我们并不缺乏很多具体领域的深入研究,甚至可以说探讨各种解题方法的文章已经“蔚为壮观”了,思考各种意义和必要性的文字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但我们却严重缺乏生动的、新鲜的内容,导致虽有深入研究但缺乏更精深的理解,眼界狭窄,只能在有限的领域打转,这说明我们似乎更缺乏的是整体文化观的建立。长期以来,我们设置的学科藩篱已经让很多学生和老师筑起思维的高墙,与其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如说是不肯走出自己划定的势力范围。但这样的结果是,我们的知识越来越抽象,学科界限越来越扩大,知识似乎成为了某种权力,绝不容许他人染指。这不是知识和文化的本来面目,其实高考方案中设立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此,那就是打开不同学科的道路,让思维自由通行。
中学学术研究一定要注重趣味性,建立让思想四通八达的网络,最终才能让孩子们感受知识的温暖和快乐,因此,中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思考怎样构建有趣味的关联。
这是一个有点陌生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下面以笔者读过的两篇和长城有关的文字后展开的联想为例,看看建构起一些有趣的关联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篇是美国人Peter Hessler写的《Walking the wall》,另一篇是中国日报记者周黎明的《太空看长城采访记》。 前一篇文章至少让读者了解到以下事实:
1.研究长城的学者或者爱好者中,有很多外国人,具有影响力和研究达到精深水准的基本上是外国人(这对于把长城视为民族象征的国人来讲,未免有些尴尬);
2.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有专门的长城研究学者,即便作为长城的东道国,学者们的兴趣似乎也不在此。外国人是这样认识的: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专注于政治体系研究,而考古学家则致力于挖掘古墓。长城在传统学术领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对于某个独立的专题,如明长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凤毛麟角。
3.文章的主角,美国人David Spindler(石彬伦)研究长城采用了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可谓遍走长城和找遍世界各地和中国长城有关的书籍。
4.长城有太多我们未知的领域,例如长城的长度,1985年,中国的卫星调查认为,北京地区有390英里的长城,但David Spindler发现的要比这一数字长得多。
《太空看长城采访记》则充满了太多的玄机,记者周黎明从一个流传很久的——长城是唯一能够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建筑——这个说法开始产生怀疑,进而展开一系列调查研究,得到了更加让人扑朔迷离的答案。
笔者从这两篇文章开始展开联想,在几个领域来回穿插,建立了这样一些有趣的关联。
历史学意义上的关联
长城如何成为能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唯一建筑?这个说法是如何形成的?根据“国际长城之友”的创办人威廉·林赛的研究,这个说法起源于西方,最早的源头是英国历史学家兼旅行家斯图克利1720年漫游欧洲,在记述罗马哈德良长城时说:这长城如此宏大,只有中国的长城超越了它,而中国的长城如此之巨,可能可以从月球上看到。
这就是美丽说法的起源,然后经过不断的揣测与口传的描述,这个说法开始顽固地在西方生长。1793年,英国军官帕里什上尉随英国使团到承德觐见乾隆皇帝,途径古北口长城,后根据印象画了一幅水彩画,又被加工成版画开始流传,画中的长城非常宏伟壮观。
1907年至1908年,英国人威廉·盖尔花费两年的时间徒步长城,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并撰写了史上第一部调查、记录、研究长城的专著。
1923年2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如此写到:依天文学家所言,在月球上肉眼可见的唯一一件人类作品是中国的长城。
1929年,英国人海斯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的长城》,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长城如此巨大,大约能从火星上看到(进一步夸张)。
这些真实的记录和道听途说、艺术夸张杂糅在一起,逐渐演变成为西方人所谓的市井神话:长城是能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唯一人造建筑。
1972年,美国阿波罗17号登月总指挥尤金·塞尔南表示,他在太空旅行中看到了长城,为这个让中国人充满自豪感的西方市井神话作了最有力的佐证。
这是这个说法的历史变化。其实根据长城这个话题,可以顺带出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比如:修长城的季节一般是在春天,此时天气晴和,而蒙古袭击者还不活跃。因为蒙古人南下全靠膘肥体壮的马,寒冬过后,马尚在恢复之中。夏天太热,蒙古人受不了酷暑,蒙古人的弓弦是兽皮做的,湿气让弓弦无力,所以袭击大多发生在秋季。再如,从秦始皇开始历朝历代都面对同样的难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修长城就可看出不同朝代的外交政策,唐朝基本上没有修城墙,说明唐朝善于应付边境冲突和有着自信灵活的外交。
科学意义上的关联
那到底能否从太空上看到长城?
2003年10月“神5”上天,杨利伟太空归来说他没有看到长城,后来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有长宽都达到500米的物体才有可能从太空被看到。这对一直以来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那个西方市井神话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是科学胜利了?还是感情输了?
2005年,中国日报的周黎明到美国休斯顿探亲,正好赶上美国宇航局的华裔宇航员焦立中在太空站执行任务,于是他们建立联系,启动了太空看长城计划。
但问题随着观察的进展而变得越发复杂起来,焦立中没有给出看到或没看到的回答,而是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回答:能看到,但无法辨认。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答案?因为在晴天,地球上的高速公路等很多建筑物都能被看到,埃及的金字塔也能被看到。但长城不太规则,而又处在山野之中,所以焦立中说他似乎是看到了,但不能确定,于是传回照片。周黎明把照片送到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魏成阶教授那里求证。求证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原来焦立中认为的可能是长城的部分,连山脊都不是,恰恰是山谷和河床。科学上的地图分析远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认识要复杂得多,况且这是相机“看”的结果,还不是通过肉眼得出的结论。
但问题是美国的尤金·塞尔南说他看到了长城,该如何解释?于是周黎明和塞尔南取得联系,并求证了当时他的太空飞行距离是160公里左右,经科学的推断证明从这个距离几乎不能看见长城。但塞尔南却非常确信:就是长城,一眼就看到了!周黎明于是又和专家进行分析论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塞尔南看到的很可能是黄河,不是长城。但他应该没有故意撒谎,很可能在美丽神话的迷惑下,以为长城能一眼望到。
在进行完科学的关联之后,笔者把思维的触角伸向航天,即便今日航天科技水平日新月异,但对于广阔的世界,人类依然还显得那么幼稚和无助,也许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成功,而忘记了我们也曾经有过那么多的伤痛记忆,比如美国的挑战者号爆炸。于是,笔者看了很多的关于挑战者号失事的材料,从占有的材料中,又发现下面两个有趣的关联。
政治意义上的关联
当面对灾难以及公共危机时,国家的处理对策具有深远的影响。当年美苏争霸的结果是苏联陨落,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实这一结果从航天斗法即可见一斑。争霸过程中,美国的很多技术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与发展,而苏联的技术就仅仅停留在了军事领域,这和公开、透明的政策密切相关。例如,苏联当年在航天探索上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苏联人的思路是报喜不报忧,这样的结果是科学失去人情味变成怪物,而美国把每一次的失败都变成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挑战者号失事后,里根总统很快就发表了一篇电视讲话,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对我们的太空计划充满信心与尊敬,今日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会降低这种信任与尊重。我们不隐藏什么,我们不掩盖秘密,我们一切都在大家和公众面前,这是自由的方式,我们一刻都不会改变这点。我们将继续我们的使命,将会有更多的航天建设、更多的宇航员,是的!还将有更多的志愿者、百姓,更多的教师。这一刻,没有任何事情结束,我们的希望和旅行继续!”
连一次失败都成了自由价值观的胜利,你不能不佩服美国人的公共危机处理能力。有了这样鲜活的材料,再来回望历史,分析冷战就有了超越课本的历史注脚,而且还带着人的温度。
英语和文学意义上的关联
在读了大量的英文原版资料后,我突然发现,无论是应对公共危机还是安抚情感,前提是必须有发自内心的艺术的表达方式,文学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
里根的两篇演讲用独特的表达方式所产生的艺术美感和情感冲击力,今天读来,依然保持着那种伤感的惯性。现节选两段:
“挑战者号的成员们用他们的生存方式荣耀了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今天早上我们最后看到他们向我们挥手道别,然后摆脱大地执拗的束缚去触摸上帝的面容。”
“我们今天齐聚于此,沉痛哀悼我们失去的7位勇敢的美国公民,共同分担我们内心深处都能感受的悲伤,也许在相互的分担中,才能发现抑制伤痛的力量,才能寻找到希望的种子。”
无独有偶,在挑战者号失事后,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发来了一封不一样的唁电:“我们至今怀念着哥伦布,他是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先驱;我也怀念挑战者号的勇士们,他们同样也在探索未知世界,我的自豪感和悲痛感同在,不过我想办法用自豪感压抑我的悲痛感。”
继续搜索,又有一篇美文出现,那就是当年阿波罗登月时,美国做了最坏的打算,即登月失败,宇航员牺牲,为此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准备了一篇失败演讲:命运注定这些登陆月球进行和平探险的人将在月球上安息。两位勇敢的人已经知道自己无法生还。但他们知道其牺牲将为人类带来希望。他们为人类探求和认识真理这一最高贵的理想而捐躯。他们将被亲友、国家、世人哀悼;他们更会被敢于将子民送往未知之地探险的地球母亲所哀悼。他们的探险,鼓舞世人团结一心;他们的牺牲,让人类四海一家皆兄弟的情谊紧密相连。在古代,人类会抬头仰望星空并在星座中看到英雄;在现代,人类也会看到自己的英雄,但我们的英雄是新鲜的血肉之躯。未来将有更多人追随其脚步,但他们会找到回家的路。人类探索宇宙的雄心壮志不会因此而被放弃。这些牺牲者是第一批,将在人们心中永垂不朽。每一个在夜晚仰望月亮的人都会知道在那个世界有某个角落始终吸引着人类。
这是多么难得的英语教学和文学教育的材料,不是抽象的单一素材,这里面有科学、情感、政治与艺术。
通过以上历史、科学、政治与文学四个方面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出,仅仅是多一些好奇心,利用手边不需费太多力气的材料,我们就能编织出一张纵横交错的知识与文化的网络,情感就会在这个网络里通行,学术问题将变得不再枯燥和生涩,而是充满生机与趣味。
最后,我们必须要重申一下,无论是任何工作,可能学术研究尤其如此,都需要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热爱与勇气。再回到第一篇文章中,文章的主角 David Spindler把人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一项得不到官方和研究机构认可的事业中去,他能把全部生活——稳定的收入、爱情、人身安全——都拿去冒险。但他无怨无悔,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快乐。有人说,有时这种固执地追寻一个非同寻常的建构行为看来是唐吉柯德式的,但实际上支撑这一切的是完全的理性。这同时让笔者想到了苹果公司乔布斯的一段话:“我确信唯一能让我坚持下去的就是我热爱我所做的事情。你必须发现你所热爱的东西。你的工作将占据你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但唯一能让你宽慰的是你所做的是件伟大的事情,而唯一能做伟大事情的方法就是无限的热爱。”学术研究不一定都要搭上生活的全部,但一定离不开兴趣以及进而产生的热爱。■
□编辑 王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