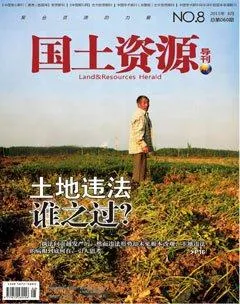土地违法为何屡禁不止
2011-12-29汤冰
国土资源导刊 2011年8期
土地执法局面的改善期待的是一次从头到脚,从根源到表象的全方位制度变革。
7月,首次土地违法问责结果正式公布,73个市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被给予纪律处分,24个市县政府负责人被给予组织处理,此次问责结果被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称为是一次“动真格的突破”。
这场问责风暴始于2010年12月,当时违法用地较为严重的5个市(州)、7个县(市、区)的政府主要负责人被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请到北京进行集体约谈,被约谈的都是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超过15%,在全国范围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排名靠前的城市。而此次问责结果名单中的部分地区亦曾出现在去年12月的“约谈名单”中,如山西省大同县、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浙江省上虞市、辽宁省庄河市等——“约谈”只是预警,如果大量土地违法违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国土资源部就只能动用其他手段。
与之同时公布的另一组数据却不甚乐观,根据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新发生违法用地2.3万件,涉及土地面积13.6万亩,其中违法占用耕地5.1万亩。徐绍史表示,上半年土地违规违法宗数、面积,包括耕地面积不同程度有所反弹,违法用地形势依然严峻。
执法问责越发严厉,然而违法形势却未见根本改观,土地违法的病根到底何在,引人思考。
特殊的违法主体
今年5月,河北香河土地违规案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这个“皇城根上”的小县城违规圈占农村土地,涉嫌占地规模高达4000亩。香河政府一边以千余元/亩的低价征收土地,一边以60~80万元/亩的高价转手出让给房产开发商,上演了一幕低吸高抛的“商业成功模本案例”。
而在年初国土资源部通报的案例中,四川省简阳市政府违法违规同样极具典型意义:2008年至2009年间,简阳市政府先后4次以政府常务会议的形式,决定将三岔湖周边20宗共6204.47亩土地出让用于旅游、商住开发,其中集体土地4659.91亩(耕地1498.62亩)。2009年4月至2010年1月,20家公司先后通过拍卖方式竞得上述集体土地,土地出让价款总额7.48亿元(已缴纳5.27亿元)。此外,2008年至2009年间,简阳市政府还以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的形式,同意将10宗集体土地和国有未利用地划拨、出让用于学校、工业和房地产项目建设,总面积1081.35亩,其中耕地621.34亩。
厦门大学财税系教授梁若冰对近年来的土地违法事件进行了统计,他说,在土地违法的实施者中,各级地方政府(包括村集体)及企事业单位违法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从土地违法的涉案面积看,地方政府的份额在2004年以前都占到了30%以上;而作为最主要违法者的企事业单位,其涉案土地面积比重仅在2000年和2001年为40%以下,其余年份均为50%左右,2004年甚至达到了65%。
梁若冰进一步表示,还有些时候,尽管地方政府未直接实施某些违法行为,但对于很多企事业单位的违法行为采取了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事实上,很多土地违法行为,没有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土地管理部门)的配合,是根本无法实施的”。
“已经公布的土地违法事例可以说只是冰山一角,现在地方政府违规占地,或者将耕地变为建设用地,或者是土地闲置的现象很多。”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博士、土地评估师张远索对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屡屡出现土地违法行为,最主要的驱动力还是利益。
而梁若冰则认为,除了土地逐利的成本原因外,违法出现的主要诱因是地方政府对GDP、财政收入与吸引外资等经济指标的热衷。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工业相对于农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又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利用土地发展工业方面的热情要远高于将其投入到农业生产上。
行政体制成羁绊?
违法主体的特殊性是土地违法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而作为主要监管部门的国土资源部门在这其中扮演的却是一个尴尬的角色。
一位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官员的话颇能说明问题:“需求在增长,但用地计划指标却难以惠及。目前下达各地的指标基本上用于保障重点项目和‘书记、市长项目’,其他如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村用地需求基本无法满足。一般来讲,计划指标经省市层层扣减后,到县级每年可支配的指标仅有200亩到300亩左右,且都投在县级政府需要保证的重要项目上,实际落到农村的很少。因此,面对违法用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无法‘硬气’地查处”——目前的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地方国土资源部门能够从上级拿回多少用地计划,往往成为了衡量其工作做得好不好的硬性指标。
除了指标式考核外,现行的行政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土地监管部门发挥其职能,甚至很多时候还不得不成为违规操作的帮凶、执行人乃至替罪羊。
不久之前引发热议的“何耘韬案”便是这样一桩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案例,廉江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何耘韬,因执行上级指令违规发证,被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何耘韬一度坚持原则,对不符合规定的用地申请拒不发证,却最终因为承受不住地方政府的重重压力而只能妥协。“明知违法的事情,办了慢慢死,不办马上死。在权力与法律压力面前,我们没有选择。”
对此,不少地方国土资源部门的管理人员颇有共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果因违法占用耕地比例越线而问责地方政府负责人,该地国土资源局局长、国土所所长能脱掉干系吗?更有甚者,一些市县政府负责人早就放出话来:撤我的职前,先把你们(国土干部)撤了。”
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副局长王延杰表示,现行的政绩考核、事权分配和行政管理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政府不但要承担行政管理职能,更要担当加快发展的重任。国土资源部门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既要贯彻中央保护耕地的战略决策,又要执行地方政府加快发展的决定,两者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很难完全一致,基层国土部门身处其间,饱受协调之难。
国土资源部一直在呼吁探索的国土资源管理共同责任实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此考虑,避免国土资源管理中“人人有责,实际人人不担责”的局面一再出现。
基层执法无力
近年来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农村土地违法比重抬头。
随着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加大,用地供地矛盾日益突出,加之国家相关法制建设滞后,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环境有进一步恶化趋势,全国范围内暴力抗法现象时有发生。
今年5月16日,娄底市双峰县井字镇国土资源所干部曾森林在土地违法动态巡查中,阻止村民违规建房却遭遇暴力抗法,造成重型颅脑损伤并颅内出血,一度生命垂危。
2009年11月12日,青海天峻县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在例行巡查中遭遇暴力抗法,导致两名执法人员因伤势严重入院……
按照《土地管理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土资源部门主要的职责是“巡查、发现、制止、查处、报告”。这也就意味着,国土资源部门在发现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后,有权报告给地方政府,但没有权力要求地方政府如何去做。
实践中,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联合执法。但相关人士透露,即便采取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等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相关职能部门也仅配合为主,“唱主角的还是国土资源部门”,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和执法程序的复杂,对国土资源非法行为处罚和震慑力度自然难尽人意。
执法能力的先天不足,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酿成了基层国土资源执法的无力状态,打击土地违法的基础同样薄弱。
土地执法局面的改善期待的是一次从头到脚,从根源到表象的全方位制度变革。
地方国土资源部门既要贯彻中央保护耕地的战略决策,又要执行地方政府加快发展的决定,饱受协调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