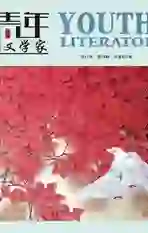“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2011-12-28黄予慧
摘 要: 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诗派和山水诗派,成为中国古代隐逸诗歌的先驱人物。二人都在仕途受阻时选择了隐逸的道路,并转向隐逸诗歌的创造之中。虽然人生经历相似,诗歌题材相类,二人但诗歌境界却大相迥异。本文借用“无我之境” 与“有我之境”两种提法,说明陶谢诗歌境界的高低,并简要分析境界不同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陶渊明谢灵运比较
作者简介:黄予慧,女,壮族,1977年4月出生,广西百色人,学士,广西大学2007级古代文学在职研究生班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6-0012-01
晋宋之际,陶渊明新创田园诗派,谢灵运宕启山水诗风,并称为中国隐逸诗风的先驱人物[1]。但陶谢二人的诗风境界却大相迥异,陶渊明的诗文已达“无我之境”,而谢灵运始终停留在“有我之境”中。本文通过对二人作品的对比分析,一探二者诗歌境界相异的原因。
一、陶诗的“无我之境”与谢诗的“有我之境”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出自王国维《人间词话》:“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陶渊明的田园诗,是“无我之境”的典型代表。王国维评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无一字臧否,任由读者自行品悟,于不动声色之中见意境,这就是“无我之境”。陶诗中的田园不仅是眼前景,更是胸中意,成为宁静内心的外界自在观照,蕴含着一种返璞归真、“似澹而实美”的无穷韵味。
而“有我之境”,则指那种感情比较直露、倾向比较鲜明的意境。谢灵运的山水诗即这一境界的代表,他的诗遣词用句精工富艳,但主要侧重于对山水的客观欣赏。如 “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二句(《过始宁墅》)。谢笔下的山水“体物为妙”,是写境而非造境、写生而非写意,虽“大必笼天地,细不遗草树”(白居易《读谢灵运诗》),却使诗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审美的距离。谢诗通篇有“我”之眼,而无“我”之心,山水景物与作者的情志之间虽互有寄托,始终达不到陶诗“情景交融,寓情于理”的境界。
二、陶谢对仕隐态度的不同是境界相异的直接原因
同为隐逸诗宗,陶谢二人对待仕隐的态度不尽相同,陶渊明超然止泊,谢灵运则难脱执迷。这种出世入世的差异,造成了两人迥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前者终老山野,后者却是被诛闹市;也造成他们诗歌的两种不同境界。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在“起为州祭酒”、“复为镇军、建威参军”、“以为彭泽令”(《宋书》·隐逸传)的数仕数隐之后,认为仕宦生涯对于他犹如“冰炭满怀抱”,断然发誓“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坚定不移地开始了彻头彻尾的田园隐居生活。通过其晚年《饮酒》组诗可以了解到,虽生活困苦,但陶渊明隐居之心并未动摇,始终誓言“吾驾不可回”。谢灵运则出身于高门士族,祖辈谢安石等人战功赫赫,继承先祖、建功立业的理想牢固扎根在谢灵运心中,只是由于刘宋压抑士族的政策和个人际遇等现实原因,迫不得已隐退。这种被动的选择是不坚定、不彻底的,谢灵运承认自己“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登池上楼》),他几度隐而复仕,仕而复隐,这种欲仕不能,欲隐不甘的矛盾,一生都在噬咬着谢灵运的心。
断然与黑暗官场决裂的陶渊明,“心远地自偏”,平心静气把自我融入田园,在理想化的田园中完成自身的人格塑造和审美追求。而对官场念念不忘的謝灵运,“离群难处心”,始终是一个疏离的过客,“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笔下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地纠结情感,纵然“游娱宴集,以夜续昼”,仍是“别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最终只剩“寂寞”二字。
三、陶谢对内心关注度的差异导致了二者诗歌的境界高低
沈德潜《古诗源》认为,“陶诗之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之不可及处在新在俊”,真、厚二字,所形容的皆是内心感受;新、俊二字,所形容的则是遣词用句的风格,这也点出了陶诗和谢诗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的最大不同。陶诗融入了自己的劳动体验和心灵思索,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辨。“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饮酒》组诗)。陶渊明认为,“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坚守一个“道”字,坚守高洁的人格操守,即使在“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艰难岁月中也矢志不改。陶渊明的思想超脱了世间物质欲望的贪求,达到了“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无我”境界。更难得的是,陶渊明能够把自己的思想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诗句之中。他的诗,情在景中,理在情中,情、景、理如水乳般自然交融,这是陶诗最鲜明的艺术性所在。
相比之下,谢灵运纵情于山水之中只为排遣抑郁之气,正如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中所写“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他的诗情景割裂,很难表露他的内心思想感情。更重要的是,孤傲的谢灵运极少对自己的内心进行反省,《南史·谢弘微传》引谢混语说他“博而无检”。当时的莲社高僧慧远,就瞧不起显达的谢灵运,认为他“心乱”,但慧远却特别写信请渊明 [2]。缺少思考与内省的诗思想性偏弱,因而谢诗多是比较机械地借用玄言佛经的词句进行说理,诗末尾往往加上“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等句子,拖上了一条玄言的尾巴。黄节《读诗三札记》“山水不足以娱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忧”一句,点出了谢诗的根本弱点。谢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在读者引发的共鸣程度方面,都远不及陶诗。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中国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历史对两人的评价却在不停变迁。南朝300年内,人们对陶渊明评价不高,钟嵘《诗品》仅列陶为中品,而列谢为上品,但宋朝之后,对陶的评价却远超谢灵运,称其为“清淡之宗”[3]。陶谢诗歌评价的变化过程,正是人们对诗歌境界再思考、再认识的过程。陶渊明在“无我之境”中写就的诗歌,历经了时间的沉淀,更彰显其“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的思想、艺术魅力,他的诗品和人品都赢得了历史的高度评价,深值后来人瞻仰学习。
参考文献:
[1] 霍建波. 宋前隐逸诗研究[M] .人民出版社. 2006
[2] 朱光潜. 诗论[M]. 北京出版社, 2009
[3] 陈寅恪.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M]. 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 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