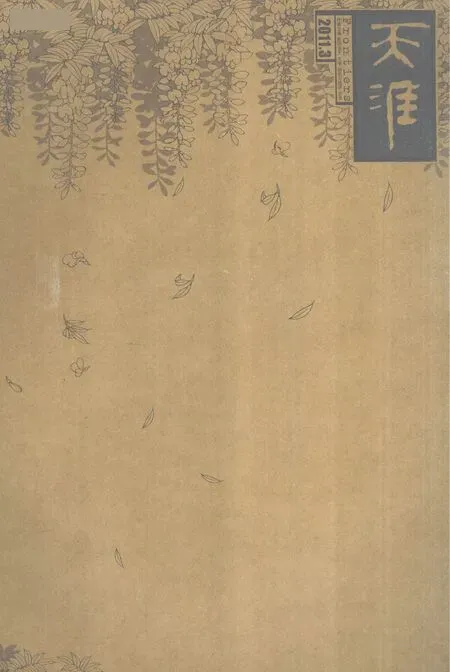风把银幕上的脸吹凹
2011-12-26巴音博罗
巴音博罗
卡夫卡曾说:“电影是一件了不起的玩具。”但是他却不堪忍受。因为电影使他“裸露的目光穿上了制服”。卡夫卡真是一个怪异而有趣的人!而我正好与这位幽魂般的小说大师的看法相左。我喜欢电影胜过喜欢生活。有好多时候,我时常会把自己当成电影里的某个人物,我用臆想中的某个电影人物的腔调说话,借用他的目光观看现实生活中的人或物,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水塘中并痴迷地爱上了那个水中倒影一样,这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啊!电影使我的整个童年史有了诗意,也使那个贫瘠的年代在现今的回忆里呈现出万千风情,仿若那些早已逝去的单调而平静的日子。我的生活因此虚幻且美丽起来,成为灰暗穹窿中的一道炫目的彩虹,重新明亮了我——一个年逾不惑的中年人的心灵。
生产队场院里的《白毛女》
我父亲是水文站里的工程师,儿时我家总是在辽东南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中生活,又总是离不开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江或大河。生活是异常孤寂而清苦的(往往上学都要走十几里崎岖山路)。那时候日常娱乐几乎没有,除了与野山野水亲近之外,在我们这些可怜的乡村少年心中,就唯有偶然盼来的露天电影能给我们饥渴的幼小心灵添加些快乐的滋润了。
最早的记忆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一个以阶级划分人群的严酷而荒凉的年代。那时我八岁半,刚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傍晚——晚秋的稍稍有些霜冻的朗朗晴夜,父母带我去前沟看电影。过了一道山冈,就看见月白光雾中有剪纸般的人影从沟沟叉叉游聚向生产队大院。我又紧张、又兴奋,一只手死死揪住父亲衣襟,生怕被甩下。
进了院子,迎面便见一黑边白布的银幕扯在中间,全村老幼乱嚷嚷自找位置。有搬来木板凳的,有捡块石头垫屁股的,也有懒散者,只叼着旱烟袋在地下唠些闲嗑。而半大孩子们则兴奋异常,在人缝里穿来拱去,时常遭到大人们的训斥。看看时间不早,队长便吆喝一嗓,闹哄哄的人群霎时静下,大伙这时才望见,那暗黢黢的人影里立了两个陌生人,此刻全都冷着脸,仿佛有啥天大横事要说。我有些害怕,便往母亲怀里倚过去。懵懵懂懂中,似乎来了啥最高指示,又说今晚放电影前,先要搞个什么忆苦思甜。有人抬上一八仙桌,有人将本来就昏暗的白炽灯遮上块青布,使整个场院阴森森暗得可怕。这时一对青年男女唱起悲悲的调子,接着又有人从煮猪食的灶房端来溲气熏天的一瓦盆野菜汤和拌了榆树皮的面糊,而围在四周荷了枪的民兵们便组织村人排队上前领取。我看见父亲绷着脸强吃,我也尝了一点,却哇地吐地上了。那东西又涩又苦还臭气哄哄,仿佛一摊狗屎。
接着便开批斗会。反绑双臂的人像一串蚂蚱被押上来,大伙呼一阵口号,复又将其押下,这时才开始放映电影——舞剧《白毛女》。我奇怪那衣衫破烂、白发飘飘的女子为何总是用脚尖走路,她的模样总使幼小的我想起村里跳大神时的巫女——瘸子刘有钱的老婆王二丫。
电影放映中途,我去场外撒尿,听到牲口棚传来狼似的惨叫声,偷偷溜过去窥看,但见几个彪形大汉正用皮带抽打地上打滚的一妇人,我吓坏了,急忙缩回头,尿把裤角都溅湿了。
月至中天时,电影终于放毕。回家路上正撞见押送坏分子的一行,父亲一边与那民兵说话,一边用手电筒照了照押在队尾的老女人,光柱下我蓦然望见一张惨白的满是皱纹的脸,在强烈的光影里死气沉沉地闭着眼。
我认得那是死去多年的老地主徐堡的老婆。
响哨村的《铁道游击队》
我家住水文站的家属房。家属房在水文站的院里,整整三栋黄泥草舍全都孤零零壁立于陡峭悬崖上,我和弟弟们在院里弹玻璃球时,一不小心,那彩色的球就会滚进崖下波涛汹涌的古洋河里。
这儿是两条大河的交尾之处。河边礁石林立,河底浪急沙涌,很是吓人。平日村民过河,都坐水文站测量用的木船,船是拴在拦河钢索上的,靠水流的冲力和舵的作用溜向对岸。
响哨村即在河流拐弯处的下游。那儿有一片绿雾状的榆树和柳树,挡住了我眺望的视线。好在水文站配有一架苏制的军用望远镜,(那是水文测流时观侧浮标的仪器),我常拿来无端地往对岸巡睃遥望。
有一次我望见一个看山的村民蹲在草丛中屙屎,还有一次我看见一头狍子在丛林里奔跑,我兴奋地大叫一声,声音空空传过河面,那狂跑的狍子竟突地立住了脚,呆呆回过头来,真是有趣极了。
河这岸沙里寨乡中学的体育老师与河对岸响哨村的女子刘香香谈恋爱。两个人总是我送你来你送我的,一副恋恋不舍的亲热劲儿。有一次我在望远镜里看见体育老师搂着刘香香亲嘴,我一叫,水文站的老王就把望远镜抢过去,再也没撒手,急得我乱跺脚。
响哨村常放电影,夏天我们常坐船过河。村里人也来凑热闹,人满满登登挤上船舱,那船晃晃悠悠几乎沉没,所以好多女子都脸色发白,慌慌地抓住身边船舷。有时候遇到激流漩涡,船便像受伤的牲口似的,身子一栽楞,惹得女子们一片惊呼。我家邻居老杨家的女儿小青,这时便会紧攥我的手,攥得生疼生疼,但我的心却山雀子一般好欢喜哩。
有一回看的是《铁道游击队》,回来时早已是夜深人静的半夜,远远地传来几声梦幻般的狗吠,对岸的村庄陷在浓浓的阴影下仿佛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十几人上了船,木蒿撑进沙底发出沙啦沙啦的暗响,而船头犁开湍急的水流则是嘹亮的哗啦哗啦的脆响。船行至河中间时,一轮铜盆大小的满月从黑黝黝的山脊上升起,将整个河谷照得亮如白昼。有人轻轻哼起《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曲:“西边的太阳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声在静谧的穹空中飞翔,传得好远好远。
有一只夜眠的水鸭子被惊起,扑噜噜飞到沙洲中的苇丛里去了。
这时船在水中起伏,我们在月光中颠簸,我们全部变成了鱼了。而我心仪的女孩儿小青就坐在我身旁,那月亮般明丽的俏脸上两只大眼睛,正久久望着我,仿佛通了电,望得我的心慌慌的。
若是到了冬天,我们看电影时就会各自坐了冰车去。大河那时被完全冻上了,千里冰封的冰面上平展展的,与两岸雪山交相辉映。如果恰好也赶上个冬月皎洁的日子,就更别有一番情趣了。冰车在冰蒿的用力击撑下在明镜般的冰面上飞驰,心儿也会鸟儿一样翱翔在神秘、美丽的夜空中,而电影不过是在那个沉闷年代降临的闪电一样的短梦罢了。
沙里寨野河滩上的《桥》
少年时代我看电影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公社所在地——沙里寨了。那儿离家整整二十华里,中途要翻过两道山梁、一条河和一大片鬼魂出没的乱坟岗子。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心灵因为极度的饥渴而慌不择食。我总是在看电影中途因害怕被同伴甩下而东张西望心神不安,我总是在归途时因瞌睡几次栽到路边的水稻田里弄得浑身湿透一副狼狈相。那时,我是多么羡慕住在公社周边的人啊,我觉得他们就像住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一样了不起。多少年后我回忆起这些事仍然耿耿于怀双目喷火。
而那次初冬的经历——那次初冬的特殊画面,强烈和深刻得如同用烧红的烙铁烙在皮肤上一样终生难忘。
我记得天边还积蓄着血痕似的晚霞时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一路走一路议论,都不知今晚放的是哪国片子。有说是阿尔巴尼亚的,有说是苏联的。就这样一路小跑走到天黑才赶到大沙河边。那儿高高耸立着一座独木桥,桥下是刚刚结了些许冰渣的河水。我们到那儿时,但见两岸人山人海,长长的人龙通过颤巍巍的桥木从这岸逶迤向另岸。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挤上桥头。两根拼在一起的桥木大概只有腿根粗,人踩在上面,整座桥都会发出令人心惊胆寒的脆响。尤其是一眼望见脚下湍急流淌的冰冷的河水,在星月的辉映下泛出黑幽幽的光泽,我不禁头晕目眩起来。我小心地把手搭到前面那人肩上,后面的人又把手搭到我的肩上,就这样仿佛一条缓缓蠕动的长虫,在天光晦暗的河面上,这人肉长虫一小节一小节向前爬行着。因为这桥中间高两头矮,有一个可怕的坡度,所以当人走到河中间时,亦是坡度最陡的地方,有人头一昏眩,脚下一滑,便跌落冰冷刺骨的河水里。
这仿佛是连锁反应,有一人滑落,往往会牵扯另一人。夜色中只听见扑通、扑通不断的水响,宛如下饺子一般,也闹不清那晚到底有多少人洗了冷水浴。
幸亏我没摊上这等可怕的事儿。到了河对岸时,便急急赶到架在野河滩上的银幕前。由于那夜十里八乡赶来的人太多,银幕两边都挤满黑压压的人头。好在我个头高,总算把那个南斯拉夫的著名二战影片《桥》看了个大概。这是我看到的最惊心动魄的战争电影,它摧毁了以往我对战争电影形成的俗套概念,好像冬夜穹空中的一道炫目的闪电。我在少年时代平庸的生活中第一次看到赤裸裸的真实的人性,看到了残忍和爱的另一层新义。我完全忘记了吹拂在脸上的寒风和刚刚的不愉快。
影片中途换片时,看电影的人群忽然潮涌起来,一些不怀好意的青年男人一边坏笑一边起哄,推来挤去的人们早已不分男女老幼,尤其一些俊俏的姑娘媳妇的周边,总有汉子们挤挤擦擦拥作一堆。而此时女人们也不生气,她们似乎也情愿有点乐趣以便驱走寒冷。我看见一个小伙把手贴到了一个姑娘的胸乳上,另一个大胡子则用大腿撞了一个肥壮女人的屁股。大伙哈哈怪笑直到电影重新开演。
那天晚上我还遇见了我班的女同学兰子,她那双星眸闪闪烁烁,总在我的身上环绕。她瘦骨伶仃的胯骨顶得我的腰好酸好酸。后来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牵了手,我的手上尽是热汗,好像我热气蒸腾的头发。我俩钻到有些干枯的柳毛子里亲了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初吻。
一次奇妙的除夕夜
那一年我十六岁,正是牛犊似的浑身有劲没处使的年纪。我们上山套鸟,下河捉鱼,整日里弄得鸡飞狗跳,难得有个消停的时候。有时自然就免不了挨骂。
记得这一年的岁末,进了腊月过小年儿,杀完年猪又包冻饺子,转眼便到了除夕这天。邻居小三子是个屁眼插电线的万事通,不知听谁传的,说离此十五里的邻县龙王庙村要放电影。冬闲里大伙正闷得浑身难受,一听这消息便猫抓般难耐,纷纷吵嚷着要去。虽然那龙王庙山高路远又崎岖难行,但电影的诱惑可远比年猪肉谗人。
龙王庙在大洋河下游,从我们村通向那儿的只有一条羊肠般曲曲折折陡峭难行的山路。这山路一边是悬崖绝壁的长白山余脉,一边是波涛湍急的古洋河水。平日里除了采蘑菇的、挖草药的山客,就是放羊的羊倌在此攀行了。白天行走都要时常借助野藤树干帮忙,更不消说在月黑风高的除夕夜了。
记得那天,我们是一共七个人瞒着家人上了路。那晚的天真黑呀,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黑暗中两耳只听得脚下滔滔的水声以及绝壁上偶尔惊起的夜鹰的啼叫。那叫声在静谧、荒凉的空气中传得极远极远。我们小心翼翼,如猿猴、如灵巧的山羊:挪、腾、跳、溜……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才听见对岸有些人语。又见一豆状灯火在徐徐前移,高声吆喝过去,那边便有人答,说也是去看电影的,不过电影早已演完散场,他们正挑灯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听,一下泄了气,有人一齐怨起小三子,小三子也苦不堪言,直叫脚磨起水泡,痛得慌。这样一伙人又无精打采往回赶,行至离村子不远的另一条山沟。我忽然想起独居于此沟的猎户曹四,就提议是否一同去他家听他讲古,本来垂头丧气的伙伴们顿时又像淋上清水的小白菜,立即兴奋起来,都齐声叫好,于是一行人便都相跟着向那黑的沟壑摸进。
曹四现在就光杆一人,原先倒娶过一个黄毛老婆的,凑合过了几年,那女人嫌他穷,便跟一过客偷跑了,遗下一丫头跟随曹四,后来那丫头长到十四岁,也早早嫁人去了北大荒。现在曹四一个人孤住在这个野山沟里,靠打野味和种药材为生。这老哥虽大字不识一箩筐,却天生会讲故事,尤其讲那薛仁贵征东最是拿手。
我们到了石墙外,有一狗吼吼乱吠,惊起胡子拉碴的瘦黑汉子,油灯亮起时,我们早窜进正屋上了炕。
“你给我们讲古吧,曹大哥,”曹四说,“大过年的不在家团圆,到处瞎逛啥!”我们便把刚才经历的事重述一遍。曹四听罢大笑一阵,便点一袋老旱烟,青烟袅袅之中有股辛辣的香味。我们几位也各燃上一支,便听那黑汉子慢条斯理讲起古来。
这是一间极简陋窄小的黄泥草房。屋地靠山墙的那旮旯,泄露下一席夜光来。仔细望去,原来是房顶上赫然现出一个窟窿,有清森森冷气悍然侵入,让我不觉打个寒战,身子往里偎偎,几乎全缩入汗臭的破被套里,好在火坑热乎,倒不觉得太冷。不一会儿,便沉沉进入梦乡了。
小镇上的《爱情故事》
后来,我家也从僻远乡村搬迁至一古色古香的北国小镇。小镇有一条青石板街,街两边皆是民国式的青砖翘脊的院套平房。小镇出玉,故磨琢玉器的手工作坊一家挨一家,展卖玉件的商铺也比比皆是。走在幽静、曲折的老旧巷子里,眼见得纯朴又有些木讷的小镇人次第行过,耳听得几声悠然的叫卖声,间或还能遇见手戴玉镯、颈佩玉链的素面女子袅袅婷婷擦肩而过,就更添一份恬淡与安适的心境了。
我因高考落榜,早早参加工作,是在一家副食公司搞宣传,整日写写画画,倒也安闲自在。不久便有人给介绍对象,我们约了个时间,我买了两张电影票,懵懂之中,便于某个春日的傍晚去了小镇那家唯一的电影院。
电影院有股尿臊味。我进去较早,简陋破败的环境中稀稀落落仅坐数十人影。我正焦躁,近前见一白衣衫的女孩,高挑的个头披一瀑布般的长发,我一慌,忽地立起,来的果然就是我那对象。
好在电影马上开演了,黑暗中我仍惴惴不知说啥好,幸亏不久即被银幕上的故事吸引住,慢慢忘了谈恋爱的事。
那晚放映的是波兰故事片《爱情的故事》——一个来自遥远异国他乡的凄美爱情故事。真是凑巧得很,仿佛某种天意,或某个神灵的暗示。我们都很快进入到别人的故事里,直到放映中途,也是在那女孩的提议下,我才有些不情愿地随她走出影院。
我俩沿着小巷慢慢踱步,借着昏暗的路灯光我偷偷打量身边的女孩,确信她是个气质高雅又有些傲气的“小公主”。而她鼻翼处那几颗雀斑也像早春苍穹上的星斗一样闪闪烁烁。
小镇上的人们乐于看电影,每次来了新片大家都蜂拥而上买票抢票,常常是阖家齐出动,一看就半夜,颇有点像意大利故事片《天堂影院》描述的情境。那时已开始放映日本电影《追捕》和国产影片《庐山恋》,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中早已春意盎然莺飞草长了。
不知不觉我俩竟走出了小镇,来到一处开阔的草甸大田里。此时的天气不冷也不热,柳树即将开始爆芽,草皮也开始返青,脚下的土地化过冰雪,在白日酣畅的阳光照耀后暖烘烘的,散发出一股发酵的醇厚酒香。我这时开始进入角色,侃侃而谈,从中国作家侃到外国作家,也大谈特谈了自己的宏伟理想。远处起伏的山丘在夜色中宛如一条条曲折盘桓的巨龙,而头顶上密密麻麻的星群轰响着,发出热烈的响应。我像一个天才演说家,又像一个未来生活中的英雄,看到姑娘眼中被我激起的愉快的火苗,我知道我的演说取得了明显实效。她后来成了我相濡以沫的妻子,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天晚上的夜空,广袤的大地和璀璨的星群,那是我俩观看一生的电影。
越来越真实的电影和越来越虚幻的人生
《圣经》开篇,上帝说世间要有光,于是真的有了光。《圣经》似乎早已预言了电影的降临,它让人们重新看到处于嘈杂巨变的人类自身,并冥想关于人性黑暗元素的本源。这是一种既新鲜又迷离的幻象——在一池春水里,在掠过树木间隙的微风中,在茫茫无涯的太空里,在埋葬万千骸骨的泥土深处。我们总能听见一个声音在叫喊——政治的、种族的、宗教的,我们总会获得重新认知的可能。
所以电影就像一面镜子,让人的生活得到回顾和重新打量的机缘。电影撩动我们内心藏而不露的情感,仿佛人类共同拥有的一个梦境,让人凭空产生时间与空间的迷乱。
也许美丽深奥的夜空天生就是一面绝佳的银幕原形,“光在天上投射,风传来声响。”我们每个人都是银幕上忽隐忽现的角色。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寓言——荒诞的而又真实的寓言!我们时常沉浸在这种光影艺术中难以自拔,分不清谁是演员,谁又是我们自己。而那幻觉力量的泡沫般的膨胀与放大,更使忧伤的回忆持续了充满沧桑的一生。
我们谁也没有能力逃离那张高悬于夜空中的梦一般的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