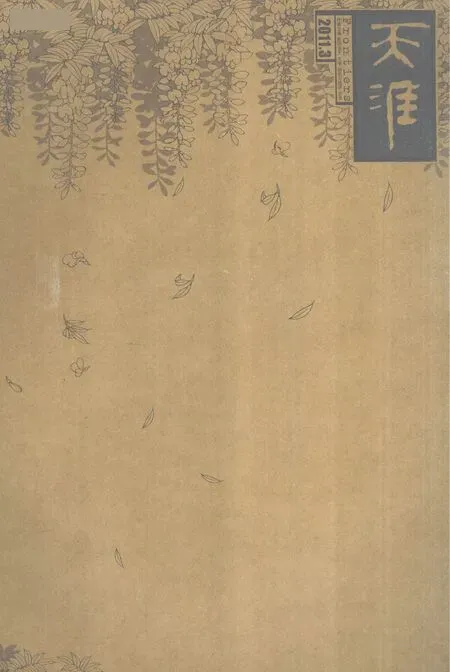四季
2011-12-26项丽敏
项丽敏
早春
站在窗口,看见湖湾草滩已抽出些许绿意。季节用它简洁的针法刺绣又一个春天了,先是草地、树枝,然后是整个山林、天空。
“午前春阴,午后春雨,暖和悠闲,而且宁静。”——这是德富芦花在《自然与人生》中说的一句话,我最爱读的一句话。这句话中包含着言说不尽的闲逸感、满足感。一切都是安静的,安静的春阴,安静的春雨,身边或许有一杯茶,或许有一本书,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有天地合一的雨声。用心品味的日常生活有其静美,懂得这美,享受这美,人生就有了简单易寻的快乐。
刚才去了菜园。几天没去菜园,里面又有了变化,豌豆地里插了密密的竹杆,豌豆苗此时已不叫豌豆苗,已经开始跑藤了;青菜地里种的是三月青,这种青菜身架小,叶子宽厚;菜苔已经开了花了,黄灿灿的,很像油菜花。
鸟儿们就在菜园下的苇丛里,站着、唱着,偶儿飞起,也只是为了换一根苇竿,站稳了再唱。
我也站着,站在菜园里——鸟声里——晨雾里,倾听着。
藤花,流水
中午,太阳蜜一样流着,三月好春光,莫辜负,于是出门,随意走走。
想起以前去过的一个山坞,那里面有一种藤花,不知现在开了没有?“藤花”是我给它的名字,它原本的名字我不知道,举在手里问过别人,也都说不知道。藤花是鹅黄色的,嫩芽一样,细碎地开在藤条上,无叶。藤花的花并不招眼,如果是开在田间草丛,谁也不会去注意它,它太小了,又没有香气,它什么气味也没有。我看到它,感觉了它的异美,是因为这花长在那样的藤上,那藤……其实,那藤也不是特别的藤,如果没有这碎黄的花,它就是一根普通的青藤。
藤和花,彼此映照,一体,就有了别样的韵味。
记得藤花下还有一条浅溪,从林中流来,不知现在那浅溪是否流水依旧。
入山,进坞,走了百米,忽然路就断了。以前这路可是一直通往山里的,多时没来果然有了不同。
于是改道,好在山间本就无所谓道不道的,只要不怕荆棘之锐、茅草之深,随便怎么走都是道。
路边有马兰头,一丛一丛,老绿。没带剪刀来,不然可以挑点回去。今年还没吃过马兰头,过了清明马兰头就不能吃了,乡间传说是鬼撒了灰,其实是老了。
听到流水了,就在那丛茅草前面,转过去,看见了,还好,它依旧在,依旧流着,绕过一块块青石、赭石、白石,一声声没有杂质,如私语,如歌咏。从远古到如今,流水的声音没变过。
藤花就在溪边,在茅草丛里,已经开了,还是那样,纤纤青藤碎碎黄花,无叶亦无香。
溪边有方白石,坐下。太阳也随我坐下了,还有风,还有一只黄蝴蝶、一只花蝴蝶,也都坐下了——在水中的石头上坐下了。
闭上眼睛,听流水。此刻这个世界只有流水,一声声没有杂质,如私语,如歌咏……
初蝉
听到今年最初的蝉声,有些吃惊,这么快就到夏天了吗?
蝉声是从小路边的松林里传出的。我站住了,仔细分辨,确定只有一只蝉。一只蝉的叫声就足以充满树林,且溢出了林外,使季节的面目也变得暧昧起来。
听到蝉声之前,我拍摄下一树紫藤花。紫藤花原本是不应该冠之以“树”的。紫藤花长在藤上,和树是两类种群。多数的紫藤都会把自己的身体攀附在一棵树上,借树的坚实使自己站立,也借树的高度延伸自己。这不是藤的耻辱,也不是树的荣耀,在自然界,生命有它们自己的道德观,和人类的道德观是迥异的,它们的法则只有一个——顺其自然,相互依存。
清明已过,谷雨将至。这两天的温度上升得极快,植物们开始了疯长。
油菜花还在开,金黄直逼人眼,气味也因过于浓郁而刺鼻。不知蜜蜂在其中飞行会不会被花香伤害,以至失去嗅觉。
水杉的叶子已长成绿荫,莹透的祖母绿。四月之后,水杉的色素逐日加深,成浓荫。过不了多久,浓荫深处就会安下蝉声的乐园了。
树原本是不会发出声音的,有了蝉、风、鸟,树就是有声的了。声音点亮了树,如同灯点亮了房子,爱点亮了心。
夏天了
夏天了,田野的草茂盛起来,草花不再溪流一样四处蔓延。
田里蓄着水,水里映着初升的日头,像一枚出了油的鸭蛋黄。田的一角有一个凹处,水从凹处淌下,流到下面的田里。
田埂新垫了泥,踩上去柔软滑腻。
有蛙的叫声,在远处。近处的田里只能看见不会出声的蝌蚪。
蝌蚪贴着水底,和黄泥一样的颜色,不动时较难发现。当我走在田埂,蝌蚪们便搅起泥浆,群体惊逃。看它们那样失措的样子,我总想笑,同时也佩服它们对外界的敏锐感觉。
昆虫对周围也很敏感,特别是蝴蝶和蜻蜓,要想用微距摄下它们极需耐心,轻手轻脚,屏住呼吸,以电影中慢镜头的速度,把相机推近,往往是在按下快门的前半秒,它们飞走了。我原地站着,眼巴巴地看它们从面前飞过,耳朵里听着它们翅膀发出的声音,像戏弄的笑。
露水很重的清晨,太阳升起之前,还是能够拍到蝴蝶和蜻蜓的,它们立在草叶,姿态端庄,翅膀潮湿,眼珠圆瞪着,却似睡着了一般,这种时候很容易摄下它们的写真。
早晨的空气好,又凉爽,适合昆虫们谈恋爱,它们在日出的光线中亲吻、交尾。昆虫们的交尾很安静,一动不动,像庄严的礼仪。它们对我的存在仍是敏感的,当我把相机靠近,它们会保持着重叠姿态,笨拙地转移到叶子背面,我跟着把相机移过去,它们又转了过来,如此反复,和相机躲着迷藏,很有意思。
昆虫们是有智慧和情感的,只是我们人类不太懂得。人类的力量对于它们来说太强大了,一念之间,轻易就能决定它们的生死。
我们人类的头顶,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呢?那种令我们无处躲避、反抗的力量,是什么?
雨声
现在是早晨,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往常这个时候我都在外面,在湖边菜地,或村庄,有时也去山谷。我去这些地方是散步和拍摄,也可以说是去采撷。
今天也出去了,刚走到曹家庄的田间就下起了雨。雨不大,凉丝丝地飘着,这样的雨是很舒润的,像一双柔软的手轻轻抚摸着你。但我还是没有在雨中停留,开始往回走,我担心雨会下得大起来。
前天早晨,也是在这个地方,我就遇到了一场急雨。
当时我正蹲在稻田边拍摄一只小青娃,那青蛙的皮肤还是褐色的,大概是刚刚褪去尾巴。它也是蹲着的,蹲在一片浮萍上,它的身子真轻,一枚比指甲盖还小一半的青萍就托住了它。我小心靠近,把相机镜头一点点地移过去,心里说:别蹦走啊,你的样子很可爱,让我拍下来吧。这只小青蛙大概是听到了我心里的话,果然没有蹦开。等我拍下它,把目光稍稍移动,又看见了另一只同样的小青蛙,接着看见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有一只小青蛙蹲在我的脚边,面朝着我,仰着头看着我,很好奇的样子。就在这时,我听到很远的地方有一种声音——像是风吹树叶的声音,由远而近,奔跑过来。我站起来,看见天色比先前暗了很多,马路上的杉树倒是没有摇动,一株株整齐排列在路边。声音更喧响了,更近了,近在头顶,然后大滴的雨就泼了下来。
我已来不及躲避,只有加快脚步,上马路,往村庄走去。
走到村庄时,我的头发和上衣已全湿了,本来就很薄的衣服贴在身上,几乎是透明的了。
我躲进一户人家厨房的屋檐下。屋里的主人,一位五十多岁的村妇,听到动静走出厨房,看见我,笑道,淋雨了吧,快进来擦一下。我跟着她进了屋,接过她手里递过来的白毛巾,擦干了头脸。村妇穿着一身蓝地碎花的棉绸睡衣,身材微丰,面目安详。
急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几分钟后雨声就歇了,天色也白了一些。我准备走了,村妇叫住我,说,拿一把伞吧,说不定在路上又要下雨。我接过村妇手里的雨伞,连说谢谢,说明天才能把伞还回来。村妇说没关系,家里还有伞呢。
回去的路上,一滴雨也没有落,空气清润,路边的植物散发着微甜的香气。
夏日晨曲
清晨的时候我不放音乐来听,自然里的声音便是极好的音乐了。有时候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宁静——万物俱寂的宁静,闭目聆听,如聆天乐。
坐在清晨自然的声乐里,内心是清明的,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很安逸。
也就是近年来喜欢自然里的声乐更甚于人作的声乐。时光荏苒,许多东西都在不觉中改变了——旧有的习惯、认识,旧有的容颜。
夏日的清晨有着丰富的声乐。蝉歌响起来了,独唱的蝉歌——独唱的蝉歌就像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也像一阕声声慢的旧词,表达着一唱三叹的古典情怀。合唱的蝉歌就不一样了。合唱的蝉歌是来自民间喜宴上的俗乐,直白、纵情、豪放、绵绵不绝。
午后的蝉歌和傍晚时分的蝉歌都是这种合唱式,听着并不觉得嘈杂,只觉得长长夏日就应当有着这样的声乐,应当有着这样不愿散去的俗世热闹,恰似一个银镶的繁华世界。
其实夏日最先醒来的还是鸟声,和春日清晨一样,莺莺燕燕,此唱彼应,闭着眼睛便以为自己是躺在田野中了,身边有着长满果子和鸟声的树,树下芳草青青,草香深处,有一脉静静流淌的河。这河来自何方?去向何处?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将以怎样的方式老去,将于何时老去……抑或可以永不老去,就像一条永远丰沛的河。
这个早晨,我看到园子里一幕浪漫的景象:一株开着嫩黄花儿的青藤旋转身姿,颤动着每一片叶子,向另一株紫花藤儿邀舞。我甚至还看见了它们羞涩又热烈的眼神,露珠轻溅,藤蔓紧缠。
风儿奏起金色的提琴,空中有飞扬的芦花为它们伴舞。
落叶纷飞
晚秋冬初,有阳光的日子里我每日游走于山林,不时抬头,想在树梢捕捉一些季节的特征——属于冬天的特征。然而在我的镜头里呈现的依然是暖艳色系——秋的光景。没有风的时候四周很寂静,草木丛中偶尔响起蹊跷的声音:瑟瑟瑟瑟、瑟瑟瑟瑟。
芭茅草已经很干了,焦黄,仍像火焰一样丛丛簇立。林间有两条小溪,一条名叫阳光之溪,一条名叫山泉清溪。阳光之溪从天空静静流下。山泉清溪从山顶一路轻歌,涔涔而下。在一些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两条溪流仿佛有约,总是能遇见,汇合一起。
山林太深,风得穿过很多条小路才能到达这里。风到达的时侯,四周就响起了密集的淅沥声,如同三月的雨,落叶纷飞。空中的叶子有急促跌落的,也有徐徐降落的。跌落的叶子连着细枝,殷切的样子似对大地思念已久,急于投奔。降落的树叶有着羽毛的轻盈,被风托举着,旋转、翩跹而下。这一段路程——从树梢到地面的路程,叶子经历了春天的嫩翠、夏天的浓荫、秋天的华灿。而到达地面,也只是几秒种的距离。
站在林间抬头看落叶,仿佛站在高楼看着从天穹飘落的雪花,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仙乐升起,是风琴与小提琴的合奏,在山林回旋,悠扬、浪漫、婉转、穿透。仙乐停下来的时候,我的发上、肩上、胸前、衣袖,已覆满铜红落叶。心里一个滚雷,被自己身上的落叶骇住,转而又恢复了平静。
总有一天,我会被落叶一层一层覆盖。我在落叶之下,在泥土之下,在树根之下,和那些与我同时落下的叶子一起,做一个与前世无关的梦。梦醒的时候,我会悄悄的从树根爬上树枝,化成一片叶子,长在很多的叶子中间,再次经历一轮生命。
霜寒之夜
连着下了几日严白的霜。下霜之前已刮了两天粗砺的霜风。
霜寒之夜,醒来看见窗前有盛白的月光。没有声音。鸟声、虫声、风声、大地的呼吸声,都没有。只有寂静——无边无际的寂静。忽然觉得害怕,对极度寂静生出的害怕。好像寂静本身就是一个魔,正迫向我,要把我吸进一个无底深渊……
第二天,对自己夜半醒来忽觉的害怕感到奇怪,这是很少有的事情,两年多来,这个楼上经常是我一个人住着,而我也早已习惯了独居,是什么令我害怕呢?也许是月光吧,过于盛大的月光是会让人迷幻的,无端就心生鬼魅。
直到看见菜地里覆盖着雪一样银白的霜花,我才明白为什么前夜会有那样深的寂静。在冬天,造霜的夜晚和造雪的夜晚一样,整个世界都湮没于深沉的寂静之水。
太阳出来了。太阳和霜花的相遇是注定的,也是致命的。它们彼此映照,它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水晶世界。
雪舞的世界
终于下雪了。
开始是小雪,夹杂在细雨中,一会儿细雨没了,雪花就密集起来。再一会儿,雪花大朵大朵摆起阵势,要痛痛快快下一场的样子。
我撑起一把浅蓝印花的伞,披上一条橘红羊毛大围巾上了楼顶的平台。我要好好领略一场雪,让精神洗个雪浴。
看雪需要心情,也需要高度和背景。
这个楼顶看雪有两面不同风格的背景。一面朝东,这个方向的远处是湖湾,近处是一排连着铜红叶子的梧桐树——我也是在看雪的此时才刚刚发觉,原来梧桐树硕大的叶子并没有在深秋落完,只是打了卷挂在枝间梢头,一派繁华未尽的样子。雪在这一片铜红背景的映衬下,落得精致艳丽。
朝南的一面是一座青山,以青山为背景的雪花落得优雅素净,隐隐似有一阕古典的筝曲为雪花伴行。
抬头看雪又是另一番景象。雪从一个辽远的虚空款款而来——随风而舞的自在,无牵无挂的从容。
近处的雪落得急一些,赶赴什么约会似的。远处的雪则落得舒缓些,因舒缓而飘逸,因飘逸而生姿。雪落的速度应当是没有急缓之别的,可能是看雪人视线的距离造成这远近不同的感觉吧。
山上已有积雪,青山渐淡,白色渐浓;梧桐的枝丫上开了一朵朵瑶花;松柏托着一层层的雪糕;湖湾静谧如梦——银亮的水晶梦。
我的脸冰凉,手也冻僵,但我并不觉得冷,只觉得快乐,无以记数的洁白轻盈的快乐,想跳舞、想唱歌。我松开了伞,张开手臂旋转、旋转、旋转……
此情此景,此时此刻,真希望有人和我一同感觉,一同欣喜——不是坐在屋子里、靠在窗前看雪落在泥泞的地上,而是一同站在楼顶,置身雪的中央,看雪花怎样的从天穹踏歌而来,怎样一点一点装裹如此美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