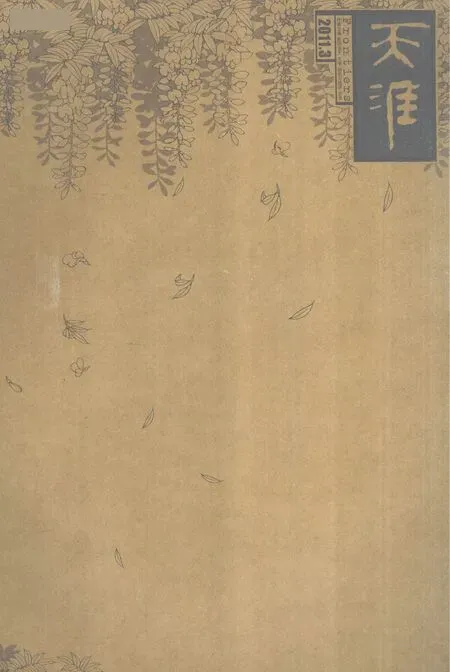来去自由
2011-12-26张宗子
张宗子
会做梦的城市
每次回国,倒时差最令人头疼。往往时差倒过来了,人也该回去了。
几年前,也是在洛阳,夜里不能入睡,白天刚买了一本《里尔克诗歌中的天使》,里面附有《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的译文,就起来读书里的诗,一遍遍反复读,一直读到天亮。
有时候,不是完全睡不着,是做一些半清醒的梦。忽而醒着,听到远处的猫叫和建筑工地上机器的声音。忽而在梦里,惊喜和绝望乱麻似的缠在一起。这样时间反而过得很慢,夏天短暂的夜,生生被拉得又细又长。
可是今年在洛阳,睡得过沉,既没有时差,也不记得做过梦。夜晚像一张白纸,原来害怕又希望有的涂抹,一丝不见。
要么是习惯,要么是贫乏。对洛阳,虽然一次次来,却完全是个陌生人。
洛阳老城区的街道,两边种法国梧桐;新城区,种紫薇。不仅两边种,街心也种。紫薇好看,不能遮荫。八月的骄阳下,紫薇一片浓艳的粉红,像是蒸腾的烟雾。我从没想到,这种明清古画上常在人家的庭院里与光秃秃的怪石相互扶持的花木,会成为古都铺天盖地的颈饰。李商隐写过一首《临发崇让宅紫薇》,“一树浓姿独看来,秋庭暮雨类轻埃”。可见当时洛阳的贵家宅第,不独养牡丹,养紫薇的也很多,而且直到秋天,开得还很茂盛。洛阳广植紫薇,或许是因了李商隐这段缘分。
李商隐岳父王茂元的宅第,位于洛阳东南角的崇让坊。李商隐屡屡在诗中提到崇让宅,不看注解,还以为是他老家。崇让宅规模相当可观,“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露如微霰下前池,风过回塘万竹悲”,“曲岸风雷罢,东亭霁日凉”,从这些诗句里,我们可以大约感受到一点大观园的味道。我回洛阳,都在夏天,多闷热天气,即使早晚坐在院子的花池旁边,也难得清爽。李商隐提到崇让宅的几首诗,除了那首《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都凄凉哀婉,这就更使人在想起他这些诗时,觉得十分遥远,十分不真实。
欧阳修离开洛阳时,写了一首《玉楼春》,算是对这座以尊贵而不是以繁华著称的城市,以及这个城市的花和女人的惜别: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肠寸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这首《玉楼春》可能是欧词中最情致缠绵的作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大加赞赏,说是“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王国维的见识没得说,但他自己是一流词人,多愁善感,说起对历代诗词的好恶,常有情不自禁的夸张,如说李后主的词“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拔高得有点不沾边了。欧阳修的《玉楼春》,既不豪放,也不沉着,只是一个缠绵,千回百转,放不下,舍不得。真性情的人,往往在这种小处沉陷极深,一时一刻,仿佛星移斗转,“归来兼恐海生桑”。外人倘不能理解,便以为是风流,是矫情,是妇人习气。欲共“春风容易别”,先须“看尽洛城花”,试想满城之花,何时才能看尽?年年之花,何时才能看尽?所谓易别,怎么可能。
历史上称为“洛阳才子”的,前有贾谊,后有杜甫,这两个人的气质都和洛阳姚黄魏紫的富贵不沾边。白居易和司马光的闲居,似乎也没有道出洛阳的心结。从贾杜到李义山,洛阳的形象是婉约和低沉的。紫薇,李商隐的诗里这样写:“不先摇落应为有,已欲别离休更开。”牡丹:“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奢华之极的时候,李商隐的诗句字字锦绣:“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用了这么多娇娜妩媚的典故,营造的气氛却是寂寞。“梦中传彩笔”云云,该怎么说呢?想起老杜诗中的惯技:说得动听的动词前,老是有一个“虚”字等着。
有一天,从餐馆出来,走上街头,忽然想起金谷园。我弟弟说,你忘了,火车站那儿不就是?李白羡慕的“罚以金谷酒数”的金谷,如今沉落在火车站对面一片拥挤的街巷里,不折不扣地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名字,一个无任何物质依附的名字。洛阳人任何时候高兴,都可以在那里竖起一面旗帜,上写“金谷园烩面”或“金谷驴肉汤”。
洛阳是父亲当年读书的地方,几十年后他和母亲搬到洛阳,也算是重回故地。有一次,在外出的路上,他还指着一片楼群说,从前的洛阳林校就在这一带。
洛阳的新城区据说正往洛水南岸发展。洛水也许会变成一条流过城市中心的河流,像在很多童话故事中,像在那些梦一般的石版画里,像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那么,将来有一天,洛阳还会出现一个洛阴区吧。
卡尔维诺可能说过,在那些有河流穿城而过的城市,入夜时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货船静静地泊在完全透明的星光下,从密封的容器里袅袅散出阿拉伯香料的奇异味道,每一个陶醉在这种香味里的居民,不仅消除了烦躁和某些季节特有的失眠症,而且全都做了同样的梦。术士们说,好的梦几乎都是这样,富人穷人,男人女人,他们的梦是一样的。只有噩梦才花样百出,像杂耍和情节剧一样五光十色。在这样整齐和单纯的好梦中,城市不再混乱,在它虚构的往事里,所有人都变成了孩子。
人是免不了要做梦的。一个会做梦的城市,最终将成为我的家。
秋天,赵翼,全唐诗
今年的秋天真是秋气十足。中秋才过,几场小雨,顿时满室凉意。街道两旁的树叶,一星期前,犹自肥绿入眼,一星期后,全体金黄。再过一星期,枝上剩下的,片片可数。昂首的墨西哥汉子,还能见到T恤短衫,华人小孩子和老人,已经大围巾加薄棉袄了。
楼外的水泥道是刚刚翻新的,青色而洁净。被泡在雨水中的落叶,留下交错重叠的咖啡色的印痕。往常正是松鼠喜笑颜开的时节,因为满树的橡果都熟了,不时掉落,打在车上,噼嘭噼嘭的。但今年的松鼠似乎少了,橡子也没那么多。
雨天其实是喝咖啡的好日子,冷暖对比,多一重滋味。容易知足,容易感激,甚至容易把一些很久没想通的问题想通。想通了,写下来,是很好的诗话或杂感。敝帚自珍,将来也可以供别人赏玩。像袁枚那样把诗话的大半篇幅用来搞诗坛排行榜,以为自己真是龙门,等着别人来跳,不免让读的人烦闷。
从国内带回的托马斯·曼,《魔山》和《绿蒂在魏玛》,打不起精神去读,篇幅太长了。钟鸣鼎食,大块的肥甘,牛羊熊鹿,梅盐和羹,想起来都累。夜深时候,如果还有余兴,便倚在墙角的床上,凑在小台灯下,读唐诗和唐人小说。明清人的诗话也很开胃,像川菜馆的冷盘,可当读诗的下酒物。
赵翼论诗绝句说,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很多大部头的论著,满篇陈词滥调,几百页一路读下来,常识而已。不如单取作者自己一点一滴的心得,写成一条两条,彼此都省功夫。
《瓯北诗话》集中论述了从唐到清的几位诗人,唐朝专列一卷的,不过李杜韩白四位。每一位虽然只有十几二十则,说得都很到位。论李白,论韩愈和白居易,论四家的不同,精辟之至。尤其是关于李白的那十九条,读完之后,回想李白的近千首诗,在大面上,觉得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在《瓯北诗话》小引里,赵翼谈到自己一辈子读诗学诗的体会。他说,年轻的时候,读唐宋各家,不等认真读完,受了点启发,窥了点皮毛,自己就好像大有所得,一脑子的想法,结果未能深入。就像一般选家,对于古人的精髓,仅知大概。到了晚年,时间充裕,找出各家全集,反复披阅,这才领略到他们的真正好处。回想以前的理解和认知,不过十分之二三。赵翼说,世上的事,总是过去之后才能知道是非,假如几十年前就能有这样的认识,读通几家,明白他们各自之所长,苦心揣摩,融会贯通,一定能够在此基础上自成一家。可惜现在人到残年(小引写于嘉庆七年五月,赵翼已经七十七岁),精力衰绝,已经无力再与古人争胜。立志虽高,终归荒废,这是很遗憾、很痛苦的事。
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这本诗话?赵翼说,过去的固然已经过去,荒废了也就荒废了,但仍然庆幸自己能在晚年投入这项工作,力追古人是不行了,但毕竟有所发现和领悟,这比终生糊涂好。世上有才的人多不胜数,很可能也像我一样,把大好时光轻轻放过,等到年老才知悔恨。我把这些经验和感悟写出来,也许可以使他们少走几十年的弯路。
(少日阅唐宋以来诸家时,不终卷,而已之才思涌出,逐不能息心凝虑;究极本领,不过如世之选家,略得大概而已。晚年无事,取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觉向之所见,犹仅十之二三也。因窃自愧悔:使数十年前,早从此寻绎,得识各家独至之处,与之相上下,其才高者,可以扩吾之才;其功深者,可以进吾之功;必将挫笼参会,自成一家。惜乎老致耄及。精力已衰,不复能与古人争胜。然犹幸老而从事于此,虽不能力追,而尚能见到,差胜于终身不窥堂奥者。因念世之有才者何限,度亦如余之轻心掉过,必待晚而始知,则何如以余晚年所见,使诸才人早见及之,可以省数十年之熟视无睹。是于余虽不能有所进,而于诸才人实大有所益也。)
这段小引,读了多遍,深为感动。近年读唐诗,逐渐明白这个读深读透的道理,开始在李杜韩和李商隐及苏轼王安石身上下工夫(赵翼于宋代诗人,取苏陆两家),以期能有哪怕一点点收获。赵翼的话,直接说到我心里。他那金针度人的长者之风,试问当今之世,几人能有?
写文章最怕多感,多感则易流于纤弱。细腻不妨,滥情一定要避免。人往弱处滑,好比水流卑湿,是自然之性。从弱中振起,好比逆水行舟,非有大毅力不可。力气不足,只好借风张帆。顺境中不得意忘形,读读杜甫和苏轼。不顺心的时候,积郁深重而不失气格,还是大声念念李白吧。
李白一生,屡遭重大打击,但李诗中罕见垂头丧气。赵翼就感叹:“青莲胸怀洒落,虽经窜徙,亦不甚哀痛,唯《上崔涣百忧章》,有‘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之语,最为惨切,盖在狱中作也。及流夜郎途次,别无悲悴语。”
李白才高志大,一切发自天性,世间一切事,不能羁縻其分毫。赵翼说,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若论其沉刻,则不如杜;雄鸷,亦不如韩。然以杜韩与之比较,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此仙与人之别也。”
《古风五十九首》的第一首,从“大雅久不作,吾哀竟谁陈”到“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麟”,赵翼指出:“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欲于千载后上接风雅,盖自信其才分之高,趋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这个意思,一直在我心里,不料竟是早年从赵翼那里贩运过来的。
李白生在盛唐,是他的幸运;盛唐而有李白,是唐诗的幸运。千载之下,我们只有合掌赞叹,俯首感激而已。
全唐诗慢慢读,相当数量的,不得不轻轻放过。最害怕那些八股气重的人,偏偏写得多,又刻意保存,不遗余力,几卷读完,身心俱疲。手头有的十数种诗话,全部找出来,可以和自己读后的感觉相印证。宋人离唐近,处在唐人巨大的身影之中。近,反而隔,好多事情想不通。明人不会写诗,读诗则有些眼光。清人有宋明人的经验可资借鉴,又距离得远,不仅看得清,心态也平和。就是迂腐的地方,读起来也轻松。
赵翼诗话的序谈切身体会,沈德潜的序夸说他在寺院读诗的清雅。环境好极,和尚又是知分寸的,敬重他的身份,应对得体,宛如训练有素的捧哏演员。那感觉,就一个字,爽!自然羡慕得紧。
薛雪《一瓢诗话》的自序则像一篇明人小品:
“扫叶庄,一瓢耕牧且读之所也。维时残月在窗,明星未稀,惊乌出树,荒鸡与飞虫相乱,杂沓无序。少焉,晓影渐分,则又小鸟斗春,间关啁啾,尽巧极靡,寂淡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处老鹤,横空而来,长唳一声,群鸟寂然。四顾山光,直落檐际,清净耳根,始为我有。于是盥漱初毕,伸纸磨墨,将数月以来与诸同学及诸弟子,或述前人,或抒己意,拟议诗古文辞之语,或庄或谐,录其尤者为一集。”
他是名医,家境肯定不坏,扫叶庄想来该和王维的辋川别墅差不多。薛雪能诗,又是叶燮的高足,不知为何写文章那么没思路。几百字的小玩意儿,前半段仿佛出自曹操,后半段的老鹤,又令人联想到东坡的后赤壁赋。真不知他老人家是写实还是虚构。
初到美国,有一次携伴出游,进了山中的大寺。寺虽新建,风景不俗。入夜万籁俱寂,尤能诱人深思。寺里接待客人,提供食宿,价钱不贵。我和主持的人说好,想暑假来住两星期,读书,写论文。后来为了生计,打工挣钱,舍不得花这些闲时间。留下一个念想,永远不曾实现。其实是很简单的事。
真去住了,以后写论诗的书,序言里也可以像沈德潜和薛雪一样夸耀一下啊。
现在的窗外,自从原来那棵椿树被伐,拉开窗帘,就只有刷绛红色漆的防火梯可看了。树没了,偶尔来的松鼠也很少来了。
一池疏影落寒花
古时候做神仙的,有一种气度是懒,懒到像我妈常挂在嘴边教育我们兄弟的话:油瓶子倒了都懒得扶。懒是天性,和日常表现没多大关系。一个人辛劳成疾,累死了,不能说明他不懒散,只是表明,好多事,他不想做,却不得不做。反过来也一样:有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实际上他做梦都想操劳。问题是,天底下没有事供他操劳。他一蠢蠢欲动,大家都说:免了,你歇着吧,你一来,添乱。
我喜欢诗,诸多理由之中,有一个理由,是可以偷懒。
上小学,老师让大家把改过的作文重抄一遍,有时候,还需用毛笔抄,以便贴在墙上。我就是那时候爱上顺口溜(俗体诗,但还是诗)的。和文章比,顺口溜的字数少得多。五言又比七言经济。老师不知道我多恨毛笔字,更不知道作业本上的临帖我是用什么姿势画出来的。好在写“批判”文章,没有明说不可以写成诗。我去问,老师居然点头。从此,批三字经,批林批孔,一律诗的干活。
来美国,在大学混。用英文炮制论文,又成一怕。想方设法故伎重演,只找到一次机会:写作课可选一门,就选了诗歌写作,所谓“诗作坊”(poetryworkshop)也。和小说和散文作坊比,诗的好处不仅在字数少,而且还可以不用囫囵句子,搭几个字组,中间一律加句号,稀里哗啦十几行就出来了。中国式的意象搭配,找一些老美没见过的。课堂讨论,教授和同学只顾捉摸那些古怪词语的意思,七绕八绕,时间已到,屡屡轻骑过关。
有一次,凑了五首短诗,美其名曰Five Zenpieces(五首禅的小品),其中一句,“死亡像初生的燕子”,差不多讨论了半节课。前一句写到墓地的红蜻蜓,这一句说“乳燕”。教授问:死亡如乳燕,什么意思?我说,表示死亡也很可爱啊。众人大惊。教授说,在我看来,刚出生的燕子,毛未长齐,皮肤发皱,浑身红赤赤的,很丑。我就讲起中国诗词,小燕子嘛,总和春天联系在一起,很温暖,很可爱,很生意盎然。后来同学们感叹说,意象的文化内涵差别太大了,难怪翻译过的诗不容易理解。
班上颇有几位,做诗已经很专业了。下课之后,常去下城参加诗朗诵什么的。好心邀过我,我哪里敢去?
有一位,因为读了加里·施奈德,正在迷禅宗。他在诗里弄了一句:一百零八下钟声。很受称赞。地铁里,这老兄问我:钟敲一百零八下,到底什么意思?解释之后,我好奇地问他: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一零八呢?他说,谁知道在什么书里见过,反正觉得挺神秘,挺东方情调的。“你知道,诗里要说钟声,教堂天天敲,谁会稀罕呐?你换成一百零八下,大家傻了,不明白呀。得,这不成好诗了。”
我一想,此言不虚,此法可取。期中作业交诗,不好再以短取胜,深夜抱着汉英词典,整了一首三十多行的。结尾一句,想不出用什么形容词修饰“早晨”,英汉汉英对着翻,翻出一个promising(有前途,有希望的),勉强套上。结果整首诗就这一句获评最好。你说,什么叫歪打正着?
人依靠坚定成就一件事。不说什么“事业”,就只是一件事。杜子春的故事演绎这个简单的道理,构成了唐人小说中的一大类别。
原型来自西域的这个故事说:子春为道士守丹炉,防止诸魔侵犯。魔由心生,一切皆是幻觉。道士告诉他,但当不动不语,安心莫惧,终无所苦。
大将军扬威而来,盛怒跳梁,子春不动;雷电破山,暴雨如注,子春不动;鬼卒加以酷刑,子春不动;虐杀亲人于前,子春不动;令其转生为哑女,备受欺凌,子春亦然不动。嫁人生子,爱子被扑杀,子春顿忘道士之言,不觉失声曰“噫!”于是大火四起,屋室皆焚。
道士说,你呀,喜怒哀惧恶欲都忘了,没能忘却的,只有爱而已。
在韦自东的故事里,先是巨蛇来袭,自东以剑击之,巨蛇化为轻烟;继而漂亮妹妹执花缓步而至,自东亦以剑击之,女子若云气而灭。第三次,飘然降下一位道士,自称是托付自东的那位道人的老师。他告诉自东,妖魔已尽,大丹将成,他是来为弟子做见证的,又朗吟道诗一首,文辞清雅,含义高深。自东再不怀疑,释剑为礼,药鼎顿时暴烈,更无遗在。
不能忘情,最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萧洞玄的故事和杜子春完全一样。为色所诱,古人视为最初级,比为富贵所诱稍强一点儿,总之是很没出息的。韦自东的故事在众多版本中,虽情节不如杜子春,却饶有新意。杜子春不能战胜爱,韦自东不能战胜的,是盲目的尊崇。
佛教看待爱和尊崇,究竟可以空忘到什么程度?杜子春和韦自东,谁的错误更可以理解和原谅?
杜子春的故事适于所有人,韦自东的故事也许更适于知识分子。
大雨已把残雪冲刷一尽。早晨外出喝咖啡的路上,风把雨伞吹折了。今年的春天到得晚,墙根的连翘花犹自未开。四月海棠和山楂怒放,在那些比较僻静的小街。一阵风过,便是一场花雨。上夜班的年代,下午看书看累了,散步四十分钟,向远离闹市的方向走,最喜欢的,便是街角的大株海棠。山楂比起海棠,毕竟逊了一筹。樱花则显得单薄了。春天的花,在这里看不到而又想念不已的,第一是碧桃,其次是梨花。想碧桃有实实在在的形象,想梨花则意不在此。
在咖啡馆里,儿子准备中文,忽然冒出一句“鸡语花香”,看我瞪眼欲怒,恍然大悟,立刻纠正:没有“又”,是鸟,是鸟。
这样的阴冷风雨天,真有鸡语花香,那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