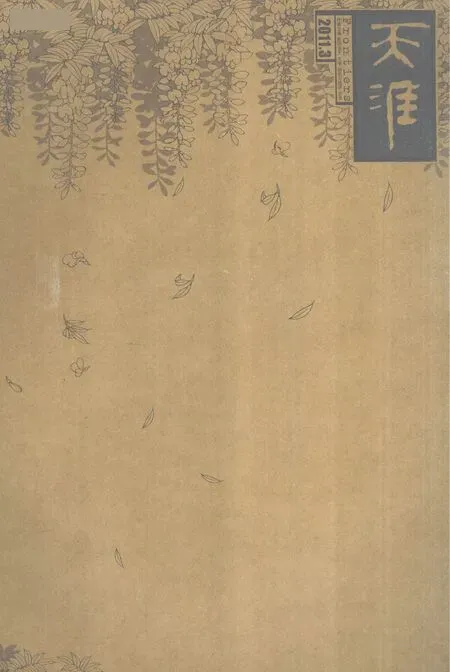证明材料(1968—1972)
2011-12-26姜庆刚
我的经历
我生于1924年11月19日,四岁时父亲死去,留下母亲、弟弟和我三人。父亲生前因吸食鸦片,将家中房产、宅地全部卖光,只留下三亩岗地(据说因早死一天而未卖成)。母亲当时因无法生活,将弟弟卖掉,带我一人到外祖母家寄居。
在我刚上初中前后,有一堂伯父死去,留下一个傻儿子,后也死去。他家有一些地,我母亲分得十亩。我初中毕业到四川上学期间(1944年以后),我母亲又从我一个堂伯母(此人儿女全无,只有一人)那里买了一小块宅地,盖了两件(间)草房,这时从我外祖母家搬回到原村居住。土改时我家评为地主成分,分得土地六亩。
我十一岁上小学,从二年级开始(1935年)。初小毕业考取了附近镇子上一个高小,读了不到一年因无钱交伙食费而停学。这时抗日战争已爆发,家乡来的军队很多,经一亲戚介绍曾到国民党军队里跟一个连长当了一段勤务兵(不到三个月的样子),在离家一百多里地的地方住下时,因顶嘴而被罚过一次跪,以后不干回家了。后又到乡附近另一个高小读书,1940年高小毕业。
1940年夏考取附近唐河县初中,第二年因交不起学费停学。这时从一些同学中得到消息,说河南省西部有一个吃饭不要钱的国立中学,但必须是战区学生(即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地区),我家乡当时还未沦陷,但靠近桐柏县以东的信阳已被日本鬼子占领,算是沦陷区,于是决定冒充战区学生,即把籍贯改为信阳人。到豫西内乡县西峡口镇伪国立一中一分校报考,结果被录取。当时同去的有另外两个同学,是同乡,此二人一个叫刘敬,解放初期听说此人在桐柏县委工作,1950年我回家时见过他一面,以后从未来往。另一位叫刘复,此人现在在鞍钢炼铁炉工作,是西北工学院毕业生。
1941年考入伪国立一中一分校(此处离我家乡有四百多华里),到1944年毕业。初中二年级(1942年)参加过三青团,但未发过任何证件,无活动,未担任过任何职务。以后也从未联系过。大约在初中二三年级时,学校学生伙食不好,传说校长贪污,闹学潮,群众在愤怒之下要打校长,部分学生冲入校长办公室,我是其中之一,当时部分教师出来劝解,并答应不开除一个人。当时出布告有五个人记过,我是其中之一。1944年初中毕业,我们五个曾被记过的学生,全部被默退,不许升入高中部。
当时同班一位同学耿玉蛰因病而未升入高中部,此人父亲在重庆搞基督教方面的工作,他打算到他父亲那里去。我当时升学的念头很强,决定和他一起到重庆想办法考学。当时两人无钱买汽车票从西北宝鸡方向进川,乃决定从湖北西部步行入川,但走了十二天之后,才走到湖北西部长江旁边的巴东县,然后由巴东坐船到重庆,这时重庆各校招生期已过,同行的耿玉蛰因有家,由他父亲想法上一个私立高中去了。我到沙坪坝伪中央工业学校,据说这个学校的校长和伪国立一中校长都是河北人,因而凡是国立一中来的学生都可免考入学,我们由河南离校时曾带了证明信,但当时一般初中毕业生都不愿上工业进修学校而愿上高中,然后入大学。我当时在没办法上高中的情况下,进入了该校土木专科部。进校后听说不少人只是把在那里上学当作食宿场所,因该校吃饭不要钱,一面把老师上的课程应付及格,保住饭碗,另外就埋头准备报考大学的主要课程,两三年后仍可以同等学力(历)的资格报考大学,我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该校读了两年(1944—1946年)而考入重庆大学的,所以我没有上过高中。
在中央工校时两年中,政治上对我有一些影响的,是同班同学王梅园,此人经常谈一些进步思想,让我参加一个什么自由组合的小报刊物。我当时因一心想考大学,整天埋头数理化课程内,对文学方面的东西不愿花气力,所以没有参加,实际上是对政治不关心。该同学解放初以军方代表之一,回到沙坪坝(当时改名王德裕),曾主持沙坪坝文化区学生的政治学习。
1946年我考取重庆大学建筑系,二年级时转入电机系。1951年毕业,学习一个月后,统一分配到铁道部文化局。由文化局转分配到哈尔滨铁道学院教学研究班学习一年,1952年毕业时留校,后院系调整来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至今。
我到重庆大学时虽然离开了中央工校,但两个学校校址紧紧相邻。我当时和中央工校有来往的学生有两种,一是河南同乡,一是国立一中校友。
重庆1949年底解放,解放前夕各校进行了有组织的护校工作,并修筑有工事。解放后一段时间,一天中央工校一位同乡(姓阎)遇到我,他说他解放前夕到成都去了,而且和一些人想捉国民党军官交给解放军,当时我告诉他中工是马肇蔚负责学校的一些工作,叫他把自己的情况谈一谈。马是一中校友,河南人,他们也很熟悉,马是地下社员(即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这时已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候补期三个月),同班同学,团小组长周学云(此人后入党,也是地下社员,现在重大无线电系)曾问我中工有一位姓阎的怎么样。这件事以后我告诉了那位姓阎的,一天他到我宿舍去,说他表现如何好,班上又要选他当班长,我当时说不会吧,组织上还在了解你呢,以后知道此人回去后曾向领导上大闹耍无赖,说为什么不相信他。此人以后被捕及镇压,宣判时我才知道他是军统通讯员,曾开过黑名单,是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我把组织上问我的话告诉了他,犯了严重丧失立场的错误,受了取消候补团员资格的处分。
我在重大三年级时曾当过学生自治会的班事(相当于委员),负责文娱工作,我当时是班上提出以无党派身份参加的,具体作过两件工作,一个是参与了每年一次的话剧演出筹备工作,另一个是具名负责六一纪念晚会,这是一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化和镇压学运的罪行的文娱晚会,是一批进步同学自编自演的节目。我只是被推为名义上的负责,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工作。推选我负责的那次会,我根本没在场,以后知道的。
我从初中开始(1941年)一直是以沦陷区学生身份靠公费上学,到四川后,我家也曾被日本鬼子占领过,所以一直没有与家通讯,个人经济来源是无亲戚供给的,买零用品靠伙食节余,另外有过两次收入(几块钱的样子),一次由同宿舍的郝振经(河北人)介绍我利用暑假到一个纱厂给他亲戚(老女工)的孩子当了一个月家庭教师。另一次由同班同学张云介绍到过一个私立中学代过几讲(节)课。解放初期学校组织过一批经济困难的同学到重庆码头上背大米,我曾参加过。
解放前夕重大电机系在抗暴、反饥饿等学生运动中是比较活跃的。我曾参加了一些活动,但总的政治态度偏于中立,重业务、轻政治的观点很浓。我大学阶段来往较多的有如下几人:
邱天纵:同班同学,地下社员,解放初为重大学生会主席,是我的入团介绍人,解放前曾给我过进步书籍阅读(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解放初是在地下党公开大会上宣誓入党的。毕业后未通信。
周景云:同班同学,团小组长,地下社员,党员,文化大革命前在重大无线电系工作。
杨可飞:重大土木系毕业,同宿舍住过。解放前曾给我说过想到解放区去,但又想等大学毕业后再去。1951年统一分配到北京矿业学院当教师,最近几年未通过信。
张延浪:重大地质系毕业,同宿舍住过,1950年毕业,因为他哥哥在北京工作(是一老干部),而自己到北京找工作(当时大专毕业生未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到地质部,以后又到华北地质队。几年来一直未通信。
郝振经:重大商学院会计系毕业,同宿舍住过,他1950年毕业,分配到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未通信。
崔雪珍:伪中央工校化工科毕业,她于1951年毕业后统一分配在四川省工作,地下社员,解放初地下社员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后,曾任团支部书记。国立一中校友,她姐姐是我一中一分校时同班同学。未通信。
贾坼:一中一分校初中同班同学。解放前随其父母由广州迁往重庆(其父在什么文史馆工作)。解放初期入西南军政大学,毕业后分派到重庆江北钢铁厂人事科工作,前些年曾通过信。1950年暑假我由重庆回河南时是由此人借给我的船费(该钱已还)。近几年没有通信。
1950年暑假我曾由重庆大学回家看我母亲一次,回校时没有路费,和母亲决定将土改中分到的六亩地卖了三亩(价30元),当时我们家乡土地是有买卖情况的。
1952年在哈院毕业后,先留哈院,后来唐院,暑假回家将母亲接来唐院,两年后她因病死去。1952年回家时,邻村一地主婆到我家串门,我母亲曾将锅盖什么东西送给她(我根本不知道),引起村干部不满,以为是我在搞什么鬼,将我押送区公所,经调查我没有什么破坏言行,第二天就回来了(区公所写有证明信)。后乡政府曾派人(是一文书)到我家向我解释,说明是误会。
来唐院的十几年当中,思想改造是有曲折的。大学刚毕业时工作充满热情、劲头很大,但主观片面,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很浓。1955年母亲死后因补助费事曾一度不满,认为领导上太不关心自己了,实际上是自己的个人主义作怪。在我校一度出现写论文、搞翻译、拿稿费、成名家的修正主义思想泛滥时,自己也参加了这个行列,搞过翻译,幻想成名成家。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一度很浓。
在党组织的教育下,自己有所进步,我觉得我的思想状态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初步认识到反动学术权威的丑恶灵魂和重业务轻政治的危险性,因而决心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主动靠拢党组织,永远跟着党走。作“党的驯服工具”的思想状态一直继续到1966年下半年。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己外出串联,在北京住了将近三周,参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使自己思想有所转变,逐渐认识到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决心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注:解放前后的经历和问题以往全写过材料。)
补充:
1、1960年3月—1961年1月在丰润县乾城人民公社以下放干部身份下放劳动。
2、1965年1月—1965年5月和同学一起在青岛市参加四清运动。
(1968.8.25于唐山)
因为孩子们的学校要了解祖父的情况,我曾给弟弟去信,请他向附近邻居和老人们打听一下,现接到他1972年12月20号的来信,其中一段谈到父亲的经济状况如下:
“另外信上所说的咱家在解放前情况,经了解有关近邻和老人,父亲叫刘长林,我(注:指弟弟)三岁时父亲病故,卖我时父亲还活着,家庭生活无法维持,父亲好吸毒品,而将我卖掉,当时旧币20串钱,应是贫农成分。”
现将给电机系党总支的一个书面说明列后:
关于我的家庭出身,以往我填表时在“家庭出身”一栏内自报“地主”成分,其根据是解放后我母亲说她在土改时定为地主成分。
我四岁时,父亲死去,因家中无地无房,随母寄居于外祖母家。我十几岁时离开她家,在外上学靠公费和救济费维持生活,因而对自己家庭情况了解不多。最近由于孩子们的学校要了解其祖父的情况,家庭出身中要填祖父的,经我弟弟向有关邻居和老人们打听后,回信说卖他时父亲还在,而且就是父亲将他卖掉的。(我原先误认为是母亲卖他的)
根据我父亲的经济状况和我与母亲的联系,我的家庭出身似应填“贫农”,理由如下:
1、父亲(刘长林)的成分应为“贫农”,他死时家中已无房、无地、无住宅,死前因生活困难,竟将自己的儿子卖掉(据说还打算卖我母亲)。他死时连收尸的人都没有,是亲邻将他随便埋掉的,没有什么埋葬仪式。
弟弟谢运发,他住在河南桐柏干氏西街,曾多年任生产队长,六几年因病在家为一般社员,贫农成分。
2、母亲因分一堂伯父家土地(约十亩)而收租进行剥削时,我早已离开家,且家乡被日本鬼子侵占,互不通信,没有接受过她的任何接济,直到解放以后才见到她。此外,我幼年时代在外祖母家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曾替她家干过放牛、放马、割草之类的农活,后因不愿看到那冷酷无情的面孔,曾三次离家找出路,但因年小未逞。最后因考取供吃管穿的初中而到外地读书。在外读书时他们从未给我任何经济上的帮助。母亲对我的影响和联系恰恰是她处于贫穷和遭受歧视的阶段。
以上是我对自己家庭出身的看法,打算在今后填表中加以改正,不知恰当否,请党组织予以审查。
此致电机系党总支。刘。1972.12.25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