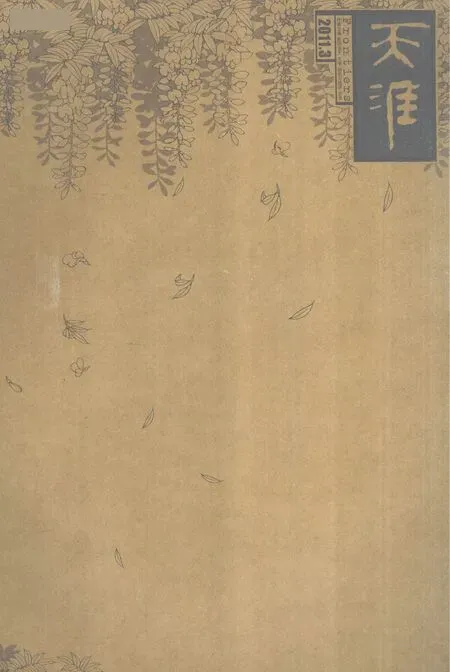行骗的社会逻辑
2011-12-26翟一达
翟一达
保罗·埃克曼是研究说谎的专家,曾在加州大学医学院任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对象涵盖新几内亚部族、间谍、连环杀人犯、精神病患者等。埃克曼长达四十年致力于研究人类的面部表情、情绪表达和人际欺骗。虽然埃克曼是“识破谎言的专家”,他总结出了许多辨别谎言的线索和方法,与这些实用策略相对,是了解行骗在社会层面上的逻辑与后果。
社会生物学倾向于认为,行骗蕴含着物种繁衍和生存的“合理性”,是进化选择的结果。在现实社会中,“骗”总与一定的利益有关,或是经济上的,或对于个人具有社会的意义,像那些对病人隐瞒真实病情的“善意的谎言”就属于后者。埃克曼对谎言的定义直截了当:谎言是一种“存心误导别人的有意行为,事先未透露其目的,并且对方也没有明确要求被误导”。这样看来,“骗”也可以说是一种扩展了的舞台艺术和表演——明知故犯地误导,传达不实信息,最终让对方“信以为真”。一个社会中,行骗的泛滥与社会信任的瓦解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作用。学者们常常感叹于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和运动肢解、离间了人际间的互信,造成了当前社会信任稀薄的现状。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当代经济物质增长中出现的新因素,也诱导了行骗的盛行。人们的合作越来越难,社会不得不发展出大量的手段和工具来确保契约的维护、合作的进行,而个体也在处处小心提防的沉重心理压力下饱受焦虑的折磨。
在这样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中,一个悖论却产生了。低度信任的社会导致的结果应该是人们互不相信,在这种风声鹤唳般高度戒备的状态下,行骗成功的几率会降低,而有限的获利机会会使行骗行为的数量缩减。然而,日常经验却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行骗在当今社会中大行其道,并且屡屡得手。媒体开辟出专门的节目报道、揭露各种骗局,但是上当的人依旧前赴后继。骗子们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通讯工具——手机短信、电话、邮件等,民众还来不及考虑自己的私人信息何时被泄漏时,很快又被中奖的诱惑“撞昏”了头脑——眼前,房子、汽车、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大奖”闪烁着炫目的光芒。面对行骗者,大众的信任感莫名地提高了。是什么样的社会逻辑导致了“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中,人们更加相信骗子”这样一个荒唐的结果?
低度信任感的社会无疑会造成人们的合作困难。人们吝啬于将个人的信任交给合作者——那些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益分享者往往是事业开拓的关键,但他们得到的信任却相对较少。相反,人们似乎愿意更大方地将自己的信任挥霍给那些随机概率性的事件。比如“中奖”。行骗的社会逻辑就在此展开。这也正是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为何行骗能够成风的原因。“中奖”的诱惑力在于两点:一是不劳而获。大奖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贪图安逸与享乐的基因将这种侥幸的心理无限膨胀。另一点是由于概率性事件对于个体而言是公平的。例如自然状态下的抽奖不会因个体的收入、性别、权力等有所偏向。如果社会流动中的其他渠道都被“不公平”的方式占据着,“中奖”在民众心里反而却成为了“最公平”的手段,这就增加了行骗者以“中奖”的方式获得民众信任的可能。面对突然而至的“大奖”,普通的民众在一阵欣喜之后却以最坦然的方式去接受,以为自己“命中注定”拥有这样的好运,这是文化基因留在一个民族血液里的信条。
也有人说,那些骗人的谎话三岁的小孩都能够分辨。但是,这些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难道心智暂时性地萎缩到三岁小孩以下的水平了吗?对于“运气”的迷恋和“好运”带来的大奖,已经将个体正常状态下的理性思考逼到无以容身之地,“上钩者”就像中了骗子的“催眠术”一般俯首帖耳。这样也就呈现出了那个有违常理的后果——人们对周围的人甚至合作者维持着低信任度,却“一反常态”地更加信任行骗者,因为后者给出了一个“不劳而获”的空头支票。对于受骗者来说,这是行骗得逞的社会逻辑。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正常的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如果被阻塞,人们过度地信任、依赖那些非常态、投机的手段,可以说这个社会肌体就开始病态化了。
行骗者在编织谎言的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追加行骗成本的过程。行骗的成本既包括心理成本,也有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这些成本的多寡和变动情况也反映着行骗的社会逻辑。人的内心深处,有一尊高高在上的道德神明,有些人把他供奉起来,去敬畏他;有些人把他打碎,不屑一顾。个人的道德水准,个人所秉持的是非明辨就是行骗的心理标尺。如果这个心理标尺高,行骗的心理成本就大,更有可能因行骗产生内心的焦虑和自责。在这样的情况下,行骗会受到道德心理上的制约。如果一个社会在对那些美好的传统道德叛逆的激流下,在失去信仰和先进科学技术营造的无所不能的自负心理下,人们缺乏对这个道德神明的敬畏感,行骗也就谈不上会造成什么心理不安,就变得轻而易举。对于行骗者而言,行骗的社会逻辑正在于此。
我们都知道,编造第一个谎言后,往往不得不说更多的谎话去圆第一个谎,就像步入了沼泽地的人,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对于行骗者而言,总会有谎言被揭穿的风险。谎话暴露的后果是行骗者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例如商业上的欺诈遭到起诉和经济赔偿,或是因欺骗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导致未来合作机会的丧失。在学术领域的抄袭,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一个社会中对行骗没有严厉的制度性惩罚,标识说谎者的信号在网络中不能迅速和畅通地传递,谎言得逞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行骗者也会低估说谎的严重后果,行骗就会更容易发生。这是行骗者的另一种社会逻辑。
行骗的社会逻辑是利用了受骗者“不劳而获”、“贪便宜”的心理,行骗者在整个社会中追逐的正是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快速致富的目标,它的社会危害要比当事方单纯的经济损失大得多。行骗者将“骗术”作为生存的技艺,以此进行的“劳动投入”并不能产生任何经济价值,是无用劳动,而且行骗的后果更是增加了社会的不信任感,恶化了人际关系,人人自危,将正常的交往、合作也误视为“骗局”。这种“误真为谎”加剧了社会信任的稀薄化,预兆着一个社会内聚性的解体。假如信任荡然无存,还谈何合作,这样的社会难道不可悲吗?
与其他的劳动形态相比,通过行骗的方式轻而易举地获得财富收入的行为,在整个社会心理中释放着不择手段致富的“毒”,这样的气氛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些年来,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甚至药品食品安全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神经,而2008年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的恶劣事件将“行骗社会”的丑态推向了一个顶点。以行骗作为获取钱财的手段,滋养的是一种病态的社会,更谈不上什么“和谐”。经济学家们说,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所以才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为钱正名”。这一观点有它提出的时代背景。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在当今也需要谨慎地补充上“以合乎法律和道德的方式去追求财富”才更为恰当。这里的社会,它的钟摆总是倾向于从一端失控式地倒向另一端,殊不知两个极端皆非正常健康的状态。致富的浮躁气息如果让整个社会都为之癫狂,成为了人们唯一的奋斗目标,大众失去了其他的审美、人生趣味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感,那将是一个遗憾的结果。
行骗的社会逻辑,除了讨论作为对象的行骗者和受骗者之外,另一条脉络就是从底层的视野来解读它。十五年前在一家国企的家属院中,就常常有电压不稳、灯泡忽暗忽明或一栋楼的总保险跳闸的情况,据说就是有人在“偷电”。记得那时一个在人事科工作的人,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回家为一个毛衣作坊熨烫毛衣,熨烫一件5角钱,但是她家每月的电费都很低,电表就不走,这就引起了周围人的怀疑。她却“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偷电”,也就是公开地说谎。再后来,保卫科的干部们也就堂而皇之地冲进了此人家,抓了一个“偷电”的现形,最后罚了200元钱,这是很大的一笔钱,是她足足熨烫400件毛衣的收入。罚款不说了,还要张榜批评、以警后人。至今我还记得她去保卫科认错“求饶”的表情。她说自己认罚,但是苦苦哀求不要张榜,“丢不起脸、丢不起脸”。这显然是行骗曝光后当事人内心的“羞耻感”使然,而非“罪恶感”。前者的恐惧来自周围人鄙视的目光与评价,而后者则是内心深处的那份敬畏之心。现在流行于社会的各种“宣誓”活动对于只有“羞耻感”人格的人来说,是丝毫没有用处的,他们没有敬畏之心,担心的只是周围人的评价和自己的面子。回想十五年前,那时的人们行骗之后,还保存有“颜面意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区中,如果因此事张榜曝光,当事人真就将抬不起头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应该已经不多见了。至少流动性的增强和陌生人的社会消除了外部的环境制约。
“诚实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就在于谎言是普世现象。从政坛精英到市井小民,从商界巨贾到谍海特工,它成为生活的潜在主线。”此言不假。今日,骗术在这个泱泱大国登峰造极、广泛散播。针对个人的行骗,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愈演愈烈。充斥着谎言的社会,降低了人们的安全感,伤害着人们脆弱的感情,更不用说“杀熟”了。审计报告中也时有披露巧立名目骗取财政资金或挪用赈灾款的现象。菜市场上不乏“缺斤少两”。我们发现,“骗”大行了庙堂与江湖,成为了社会中最为普遍的常识——一种畸形、歪曲了的“常识”——“不被骗就不正常了”,真是荒唐至极!虽然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提高了,现代人为警惕、防备行骗备受了更大的心理折磨。
在社会层面上,行骗的危害在于瓦解了人际信任的基础。近年媒体多有报道,路人不敢搀扶跌倒的老人、孕妇等,担心“惹麻烦”。于是也便有了有人在地上躺了二十多分钟、半小时无人搀扶的故事。接受采访的人诉说了担心——“被冤枉上,说也说不清”。这样的担心和恐惧并非空穴来风。之前,就有许多好心扶助了摔倒的人,却被冤枉是“肇事者”的先例。类似这样的行骗,表面上是为个人讹取医药费或经济补偿,实际上腐蚀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因为实施救助者,本心是想助人为乐,却遭此诬陷,这是对救助者同情心的欺骗、污辱,留下的不仅是个人的心灵伤痕,更是社会的道德伤痕。周遭的人,并不需要亲身经历这样极其恶劣的行骗事件后,才小心提防。作为一种“社会学习”,人们在观察到了别人的类似经历后,就会自然形成条件反射——自己将来遇到跌倒的人也不敢扶助——“不是不想扶,而是交不起搀扶费”。这样一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也就有了市场,这样的影响简直是太恶劣了,催生了一个人情冷漠、高度戒备心的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的腐化是从内部开始的一样,社会的危机和解体也是从其民众的信任崩溃开始,而这样的信任崩溃是从欺骗对方的同情心开始。
总之,一个行骗盛行的社会并不健康,可以设想人们把行骗作为一种“常识”,甚至谋生、致富手段,这样的社会有何希望可言?即使物质生活比几十年前富裕了,道德精神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其所得。道德的重建是要塑造个人内心的神圣与敬畏感,而制度与网络的建设则是要增加行骗行为的成本和降低行骗得逞的几率。对于个人来说,少一些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地生活和工作,每个人都召回那份宁静的内心和信仰,才能达至祥和的人生与和谐的社会,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