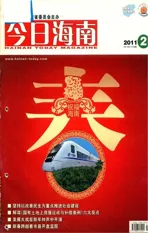儿时的春节
2011-12-23周骏
□ 周骏
儿时,最巴望的,就是过年。饱满的瓜子花生、花花绿绿的新衣裳、香喷喷的鸡鸭鱼肉……于我们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在这种诱惑的作用下,几乎当第一枚落叶在窗前翻飞时,我们就会掐起指头,认真计算起距离过年的时间了。那份心情是急不可耐的,甚至梦里也时常反复着过年时的情形,常常笑着从梦乡甜蜜地醒来。
在那种望穿秋水的日子里,时间也就似乎过得特别慢,等到田野变得清清爽爽,屋檐下挂满冰棱,大地白雪皑皑,河面不时传来冰层断裂的声响时,春节才算真正走近了。待到学期结束、寒假开始后,古朴宁静的村落里,迎来了另一番全新的景象:“砰”的一声闷响,惊得猝不及防的鸟儿一哄而散,留下几片零乱的羽毛随风飞舞,爆米花或炒米的香味却毫不含糊地弥漫开来;走在逼仄狭长的巷子里,不经意间就有手持年货、一脸喜气的村民或是一对红晕满面的新娘和神采奕奕的新郎擦肩而过;村头巷尾充斥着铲子与铁锅摩擦的声响,虽然单调而刺耳,却不妨碍炒熟的葵花籽和花生的香气四溢;村中心的高音喇叭里,响彻着新年祝福的歌曲,悠扬的旋律,又洋溢着喜庆的调子……过年的气氛渐渐浓烈了起来,具体了起来……
在我们抻长脖颈的巴望下,除夕终于姗姗来迟。经历了一夜的辗转难眠后,第二天一早,在急切和亢奋的心情的激烈鼓荡下,在不绝于耳的鞭炮声的催促下,我们早早就起床挨家挨户拜年去了。朴实的庄稼人,喜欢热闹,更图个吉利,不管相识不相识的,只要有儿童和少年前来拜年,总会毫不吝啬地拿出糖果。拜年者中年龄稍大一些,心思灵巧一些的,看见人家屋里贴了“双喜”,就恭喜“早生贵子”;遇到家境差些的,就恭喜“发财”;若户主是年长者,就恭喜“长命百岁”……每每能投其所好,得到的糖果也就多了几倍,有时甚至要送回家好几次。彼情彼景,只属于那个年代、那个年龄……
初二到初十,跟随家人走亲访友,喝喜酒、收红包、放鞭炮、接财神……日子快乐地飞奔,重复而又充满情趣。还没等回过神时,我们就已端坐在课堂上了。但此时,我们的心情根本无法平静,常常怔怔出神,不是想着床前瓦罐里的花生葵花籽,就是回忆着过年时的种种情状。等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一等到放晚学的铃声响起,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撒开脚丫,奔跑如飞地回到家里,草草扒完晚饭,拿起浸在柴油里用铅丝扎着破棉衣、棉鞋做成的“火把”,三五成群地相约来到寒风料峭、残雪未尽的田野。不一会儿,一团团火光在空旷的夜空亮起,犹如次第盛开的鲜花。火把一会儿排成一队,像一条条火龙或上或下,或高或低地翻腾跳跃;一会儿又围成一个个不太规则的火圈,随着“预备——走——”的口令,火圈或急或缓地向前滚动,煞是壮观;不知在谁的号召下,火把四处散开,然后,又不知是谁攒足力气,掼出了正燃烧着的火把,远远望去,如一颗流星猝然划过夜幕,接着,两个,三个……无数的火把脱手而出,就有无数颗美丽的流星从眼前滑过,四周的欢呼声顿时响成一片……一簇簇的野草被点燃了,熊熊的火光映亮了夜空,也映亮了一张张因兴奋和沉醉而红扑扑的脸庞……
舞完火把,也就意味着春节的正式结束。于是,在新的一年的落叶纷飞的时节,我们又会眼巴巴地盼着过年。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巴望中,我们经历了童年,走过了少年,从无知到成熟,从单纯到复杂,等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拥有儿时的那份心境时,那是因为我们已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