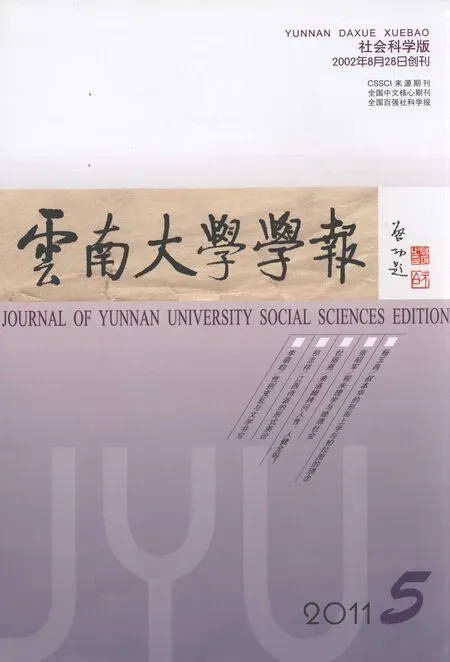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在 “无”之思中相遇*
2011-12-09陈蓓洁
陈蓓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1]
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在 “无”之思中相遇*
陈蓓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1]
无;非同一性;缘起;空;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思想与大乘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起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对关注无之问题的根本追问中,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达到了某种内在精神的契合。海德格尔通过追问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的问题,试图超出形而上学而开显非自我同一性的存在之真理。大乘中观哲学则依缘起法而批驳一切外道理论并彰显空有不二的中观法门。无对海德格尔而言是自身遮蔽的澄明,对大乘中观思想而言则是有无双遣的中道观照。据此而言,海德格尔与中观思想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虽然路径不同,言语不同,但是在对无之问题的澄清中,在显示出“思”的任务与事情。
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东方思想之间的渊源是一个引起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似乎在许多方面被东方思想所吸引,他曾经主动了解东方古老的传统,并且与一些东方的思想家如田边元、萧诗毅、九鬼周造等人有过交往。如今,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往来比半个多世纪之前更为频繁,重视和反思东西方文化根本境域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虽然思想之间的通达可以从各种角度和层次来进行,但是,假如不首先对彼此的存在论境域加以澄清,那么所有的比较和解释都将缺乏坚实的基础。当海德格尔自己认为他“与东亚的思想之间有着 ‘深深隐藏着的亲缘关系’”[1](P111)时,这样的亲缘关系就不能只从表面的相似与否来理解。因此,本文将关注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所达到的对存在的根本领会及其会通;而这样的会通将通过在海德格尔与中观思想那里都具有本质重要意义的“无”的思考而展开。
一、海德格尔:“无”与非同一性存在论
在海德格尔看来,“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然而,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这个问题成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这里的“基本问题”何所指?这个基本问题又为何要追问“无”?当然,所有这些疑问都要通过回溯这样一个问题,即到底什么是海德格尔所意指的形而上学,才能获得澄清的可能。
何谓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思考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2](P430)而并不思及存在本身。在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或被解释为唯灵论意义上的精神,或被解释为唯物论意义上的质料和力量,或被解释为变易和生命,或被解释为观念、意志、实体、主体、能力,或被解释为同一者的永恒轮回”。[2](P431)但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什么?换言之,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根据是什么?对这样的问题,形而上学既不愿意去追问,也没有能力回答;但这个本质根据却是形而上学得以立足的前提和基础,是它扎根于其中的土壤。这个长久以来就被形而上学遮蔽和遗忘了的根本,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存在的真理。
那么,科学是否可以通达这个根本?对此,海德格尔直言不讳地说:“一切科学的运思都只是哲学运思衍生出来的和凝固化了的形态。”[3](P26)现代科学不仅无法通达存在之真理,反而仅仅是“对存在者的计算性的对象化之方式”;这种方式消耗性地使用存在者,[2](P354)而无能于存在之思。
因此,若想达到存在之本身,我们就不能继续从形而上学或科学出发,即不能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出发,而必须直接契入存在本身,契入那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基础与根本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为什么要从“无”入手呢?海德格尔的“无”到底指什么?在他看来,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学统,而且是西方历史的天命。西方自古希腊以降,对世界的理解无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展开和进行。只要我们思考,就会习惯地从给定的存在者出发,亦即从形而上学出发,从而一再地使存在本身湮没无闻。因此,思及存在之真理,必须摈弃形而上学,必须首先不从任何可能遗忘存在的前提出发,而要从与存在者不同的东西出发。海德格尔把这个与一切存在者绝然不同的东西叫做 “不—存在者 (das NichtSeiende)”。[2](P356)在此意义上, “无”被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无乃是对存在者全体的完全否定”。[2](P126)
通常意义上,无有两种情况:一为与存在者相分离的无物存在的虚空、真空或绝对空间,一为存在者的毁灭、消失和死亡。但无论是无物存在还是在者的毁亡,都首先承认了存在者的存在,然后再将“无”理解为存在者存在的相反情况,所以,这里的无一直都是存在者的附庸。然而,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却从来不是这种相反情况,也从未以存在者为前提,毋宁说,它比一切存在者和一切存在者的缺场和消失更为根本。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再三重申“无”乃是“对存在者全体的完全否定”,即无不以存在者为前提;同时又强调,“无比不和否定更为源始”,[2](P125)即无不是存在者存在的相反情况。应该说,通过对存在者的这一双重否定而开显出来的无,是一个完全超出形而上学和现今一切科学的新的出发点和原则。正是从这一崭新的基础出发,海德格尔才使这样的发问成为可能:“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而且也惟有处身于这一崭新的境域中,我们才可能真正与海德格尔的这个问题相遇。
根据存在者对于存在的优先性地位来思考存在者整体,是形而上学之路;不从给定的存在者出发,而是从否定这种给定的存在者整体,亦即从无这里追问,且追问被形而上学所遗忘的存在,则是思的任务。因为离开那全部的存在者,我们还有什么可思的呢?难道还有一个“无”吗?若如此,“无”不就又成为一个存在者了吗?而且,我们不都是存在者中的一员吗?离开那全部的存在者,还有谁来思呢?而海德格尔却一再坚执地向我们宣称,正是对存在者全体的否定才是无的现身方式。
事实上,惟当我们的理性被如此这般地驱迫时,才有可能在这样一个万物消隐不现、诸义趋暗归无的状态中迎来那个新的境域;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我们是“在无中去经验为每一存在者提供存在保证的那种东西的宽广性,那种东西就是存在本身”,在这种根本性的体验中,“无把存在的深渊般的、但尚未展开的本质送给我们”。[2](P357)可见,无的本质就是存在。
当然,对海德格尔而言, “无”之思不仅意味着对形而上学思考的超越,在其基础存在论的建构上, “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解同一性,彰显非同一性的存在视域。
同一性即自身同一性,意指某存在者是其自身而非其他存在者。非同一性即非自身同一性或非自我同一性,是对自身同一性之坚持的消解。用非同一性标识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或许让人疑惑,其实非同一性本无量义,深者深见,浅者浅见。
西方形而上学对存在者整体的探究,一直都以对存在者的自身同一性的坚执为根本前提;在它看来,存在者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由,乃在于理智自身。所以海德格尔又把西方的形而上学称为 “逻辑学”。[4](P518)这门学问到处以概念逻辑的名义掌控一切,其结果必然是把完全超出它控制的、非概念的、具有个性和差异的真实生命 (或生气,或命运)还原为或者说同一化为概念或范畴的实例。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这种概念逻辑的能力“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一般原则之下”,“它不会停在某个特定的内容之上,但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5](P111)这个不能屈从于思维同一性的真实的质的领域,这个具有个别性特殊性的有生命的存在领域,我们常常就以“非同一性”来标识。
对形而上学的这种理智主义或主观精神的批判,海德格尔并非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在对如此这般的非同一性领域的阐释中,几乎还无需“无”的出场。虽然伽达默尔力图指证20世纪的哲学对主观精神的批判,由于有了尼采的哲学作为后盾,故而与黑格尔对主观精神的批判开始产生了区别,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即使尼采本人也未能真正阐明这种区别,并恰恰是在尼采那种个性张扬的思想中,“不仅现代形而上学得到了完成,而且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也得到了完成”。[4](P639)究其原因,乃在于这里的非同一性还只是作为同一性的反动而出现的,并由于仅仅是反动而不得不将自己塑造为另一种同一性,从而获得自己的权利和自律。倘若我们仅在这一意义上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非同一性,那就是浅见;因为那更为本质的工作,即对作为非同一性的所谓真实的生命领域的审查,还从未真正展开。也许因为觉得毋须再说,那毕竟是与我们如此亲缘的生命领域;但我们正是在这种熟视无睹中落入真正的无思,这种无思从本质上保证了我们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天然展开。
在海德格尔看来,以理性概念界定存在者之本质的另一后果是遮蔽存在,这是同一性更为隐秘的作用。虽然形而上学从未回避过存在,相反它命名存在,以至用不同的方式言说存在,但由于形而上学总是在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中思考存在,而存在者又是事先就通过思维概念而被建立和表象出来的,因此形而上学一直“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活动于对存在者与存在的普遍混淆之中”。[2](P436)但通过对无的追问 (由于这是一切形而上学都无法通达的领域),形而上学对存在的混淆和离弃便无法得到维持,存在者与存在之间被混淆的同一性得到分离,我们最终经验到了“一切惊奇之惊奇:即‘存在者存在’这一实情”。[2](P358)这是无对存在的解蔽,也是无对非同一性再度被形而上学所奴役的拯救,因为这几乎是未曾被涉猎的神秘领域,思被从无思状态中惊醒。
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无通过对存在者全体的否定来现身,但无不是否定的结果,而是否定的本源,可见无的现身方式既不同凡响又难以理解;然而无却正是凭借如此神秘而又伟大的现身之力量完成了对存在本身的敞开。在这个敞开域中,所有存在者所固执的自我同一性被打开:存在者不再是现成之物,不再是保持在自身之内的自我同一的东西 (无论它是凭借什么而达到的同一),而是超出自我之内在同一性的具有绽出特性的存在;同样,在这绽出性的存在中,人也从来不首先是他自己 (作为主体的自我同一),而是作为“此出—离地在”[6]的非自我同一,出—离于意识之内在性而一向在外,但这出—离却也不同于混沌的生命热情的懵懂勃发,而是在存在之无蔽状态中保持着开放性,亦即向着存在之真理的敞开。
对于这个彻底祛除自我同一性的绽出领域,海德格尔有时用“因缘整体”来标识:存在者并非存在者自身,而须在世界之因缘整体中成其所是;事物之自身性本不存在,对自身同一性的坚执恰好是割裂了因缘整体才派生出来的。由于形而上学思维的无孔不入,所以海德格尔强调道:不能将因缘整体裂变为现成事物的因果网络,因缘是对“存在者的存在之存在论规定,而不是关于存在者的某种存在者层次上的规定”。[7](P98)
总之,这种超越了形而上学的以非同一性为基础的思想是通过“无”才得以深化和演进的。从“无”来理解非同一性,始契本义。
二、中观思想:无与中道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真正的存在论问题必须追问那“使存在者之被规定为存在者”[7](P8)的存在本身。若依海德格尔的问题域来检视,那么佛学的宏大体系中无疑也包含着对存在问题的追问。与通常的哲学相比,虽然大乘佛学以了脱生死、普度众生为目标,以行门实证为指归;然而作为解行合一的法门,大乘佛学同样十分重视解门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世界和世间万物的存在性,对于佛学而言同样是需要给予解答的问题。大乘中观学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好地显现出佛学的精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乘中观学派的佛学思想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存在论,而且这种存在论以其对“无”的深刻领悟,与海德格尔哲学恰可形成一种奇妙的比照。
在佛学中,“无”的根本含义是“无相”,意即,尽管一切事物都有形象可见可闻,但这可见可闻的形象只是表象;事物并不是依照你所标示的样子存在的,因此一切“有”相都非真实。般若部经典常论及无相,如《金刚经》中说: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8]《大乘起信论》同样认为,“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9]
为阐明相的虚 (不实)妄 (不真)性,佛法更以“缘起法”来说明。“缘起法”被认为是佛法教义的基石与纲宗,是大乘佛教诸宗所共尊的不二法门,也是大乘中观学派的根本教理。可以这样认为,大乘中观学派的存在论思想,正是依“缘起法”而成立的。中观学派的重要论典《中论》便是如此表达其思想的: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这个以无 (空)、假、中“三谛”为核心的著名偈子,所表述的就是依“缘起法”而建立的存在论。那么, “缘起法”是如何开显出“无”的?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成其为存在论基础的?以下将通过对“缘起法”根本意趣的辨析,通过其与流俗见解的区别,彰示其内含的真实意蕴。
“缘起”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略称。 《中论》的阐释者青目论师的解释是, “众缘具足和合而物生”。[10]一切存在者其实都依各种因缘而生,事物在我们这里的映现,作为法相,亦是根、尘、识三缘和合而生。换言之,任何存在者 (无论是物还是观念)都是众缘变现出来的,在其内部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体。在此意义上, “缘起法”与传统的存在论背道而驰。因为传统的存在论都建立在某种确定不变的本体之上——或者是心,或者是物,或者是心物二元等;但不论是何种存在论,都无法接受其本体本身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缘起法”所达到的不仅是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且也是存在的有条件性。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原因就是众缘和合。物不自物,必待缘而成其为物;正因为如此,诸存在者便都依缘 (亦即条件)而成立。若果真如此,那么从逻辑上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出如下结论:若一存在者完全依凭诸条件而显现为某存在者,那么,作为存在者本身而言,它就是“空”的。这就如同聚沙所成之“塔”,不过是众多沙石通过工匠的劳作而成为塔的形象;若执著于塔,便是执著于塔的无常相续相。上述的“三是偈”的第一“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就表达了中观的思想。在大乘中观哲学中,众缘和合而生则直接意味着无或者空,所以《中论》又有偈语: “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10]在这个意义上,大乘中观学派确立了一种独特的存在论,即以“缘起”与“无相”作为诸存在者的存在本质。“缘起”即意味着“无”。
然而,“缘起法”及其达到的对事物之无相的理解,仍然存在着有可能陷入某种流俗解释的危险,即将“缘起法”重新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实在论。例如某些观点或许会这样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依条件而成立的,就像一个苹果确实是由红、圆球状、香和甜等表象特征所组成的,因此这个苹果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条件存在物或者关系存在物;同样,事物的存在依条件的转移而转移,比如当一个苹果被切碎或者因腐烂而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因为条件分解而使得该物不再存在了。或者换言之,一旦某些条件组合在一起,构成某物的时候,该物不就因此而获得了实在性了吗?尽管这种实在性是关系性的,但总不能说这个事物就全然是“空”的吧?当我们吃这个苹果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在吃一个实在的东西吗?同样的理由,尽管佛学将人身理解为“四大”和合而成的,但当我们活着的时候,难道不是一个整体吗?我们难道不是作为真实的个体而存在的吗?难道还有比这样的看法更符合常理的吗?
而当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缘起法”时,这种解释方式不仅没有超出以往的存在论,反而以更为隐秘的方式重新强化了它。何以这样说呢?因为这种解释方式并没有因为事物的缘起性和无常性而生起出离心乃至波罗密多心,反而就执留在这种关系存在物之中;也正因这种缘起物是如此地转瞬即逝,反而更加坚执于这短暂拥有的东西,从而其实是将这种关系存在物取代了原有的实体性存在物并确定下来。在这种解释方式中,所达到的仅仅是对物的有条件性的认识,却根本没有意识到:中观思想不仅在于启示物的有条件性,更在于指明物的无自身性;不仅在于获得某种对外物的理解,更在于破除自心的执著。上述的这种解释方式最多达到对“缘起法”名相上的认识,而对于法界缘起的领悟仍然付诸阙如。这种对缘起法意蕴的解释,不但没有真正理解中观学派的思想,反而失落了其最内在的精神。事实上,针对这种对中观思想的错误理解,古三论师早有指斥。比如僧肇在《不真空论》中就针对心无宗“万物未尝无”的观点而批评其“失在于物虚”。
因此,若要真正理解中观学派的“缘起法”,便须知“缘起”不仅意味着“相空”,同时还意味着“性空”。离开“性空”,中观思想便失去了立足的基础。性空的完整说法为“自性空”。诸法因缘而起,正因为如此,诸法都没有自性,或者说诸存在者都不住自性;说得更分明些,一切存在者都没有自身同一性。世亲《摄大乘论释》中说: “依大乘理,说一切法,皆无自性。”[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乘中观思想不同于一般的存在论,尤其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如前所述,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以自我同一性为不言自明的前提。非自我同一性不仅意味着原则的破裂,而且将使一切存在者失去存在的基础。然而,在般若部经典如《金刚经》中却充满着“所谓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这样的违反逻辑的说法,这种说法无疑在力图表明事物的非自身同一性。那么,大乘中观学派的存在论又是如何奠定在这种非自身同一性或者说自性空之基础上的?
事实上,虽说“性空”或者“空性”是佛法精髓,但也是最常被人误解的。比如认为空性就是否定任何事物的存在;或者认为抑制对事物的判断,对它们漠不关心,便成就了空性;或者认为空性是隐藏在一般现象之后的某种本质,只有具足智慧的人才能看到;或者认为空性就是空无所有,并执著于这个想法而试图去观修空无所有。这些见解都是基于有与无的对立,并力图用我们所假想的一种关于“空性”的图像来取代心中已经有的图像。对于空的这种执著,属于“断灭空”见,害处甚大,向来为大乘诸宗所驳斥,如明代藕益大师在《金刚经破空论》中开首就引经云: “宁起有见如须弥山,勿起恶取空见如芥子许”。
与之相反,中观思想所说的空性并非与有相对,而是要依“缘起法”才能开显的。对中观而言,缘起和性空本为一义的两面。所谓空,并非在万有之外还有一个空,而即是万有之当下本体,以故《心经》在说“色即是空”后即说“空即是色”,意为五蕴就是空,离五蕴就无空。所以,中观所达到的自性空乃是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 (因为无有二)的境界,是空有不二的如实空:一方面,诸存在者依缘而起,所以不有,这是空谛的意思;另一方面,诸存在者依缘而起,所以不无,这是假谛的意思。《肇论》云:“故摩诃衍论云,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应有。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不应有。一切无法,一切因缘故应有。一切有法,一切因缘故不应有。寻此有无之言。岂直反论而已哉。”[12]因此,中观思想中的无,并非绝对的空无,而是有内容的无,故称为“真空妙有”,以区别通常所谓的断灭空。妙有并非实有,以其性空而被称为“假有”;因为假有,所以立“假名”,即《金刚经》中所谓的“是名某某”。至此可以发现,大乘中观思想的“无”最终要达到的是有无双遣的中道义。从缘生故,名之为有;无自性故,名之为无。是故诸法非有非无,即有即无。空有不二,真俗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是为中道。
综上所言,大乘中观哲学的“无”依“缘起性空”而建构起了新的关于存在的根本理解。其所言“空相”义,乃是针对执有而言;所言“性空”义,针对的则是执空;而不有不无则彰显出缘起性空的不二法门。
三、海德格尔与中观思想:在“无”中相遇
虽然我们不能确知海德格尔究竟读过哪些佛学典籍,①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海德格尔“对禅宗虽然很感兴趣,并且多次认为那正是他一生所想言说的东西,但他在文献上主要是借助于铃木大拙的《禅宗》(Zen Buddhism,Garden city,NY 1956)一书,可能还有大峡秀荣所编的德语禅宗文献《禅:日本当前的佛教》”。也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极有可能——几乎是确定无疑——非常了解这两篇文献,并感谢这两篇文献加深和丰富了他在这个领域中的知识。”这两篇文献分别为禅宗三祖僧璨的《信心铭》与永嘉玄觉禅师的《证道歌》。参见《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德]莱茵哈德·梅依著,张志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51页。另,据另一位日本学者西谷启治Nishitani报道:1938年时他曾给海德格尔看过铃木大拙所著的关于禅宗的论文,后来海德格尔自己到大学去借了仅有的一本有关禅宗的书。可参见《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张祥龙著,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52页。更无法确定他在什么程度上受到过佛学的影响;但在内在的思想境域上,海德格尔与佛学思想显然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已知,大乘中观思想对于断灭见的批判非常严厉,因为这种顽空的见解不仅无法去妄显真,反而容易将人们的思想引入毫无生命力的歧途。因此,藕益大师在《金刚经破空论》中说:“盖空见拨无因果,能断五乘善根故也。”《成唯识论》也说:“拨无二谛,是恶取空也。”[13]《金刚经》说:发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
同样,海德格尔也反对把“无”仅仅理解为存在者的反面。他指出:我们常常在“我们所愿望、猜度、寻求、要求、期待的事物没有现成存在、不存在的地方,我们就会说‘虚无’”。[4](P688)这种对无的理解虽然最为常见,却也最为错谬。因为它往往产生如下的消极情绪:世界决不会与我们的理想相同,“这个世界因此是所有世界中最糟糕的……在这个最糟糕的世界中,生命是不值得经受和肯定的”,[4](P728)“一切皆虚无……生亦无谓,死亦无谓”。[2](P354~355)这种对无的理解大体上就是佛学所批驳的断灭空见;而海德格尔则把这种无的哲学叫做 “完全的虚无主义”。[2](P356)
出于对这种“完全的虚无主义”的抵抗,形而上学急迫地要抓住存在者。为此,形而上学从没把无当作真正的问题来思考,而是以轻视的姿态把无抛弃掉了:古代形而上学把无理解为不存在者,即无形的质料,基督教把无理解为与至高存在者相对立的受造的存在者,科学则以一种高傲的对无漠不关心的态度, “把无当作‘没有’(es nicht gibt)的东西”。[2](P137,138,123)但是,当形而上学试图抓住存在者,并将“无”仅仅当做存在者的反面排斥出去时,事情反而变成了这样:形而上学不仅没能把握住存在者,反而使存在者陷入到了纯粹的虚无之中,形而上学本身成了虚无主义,而且是“本真的虚无主义”。[4](P980)这是一切形而上学始料未及的。
至于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何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其本质乃是虚无,以及形而上学何以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此等问题事实上是海德格尔自《存在与时间》的基础存在论直至其晚年所一直思考的主要问题。诚如莱茵哈特·梅依在其《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中所中肯地指出的那样:“无 (das Nichts)这个概念,它像一条红线一样,意义深远地贯穿于海德格尔的著作”。[14](P40)可以这样说,对“无”的深刻领会是理解上述所有问题的前提。换言之,正是由于人们对无本身总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即从来不认真地对待无,思考无,并提出关于无的问题,虚无主义才会一直“阴魂不散”。在西方历史的定命中,无本身 (作为存在的真理)一直“处于概念的视野里,甚至在思辨辩证法的绝对概念的光芒中——但一直是未被思考的”,[4](P983)所以,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虚无主义 (执空)以及对虚无主义的一切抵抗 (执有),才会殊途同归。
然而,不论在海德格尔那里,还是大乘中观思想那里,关于无的问题却一直是最为首要和最为深刻的问题。凭借对这个在无蔽状态中又自行遮蔽着的东西的追问,他们使得自身能够区别于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以及作为其完成者的虚无主义。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海德格尔哲学在“无”中所通达的对存在之真理的非自身同一性的理解,与大乘中观“缘起性空”的思想,在基本的领悟上才得以相互应和。而海德格尔与中观思想各自对固执于存在者意义上的“有”、“无”(及其各种表现形态)的批判,同样是出自这个彼此相通的基本视阈,并在这个视阈中得以展开。对“无”的领悟,在海德格尔而言即是自身遮蔽的澄明,对大乘中观思想则是有无双遣的中道观照。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与中观思想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此外,无论对海德格尔还是大乘中观思想而言,对无本身的追问,以及在这一追问中所展开的种种思想境域,其实都不再只是一种哲学观的表达,毋宁说,它要求一种真正彻底的实践。所以,佛法讲空性,讲缘起,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由如实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而消除自心对一切法相有其自性的执著,息灭生灭相续的烦恼妄心,最终达到心与真如实相的契合。
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佛理上十分通晓无常无我的道理,并且也深服其高妙,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却依然会对无常无我的有为法心生执著?换句话说,为什么明明知道一种理论是错误的,却依然无法真正地克服和避免它?对此,海德格尔是深有体会的,他说:存在之真理的被遮蔽 (作为形而上学)是自行发生的。这一自行发生出于生命的本质。生命,尤其是人类的生命,都具有自我保存的功能,生命在其生存中关心的只是把它本身及其持存不断地保存下来。由于人“关心的是持存性、延续和永恒,所以,这种人同时已经把其生命中的这种关心置于‘世界’之中,置于‘整体’之中了。这种关于存在者之本质的解释方式 (即把存在者之本质解释为持续性)起源于人类生命对自身的本真因素的理解方式,亦即把自身看作对生命的持存保障。因此,惟有这些规定性——持存性、延续性和固定性——才道出了什么存在,什么可以被称为存在着的”。[4](P531~532)所以,对于生命而言,它并不真正关心什么是真实的,而只是把它所关心的对自己的持存保障 (即自我持存)设定为真实的。也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一再说: “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形而上学就是此在本身”,“只要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已经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了”。[2](P140~141)为了克服人之本性的这种冥顽不化,海德格尔与大乘思想一样地勇者无畏。既然种种有为法皆是虚妄,它们并无自性而只是依心的执著才建立自身,那么对虚妄的克服就必须从心上用功,痛下功夫。为此,佛学要求“自知其心”,“自治其心”,“自净其意”,从而达到对实相般若的观照。而海德格尔为了达到对形而上学 (作为生命的基本结构)之克服,也要求克服人向来的自我性,按照他的表达就是“放弃意识的优先性及其后果——人的优先性”,[6]摆脱 “求意志的意志”,[2](P354)因为求意志的意志,作为生命的意志,并不要求真理。因此要改变人的居所,要进行思想的移居,思想不再是为我的,思想是被存在居有的,思想要从存在而来,倾听存在的声音。
对海德格尔而言,思及存在之真理的思想不再满足于形而上学,而是要克服形而上学。但海德格尔并不把对形而上学的克服理解为对形而上学的消灭,并不是为反对形而上学而思,而是要为形而上学的根基“挖地犁土”。所以,对于基础存在论来说,存在者并非毫不重要,非自身同一性的存在诉求所要求的也不是消灭存在者;重要的事情仅仅是:存在者必须在“无”中向着此在而显现出来,“勇气在惊恐的深渊中认识到几乎未曾被涉及过的存在之空间;从存在之澄明而来,任何一个存在者才回转到它所是的和所能是的东西中。”[2](P359)
在此,我们又一次发现了海德格尔思想与大乘中观学派“空、假、中”三谛圆融思想在深刻处的通达。 《中论》极言“空,假,中”互具互融。何以言“空”后又言“假”呢?事实上,“假”谛用意极深。所言“空”谛,是般若智慧,知一切有为法皆无自性,为自性空,又名如实空。然而,佛学以慈悲度世界为宗旨,大乘佛学尤重随缘应世。因此,学者不能只停留在空性智慧之中,智慧须与慈悲兼备。对于“假”谛,青目论师解释道: “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这里正体现出佛学“为他”的慈悲之心。《大乘起信论》中亦言:“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故。二者、如实不空,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所谓如实不空,便是佛学中慈悲利他的无漏功德。这一思想见诸各种中观典籍,如《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行于布施”,[8]以及《大智度论》中所说:“般若将入毕竟空,绝诸戏论;方便将出毕竟空,严土熟生”,[16]都是同样道理。因此,“空”是智慧,“假”是慈悲;空假双运,即是第一义谛。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大乘中观哲学并不仅仅是某种单纯的理论,而是包含着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 “缘起性空”思想中所包含的慈悲与智慧不二是贯彻始终的——性空 (真空)即是智慧,缘起 (假有)则为慈悲,“缘起性空”意味着悲智双运。真正的般若智慧,不在于对世间的厌离,而在于如实正观。因此,在大乘中观思想中亦可以说:“有”乃是通过“无”而被更深刻地理解了。
同样,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也弥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其文中到处可见他对人类前途的担忧,对当代人无家可归状况的喟叹,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沉思。但同时这种哀悯却不是浪漫主义的软弱呻吟,因为他洞观到苦难的根源(根源于求意志的意志),并向人的本质要求有一种根本性的决断和转变:不是再利用大地,而是要领受大地的恩赐,并且去熟悉这种领受的法则,为的是保护存在之神秘,照管可能之物的不可侵犯性。[15](P101)为此,他对语言之沉沦痛心疾首,因为语言委身于我们的意志而成为对存在者的统治工具。为了再度置身于存在的近旁,海德格尔要求我们在说话之前先让自己重新接受存在的招呼,但这时就会出现一种危险:“他在这种呼声之下鲜有可说或者罕有可说”。[2](P373)所以,人首先要学会在 “无名”中生存。是的,在今天,若与那最深刻的东西相遇,我们一定是无言的。对海德格尔如此,对大乘中观亦如此。所以,空性的究极义是“不可说”。用概念表述空,终归是假名;离于主客二元对立来说,又无可说;当我们的心企图去捕捉空性的见解时,即是错,因为有执著即非正见。所以实相真如不可说,不可思虑得知,是大乘经一致之谈,此所谓“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只能以绝对无二的心去契证,并且这种契证只有依佛法修持才可能发生。但为方便度人,要勉强解说,同时又随说随扫,来显不二之真理。此中皆见中西方大思想家之苦心与悲心。
就像海德格尔自己一再言说的:“本质性的思想家们总是道说着同一者 (dasSelbe)”。[2](P428)虽然就理论的细节上,两者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对于他们整体的思想气质而言,那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比较,其本意并非要在学术上进行精致的细节考据。我们并不想让自己散落在对细节的追寻上,因为对一个真正对思想怀有敬意的人来说,契入那长久以来被人道说的“同一回事”才是最重要的和当下最紧迫的事情。
[1][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德]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6][德]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3).
[7][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08册 No.0235.
[9]大乘起性论[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册No.1666.
[10]中论[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0册No.1564.
[11]摄大乘论释[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1册No.1597.
[12]肇论[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No.1858.
[13]成唯识论[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1册No.1585.
[14][德]莱茵哈德·梅依.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M].张正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5][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6]大智度论[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册No.1509.
B1
A
1671-7511(2011)05-0087-08
2010-09-02
陈蓓洁,女,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
* 本文为“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项目号:YQ09CBJ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卢云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