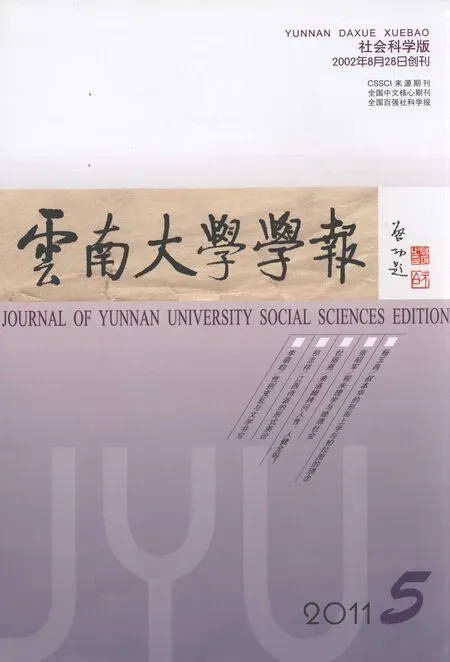江西诗派的形式美论*
2011-12-09祁志祥
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江西诗派的形式美论*
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活法;法度;余意;余味
隋唐宋金元时期,尽管儒家道德美学覆盖了整个诗文美学领域,但仍有一条形式主义倾向的美学线索在延续和发展。江西诗派的形式美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开其端,吕本中的“活法”论继其踵,杨万里的“意味”及“余意”、“余味”说承其绪,姜夔的“法度”论及“余意”、“余味”说封其后。他们以与诗歌内容相联系的方式,探讨了诗歌获取审美意味的形式规律和技巧,为形式诗学做出了一份独特的贡献。
隋唐宋金元时期,尽管儒家道德美学覆盖了整个诗文理论领域,并占据了诗文美学的主流,但仍有一条形式主义倾向的美学线索在诗学领域延续和发展,它们承接着六朝以“文”为美的形式美学狂飙的余威,在唐代以诗赋取士政策的支持下,①唐代设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所试诗体就是格律诗。《唐会要》卷七十五《帖经条例》云:“进士以声律为学。”坚守并捍卫着诗的自律,与道德美学的正统声音相抗衡,为道德美学不断地提供批判对象和存在理由,成为这个时期道德美学的反题。其历史坐标有隋唐之际以刘善经、上官仪、元兢、崔融为代表的诗律论,盛唐王昌龄的格律论,中唐皎然的诗法论,晚唐以贾岛、齐己为代表的苦吟派,宋代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崑派和以黄庭坚为祖师的江西诗派。本文主要探讨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形式美论。
一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涪翁,洪州分宁 (今江西修水)人。北宋治平四年进士,曾官校书郎、著作郎,出知宣州、鄂州等处,谪黔州、宜州。著有《豫章黄先生文集》、 《山谷全集》。 《宋史·文苑传》有其传。
黄庭坚是宋代形式主义诗学流派江西诗派的始祖。他本为苏轼弟子,居“苏门四学士”之首,但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却与其师有所不同。苏轼为诗为文,主张称心而言,快意累累,故“波澜富而句律疏” (刘克庄: 《后村诗话》),黄庭坚则取法杜甫对诗律的重视, “锻炼精而情性远”(刘克庄:《后村诗话》)。故黄诗更能代表宋诗的特色。严羽《沧浪诗话》云:“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这些评论均可在黄庭坚的文论中找到印证。
唐宋形式美学论者在阐述美学主张、探讨形式美问题时大多并未陷入单一化,往往同时祭起诗教传统的大旗, 《文镜秘府论》所载的初唐诗律论、《吟窗杂录》所载的晚唐五代诗格论是如此,宋初西崑体代表杨亿以及北宋中后期江西派始祖黄庭坚也是如此。他们有的是装装门面、走走过场,有的看似文道兼顾,实则重文轻道。身处道德至尊、儒家主宰的文化氛围中,黄庭坚深知: “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答洪驹父书》),但又指出:既然“索学”文章,就“不可不知其曲折”(《答洪驹父书》)。因此,他论诗,虽然不废《风》、 《骚》之旨,如《戏呈孔毅父》说:“文章功用不济世,何异丝窠缀露珠”。《胡宗元诗集序》说:“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但其全部理论的倾向,则重在形式技巧之美。 《答洪驹父书》指出: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里提出了“点铁成金”。又据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引:
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这里提出了“夺胎换骨”的创作法则。“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可代表黄庭坚形式主义诗学的个性。金人王若虚《滹南诗话》描述当时文坛的状况: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比喻性的概念,其要义有如下数端。
首先,要熟读前辈诗书,掌握形式技巧。《答洪驹父书》对外甥洪驹父说:“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继以叹息;少加意读书,古人不难到也。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所寄《释权》一篇,词笔纵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一》云: “……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或词气不逮初造意时。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跋书柳子厚诗》又云:“予友生王观复作诗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珮之音,左准绳右规矩尔。意者读书未破万卷,观古人文章未能尽得其规摹及所总览笼络,但知玩其山龙黼黻成章耶?”《与徐师川书》亦云:“诗政 (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 《论作诗文》总结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所写诗文要具有“高胜”的“词意”,必须对以前的名家诗文有广泛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前辈的作品既是超越的基础,也是超越的参照。这便使黄庭坚的理论带上了一层拟古的色彩,因而招来了一些非议。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批评他:“黄庭坚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宋末元初另一位学人方回《桐江集·刘元晖诗评》谓: “黄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 《世说》中不紧要字融液为诗。”说黄诗喜化用前人语言故事为诗属实,说黄氏偏尚拟古则不够全面。
其实,在充分学习、掌握前辈作品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是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的另一层含义。黄氏论诗宗杜甫、韩愈,杜甫、韩愈对创新都有所强调。杜甫赞赏:“诗清立意新” (《奉和严中丞西域晚眺十韵》),“赋诗新句稳”(《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愈追求“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 “惟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然而,杜甫、韩愈同时又都反对驾空创新,而主张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如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韩愈自述:“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进学解》)杜甫、韩愈的这一思想对黄庭坚有直接的影响。黄氏崇尚“自作语”,认为“自作语最难” (《答洪驹父书》),提出“以故为新”(《再次韵杨明叔小序》),正可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注脚。在上引关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两则材料中,这“故”与“新”的关系还是明白晓畅的。“取古人陈言”,这是“故”,“陶冶万物”,这是“新”; “不易其意”是“故”, “造其语”是“新”; “窥入其意”是“故”,重新“形容”是“新”。或意故而语新,或语故而意新。总之,要“词意”有所“高胜”前人处。在这里,“故”是“铁”,“新”是“金”,“以故为新”的艺术创造在这里施展了“点铁成金”的“点金术”。可见,黄庭坚主张学古,但反对拟古。《赠高子勉》说得很明白: “着鞭莫落人后”, “我不为牛后人”。这一点不可不加以注意。
再次,无论学古还是创新,黄庭坚都主张把注意点集中在“字句”、“法度”等具有形式美的规律上。黄庭坚强调“词意高胜”,这“意”是指创作之构思,谋篇之匠心,与“词”一样都属于形式问题。黄庭坚论诗文创作,非常重视法度的谨严、字句的锤炼、篇章结构的惨淡经营,如说:“语约而意深,文章之法度,盖当如此。”(《答何静翁》) “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合,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答洪驹父书》) “文章之工难矣。而有左氏、庄周、董仲舒、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韩愈、柳宗元及今世欧阳修、曾巩、苏轼、秦观之作,篇籍具在,法度灿然,可讲而学也。”(《杨子建通神论序》) “诗者,人之情性也。……情之所以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比律吕而可歌,列干戚而可舞,是诗之美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黄庭坚好论“句法”、“句眼”,如云:“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沉江。”(《奉答谢公定与荣子邕论狄元规孙少述诗长韵》)“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 “庭坚之诗,卒从谢公得句法。”(《黄氏二室墓志》)“其 (指陈师道)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答王子飞》) “一洗凡马万古空,句法如此今谁工?”(《题韦偃马》)“诗来清吹拂衣襟,句法词风觉有神。”(《次韵奉答文少激纪赠》)“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赠高子勉》之四)宋代佛教禅宗盛行,文人士大夫多染指佛教,结交禅友。黄庭坚亦然。《豫章黄先生文集》中就有不少篇佛学论文。“法眼”是佛教尤其是禅宗经典中常见的话语。宋人探讨诗歌艺术规律的诗话中也常见“法”、“眼”一类的词语。黄庭坚要求学习前辈作品的“法度”、“句法”,自己创作的作品也句法工稳,“法度灿然”,是其诗文美学形式主义特征的突出体现。
复次,黄庭坚重视形式美,但又反对唯形式美是求,而主张“以理为主”,形式为表情达意服务,“平淡而山高水深”,不留人工雕琢痕迹。这方面他以杜甫为典范,他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之一) “……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耳。”(《与王观复书》之二)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大雅堂记》)黄庭坚此论,上承苏轼的“随物赋形”、“寄至味于淡泊”的思想,下启吕本中的“至法无法”的“活法”论。他所说的“法度”,并不仅仅指可以授受、静止不动的“规矩方圆”,而具有某种因意适变、不可捉摸的色彩。
专注于“文章”又以“文章”为“末事”,留意于“文”(形式)又主张“无意于文”,学古又不满足于泥古,创新又强调“无一字无来处”,爱“佳句”又恨“雕琢功多”,求“法度灿然”又主张“更无斧凿痕”,尚“平淡简易”又要求包含“山高水深”之“大巧”,追慕“不烦绳削”而又要求“自合”于形式美规律,有法而又无法,无法而又有法,如此等等。黄庭坚的理论中充满了道家相反相成的“玄机”(老子称“玄之又玄”,唐代道家学者成玄英谓之“重玄”)和禅家“双非双遣”的“机锋”。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后来被江西诗派奉为不二法门。
二
黄庭坚虽被后人奉为“江西诗派”的始祖,但他本人并未有意识地建派立宗。“江西诗派”之名源出北宋末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载:“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即洪驹父)、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又据《宋史·艺文志》,吕本中曾编《江西宗派诗集》一百一十五卷,曾纮曾编《江西续宗派诗集》二卷。一般认为,除吕氏所列26人外,吕氏本人及陈与义、曾几、曾纮、曾思父子亦为江西诗派的重要作家。除上述31人外,南宋受江西诗派影响的诗人还有很多,下文将论及的杨万里、姜夔就是其中的两位。上述“江西诗派”中人,不都是江西人,但均奉江西宗祖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强调以故为新和有法至于无法的“活法”。其中尤以吕本中、杨万里、姜夔的诗论值得注意。
1.吕本中:“活法”论
吕本中 (1084~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 (今安徽凤台)人。南宋绍兴中赐进士出身。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因得罪秦桧被罢官。著有《东莱集》二十卷、《外集》二卷、《紫微诗话》一卷、 《吕氏童蒙训》一卷、《春秋集解》十卷。《宋史》卷三百七十六有其传。
吕本中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是最早提出“江西诗派”之称的人。其论诗宗法黄庭坚,偏重文字锤炼,主张从“工夫” “悟入”,源于规矩而又超越规矩,最后达到有法而无法的“活法”。
黄庭坚论诗偏重“法度”、“句法”。吕本中亦然。《童蒙诗训》对此论之甚详:
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柂春江流,予亦江边具小舟”,“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如此之类,老杜句法也。东坡“秋水今几竿”之类,自是东坡句法。鲁直“夏扇日在摇,行乐亦云卿”,此鲁直句法也。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
渊明、退之诗,句法分明,卓然异众,惟鲁直为能深识之。学者若能识此等语,自然过人。
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如《封主簿亲事不合》诗之类也。东坡诗有汗漫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皆不可不知。东坡诗如“成都画手开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皆穷极思致,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贤所未到。然学者专力于此,则亦失古人作诗之意。
陆士衡《文赋》云: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老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老杜云:“新诗改罢自长吟。”文字频改,工夫自出。近世欧公作文,先贴于壁,时加窜改,有终篇不留一字者。鲁直长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见大略。如《宗室挽诗》云: “天网恢中夏,宾筵禁列侯。”后乃改云:“属举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1]
江西诗派论诗宗杜。杜甫诗以抑扬顿挫为主要特征。故江西诗派多以“响”论句法,所谓“五言诗第三字要响”、 “七言诗第五字要响”。《童蒙诗训》云:
潘邠老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
吕本中本身是道学家,曾给儒家经典《春秋》作过集解。他深知“诗”与“道”相妨,所谓“诗日进而道日远”(《紫微诗话》),“稍知诗有味,复恐道相妨”(《试院中作》),但还是把心思放在诗上,放在诗律、诗法上,所谓“好诗有味终难舍”(《次韵答曹州同官兼简范寥信中》), “平生事业新诗在”(《汴上作》)。这样说来,吕本中又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道学家,与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已然有别。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位诗人,一位形式主义诗人。
黄庭坚主张,对于前人作品中的“句法”、“法度”要下苦功学习,如此才能推陈出新。吕本中亦然。《童蒙诗训》引徐师川语表达创新追求:“作诗自立意,不可蹈袭前人。”同时黄庭坚又指出:“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所谓“悟入”,即领悟、进入、把握到前辈典范作品的“法度”之谓。它必须从“工夫”中得来。 《与曾吉甫论诗第一贴》亦云: “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在通过勤奋的工夫“悟入”诗歌“法度”、 “规矩”的基础上,吕本中又强调不要为既有的“法度规矩”所限而一成不变,而要运用这些“法度规矩”,为表现“万变不穷”的诗“意”服务。如此,这“法”就是“变化不测”的“活法”。这些思想,虽在黄庭坚诗论中已有,但吕本中首倡“活法”概念,有更大的提升和发展。《江西诗社宗派图》云:“诗有活法。若灵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夏均父①即夏倪,江西诗派作家之一。集序》云: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
吾友夏均父,贤而有文章,其于诗,盖得所谓“规矩备具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者。后果多从先生长者游,闻人之所以言诗,而得其要妙,所谓“无意于文”之文,而非“有意于文”之文也。
吕本中所言“活法”,要义有二。
一是以达意为主。“活法”虽然是“法”,但又是为达意服务的,是对“法”的超越和对纯形式之“文”的超越。黄庭坚《大雅堂记》曾赞美杜甫诗之“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吕本中这里寄希望于诗人夏均父的正是这种“无意于”形式之“文”的有为而发,“惟意所出”之“文”,能够用以从前人作品中学到的一切技巧、方法为表达“万变不穷”之“意”服务。
二是“有定法”与“无定法”的关系。“活法”为达意服务。 “自得”之“灵均”、“万变不穷”,相应表现出来的“句法”、 “规矩”也就“变化不测”。在这个意义上, “活法”无一成不变之“定法”。另一方面,诗在表达自得之“意”时,又有一定的技法,它们是从前辈典范作品中留传下来的、学习得来的,这是“定法”。“活法”就是运用“定法”为表现变化不居的己意服务的“无定”之法。这就是“有定法而无定法”, “无定法而有定法”;“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稍后的俞成在《文章活法》(《萤雪丛说》卷一)中进一步阐释道:“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 ‘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故为‘死法’,生吾言者故为‘活法’。”
可见,“活法”既是形式美的法则,又不是唯形式、纯形式的创作法则,它借用佛家“活”的中观思想分析诗法,在“言”与“意”的相反相成中寻找到最佳的契合点,既符合形式论者的美学趣味,又能为主张“言之有物”、“有为而发”的内容论者所兼容,不只在宋元,而且在明清文艺美学中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张孝祥、杨万里、严羽、姜夔、魏庆之、王若虚、郝经、方回、苏伯衡、李东阳、唐顺之、屠隆、陆时雍、李腾芳、邵长蘅、叶燮、王士祯、沈德潜、翁方纲、章学诚、刘大魁、姚鼐、袁守定等人,或以“活法”要求文学创作,或批评不知变通、专事摹拟的“死法”,可见其影响之大。
2.杨万里:“意味”及“余意”、“余味”
杨万里 (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县 (今属江西)人。绍兴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著有《诚斋集》、 《诚斋诗话》、《诚斋易传》。
杨万里比吕本中小43岁,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罗列的江西诗派作家中未及收入杨万里。但杨万里亲自给吕本中编辑的《江西宗派诗集》和曾纮编辑的《江西续宗派诗集》作过序。尽管他的诗歌美学并非江西诗派所能范围,但其深受江西诗派影响则毫无疑问。
杨万里道统观念很浓,一生为官,方正清廉,关心国事民生,富有民族气节,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将其列于《儒林传》中。不过,他又不同于道学家鄙薄文词,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全心全意倾力于文词的诗人。《唐李推官披沙集序》自述此旨: “予生百年所好,而顾独尤好文词,如好好色也。至于好诗,又好文词中之尤者也。至于好晋、唐人之诗,又好诗之尤者也。”那么,“诗”是什么呢?《颐庵诗稿序》云:
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乎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
诗虽然是文词的艺术,但它的艺术价值却不在文词本身,而在文词所表达的“意”;同时,又不在言内意,而在言外意也。言外之意,如同先苦后甘、回味无穷的“荼”一样。杨万里多处以类似于“荼”的“味外之味”论诗之美:“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者也。”(《诚斋诗话》) “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否也。《国风》之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吾取以为读书之法焉。”(《习斋论语讲义序》)“五言长韵古诗,如白乐天《游悟真寺一百韵》,真绝唱也。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后山《送内》,皆是一唱三叹之声。”(《诚斋诗话》)他认为,江西宗派的诗就是具有这种“雅淡”而“深长”的“味外之味”。《江西宗派诗序》指出:
“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东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唯当时闻者呒然,阳应诺而已,今犹呒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呒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师川,师川不似陈后山,①二谢,指谢逸、谢薖。三洪,指洪朋、洪刍、洪炎。陈后山,即陈师道。高子勉、二谢、三洪、徐师川、陈后山等,均为《江西宗派诗集》中人。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胹 (煮也)之妙,出乎一手也。似与不似,求之可也,遗之亦可也。
江西之诗,世俗之作,知味者当能别之矣。
杨万里认为,“江西之诗”与“世俗之作”的最大区别,是“江西之诗”有“味”,“世俗之作”无“味”。把二十多位不是出生于江西的诗人命名为“江西宗派”,不是根据“形”,而是根据“味”。从“形”上看,江西诗人之诗“不似”;从“味”上看,江西诗人之诗相“似”,都可归结到江西宗师黄山谷门下。
杨万里所高标的“味”,要义有二。一是“意”;二是类似于“味外之味”的“意外之意”,亦即“言外之意”。
(1)先来看“意”。
首先,重“意”是江西诗派的一贯传统。在前述黄庭坚、吕本中诗论中已分明可见。杨万里论“意”,要求诗须表现道德性情。 《诗论》云:“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盖圣人将有以矫天下,必先有以钩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随以矫,夫安得不从?……圣人引天下之众,以议天下之善不善,此《诗》之所以作也。故诗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杨万里继承“《诗》之教”,要求诗表现道德性情,使之成为复道矫世之工具。这样,他“好词”、“好诗”与“好道”就不矛盾了。
其次,他主张诗要写得有创意。有创意,也是江西诗派所一贯倡导的。杨万里说:“传派接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诗》)黄庭坚、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祖师,陶渊明、谢灵运是杨万里曾深深推崇的诗人,即便对于这样的高手,也不应一味摹拟,而应当加以超越,有所创新。也正是这一点,使杨万里最终走向了对江西派的背叛。 《诚斋江湖集序》自述云:“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诚斋荆溪集序》又自述其变化经历:“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 (王安石)老人七言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然有寤 (悟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
复次,新意从哪里来?杨万里主张从鲜活的大自然中汲取,而不是闭门造车,苦思冥想。他屡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情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 “城里哦诗枉断髭,山中物物是诗题。欲将数句了天竺,天竺前头更有诗。”(《寒食雨中同舍约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此行诗句何须觅?满路春山总是题。”(《送文黻叔主簿之官松溪》)“哦诗只道更无题,物物秋来总是诗。”(《戏笔》)“江山岂无意?邀我觅新诗。”(《丰山小憩》)“……诗皆感物而发,触兴而作,使古今百家、景物万象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应斋杂著序》)他把这种由自然触发的鲜活诗意叫作“兴”,并重新解释了“兴”:“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焉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也?天也。斯之谓兴。”因此,鲜活的富有创新意义的诗意是大自然的馈赠:“……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 (扇也),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 (挥也)之不去,前者未雠 (通酬)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诚斋荆溪集序》)杨万里此论,受江西派宗师之一陈与义影响不小。陈与义类似的言论也有好多,如:“方其寓目时,万象供啸呼。”(《寄题康平老眄柯亭》) “物象自堪供客眼,未须觅句户长扃。”(《寺居》)“邂逅今朝一段奇,从来华屋不关诗。”(《同继祖民瞻游赋诗亭》) “莺声时节改,杏叶雨气新。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题酒务壁》) “柳林行不尽,想见春风时。点点羊散村,阵阵鸿投陂。城中那有此?触处皆新诗。”(《赴陈留》)“且复哦诗置此诗,江山相助莫相违。”(《次韵光化宋唐年主簿见寄》) “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可以说,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的富于创造性的诗意,是江西诗派的一个重要美学主张。究其根源,与佛教的影响很有干系。宋代佛教更广泛地走进文人士大夫中。江西诗派中人多与佛教、禅宗有染。禅宗追求自主自由,自悟本性,自立门户,反对俯仰人后,头上安头,叠床架屋,又主张随物应机,当机煞活,在万象中悟道,为诗人们从物感中求新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宋人说:“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与禅宗话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莫非般若”何其相似!
(2)再来看作为“味外之味”的“意外之意”。
诗人从大自然的感触中获得了富有新意而又不逾礼义的道德性情,这是诗的本体。但诗在用文词表达本体性的诗意时,则不能过于直白、简单化,有一说一,了无余韵,而应讲究艺术性,以少总多,以淡藏浓,以言内意吸附、包容最多的言外意,从而获得一种“味外之味”,使人回味无穷, “一唱三叹”, “不胜其甘”。 《诚斋诗话》主张“诗已尽而味方永”,崇尚“句雅淡而味深长”,《应斋杂著序》推崇“平淡简易,不为追琢,不立崖险”之文,均是此意。这是江西诗派津津乐道的“活法”创造的审美境界。 “活法”追求“至法”归于“无法”,故“无法”中包含“至法”,“平淡”中包含“浓丽”,“去意”后可包藏无限之意。这就叫“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大体说来,对这种包含浓丽的“平淡”之美的理论说明发端于唐代,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说“淡者屡深”,韩愈《醉赠张秘书》说: “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到宋代则成为理论界普遍的美学追求。如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苏轼《评韩柳诗》:“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葛立方《韵语阳秋》: “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周紫芝《竹坡诗话》引苏轼语:“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并说: “余以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吴可《藏海诗话》:“凡文章先华丽后平淡……若外枯中膏者是也。”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之二:“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陆游《示桑甥十韵》: “大巧谢雕琢。”《读近人诗》:“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鳌哈柱岂同科?”刘克庄《跋真仁夫诗卷》:“繁浓不如简淡。”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平夷自然为上,怪险蹶趋为下。”如此等等。其中,江西诗派的影响功不可没。正是在这种审美趣味下,陶渊明的价值在宋代得到了空前地提升。宋人的这种审美趣味,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人戴表元《许长卿诗序》云:“酸咸甘苦之于食,各不胜其味也,而善庖者调之,能使之无味……无味之味食始珍……”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王世贞《书谢灵运集后》:“秾丽之极而反著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四: “炫烂之极,归于平淡。”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出色而本色”,“极炼如不炼”。
3.姜夔:论“法度”及“余意”、“余味”
姜夔 (1155-1221),字尧章,鄱阳 (今属江西)人。后寓居浙江吴兴,邻近苕溪白石洞天,故号“白石道人”。屡试不第,终身未仕。工诗,通音律,尤以词著名,被张炎推崇为“清空”词的典范。著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诗说》等。
姜夔并非江西诗派中人。《白石道人诗集·自序》曾自述其从江西诗派入、最后又从江西诗派出的经历:“近过梁谷,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胶如也,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然而,尽管他最终跳出了江西诗派的框框,但《白石道人诗说》仍带有明显的江西诗派的痕迹。现加撮述,以见江西诗派形式美学主张影响之一斑。
江西派论诗重句法、声律。白石亦然。《诗说》云:“守法度曰‘诗’。”“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 “句法欲响。”“作大篇,尤当布置,首尾句匀停,腰腹肥满。”“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江西诗派重用事使学,白石对此尤有心会:“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南宋末年张炎著《词源》,批评南宋词人吴文英用典过于“凝涩晦昧”,“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有“质实”之弊。姜白石词也用典,但由于他“善用事”,所以“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古雅峭拔”,有“清空”之美誉。
江西诗派重形式,但是,第一,不唯形式,而主张与“意”相连;第二,就形式本身而言,主张平淡自然,无人工雕琢痕迹。这两点在姜白石《诗说》中体现得也很分明。关于第一点, 《诗说》云: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 “意格欲高……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他尤其推崇“词意俱不尽”的“余味余意”:“词意俱不尽者,不尽之中,固已尽之矣。”“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这与杨万里说的“删词删意”、 “味外之味”何其相似?关于第二点,《诗话》说:“雕刻伤气,敷衍露骨。”“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陶渊明……诗散而庄、淡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白石词清空淡远,令人回味无限,正是这种诗学主张的实践。
[1]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I052
A
1671-7511(2011)05-0047-08
2010-10-25
祁志祥,文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与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史的重新解读”(项目号:05BZW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林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