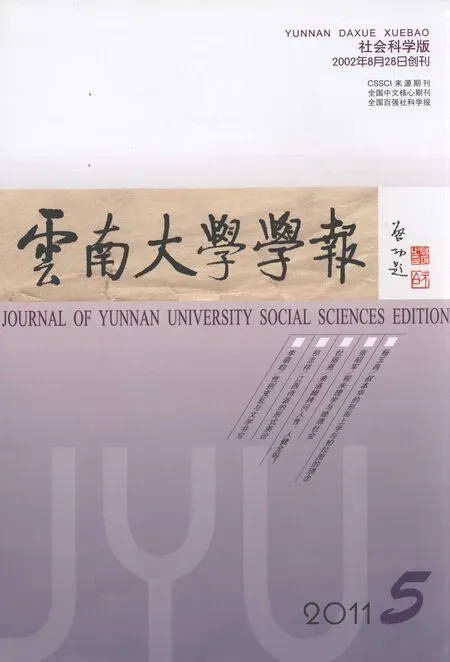性别变乱与文学书写
——隆庆二年山西男子化女事件的叙事研究
2011-12-09李萌昀
李萌昀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性别变乱与文学书写
——隆庆二年山西男子化女事件的叙事研究
李萌昀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李良雨事件;性别变乱;文学书写;叙事研究
明穆宗隆庆二年,山西太原府静乐县发生了一起男子化女事件。出于某些原因,此事件在当时轰动朝野,并在官史、私史、诗歌、笔记、通俗小说当中都留下了面貌各异的叙述。王世贞、刘凤、徐应雷等人的诗歌秉承灾异话语的正统观念,从现实关怀出发,将性别变乱当作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的隐喻,构成了“李良雨事件”之书写历史的主流。《型世言》等小说作品则从民众趣味出发,对此事加以生活化和娱乐化的想象和改编,从而构成对主流叙事的消解和颠覆。此外,还有些士人热衷于对此事件的理性思考,表现了传统思想中蕴含的格物精神。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五月,山西太原府静乐县男子李良雨不知为何变成了女子。本来这件事应如中国历史上众多真假难辨的变性传闻一样,迅速湮没无闻,最多成为正史《五行志》中无关痛痒的一则记载,但是出于某些原因,“李良雨事件”居然轰动朝野,上至穆宗皇帝、阁部大员,下至基层官吏、布衣文人,纷纷卷入到对此事件的传播与书写当中,在官史、私史、诗歌、笔记、通俗小说当中,都留下了对此事件的不同叙述。这一事件展现了晚明时期当代题材之文学化的诸种面相,也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社会心态与思想观念的微观视角。
一、“李良雨事件”的官方叙事
隆庆二年十一二月间,山西太原府静乐县官员报称:该县龙泉都男子李良雨忽转女形,已拘执审实。山西巡按御史宋纁迅速将此事写成奏折,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送抵北京。《明史·宋纁传》保存了他的奏折大意:“静乐民李良雨化为女,纁言此阳衰阴盛之象,宜进君子退小人,以挽气运。”[1](P5889)我们无法明确判断他的上奏意图——是作为监察官员例行公事地汇报灾异,还是出于对国家现状的忧虑而借机进言。我们只知道,在他看来,“李良雨事件”并非寻常的“怪力乱神”,而是有着巨大阐释空间的灾异事件;此事证明,帝国气运已呈阳衰阴盛之势,为了引导阴阳二气重归平衡,应该进行政治变革。此时是隆庆二年,国家远未从嘉靖后期的政治混乱中恢复过来。
相比之下,礼部官员的态度则尖锐得多。《明穆宗实录》卷二十七载,二年十二月庚子(二十六日):
礼部类奏:是岁四方灾异比往年特多,而山西天鸣地裂、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为异常,宜痛加省。
此日是宋纁奏折送抵北京后的第二天,礼部官员的奏折便摆在了皇帝面前。这份奏折即礼部尚书高仪的《类报灾异疏》。*见[明]贾三近《皇明两朝疏抄》,万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高仪称,“李良雨事件”是“人事不修,臣职未尽”而导致的“上天谴告”,绝非偶然,建议诸臣“深思愆咎,痛戒荒宁”,希望皇帝“仰体天心,俯修圣政”,如此则“天意可回,天变可弭”。对此,穆宗皇帝批示道:
上天示儆,朕夙夜惊惕,不敢怠荒,尔内外臣工,其务实心体国,修举业职,共图消弭,以仰承仁爱之意。[2](P731)
虽然宋纁和高仪的奏折可能只是例行公事地灾异汇报,穆宗的批示也只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礼节性表态,但是,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与正面回应,“李良雨事件”便引起了晚明士人的广泛兴趣,成为在百年间被不断书写的文学题材;更重要的是,穆宗批示和宋纁、高仪奏折一起,构成了对“李良雨事件”的官方叙事,与下文将要分析的诸多个人化书写形成了鲜明对比,衬托出官方话语之外的思想世界之丰富景观。
二、“李良雨事件”的原始面貌
在分析“李良雨事件”的诸多个人化书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此事件的原始面貌做一番考索。沈德符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见之奏牍,天下所信。”[3](P923)从明代的信息传播途径分析,宋纁奏折很可能经过六科官员的编纂,被记入邸报,从而广为人知。如果这份邸报存在,那么它便是后来各种个人化叙事之“母本”,也是最能反映该事件原始面貌的叙述。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载:
隆庆二年,山西太原府静乐县龙泉都民李良云弟良雨忽转女形,见与岑成都民白尚相为妻。先云父李怀生弟雨,怀病故于嘉靖三十一年,雨年二十八岁,至三十七年娶马积都民张浩长女为妻。四十一年间,两相反目,将妻出与本都民高明金。雨无营计,往本县地名也扒村投姐夫贾仲敖家工作。隆庆元年正月内,雨偶患小肠痛,旋止旋发,至二年二月初九日,卧床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亦无妻,于雨病时,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内,雨肾囊不觉退缩入肚,转变成阴,即与白嬲配偶。五月初一日经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后每月不爽。雨方换丫髻女衣,裹足易鞋,畏赧回避不与人知。九月内,云访闻之,令妻南氏探的。十一月初二日,禀县,拘雨、相同赴审实,稳婆方氏领至马房验,系变形,与妇人无异。又拘雨出妻张氏勘明,娶后三年内往来交合,但未生息,止缘贫难嚷闹,卖离邻里。姚汉周等执结,与前相同。巡按御史宋纁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奏闻,称男变为女乃阴盛阳微之道,以祈修省。[4](P181~182)
此条笔记精确地记录了“李良雨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人物及具体过程,叙事清晰简明,颇类邸报文体。高仪《类报灾异疏》叙此事有“于本年四月内,将肾囊不觉退缩入肚,转变阴门”之语,与《漫笔》文字基本一致,可见同出一源。《类报灾异疏》之文字必然直接采自宋纁奏折,由此,《漫笔》之材料来源即使不是邸报,也应是类似邸报的某种奏疏抄本,可以作为考索此事之原始面貌的主要依据。
《内经·灵枢》云:“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此病多由客寒蕴热、气滞郁结或气虚不禁所致;发作时多见口疮、痔疮、控睾、疝气等症。从李良雨的身体变化过程来看,自病发至肾囊退缩入肚,“控睾”——小腹腰脊处疼痛,并牵引睾丸——很可能是其主要症状。这份材料所谓的“小肠痛”与中医意义上的“小肠痛”自然并非一事,可能是出于这一症状上的相似,才将这种罕见的身体变异冠以“小肠痛”之名。
关于李良雨的结局,《漫笔》未有记述。于慎行《谷山笔麈》载:“守臣以闻,良雨自缢死。”[5](P177)于慎行是《穆宗实录》的编者之一,有可能接触到“李良雨事件”的原始材料。王同轨《耳谈类增》亦云:“邑以闻,按台行文解验,惭惧缢死。”[6](P121)可为旁证。李良雨之死,似乎是由于变性事件被曝光后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不过也不能排除被官府作为“妖异”而秘密处决的可能。
总之,在原始叙事中,李良雨的性别变化仅出于某种类似小肠痛的未知疾病,而并无神秘力量的参与;在事件曝光后,李良雨自缢身亡。另外,按照《漫笔》推算,变性时的李良雨已是一个四十四岁且饱经艰辛的佣工,恐怕不会有多少姿色了。
三、格物热情
“李良雨事件”迅速以各种方式在明代社会流传,引起了士人阶层的广泛兴趣。他们不但将此事记入笔记、私史,而且以之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由于身份、地位不同,思想、趣味各异,形成了众多游离于官方叙事之外的个人化书写。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这么多文人在百多年间对此事反复书写?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这些个人化书写呈现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思想面貌呢?
首先来看一看那些具有强烈的格物热情的明代士人。面对超乎常情的事情,他们常常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解释冲动: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如果发生了,如何将其整合到理性的框架之内?多数人宁愿在超自然的事情面前持谨慎的存疑态度,例如李时珍和沈德符。
在《本草纲目》“人傀”一节中,李时珍列举了人类身体的诸多反常现象,提出了若干可能的解释。性别变化——“李良雨事件”被作为此问题的一个案例而记载——便是他思考的问题之一。李时珍怀疑性别变乱是游离于阴阳二气之正常秩序之外的“乖气”所致,不过同时他诚实地表示,“男变女”、“女变男”所必需的那些脏腑、经络的微妙变化,已经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范围。因此,他主张承认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应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变化无穷的世界。我们虽然知道万事万物生灭变动皆出于气之变化,但是对其中的微妙规律,我们还所知甚少,“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物为迂怪耶?”
对于“李良雨事件”的可信与否,沈德符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举出了他在阅读和生活中遇见的两件小事:
后见郎氏《七修类稿》云:“雄黑猿多有化为雌者。”余怪笑谓郎老儒为人所绐。及见嘉靖间吴兴王济著《日询堂手录》,则云:“广西横州山中,猿皆黑,老则转为黄,其势与囊俱溃去,化为牝,与黑而壮者交,辄孕。”此王官彼中所亲见者,盖其地凡为猿者皆然矣。……宇宙中非目睹者,断不可臆断。向传兔生具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则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恒兽,古语盖难尽信。[3](P923)
沈德符试图强调的是经验主义的重要性,或者说,是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在未经目睹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一件事(“牡猿化牝”),也不能轻易肯定一件事(“望月而孕”)。因为,相对于宇宙之大来说,我们的知识过于渺小。那么,对于“李良雨事件”也是一样,既然不能目验,那么过分地肯定或者否定都是盲目的,存疑可也!
四、作为政治和道德隐喻的性别
在“李良雨事件”的诸多书写中,王世贞、刘凤、徐应雷等人的诗歌在思想观念上与官方叙事最为接近,但却比官方叙事增加了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和个人情怀。这些诗歌将性别变乱当作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的隐喻,构成了“李良雨事件”之书写历史的主旋律。
隆庆四年七月至十月,王世贞在山西担任提刑按察使。此时距事件的发生刚刚两年,李良雨的故事或许还没有淡出当地人茶余饭后的闲谈。如果王世贞此前从未经邸报等途径获知此事的话,那么在山西三个月的任期足以为他提供听说此事的可能。《山西丈夫化为女子》云:
万事反复那足齿,山西男儿作女子。朝生暮死不自知,雌伏雄飞定谁是?谢豹曾闻受朝谒,於菟亦解谈名理。渭南巾帼不可呼,此曹变化无时无。只今龌龊不能去,羞向人间唤丈夫。*见[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此诗可与刘凤诗同观:
鸿蒙乃与阴阳事,犹疑天地未分明。有时埏埴作狡狯,倏忽善幻非常情。不见晋人一旦遂为雌,人事反覆绝难知。牛哀已尔成异类,蝉蚹齐后何论为?丈夫作计无自喜,早晚会随风云起。但尔藏头向闺里,世间不复几男子。[7](P480)
王、刘二诗皆以山西男子化女事件作为感慨世事变幻、难以测度的缘起。“雌伏雄飞”典故的引入为“丈夫”、“男子”成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作了铺垫,也暗示出诗人“万事反复”、“人事反覆”的感慨背后,其实是对道德沦丧之社会现实的深重忧虑。作为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王、刘二人一方面对社会现实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一方面其措辞也相对含蓄、谨慎,甚至有些晦涩。相比之下,一生以布衣文人自傲的徐应雷则显得意气飞扬、锋芒毕露:
山西丈夫化女子,此事平常何足奇。仪衍从来是妾妇,须眉空自称男儿。司马仲达太畏蜀,奸雄甘受巾帼辱。丈夫意气不慷慨,任尔雄飞是雌伏。请看风俗太委靡,天下何人不女子。[8](P180)
此诗意义显豁,不留余地,显系激愤之词。
在这些诗中,“男变女”被直接赋予了道德含义,性别变化成为道德沦丧的隐喻。嘉靖朝是明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世宗皇帝沉迷道教,严嵩父子弄权乱政,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王世贞、刘凤、徐应雷三人的诗歌皆作于隆庆中至万历前期,他们借“李良雨事件”大发议论,锋芒所指正是嘉靖以后社会风气的衰颓。
经过万历朝的荒殆和天启朝的珰祸,帝国的腐败愈发不可收拾。愤激的士人们重新发现了李良雨的故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私史《皇明续记》与通俗小说集《型世言》第三十七回。卜大有《皇明续纪》云:
学术界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关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因素;二是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和价值链升级的方向和路径的探讨;三是关于制造业发展升级的指标体系的构建。
(隆庆二年)五月,陕西民李良雨忽变为妇人,与同贾者苟合为夫妇。其弟良云以事上所司,奏闻。*见[明]卜大有《皇明续纪》,万历刻本,北大图书馆藏。
这则记载通过沈国元《皇明从信录》,间接地影响了陆人龙白话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写作。相比原始叙事,事件发生地由山西变成了陕西,李良雨由弟弟变成了哥哥、佣工变成了“贾者”。这些变化均被《型世言》所承袭。
《型世言》出版于崇祯五年(1632)前后,陆人龙编著,陆云龙评点。此书是布衣文人所写的一部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品。作者敏锐地把捉到了“李良雨事件”所蕴涵的批判性,将其改写重述,赋予了其新的生命。二陆非常鲜明地将性别直接与道德等同:“人若能持正性,冠笄中有丈夫;人若还无贞志,衣冠中多女子。”[9]所谓“正性”、“贞志”,完全代替了生理结构上的性别区分,成为性别的唯一标志。作为道德隐喻的性别,是对王世贞等人诗歌之修辞方式的延续,并非二陆的创新,但二陆选择性别问题来做文章,实际上有着非常明确的现实指向。入话云:
我朝自这干阉奴王振、汪直、刘瑾与冯保,不雄不雌的,在那边乱政,因有这小人磕头掇脚,搽脂画粉,去奉承着他。昔人道的,举朝皆妾妇也。[9]
宦官专权从正统朝开始,一直是明帝国的痼疾,从王振到魏忠贤,愈演愈烈。二陆生于明末,对天启朝的阉党乱政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他们选择了李良雨之性别变乱作为宦官之身体阉割的隐喻。回评曰:“一雌奸乘政,群雌伏附之,阴妖遍天下矣!”二陆措词激烈,矛头鲜明,体现了布衣文人激进的愤世情怀。开篇诗“莫嗟人异化,寓内尽模糊”的感叹,更超越了性别变乱的范畴,把目光投向了整个王朝秩序的崩塌。
我们不清楚于慎行第一次听说“李良雨事件”是在何时,或许是隆庆三年在翰林院编修任上,或许是万历初年参与编修《穆宗实录》的过程中。但不管怎样,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将其写入了《谷山笔麈》,还在《谷城山馆诗集》中留下了一首吟咏此事的五言歌行。《谷山笔麈》是于慎行晚年所作的历史笔记,叙事比较严肃;而《晋阳男子行》*见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一诗则透露出另外一种趣味。诗云:
太原有男子,壮烈世所无。身长九尺余,白皙好眉须。自负良家子,募作材官徒。腰中辘轳剑,横击当路衢。并州恶少年,见之伏且趋。
《谷山笔麈》中的记载说明,于慎行显然清楚李良雨的佣工身份,但是在本诗开篇,他偏偏将其塑造成一位横击路衢、威震并州的壮烈男子。这样一个具有强烈阳刚气概的英雄形象的出现,几乎否定了任何性别变化的可能,然而,变化偏偏出现了:
一朝揽青镜,侘傺空堂隅。三日不出户,忽然见彼姝。绰绰夫容颜,盈盈玉雪肤。娥眉娟且长,高髻堕马梳。脱我金锁甲,系我绣罗襦。挂我白貂帽,珥我明月珠。
诗人用乐府诗的笔法,勾勒出了一个美人的诞生。“脱我”、“系我”、“挂我”、“珥我”的句法,显然是性别变化主题的经典文本——《木兰诗》的投影。《木兰诗》是《晋阳男子行》对话、互文、戏仿的对象。在《木兰诗》中,木兰由女变男、由男变女的两个过程,都是通过装扮实现的,生理结构并未发生任何变化。而在《晋阳男子行》中,我们同样找不到主人公生理结构发生变化的任何证据。诗人在此并未直接交待性别变化的原因,只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揽镜自照的忧郁形象。结果,英雄闭门三日以后,忽然变成了美人。从英雄到美人的变化,仅仅是通过妆扮实现的,而变化的原因,很可能只是心理上的:
委心怀燕婉,不惜健儿躯。
性别认同的错位,是英雄“化为”美人的真正原因。虽然不能在事实上改变性别,但是“系我绣罗襦”、“珥我明月珠”,也可以略慰性别认同错位所导致的惆怅了。
昔为云中鹄,今为水上凫。昔者一何厉,常关十石弧。今者何柔曼,巧笑倾城都。仰视浮云驰,变化不须臾。茫茫窥元运,玄黄无乃渝。世人但云好,不必称丈夫。
其实,真正让人感慨变化无常、元运难测的并不是今昔的巨大反差,而是人之内心世界的复杂微妙。《晋阳男子行》是于慎行对《木兰诗》的戏仿之作,是对“李良雨事件”之历史面貌的解构和重塑。即使我们把“委心怀燕婉,不惜健儿躯”解释为道德批判的隐喻,这种批判仍然是隐藏在戏仿的叙述之中的,相对同时代的王世贞等人来说,要含蓄很多。于慎行的创作独立于主流书写之外,体现了当代题材之文学化过程中的另一面相:游戏情怀。
五、被管制的性别
至此,本文已经分别考察了官史、私史、笔记、诗歌、白话小说诸文体对“李良雨事件”的书写,我们发现,由于时代、文体以及作者身份、趣味的不同,对此事件的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实际上,即使在同一篇作品中,出于某些原因,也可能并存着相异的思想趣味。再回过头来阅读《型世言》第三十七回,我们发现,本篇的现实批判主要集中在小引、回评、开篇诗与入话;整个正文部分,除了结尾以及中间的极少数细节,基本与现实批判无关。这种现象根源于作者之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作为传统士人精神的信奉者,作者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和忧患意识,反映在作品中,便是鲜明的现实批判指向;然而作为以白话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为职业的布衣文人,作者又具有异于正统文人的民间趣味和下层视角,这使得小说在无意中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和道德批判,转而在传统社会关系中思考这一性别变乱事件所反映出的伦理问题。
如果说《漫笔》是官方视角下对“李良雨事件”之记录的话,那么《型世言》便是出自民间视角的对此事件的想象性重构。我们可以将故事分成四个层次:(一)李良雨是如何由男变女的;(二)李良雨是如何接受自己的性别变化的;(三)社会对李良雨的性别变化的反应;(四)国家对李良雨的性别变化的反应。
陆人龙承袭了《漫笔》的叙述,将疾病作为李良雨变性的原因,但是却把“小肠痛”替换为“广疮”,也即梅毒。此种安排在增加情节的戏剧性之外,还有两方面用处。首先,梅毒是明代中晚期的“时代病”,很多晚明文人都不能幸免。本篇小说本来就是对当代题材的再创作,又增入梅毒这种“时代病”作为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使全篇呈现出更强的时代色彩。另外,梅毒的引入使李良雨在变性事件中不再是无辜的。正是因为他本人经不住诱惑,于妓家歇宿,方才染上此病。
李良雨先是“周身发起寒热来,小肚下连着腿起上似馒头两个大毒”,“不上半月,只见遍身发瘰,起上一身广疮”。又由于治疗不当,“作了蛀梗,一节节儿烂将下去,……不上几日,不惟蛀梗,连阴囊都蛀下……那根头还烂不住,直烂下去”。在原始叙事当中,李良雨变性仅仅是由于疾病,并无神秘力量的参与;而《型世言》却在描写其感染梅毒、下身溃烂之后,插入梦游阴司的情节。原来,李良雨本应投胎为女,却贿嘱阴间书吏,将女成男。如今被阴司发现,判其“仍为女身,与吕达为妻”。自然,下身虽然溃烂,并无溃成女阴之理。梦游阴司情节的插入,为小说引入民间信仰背景,按照民众的习惯思维解决了这一问题,使情节的发展更加合理。李良雨醒来以后,“暗自去摸自己的,宛然已是一个女身”,其身体上的性别变化至此全部完成。
下面的问题是心理上的性别变化是如何进行的。李良雨心理性别的变化始于阴司之梦。在民间信仰中,阴司是掌管死后世界的权力机关;从运作方式看,阴司又是现实世界中的国家权力在死后世界的投影。出于对宗教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双重敬畏,李良雨无条件地接受了阴司对自己的判决,为在现实生活中接受自己的性别变化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李良雨心理性别的变化是在与吕达的关系中一步步实现的。
首先是“羞惭”。在《漫笔》中,李良雨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佣工,即使变成女人,也不会有多少姿色。《型世言》却将李良雨设定成一个二十出头、“媚脸明眸”的“俊逸郎君”,身体变化完成之后,“髭须都没,唇红齿白,竟是个好女子一般”。这时,面对吕达,李良雨生起强烈的羞惭之心,开始与之保持身体上的距离:“当时吕达常来替他敷药,这时他道好了,再不与他看。”
然而,李良雨的羞惭引起了吕达的疑心:“终不然一烂,仔么烂做个女人不成?果有此事,倒是天付姻缘。”一日,吕达将李良雨灌醉,“轻轻将手去扪,果是一个女人”,便要强行与他发生关系。在李良雨心理性别的变化过程中,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最初,他还坚称二人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今日虽然转了女身,怎教我羞搭搭做这样事”,吕达拒不歇手。他开始一点点妥协:“就是你要与我做夫妻,须要拜了花烛,怎这造次?”吕达不为所动。万般无奈之下,李良雨终于承认了现实,与吕达做了“暗里夫妻”。在身体上接受吕达,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心理上接受了自己的新性别。
既然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身份,改换女装便理所当然。李良雨的换装仍然与吕达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李良雨自己来说,他能独立做到的似乎只是放弃自己的男性装束,最终的换装仍然是出于男人的要求。吕达为他准备了女装和脂粉,说:“男是男扮,女是女扮。”李良雨顺从地改换了发型,开始化妆和缠足,并且公开当起了家里的女主人,承担起女性的社会责任。至此,李良雨的自我性别认同才彻底完成。
自我性别认同完成以后,李良雨所要面对的就是家族和国家的干预。对于旁人来说,李良雨的变性事件不过是一件与己无关的“奇闻”,但是对当事人的家族来说,此事不但关乎感情、伦理,而且直接关乎经济利益。此处,《型世言》对原始叙事进行了一些巧妙改编。首先,在原始叙事中,李良雨在变性之前已因贫出妻,所以变性发生时,二人没有感情上的牵涉;在《型世言》中,二人感情深厚,夫妻和睦,矛盾变得更为复杂。其次,在原始叙事中,李良雨兄李良云派妻子探得李良雨变性属实,便将此事作为怪异通报官府。也就是说,李良云一开始就接受了李良雨变性的事实。《型世言》中,李良云和李良雨的妻子韩氏不但对李良雨的变性拒不承认,而且怀疑是吕达谋财害命后编出的故事,最终将二人告上公堂。在亲情之外,对经济损失的担心是李良云叔嫂申请国家权力干预此事的主要原因。
政府为什么会对性别变化的事件进行干涉呢?李良云在公堂上的一句话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小的哥子良雨上册是个壮丁,去时邻里都见是个男子,怎把个妇人抵塞?”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命天下郡县编制赋役黄册。黄册详载各户的人丁与产业结合状况,以此定户等,以户等征派徭役。上册人丁之数目、性别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赋役征收。因此,一旦出现“男变女”事件,政府必须对其加以检验,避免其成为逃避赋役的手段。
“李良雨事件”为我们揭示了晚明时期笼罩于民众身体上的权力关系网络。在整个故事中,李良雨始终对自己的身体和性别无能为力。影响他的第一种力量是对称于阴阳两界的阴间政府和阳世政府——我们既可以将它们看作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平行,也可以将它们作为国家权力在两个世界的双重投影。影响他的第二种力量是吕达所象征的男性权力——推动着他的性别变化的一步步实现。影响他的第三种力量是他的弟弟李良云代表的家族权力——出于对经济损失的担忧将他告上公堂。
最后再谈一下王圻《稗史汇编》和褚人获《坚瓠集》中的李良雨故事。这两则故事虽然用文言记载,但其旨趣却与《玉芝堂谈荟》一类的灾异话语迥异,颇富通俗文学的想象力和娱乐性。《稗史汇编》卷一百七十二“男化女”条云:
洛中二行贾,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亟为医治,幸不死。旬馀而化为女。事上巡抚,具奏于朝。适二贾皆未婚,奉旨配为夫妇。此万历丙戌年事也。[8](P773)
《稗史汇编》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从表面上看,此条故事的核心是友谊,由男化女似乎是上天成全的对朋友的报偿。少者虽化为女,二人却未苟合,而是待巡抚具奏于朝之后奉旨成婚,满足了民众的道德想象和荣誉期待。但是,从深层上说,此条故事更像是对一个同性恋事件的委婉叙述。褚人获《坚瓠集·庚集》卷一“丈夫化为女子”条云:
隆庆二年,山西李良甫侨寓京师。元宵夜看灯,夜静,见一女子靓妆而来,侍儿提灯前导。良甫就戏之。偕至寓留宿,化为白鸽飞去。良甫腹痛,至四月中,肾囊退缩,化为妇人。[10](P180)
至此,本文梳理了百年间关于“李良雨事件”的多种书写。我们看到,关于此事的叙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式。王世贞、刘凤、徐应雷等人的诗歌秉承灾异话语的正统观念,从现实关怀出发,将性别变乱当作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的隐喻,构成了“李良雨事件”之书写历史的主流。《型世言》、《稗史汇编》、《坚瓠集》则从民众的趣味出发,对此事加以生活化和娱乐化的想象和改编,构成了对主流叙事的颠覆力量。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些士人热衷于从理性上对此事本身加以思考,表现了传统社会中蕴含的格物精神。如果将“李良雨事件”定性为灾异,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它就是一个意义确定的符号,以此为出发点的文学创作即使由于时代和作者的不同而呈现差异,但其基本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同一的、封闭的、明确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单调的。通俗文学将此事从封闭的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入广阔的生活世界中展开想象,超越了单一的意义关联,使之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面貌,也为我们开掘了进入当时的观念史、生活史的一个微观视角。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型世言》、《晋阳男子行》之类具有多重意义的文本——它们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本身便是观念史和叙述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黄彰健.穆宗实录.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明]于慎行.谷山笔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明]王同轨.耳谈类增[M].续修四库全书第1268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8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5.
[8][明]王圻. 稗史汇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2册[C]. 济南:齐鲁书社,1995.
[9][明]陆人龙编.型世言[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清]褚人获.坚瓠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26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I106
A
1671-7511(2011)05-0060-07
2010-01-05
李萌昀,男,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林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