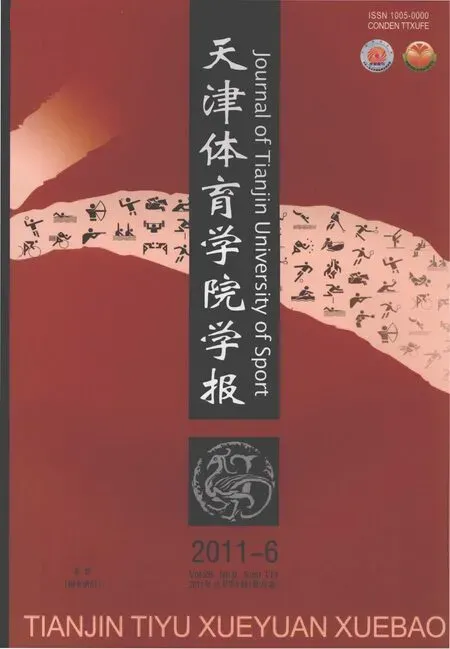论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特别述及国际体育仲裁院之规则与实践
2011-12-07张春良
张春良
●专题研究Special Lecture
论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
——特别述及国际体育仲裁院之规则与实践
张春良1,2
国际体育仲裁协议是体育仲裁机制的宪章,赋予其自治属性可据之免除司法机关的不当牵制而最大限度维护体育仲裁协议之有效性。根据国际体育仲裁规则与实践,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表现为管辖权自治、法律适用自治和地位自治。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国际体育世界的“最高法庭”,以其权威实践诠释了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特征,实现了行业自治与接近正义精神的两全。
国际;体育仲裁;仲裁协议;自治性;仲裁院
国际体育仲裁协议是国际体育法律关系当事人于纠纷发生前或纠纷发生后,就与该体育性纠纷相关的争议提交某一常设或临时仲裁机构予以裁决之书面协议[1]。因应国际仲裁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国际体育仲裁协议逐渐展现出自治的特性,并具体表现为如下三方面,即管辖权自治、法律适用自治和地位自治。管辖权自治涉及的是仲裁协议效力发生歧异时,仲裁庭能否自行裁断其有效性;法律适用自治涉及的是仲裁庭或者法院在裁断仲裁协议效力时是否依据独立的规则,使其与调整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的法律规范区别开来;地位自治探讨的是仲裁协议在性质上与其他合同条款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效力状态。必须指出,国际体育仲裁协议是整个国际体育仲裁机制得以有效运转的基点,其效力直接影响着体育仲裁管辖的正当性、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及裁决的可承认或执行性。赋予体育仲裁协议以相对独立的自治性,可有效降低乃至避免因将体育仲裁协议与其他问题相关联而易被连带否定之风险,进而可依“有利于有效”之仲裁理念最大限度地维护体育仲裁协议的效力。对于国际体育仲裁实践而言,诸如国际体育仲裁院等仲裁机构可据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免除世俗司法机关的不当牵制,便利体育争议之合体育规律地专业化裁决,兼顾和两全了行业自治与接近正义之精神。
1 管辖权自治
仲裁协议首先是有关管辖权的选择合同,它通常是体育争议当事人选择仲裁机构、排除法院干涉的协议,此即谓仲裁协议的抗辩碍诉力。但体育仲裁庭取得管辖权的前提条件是该体育仲裁协议为有效协议,由此在逻辑上必须首先判断该体育仲裁协议是否有效,只有得出肯定判断后,才能组建体育仲裁庭展开仲裁程序。而仲裁协议效力的判断在各国立法和实践中主要由国家法院和仲裁庭承担。在仲裁庭裁断仲裁协议效力的情况下存在一个循环论证,即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是仲裁庭组建的根据,而仲裁协议有效性之判断却依赖仲裁庭这一主体。于此处可见国际体育仲裁庭采取的是推定有效原则,即首先假定体育仲裁协议有效,继而在这一假定基础之上再反证其效力。
2 法律适用自治
所谓仲裁协议法律适用自治,是指判断仲裁协议存在与效力的法律规则即准据法之确定和选择自成一体,不依附或受制于调整案件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的法律适用规则。由于国际体育仲裁协议涉及的体育争议具有跨国性,因而存在适用何国法律予以裁决的问题,即法律选择与适用的问题;又由于传统国际仲裁协议通常都由调整案件实体问题或程序问题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从而使国际体育仲裁协议在法律适用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依赖性。但国际体育仲裁协议毕竟是不同于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的相对独立的问题,其个性特征要求发展出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由此导致国际体育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自治倾向。
2.1 本因:仲裁协议的独特性质
仲裁协议在性质上不同于仲裁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其性质的独特性决定了它应该具有独立的准据法,这是仲裁协议法律适用自治的本因。按照国际私法的精神,调整包括体育关系在内的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是以该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当萨维尼提出法律关系本座说完成了对巴托鲁斯以降的法则区别说之革命后,以法律关系性质而非法则本身性质决定法律适用规则的方法论就成为迄今为止最主流的调整方法。因此,对仲裁协议性质的不同界定将导致不同的法律规则被适用。学界对体育仲裁协议性质的界定主要有实体法上契约说、程序法上契约说、混合说以及独立类型契约说4种观点。笔者以为,体育仲裁协议首先是一个契约,其直接效果是程序性的,并通过程序选择产生间接的实体效果。正如某些学者所精辟论断,将仲裁协议并归合同并无不妥,但其也与后者存在某些质的区别,从而表现出程序性特征。这一属性决定了涉外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是一个兼具实体性质和程序性质的问题,既会受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方法及其规则的影响,也会受国际私法中有关程序问题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制约,形成与其二元特性相对应的规则体系。在这些规则中,‘场所支配行为’原则即行为地法与‘意思自治’原则即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妥协与兼容得以凸现。在一定意义上讲,涉外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就是国家的属地主权与私法自治斗争与妥协的结果。”[1]
鉴于体育仲裁协议性质与体育案件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的性质之间的客观差异,其法律适用自治化也是当然之理。体育仲裁的程序性问题与实体性问题在国际层面并不一致认识,较为接受的共识是,诸如仲裁庭的组建与仲裁员的撤换,仲裁裁决的作出与对裁决的异议处理、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通常都作为程序性问题;而对于除外之问题,特别是体育争议事实之认定,包括对有关体育章程或规则如《奥林匹克章程》或反兴奋剂条例的解释就被识别为实体性问题[6]。CAS仲裁之实体问题即体育争议就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是“纯粹的体育争议,如选拔与资格问题,包括反兴奋剂在内的纪律处罚问题”;二是“商事争议”[7]。在二者之外,体育仲裁协议被单独对待,它既不属于单纯的实体问题,也不属于单纯的程序问题,这可主要从两方面得以直观证明:第一,在内容构成上,体育仲裁协议兼具实体与程序事项。如《奥林匹克章程》第74条作为一个CAS仲裁条款就涵纳了实体与程序问题:其所涉实体问题是关联于或产生于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所有争议;其所涉程序问题则以概括援引的方式转致给CAS仲裁法典与奥运会仲裁规则,后两者的内容构成奥运会仲裁的程序框架。第二,在功能效应,体育仲裁协议兼具实体与程序效果。一方面,体育仲裁协议的生效运行首先激活了体育仲裁机构的管辖、决定着体育仲裁庭的组建与补救,预设了仲裁庭审的实施,最终导致仲裁裁决的作出;不仅如此,有效的体育仲裁协议还直接支持着仲裁裁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8]。此类效果即为体育仲裁协议的程序效力。另一方面,体育仲裁协议还在实体方面限定着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即体育争议,决定着案件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并据此决定着案件的实体效果。此种性质上的独特性是决定其法律适用个性化发展的内在根据。
2.2 助因:仲裁自治精神的逻辑延伸
意思自治是体育仲裁的基本精神。作为仲裁自治精神进一步延伸的逻辑结果,仲裁协议法律适用逐步从属地因素中解放出来,这是仲裁协议法律适用自治化的助因。无论仲裁协议作为实体契约还是程序契约,在萨维尼本座学说的规定下,仲裁地作为关键连接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作为一种标竿将仲裁地法与仲裁协议关联起来,另一方面则束缚了仲裁协议在法律适用上的弹性。仲裁自治精神的强力发展首先致力于对物理空间的突破,试图在世俗法律体制的空间范围内拟制出一片仲裁净土。在这一法律适用思潮的影响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自治化意识得以培育并生长,它通过仲裁法律适用“非当地化”[2],即摆脱仲裁地法律规范的束缚而完成自身的第一次自治过程。在仲裁法律适用的非当地化,尤其是程序法律适用的非当地化进程中,仲裁协议与其他仲裁问题一起开始抵抗地域重力的吸引,“不再受制于特定的法律,并因此而漂浮。”[9]
CAS仲裁法典就明确将其仲裁地确定在瑞士洛桑,使其法律适用脱开了事实仲裁地的法律干扰,表现出独立自治的特性。此种独特的仲裁地安排对于体育仲裁、尤其是对于奥运会仲裁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在法律效果上需要稳定的仲裁地,因为稳定的仲裁地将影响案件的法律适用、裁决及其国籍,其被承认和执行的程度[10];另一方面,在实践操作上则需要随赛场而变的仲裁地,“奥林匹克赛场仲裁安排证明了在复杂、多方、涉及多法律的争议中进行仲裁的力量与灵活性,很明显,这是由富有责任且业务精湛的专业人士所设计的。”[11]在稳定性与浮动性这两个矛盾的要求之间,CAS仲裁制度智慧地采取了名义仲裁地与事实仲裁地的分离做法:将名义仲裁地确定在瑞士洛桑,并将事实仲裁地确定在各届赛场。参赛人员以其参赛行为及所签署的参赛表格、协议等方式与国际奥委会就仲裁地之选定进行意思自治,并据此将体育仲裁中所适用的法律从仲裁地的事实进行地解放出来。
2.3 技术因:“分割论”思潮之兴起
法律适用精细化的发展及作为其产物的分割论方法的兴起[12],促使体育仲裁协议从仲裁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中游离出来,为仲裁协议的单独法律适用奠定了基础,这是其法律适用自治化的技术原因。借助分割论的法律适用方法,人们对涉外法律关系包括体育争议的性质理解得越来越深刻,原来被一体对待的实体、程序问题开始不断地离析出来,即便是同一涉外法律关系也依其性质被分解为若干个不同的方面。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为法律适用规则的独立化和自治化制造了空间,法律适用开始变得细腻和精准。在此背景下,体育仲裁协议也开始从原来对体育仲裁程序问题的依附中释放出来具备独立的身份,并终致于导向自治之途。按照分割论的逻辑,国际体育仲裁中的问题一分为三:国际体育争议实体问题,国际体育争议的程序问题,国际体育仲裁协议。每方面都有独立的法律适用规则,而且在一些仲裁实践中,仲裁协议尚可继续划分为体育仲裁协议当事人的能力问题、仲裁协议内容问题(诸如仲裁主题的可仲裁性)以及仲裁协议的形式问题。分割论方法的贯彻最大程度地将体育仲裁协议独立出来,成为独立主题被单独对待,CAS诸多判例证明了这一点,此即集中表现为法律适用的非当地化趋势。
2.4 集中表现:非当地化趋势
在国际体育仲裁中,对于仲裁协议法律适用似乎仍然沿袭传统的“场所支配行为”原则,即由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作为调整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法律规范。尽管属地因素仍然在体育仲裁协议准据法的选择上占据了重要作用,但其自治化趋势仍然十分强劲,这可从体育仲裁协议三方面的法律适用上得出这一结论。
2.4.1 能力问题法律适用的脱法律化在当事人缔结体育仲裁协议的能力或者资格的法律适用上,无论是CAS仲裁庭还是有关司法机关几乎都明示或者默示地不采取任何法律规则进行调整,而直接推定其有效。奥运会赛事参与者包括很多未成年人,尤其是诸如低龄化的体操之类的赛事,其参赛人员未成年化现象非常突出,如果按照法律选择规则或者实体规则,依当事人属人法或者行为地法等来判断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即便他们签署了CAS仲裁协议,也会因为不具备行为能力而被确认为无效体育仲裁协议。但迄今为止CAS和相关司法机构颁布的资料显示,尚无一例因参赛人员属未成年人而宣布其缔结的仲裁协议无效。更普遍、也更广为接受的做法是,“如果不考虑未成年运动员签署的仲裁协议的问题,我们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类仲裁条款都应当是合法有效的。”[13]简言之,在体育协议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仲裁庭或司法机关几乎奉行的是“无规则的规则”,法律适用自治化达到了“脱法律化”的状态,此为仲裁协议自治化表现最极致的方面。
2.4.2 形式问题法律适用的有效推定在体育仲裁协议形式的法律适用方面,体育仲裁庭与法院表现出不同的态度。CAS仲裁庭在解释体育仲裁协议的形式时总是倾向于依据其仲裁规则而非仲裁地等客观连接点指向的法律作出有效认定,只要有一个不无效的理由,该体育仲裁协议的效力即告有效,其判断准则可归结为“有利于有效”。而司法机关在确认形式有效性时,则倾向于按照仲裁地的法律进行判断,在R vs.国际篮联的案件中,R首先向CAS申请仲裁国际篮联对其作出的处罚性决定。在CAS维持原处罚决定后,R继续向对CAS仲裁庭之裁决拥有适格管辖权的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CAS仲裁裁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仲裁协议形式有效性作出解释。它根据仲裁地法即《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78条之规定,指出仲裁协议可以是书面的、电报或者传真等能够予以确认的形式,这并不要求在当事人签署的契约性文件中一定包括仲裁条款,对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适用瑞士法[14]。事实上,国际仲裁领域中,仲裁机构采取仲裁规则、而司法机关采取本国冲突规范选择准据法的二元格局一直存在,不同的判断主体及其所采取的标准不同,这为二者的冲突埋下伏笔。尽管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倾向于以仲裁地法判断体育仲裁协议的形式有效性,但从其司法精神来看仍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支持自治”动机,在理解和解释相关问题时着眼于国际体育精神予以培育和维护。
在很多案例中,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虽然以仲裁地法即瑞士法判断仲裁协议的形式有效性,但瑞士法院明显地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按照自治精神来最大限度地容忍体育仲裁协议形式的独特性。在上述R vs.国际篮联的案件中,法院进一步根据瑞士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到该争议的具体情况后认为:第一,当事人对某全球性体育组织的章程性文件的同意可以解释为接受了该文件中所含有的CAS仲裁条款;第二,一般地讲,可以推定的是,如果某当事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一个全球性组织的章程文件,则表明他熟悉其中包括的仲裁条款并且同意该仲裁条款的内容;第三,还可以推定的是,一个运动员如果申请参加某体育协会举办的一般比赛或者获得比赛的许可,他应当被视为了解该体育协会的规范内容,并愿意接受这些规范的约束[14]。通过上述判决推理,法院将其国际私法典中第178条关于仲裁协议形式的要求大胆而巧妙地扩展开来,用以引证和合法化CAS体育仲裁协议的形式。
在与此案类似的另一个案例中,原告签署了一份格式化协议,表明其应当遵守国际马术协会(Federation Equestre Internationale,下称为FEI)的有关规则,在FEI有关规则之中就含有CAS仲裁条款,但是该格式化协议并没有具体说明其中的CAS仲裁条款的要求。仲裁地所属法院需要解释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协议是否应当认为是概括地援引了CAS仲裁条款,该概括援引是否符合《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78条要求的形式。受理案件的瓦特州法院认为,仲裁条款的形式有效性问题必须接受仲裁地法即《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78条的约束,并应根据当代大多数国家的仲裁实践,在仲裁条款的形式问题上,不需要过于严格的限制。法院据此依第178条第1款之规定,仲裁协议是以书面、电报、电传、传真或者其他能够以文字证明该仲裁协议的通讯方式订立的,即在形式上有效;根据《司法组织法》第63条第2款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可认定该仲裁条款形式具有有效性[13]。
2.4.3 实体问题法律适用的法理化在仲裁协议的内容方面,其法律适用也开始摆脱属地因素的控制,转而适用一般性法理。体育仲裁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其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其可仲裁性问题。由于专业性或竞技性体育仲裁主题事项通常是针对体育组织作出的处罚性决定,具有行政化色彩,其可否仲裁尤其决定于准据法的择定。CAS仲裁庭和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等司法机关均通过判例肯定了可仲裁性问题法律适用的自治性。
在CAS仲裁的R案中,涉及对吸食违禁物质之处罚决定的可仲裁性问题。仲裁庭明确裁定:“在作出裁决过程中,本庭认为大麻的使用范围应当受到限制,也认为体育管理机构有权将服用大麻的运动员驱逐出赛场。但是如果体育管理机构希望增加国家机关立法确定的制裁措施,必须采取明确的方式。然而体育管理机构并未如此行为。本庭裁定,从伦理和医学观点来看,服用违禁物质是一个社会关注的严重问题。然而CAS并不是一个刑事法院,既不能颁发也不能适用刑法。本庭必须在体育法范围内作出裁决,且不能创造从未出现过的限制或制裁措施。”[15]即按照CAS仲裁庭的意见,该仲裁协议的主题内容是否合法取决于体育法的判断,而此处的体育法更多意义上是指国际体育一般法律原则。
在Gundel vs.FEI案件中,上诉人就指出,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90条第2款的规定,鉴于争议事项具有刑事处罚性,CAS无权处理该类争议。受案法院则认为:“通过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契约来规定某一种处罚措施的做法,是能够为法律所接受的。”换言之,对于该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依赖于当事人间的契约,从而在法律适用上表现为高度的意思自治[13],不受确定的法律规则之限制。
此外,按照CAS体育仲裁法律适用的一般精神看,要求摆脱地方属性构建全球一体化争议解决机制和全球化体育法制精神的趋势日益明显[16]:实体问题通过适用一般法律原则而导致全球化、程序问题通过适用仲裁地瑞士法而实现非当地化。这一趋势及其代表的法律适用精神所形成的仲裁自治化信仰,也必然延伸影响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规则架构和发展态势。因此,可以合理推断,随着体育法制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包括仲裁协议在内的体育仲裁法律适用必然超越任何地域性法律之限制,在全球层面形成自治的格局。
3 地位自治
体育仲裁协议地位自治,是就仲裁协议本身与作为仲裁协议载体的体育合同或体育协会章程中其他合同或章程条款的关系而言,它有别于体育合同或协会章程其他条款而自成体系,此即为体育仲裁条款的独立性问题。国际体育法律关系当事人通常都是在相关合同文本中列示仲裁条款,而不是签订单独的体育仲裁协议。这一条款与该体育合同中的其他条款之关系如何,一直都是国际体育仲裁理论和实务界所关注的问题,究其实质,它探讨的是合同其他条款之存在及其效力是否会影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但凡坚持仲裁条款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不因其他条款效力状态之拘束而保持超然独立之地位者,即赋予仲裁协议地位自治的属性。应当指出,体育仲裁协议本身并非当事人缔约之目的,它只是当事人之间预先采取的一种救济性制度安排,当事人甚至“希望自己永远不用援引这个值得怀疑的条款”[17],而让该条款永久性地成为一种摆设。如学者所言:“该条款订立于纠纷发生之前,存在于有关合同之中。同时,它又具有与该合同的其他条款不同的性质和效力,其他条款的无效,并不必然引起仲裁条款随之无效。”[18]仲裁协议,尤其是仲裁条款与当事人签订的其他条款存在的此种关联性是否足以将二者的命运关联为一体,其他条款因其存在或瑕疵而发生效力危机时是否足以影响仲裁协议,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关于体育仲裁协议地位的两种理论。
3.1 主从合同论
根据合同法通理,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合同分为不同的类别。主从合同的划分就是依据合同相互间的主从关系进行的。所谓主合同,指无需依赖其他合同即可独立存在的合同;所谓从合同则指不能独立存在,而尚须依附主合同的合同。合同的这种分类,其法律意义在于:从合同以主合同存在为前提;主合同消灭,从合同也将随之消灭[19]。持此论者认为,仲裁条款是含有该条款的主合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该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作为从合同当然也无效。英国曾流行这一理论。无论是主合同,还是作为从合同的仲裁条款,当对其最初存在或有效性产生争议时,以及对主合同最初缔结时有效,后因不法性导致无效而产生的争议,均主张由法院解决,而不能交由仲裁庭解决[20]。具体到CAS仲裁条款之存在形态而言,它在形式上并非单独存在,而多由体育组织的章程性规范予以援引。《奥林匹克章程》第74条即是此种表现形式。此类援引是将CAS仲裁条款列作为章程规范中的某一条款,竞技运动员在加入体育协会或者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并不会单独就该CAS条款进行签署,而是对包括该仲裁条款在内的全部条款进行签署或者整体接受。这就产生了CAS仲裁条款是否与其他条款区分开来单独处理其效力的问题。主从合同论的观点即认为,CAS仲裁条款是从属于此类章程的从合同,其他条款导致的章程性规范无效则CAS仲裁条款也将无效。
主从合同论的缺陷在于否认CAS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主张CAS仲裁条款因主合同的失效而失效,这显然违背了体育仲裁的价值取向,也与当代国际体育仲裁实践相背离。这种传统观点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批评。无论合同或章程性规范无效的原因如何,当事人将体育争议提交CAS仲裁的意愿是真实且一贯存在的;而且在仲裁过程中,一旦争议涉及到合同或章程规范无效的问题,根据传统观点,CAS仲裁条款的有效性便成为疑问,仲裁机构的管辖权也将受到挑战,但仲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管辖权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仲裁庭来说都是不合理的[21]。在某种意义上,CAS仲裁条款的有效运作正是以主合同的无效或不存在为前提的,此种“联锁”关系深刻揭示了CAS仲裁条款与其载体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主从关系,而带着平行且背反的对生关系[22]。展言之,体育仲裁协议效力的现实发挥必须以其所立足的合同、参赛报名表或章程中的其他条款出现问题为前提。以奥运会仲裁为例,国际奥委会与参赛国及参赛运动员之间的CAS仲裁条款主要是以《奥林匹克章程》中的第74条表现出来的,在该宪章其他条款所指向的事项发生争议,不论该争议是涉及其他条款的存在性问题,还是效力问题,它并不影响第74条CAS仲裁条款的存在性与效力,而应首先推定其存在且有效,再由CAS仲裁庭通过自裁管辖权的行使来判断其存在性与效力。此种做法即是在宪章74条与其他条款之间维持了一种区别对待的做法,在二者之间插入了一道防火墙以此隔开其他条款可能存在的瑕疵对74条产生的干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区分开74条与宪章其他条款的关系,如果真是要维持二者之间的此种隔绝关系,则该74条之设立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换言之,该74条更类似于一种具有免疫力的监护性条款,它在豁免于其他条款的消极干扰的前提下能够积极地发挥其功效以解决这些条款可能出现的危机。因此,在此意义上而言,宪章第74条与其他条款之关系就既不是主从关系,也不是毫无关系,而是平行且背反的对生关系。
3.2 自治论
仲裁协议的自治理论是建立在对传统观点的反思和尊重仲裁实务发展的需要之基础上的。国际体育仲裁参与者希望他们之间的国际体育纠纷按照他们事先预定的CAS仲裁程序予以消解,不管他们对于其他条款的合意是否足以构成有效的约定,至少当事人达成的CAS仲裁合意是真诚的。根据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仲裁协议的地位应当不同于其他条款,并与它们效力无涉,形式上的连带关系不能转化为效力上的连带性。仲裁协议自治论代表了当今国际体育仲裁发展的方向,“仲裁协议被认为是独立于包含它的合同的。这种仲裁条款的自主权或可分性是国际仲裁一个观念上的奠基石。”[22]事实上,赋予仲裁协议以独立的地位和自主的权利不仅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精神的体现,也是仲裁协议自我实现的需要,它还是仲裁效率价值得以发挥的根据,从而构成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石[23]。斯蒂芬·西魏博(Stephen Schwebel)在考察国际仲裁的立法和实践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24]:第一,这一理论是可靠的;第二,实际上,该原则得到了包括国际公法、国际仲裁及国内仲裁等方面的仲裁惯例、规则以及法院判例的明示和暗示的支持;第三,对该原则的学术上的支持是广泛且显著的。仲裁协议地位的自治赋予它以无因的属性,无因原则可以有效维护法律交往的方便性和安全性[25],基于这一原则,CAS仲裁条款一经成立生效便独立于基础合同之外,而无论基础合同之情况如何,它将仲裁条款自治理论提升到更远、更高的程度。在CAS业已仲裁的一些判例中表明,即便CAS仲裁条款所立足的基础文件不存在或未经签署的情况下,也不影响该仲裁条款的存在与效力,而可据之首先启动CAS仲裁程序,2002年由CAS仲裁庭所管辖并裁决的Bassani-Antivari一案就说明了CAS仲裁条款的此种自治地位。
在该案中,申请人是一位23岁的格林纳达(Grenada)国民,她自1998年即开始代表该国参加国际滑雪竞赛,且都是在格林纳达国际体育基金会(Grenada International Sports Foundation,简称为GISF)的赞助下参与比赛。在2001年8月,GISF向该国奥运协会(Grenada Olympic Association,简称为GOA)提交了申请人参加盐湖城冬奥会所需资料,但GOA并未将参赛报名表提交给冬奥会组委会,且在同年9月通知组委会该国将不参加此次竞赛。GOA在次年1月通告GISF,GOA无权禁止申请人参与比赛因为GISF在组织关系上并不隶属于GOA。申请人为解决参赛资格问题而从其朋友处得到了一份参赛报名表,填写完毕后直接提交给了盐湖城组委会。但当申请人于冬奥会开幕式赶赴参赛地点之日,国际奥委会通知并裁定她不能参赛,因为该参赛报名表未经GOA签署。申请人不服该裁定而向CAS奥运会特设分庭提起仲裁申请,CAS奥运会特设仲裁分庭主席指定了3名仲裁员组成合议制仲裁庭受理了案件[26]。
该案中CAS仲裁条款存在于其基础合同即参赛报名表之中,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范,参赛报名表必须要由参赛国的国家奥委会签署方为有效,因此,该案中的参赛报名表由于未得GOA之签署而并不产生法律效力。但这并不影响报名表中CAS仲裁条款的存在和有效性,正因为此CAS仲裁庭才得以成立。从传统主从合同论的立场看,只要作为基础合同的主合同即参赛报名表无效,其所载的、作为从合同的CAS仲裁条款也就当然无效。在CAS仲裁条款无效的情况下,CAS奥运会特设仲裁分处就不能受理案件,也不能组建仲裁庭进行仲裁。CAS仲裁分处的做法显然并没有采取此种立场,而是采取了CAS仲裁条款地位自治的观点,将该仲裁条款之存在及其效力与作为其存在基础的参赛报名表之存在与效力区分开来,区别对待,赋予CAS仲裁条款以自治性。这种实践使CAS仲裁条款与其他条款之间表现出一种无因性,即无彼此因果关联性。但如果强调仲裁协议的无因性则似乎走得过远。首先,它虽然强调了CAS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但却割裂了CAS仲裁条款与基础合同的联系,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即CAS仲裁条款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基础合同的运行发生了障碍。换言之,CAS仲裁条款之于基础合同并非“无因”,而是“生死攸关”的互异程序。此学说与主从合同论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都在强调某一方面的同时,漠视或牺牲了事物的另一面。其次,根据无因原则理论,“如原因行为有瑕疵,则在原因行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上,无因原则并不能产生取得人虽无有效的原因行为也能保留其所取得权利之后果。”[25]这句话放在CAS仲裁条款与基础合同关系中去理解,就是指基础合同若存在瑕疵,如不存在或者欺诈等,则CAS仲裁条款的当事人(同时也是基础合同当事人)不能依无因原则保持该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其得出的结果有悖于创造此论的初衷。因此,无因性在诸如合同的转让与承受,代位权的行使等方面可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但在基础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却有着致命的先天痼疾。为此,应当采取一种附条件的自治理论来定位和理解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地位。
4 结语
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立法与实践对该原则的千锤百炼使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再难受到挑战,迄今没有一例纠纷当事人或者司法机关质疑或者否定过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当然,这与体育仲裁协议的存在形式和特征密切相关。在商事仲裁领域中仲裁协议独立性问题相对突出,这是因为商事仲裁协议形式上的依附性,以及仲裁协议依附的基础合同经常面临无效、失效状态。而在国际体育仲裁领域,仲裁协议几乎都是载于各体育协会章程中的制度化格式条款,此类制度化格式条款所依附和针对的母体即体育协会章程等是不可能如同商事合同一样处于无效或者失效的状态,这一特征弱化了体育仲裁协议独立性的需要。弱化并不等于排除,相反,必须揭示并承认国际体育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地位,并且不仅在体育组织章程背景之中去考察并维护其中的仲裁条款之自治性,更具实践意义的是,应当在国际奥林匹克章程的背景之中去考察并维持其中的CAS仲裁条款之自治性。只有肯认CAS仲裁条款的自治性,才能最大程度地从各国的地域性司法管辖权之争夺中解放并巩固CAS的管辖权之适格性,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CAS仲裁机制排解纠纷、建构国际体育清明秩序之功效。在此意义上可认为,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治性是解放CAS生产力的前提和保障。
[1]刘想树.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W Laurence Craig,William W Park,Jan Paulsson.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rbitration[M].New York:Ocean Pub,Inc. /Dobbs Ferry,2000.
[3]Gabrielle Kaufmann-Kohler.A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s:Issues of fasttrack dispute resolution and sports law[M].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
[4]Matthieu Reeb.Digestof CASAwards II 1998-2000[C].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808-813.
[5]Richard McLaren.The CAS AD HOC Division at the Athens Olympic Games[J].Marquette Sports Law Review,2004(15):175.
[6]潘喜梅.日本体育仲裁运作模式对我国体育仲裁机制建设的借鉴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4):45-49.
[7]Ian SBlackshaw.Sport,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M].Hague:T.M.C. Asser Press,2009.
[8]石现明.略论申请撤销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的理由[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26(3):237-240.
[9]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M].Beijing:CITICPublishingHouse,2004.
[10]黄晖.国际体育解纷机制的复级化及其正当性——基于CAS仲裁体制之研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26(4):325-328.
[11]Gerry Tucker,Antonio Rigozzi,WangWenying,etal.Sports Arbitration for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Ian S Blackshaw,Bobert C R C//Siekmann,Janwillem Soek(eds.).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1984-2004).Hague:T.M.C.Asser Press,2006.
[12]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13]布莱克肖.体育纠纷的调解解决:国内与国际的视野[M].郭树理,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14]黄世席.奥林匹克赛事争议与仲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5]RobertCR Siekmann,Janwillem Soek.Arbitraland Disciplinary Rulesof InternationalSportsOrganisations[C].Hague:I.M.C.AsserPress,2001.
[16]James A RNafziger.Lex Sportivaand CAS[C]//Ian SBlackshaw,Bobert C R Siekmann,Janwillem Soek.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1984-2004).Hague:T.M.C.Asser Press,2006:409.
[17]Stephen AKaufman.Issuesin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J].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1995,Fall(13):527.
[18]黄世席.奥运会争议仲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9]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0]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1]赵威.国际仲裁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22]刘想树,张春良.关于仲裁条款独立性的两个问题[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1,16(6):69.
[23]刘想树.仲裁条款的独立性问题[J].现代法学,2002,24(3):32.
[24]Stephen Schwebel.The Severability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J].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1987(1):60.
[25]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76-178.
[26]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OWG Salt Lake City 2002)003,Bassani-Antivari/InternationalOlympic Committee(IOC),award of12 February,2002:585-587.
Autonomy of International Sport Arbitration Agreement:Specially on the Rulesand Practiceof ICAS
ZHANG Chunliang1,2
(1.School of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the charter of sports arbitrationmechanism;autonomy can be taken as the justified reason to avoid the improper interruptions from judicial bodies,and so that the validity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would bemaintained atmaximum.It includes autonomy of jurisdiction,autonomy of law application and autonomy of statu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rules and practices.As the Supreme Court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circles,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 displays the autonomy character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agreement through its classic cases,and the autonomy of sport circles and access to justice principle have been held completely.
international;sportarbitration;arbitration agreement;autonomy;CAS
G 80-05
A
1005-0000(2011)06-0510-06
2011-09-01;
2011-10-20;录用日期:2011-10-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C820161)
张春良(1976-),男,四川泸县人,博士,武汉大学在站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
1.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401120。
在体育仲裁庭裁断体育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即裁断自己管辖权基础的情况下,该种制度称作自裁管辖权,或“管辖权—管辖权”制度[2],该制度以逻辑圆环的形式维持了体育仲裁制度的自治性和独立性。设立自裁管辖权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司法机构对体育仲裁可能实施的不当否定,因为管辖权问题是关系到体育仲裁程序能否具体展开的前提性问题,如果体育仲裁庭的管辖权必须先决于司法机构,则仲裁程序尚未启动即可能面临司法机构的否定性评价,有损体育仲裁管辖权的独立性。
在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下称CAS)仲裁的许多案件中,当事人基于种种理由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质疑,并据此提出管辖权抗辩,但CAS仲裁庭均行使了自裁管辖权,在司法机构之外独立判断仲裁协议的有效性。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在CAS奥运会特设分庭仲裁的鲍曼案件中[3],被申请人国际田联(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s,下称IAAF)首先提出管辖权抗辩,因为IAAF的规章中并没有设立CAS仲裁条款以规定将体育争议提交CAS仲裁。因此,IAAF认为其内部仲裁裁决即为终局的、具有拘束力的裁决。CAS将其抗辩视作是对仲裁庭缺乏管辖权和基于既判案件而提出的答辩。仲裁庭认为,IAAF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应根据《奥林匹克章程》第74条之规定,就与奥运会相关的争议接受CAS的仲裁管辖。换言之,尽管IAAF章程之中没有CAS仲裁条款,但其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事实就使存在于《奥林匹克章程》中的CAS仲裁条款延伸拘束IAAF,因此CAS奥运会特设仲裁庭据之获得了管辖权。除了IAAF仍然反对外,其他仲裁当事人均以行动事实性地接受了CAS的管辖。
在涉及IAAF的另一个案件中,仲裁申请人梅林特是罗马尼亚运动员,她是当时女子链球的世界记录保持者。在她准备参加资格赛时,IAAF官员告知她,其尿检呈阳性,竞赛资格被剥夺。梅林特随即向CAS特设分庭提交仲裁,请求保留竞赛资格,参与第二天下午举行的决赛。该决赛要求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最迟在次日清晨参加资格赛。由于时间紧急,庭审在申请提出后数小时内举行。IAAF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但被仲裁庭以与鲍曼案一样的理由驳回。
在上述两案中,仲裁协议是否存在及其有效性由CAS自行管辖并裁决,这使仲裁庭具有很大的自主权。此种管辖权自治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使仲裁庭摆脱了对司法机关的依赖,也是CAS仲裁机制更为有效运转的制度保障。在R vs.FIBA、CAS案件[4],Sullivan vs.Raguz,以及Raguz vs.Sullivan等案件中[5],CAS仲裁庭都通过自裁管辖权的行使维持了自身管辖权的有效性,并审理和裁决了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