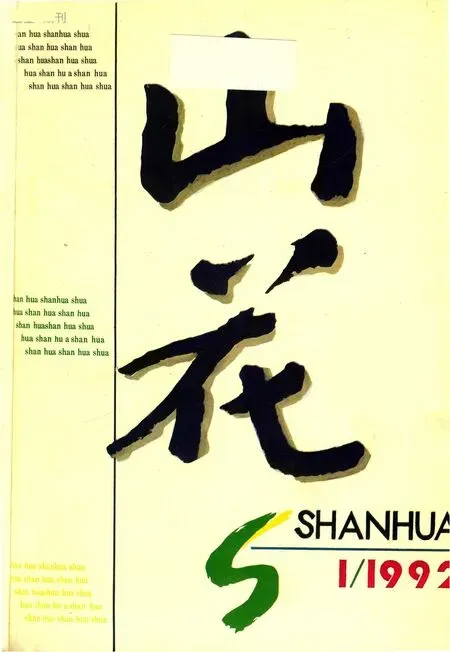东莞,东莞(三题)
2011-11-30祝成明
祝成明
东莞,东莞(三题)
祝成明
酒精中的东莞
酒精是一个外表清透、单纯、安静,内心叵测、狂热、冲动的名词。它既是友情的组成部分,也是友情的外延部分。我认为酒精是有生命的——它是液体的,易挥发,模仿了水的一切特征,有着自己的呼吸、体温和能量,带有很大的麻醉性、欺骗性和鼓动性,在不同人的杯具中,又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姿态和情致,把人引往前方未知的道路上,或上升为神仙,或堕落成魔鬼。酒精的醇香从远古的诗歌中飘来,时光这个酵母把它催化得古色古香,芬芳迷人。“酒史”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它是文学的美化剂,生活的润滑液,等待一代又一代人对它进行阅读和书写,它的光辉比火光耀眼,它的流淌比河流更有力量。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酒精就是这样一个词条。在东莞,我就深陷在酒精的怀抱中。2007年10月6日,我来到东莞,酒精的清香便开始弥漫,飘荡。于我而言,东莞其实很小,以酒杯为圆心,以友情为半径,东莞的面积其实只有一张圆桌子那么大。2007年岁末和2008年上半年,赵原,吾同树,黄吉文和我在一起做了饮者。傍晚时分,我们相约,在某一个饭店里开怀痛饮。我能记起每一个饭店的名字和位置(有些店已经关闭了)——川满人间、好日子、外婆楼、强记食街、湖南大碗菜、安天民饺子馆等;深夜,我们又转移到聚福市场的麻辣烫和烧烤档上,吃砂锅粥,继续纵酒放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沉迷于白酒的火辣和啤酒的清凉中。酒花荡漾,在酒杯里挤挤挨挨地盛开着,闪烁着,像一群淘气的孩子,一刻也没有停下它们的奔跑。黄色的啤酒开出的却是白色的啤酒花,一朵挨一朵,一层铺一层,不断盛开,又不断破灭,闪着迷幻的、眩晕的光芒。透过玻璃杯子,我看到了另一种花朵的生长道路。我们一杯接一杯的干,“哐”的一声,四个杯子发出脆亮的撞击声,我们就在这个声音中仰起脖子,一饮而尽。那些液体流入了胃部,也有一部分进入了血液,我们再也寻找不到,就像快乐时光。我永远记得那一次,2007年岁末,在雍华庭的安天民饺子馆,吾同树从家乡梅州带来一瓶“梅州常乐烧”,50多度的白酒,劲道很猛,我们平分殆尽,感觉意犹未尽。然后,我们照例晃到聚福市场那里吃砂锅粥、烧烤,每人继续喝掉三五瓶啤酒,乘着微微的醉意回到出租屋。电话响起,说吾同树醉酒,胃出血,在南城医院挂点滴。我赶紧下楼,跑到南城医院,看见他靠在躺椅上,一滴一滴清凉的液体正顺着细长的管道,进入了他的身体。坐在深夜的医院里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赵原、黄吉文和我来到医院对面的银丰路,在“一碗水”火锅店里,支起一个小火锅,扑闪扑闪的小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汤水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似音乐。我们继续喝了几瓶啤酒,阴冷的冬夜变得不再寒冷和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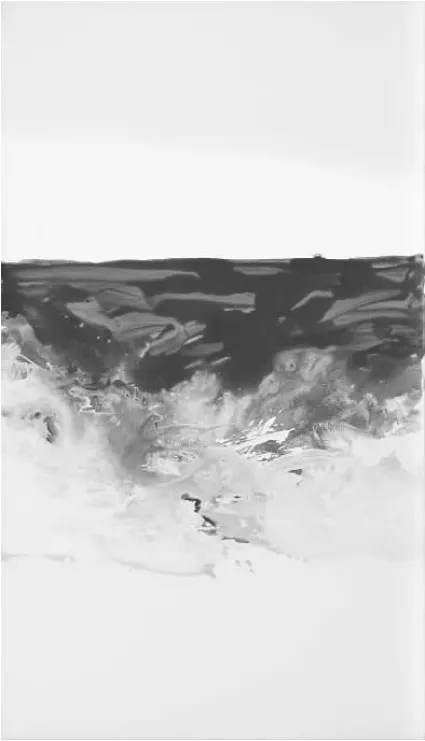
王承云作品·被固定了的海浪6 175×100cm 布面丙烯 2002
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是不是一种昭示?昭示以后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后来,吾同树从金地地产公司出来,去深圳创业,不顺,又回到东莞。2008年7月24日左右吧,我们在体育路口的湖南大碗菜,叫吾同树出来吃饭,他已经不再喝酒,精神萎靡,老赵鼓励他,“男人应该有点钢火”,我们以为他能迈过眼前的这道坎。7月29日,陶天财请吾同树在万江高埗路口的湖南大碗菜吃饭,我也去了,他喝了一点啤酒,然后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回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8月1日中午,我回到老家江西广丰,正与朋友们一起喝酒,接到来自东莞的电话,说吾同树已经自缢身亡,我手中的酒杯“哐当”落地,头脑霎时一片漆黑,此后便是无尽的悲伤,追念。
“诗酒趁年华”,下一句便是“风雨暗万家”,千年之前的天才诗人早就预言过。我们的诗酒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百年之后,在天国,在酒乡,我们再相聚,我们继续喝。
2009年7月,我到文联上班,做编辑,隔三差五的,和詹主席、侯平章、吴亮痛饮过许多回。衡水老白干、汾酒和北京二锅头燃烧着我们的身体,铺满红辣椒的四川菜和湖南菜填充着我们饥渴的胃口。酒精消弭了我们的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别,相同的酒精度把我们串在一起,那气味,芳香,无需多说的话语和共同的生活困境,都沉潜在透明的酒杯中。我们紧紧地握住酒杯,端起,仰脖一饮,而又轻轻放下。
我对酒精的描述,是那样的唯美,颓废。一杯摇晃的酒,银白、诡异的光芒,芬芳、眩晕的气味,倒映着我们转瞬即逝的面影,粗线条的勾勒出我们颤动而易碎的命运,这多像身患重度偏风的老人,站立不稳却又蠢蠢欲动。透过某一个酒精的分子或原子,我似乎看到了我的过去和现在,我的渺小如尘埃一样的躯体,越走越远的青春背影,薄如废纸的命运,它在挣扎,嬗变,它总是在四处流浪,找不到归宿。而酒精的辛辣依旧,一如我线性的生活历程,曲折,艰难,用50多度的热量和惯性推动我向前拥挤,奔突。再没有比酒精更加贴近身体和心灵的东西了。酒精美好而惨烈,它是灵魂的血液,它是身体的能量,我最终依靠它与朋友们抱成一团,相互取暖,相互砥砺,以换取前行的盘缠和力量。
酒精总是那么容易聚合,重逢,也容易挥发,别离。吴亮在东莞的出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此,我唯有献酒一杯,以表我心。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喝酒?只有时间知道。
每一滴酒精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酒杯都有它的命运。少一个酒杯,或者多一个酒杯,对于生活而言,都是正常的。我当然记得与他们碰杯的清脆声音——海量且风趣的龚冠夫老师,当我离开了东莞群艺馆,我就难得和他在一起切磋了;被称为兽医的杂志主编蒋楠,我们还常常在四川小吃喝上几杯;诗歌写得漂亮的巾帼女侠蓝紫,携带着一个大号的酒瓶;英气逼人的80后诗人陈亚伟,流浪歌手成功转型为个体老板的蒋厚伦,一喝酒就脸红的孙海涛,喝醉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的陶天财已经远走福建莆田,至今单身的瘦弱诗人池沫树,老当益壮的刘枫老师,从宁波杀到东莞来的老表朱爱民……这些都是我的朋友兼酒友。一个热爱酒精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有生机和活力的人。当一个善饮的人不能再喝酒的时候,那一定是老了,病了。他内心的悲哀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他内心的世界日渐萎缩,他的创造力也在萎缩。现在,我已经基本不再喝酒了,我瞧见了我的窘态和苍老,酒精带走了我的青春、激情和诗歌。
酒精有一条属于它自己的道路,沉郁,崎岖,向上。它在每一个人身上经过,驻留。对于我而言,东莞的某一条街道和小巷是通往酒香的。我与一些人曾经在这条路上折返,徘徊,带着异乡人的疲惫、文字书写者的沉迷和壮志未遂者的缺憾。酒精养人,也伤人。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是个郎当少年,归来时已是迟暮老人。在东莞,酒精呈现给我们的,是另一种精神的食粮。它是液体中的最高帝王,它聚合了光,也聚合了哀乐,让我们忍不住伸出双手,捧住酒杯,久久不放。它使人幸福,也使人疼痛,在它温润的身体里,我们获得了一种暂时的欢悦与满足。
文林坊65号
穿过几条小巷,拐入一扇小门,再蹬上几层楼梯,取下挂在裤腰带上的钥匙串,先打开一把厚重、漆黑的挂锁,顺手将挂锁空锁在铁皮门上,然后再用另一把钥匙插进门上的暗锁,一拧,一推,门“哐当”一声,开了,一缕亮光和一股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当我这样描述的时候,我就进入了文林坊65号,五楼,503房间。这是东莞市南城区亨美社区的一间出租屋——暂时属于我的10来平方米的东莞,平淡,简陋,安静,切合居住者漂泊、动荡和困窘的特性。
出租屋总是藏着太多蒙灰的生活、红尘中怀抱的温暖和臆想中磨砺的锋芒。我一直生活在租与被租的关系中,出租屋与我的青春和理想同行——2003年下半年,南昌,江大南路青山湖小区,一楼,那个暗淡、破旧的二室一厅,竟然熬出了4个研究生;2004年上半年,广州,华南师大运动场后面的一间房子,我在等待煎熬之后姗姗来迟的消息;2006年5月至10月,贵阳,煤矿村的一间民房,我居住在那里读书,写作,喝酒。10月初的一个深夜,我被窃走了2个手机,这是我离开那里的唯一理由。
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一个屋檐到另外一个屋檐,出租屋是我的驿站,也是我的命运。我像候鸟,注定了不停地飞翔和迁徙。那些从空中飘落的,除了一些尚存体温的羽毛,还有对于下一个归宿的迷茫和渴望。2007年10月6日,我携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这里——文林坊65号,五楼的503房间。这个10来平方米的小房间,摆着一张床,一台电视,几只箱子,两张便于折叠的旧桌子,一撂书籍和一堆散落在简易灶台上的锅碗瓢盆,散发出尘世的庸常气息和寄居者的漂泊味道。简陋的空间存放着我白天的疲惫,苦涩的日子,难以入睡的辗转和对于明天的期盼,以及越来越远的梦想。
出租屋像一个蜂房,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我的左边,505房间(二手房东避开了504这个数字),住着一对男女朋友,男的叫小张,小学毕业,做平安保险,女的叫小谢,高中毕业,做玫琳凯。我的右边,502房间,也住着一对男女朋友。先说505的这一对吧,从事保险行业的小张,从外面奔波回来,只要看到我的门开着,就会径自走进我的房间,顺便把皮包、手机和钥匙往我的床上一扔,开始吹水。三句话之后,谈话便变成了他的保险推销专场,他鼓吹了一大通关于保险的话题,还给我介绍了好几个险种。每逢我有朋友或客人来访,他都要死缠硬磨地推销一下他的保险。他还是个健忘的人,很多时候他回到505,却将皮包和手机留在我这里了。他的女朋友小谢,每天专心致志地描眉,抹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出门做玫琳凯。她也经常过来和我的老婆谈玫琳凯,翻看玫琳凯的画册,介绍玫琳凯的产品,蛊惑得我的老婆很想买一套玫琳凯。化妆品于女人,犹如酒于男人,灵验得很。他们小两口经常吵架,有一回,我听到一阵轰天雷声过后,接着是一阵噼噼啪啪的大雨,女人的尖叫声随之刺破了五楼的平静。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小张将雪白的菜刀架在小谢的脖子上,小谢大叫,“我要报警了,我要报警了!”她真的拿起手机拨打了110。不一会儿,派出所的几位民警和治安队员赶到这里,了解了一下情况,带走了小张。小谢又后悔报警了,她很快跑下楼,去派出所,交上几百元钱,领回了小张。
再说右边的,502房间的这对情侣吧,姓名不详,男的个子不高,瘦瘦的,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女的据说是贵州民族学院休学的大学生,来莞打工。他们的铁皮门常常紧闭着。他们在楼下不远处的网吧上班,经常深更半夜回来,俩人嘻嘻哈哈的说着什么,似乎有讲不完的笑话,然后打开水龙头,哗哗哗哗的,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响起,像一把冰冷的剑毫不犹豫地刺进了我的梦乡。他们一直要睡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过后才醒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做爱,那女的叫床声很尖利,大呼小叫的,一阵紧似一阵,像春天的猫叫,一直要持续二十多分钟,让五楼的空间布满了异常的气息。他们的功课每天都很准时,那个时段,我一般在吃饭,弄得我很不自在。有一回,隔壁的小张从房间里探出头来,伸出一根手指,“嘘”的一声,示意我不要声张,便拿出自己的手机,按下录音键,踮起脚尖,轻手轻脚的走过去,把手机放在502的铁皮门下,收藏了这曲“叫床门”的乐章。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整理完毕,一起走出房间,下楼吃饭,我们都用怪怪的眼神盯着他们。这种声音每天中午都会准时响起,505的小谢就开始敲打自己的铁皮门,“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敲击声猛烈,响亮,502室内运动的人似乎意识到什么,舒畅的“呀呀呀呀”的声音变成了低沉的“呜呜呜呜”。自从这次敲门事件之后,他们收敛了很多。小张一直很想和右边这位瘦瘦的男生取点经,至于后事如何,我也不甚清楚。
后来,502的小两口就搬走了;再后来,505的小两口也搬走了。出租屋里又住进了其他的人。
我还住在这里,那里;我们还住在这里,那里——那些或宽敞或狭窄,或明净或阴暗,或喧嚣或宁静的出租屋里。除非我回到故乡,或者拥有了那扇属于自己的灯光的窗户。对于一个行走在异乡的人来说,出租屋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可以消解青春,困顿,疼痛,乡愁和壮志难酬的空间。随出租屋一起出租的,是青春的背影,挽留不住的时光,日渐暗淡的激情,而安逸和幸福却遥遥无期,像头顶上闪烁着的明明灭灭的星光。出租屋的空气里,流淌着汗味、湿气和油烟味,还有一缕微弱的书卷气息。往往,从外面看里面,出租屋显得阴暗,逼仄,压抑;从里面看外面,灿烂,宽阔,自由,这是否昭示了某种深刻的含义?
相对于城市光鲜的高楼大厦和璀璨灯火,城中村的出租屋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地带和生活。出租屋似乎是城市的细枝末节,可有可无地存在着。这群行走在城市边缘的人,倾听着雨水敲打着铁皮阳台,啪嗒,啪嗒……雨水那么有耐心,那么有力量,一直要持续到天亮。这冰冷、单调的声音也敲击着寄居者的身体和心灵。正如我在一首诗歌《凌晨四点的出租房》里所写的:
凌晨四点的出租房
一场秋雨意味着什么
闪电取走了台灯的光芒
雨水却给了我足够的宁静
我想写的诗歌还在路上
我想拥有的梦还未抵达
我不能抓住的忧伤和甜蜜
瞬间被一朵水花惊醒
我还剩下什么,我还祈求什么
“请把这场雨水的到来当作馈赠”
出租屋里的人,轻微、均匀的鼾声已融入雨声和夜色中,这个世界暂时归于安静。东莞,南城区,文林坊65号,五楼,503房间的灯光依旧亮着,轻微的闪烁着。这盏耀眼的灯光啊,轻而易举的照亮了这个我居住了三年的、10来平方米的东莞。
寄居者
当我写下寄居者,我写下的是我这个人,一个寄居在他乡的、外表平静、内心焦灼的漂泊者,他有着底层者的窘迫生活、桃花一样的梦想、诗人一样的忧虑和尘埃一样的命运,毫无生动、精彩可言。我尝试着,开始从我租借的那片空间来描摹我的东莞生活,沮丧,悲壮,“下落不明”或者阳光灿烂,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透过锈迹斑斑的门牌,地名依稀可辨。东莞,莞城,澳南二马路二街一巷10号3楼,这是我在东莞的第二个驿站。从南城到莞城,从文林坊65号5楼503室到澳南二马路二街一巷10号3楼,我走了整整3年的时间。一张轻飘的房屋租赁合同书,白纸黑字,上面书写着“租赁日期为2010年4月11日至2011年4月10日,每月租金750元整”,它用冰冷、确凿的书面形式,界定了我每月必须按时交纳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以换取在这里睡眠和做梦的资格。

王承云作品·玩水的女孩1 Ⅰ175×100cm 布面丙烯 2004

王承云作品·玩水的女孩3 175×100cm 布面丙烯 2004
白天,黑夜,上班,下班;白天,黑夜,上班,下班……生活周而复始着。时间总是向前的,像列车,经过一个个站台和隧道。这个近10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竟然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儿子的玩具在这里找到了随意摆布的空间;一个房间用作卧室,安放一家三口均匀、甜蜜的鼾声;另一个房间用来摆放我的电脑和书籍,我的欣慰感和安定感很大一部分源自于这里。空空荡荡的客厅,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建筑工地,儿子的挖机、铲车、汽车、飞机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一大堆随时准备用作建筑材料的积木,堆在墙壁的一角。已经竣工的楼房、处于搭建中的桥梁和台阶,不断向前延伸的铁轨……在这里建构起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儿童乐园。这里也是儿子的运动场和跑马场,瘪了气的足球蒙尘已久,滚在一边,像耷拉着的无精打采的头颅,斜视着房间里乱成一团的局面。“驾——驾——驾——驾”,儿子骑在绿色的充气小马上,双手抓着小马的耳朵,在客厅里蹦跳着,转了一圈又一圈——马尾巴上系着一根绳子,绳下捆着一张塑料凳子,后面还用废弃的塑料袋绑着三条塑料凳子,这就组成了一列火车,伴随着儿子的跳跃,凳子被拖动,颤抖着,凳脚摩擦着地板砖,“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发出刺耳的噪音。三岁的儿子说,这是他的“托马斯”(动画片里的火车),他是火车头,拖着好长好长的火车厢。他这样蹦蹦跳跳的,一个人玩得很快乐。有时,他也叫我上车,说,要开车啦,要带我去乡下奶奶家。一个寄居者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小小的寄居者,至今未上户口。但他暂时还不明白这些。他只需要简单的快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扮演着一位身份不明的漂泊者的角色,我也许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或者是盲流、社会闲杂人员等,按照官方的说法,我们是新莞人。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哪里的人了?我说着浙江江山方言,在江西广丰生活、工作了30多年,后来去贵阳读研究生,毕业后流浪到东莞,把户口丢在了苍茫的云贵高原上,至今音讯渺茫。我从一个热血青年到一个儿子的父亲,一位妻子的丈夫,同时还是一个徒劳无功的写作者、部分政治权利被剥夺的不合格公民和凌空蹈虚的理想主义者。理想真是一个好东西,它让有家的人无家可归,让有归宿的人四处流浪。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寄居者。
寄居者最大的财富就是漂泊,动荡。我之所以选择居住在这里——澳南二马路二街一巷10号3楼,完全是为了攫取方便。小区大门口就有一个“元岭路”公交站台,从这里出发,我可以抵达南城车站、汽车东站、人民公园和我供职的单位。不消一根烟的功夫,老婆步行就能到达800米之外的公司去上班。从居所的门口出来,往左行走200米,就是儿子上学的小袋鼠幼儿园,那里寄存了他白天的欢笑和哭泣;向右踱步200米,就是一个菜市场,随时可以买来水灵灵的蔬菜、沾着鲜血的鱼肉和熟透的水果。沿着菜市场的那条小街往上走,街道两边是蜂箱一样排列的小吃店、小饭馆和便利店。小贩们推着平板车,沿街摆卖水果和蔬菜,他们和城管之间进行着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天天都在不停地重复上演。地上常常有掀翻的平板车,骨碌碌滚动的苹果,摔裂的西瓜,踩烂的葡萄……那是未来得及逃脱的不幸。不算宽阔的街上,晚上则排出很多烧烤档,烟熏火燎的,一帮青年人坐在那里喝啤酒,划拳,热闹着他们的热闹,喧嚣着他们的喧嚣。多少回啊,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要一打冰啤酒,叫几个烤鸡腿、几串肉丸子和蔬菜,暂时迷醉于啤酒花的清凉、醇香中。这样的夜晚总是像酒花一样迷忽而易逝。我不知道明天我会搬迁到哪里——南城,莞城,东城,还是万江?或者回到故乡,或者抵达另一个城市?在那里开始新的生存。实际上,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在生存的土壤中进化成了一株无根的草,既回不去故土,也移栽不了新的沃土,就这样被大风吹得不知所向。当然,所有这些,生活都无法提前通知我,我也无法确定以后抛物线的运动轨迹和具体位置。
在这里,我似乎也找到了小小的幸福。还算宽敞、亮堂的住所,比我的第一个驿站——文林坊65号的居住水平提高了整整两倍;每天晚上,我有大把的时间陪儿子守着中央电视台的少儿频道,看动画片,沉浸在《花园宝宝》、《托马斯和朋友们》、《巴布工程师》、《小熊维尼和跳跳虎》、《哪吒》、《蜘蛛侠》、《米奇妙妙屋》、《爱探险的朵拉》的对白和故事中……我也看得妙趣横生,烂漫天真。
夜已深,孩子睡了,城市的灯光和声嚣还醒着。我转到另一个房间,打开电脑,敲打着键盘,移动着鼠标,消磨上一段时间。一台电脑吸收了我的多少时间?我无法计算。电脑成了我阅读的书本、书写的纸张、娱乐和交流的工具以及加班加点中模糊的面容。电脑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正在改写着人类的文明。
尘世生活总是相似的。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些披着水泥外衣的道路和墙壁,是一个更大一些的乡村。从澳南二马路二街一巷10号3楼出发,我们偶尔去逛逛超市,爬爬旗峰山,都不会太远。生存压倒一切,生活永远都是步步紧逼、迫在眉睫的,容不得我们懈怠。
最远的是故乡,明天和梦想。下一站,继续扎根东莞,还是飘向另一个异乡?我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这是我暂未完成的东莞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