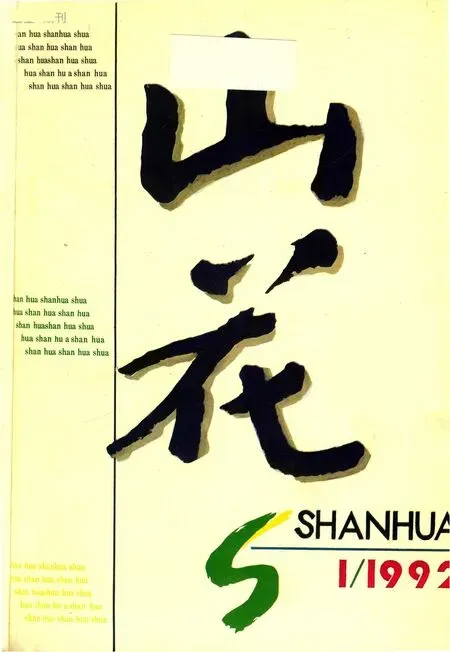海归艺术家的创作图景
2011-11-30蔡芳芳
蔡芳芳
海归艺术家的创作图景
蔡芳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很多中国艺术家走出国门,到海外寻求发展。随着国内文化意识有所开放,艺术生态逐渐好转,一批海外艺术家开始回归国门,创作了不少新的作品。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徐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移居美国,代表作品有《天书》(1987)、《鬼打墙》(1990)、《新英文书法》(1994)、《烟草计划》(2000)、《何处惹尘埃》(2004)等。其真正的代表作是《天书》和《新英文书法》。《天书》是徐冰早期作品,这件作品中,徐冰刻了上千个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字,这些文字没有一个是可以解读的,用徐冰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在吸引你阅读的同时又拒绝你进入的书,它具有最完备的书的外表,它的完备是因为它什么都没说,就像一个人用了几年的时间严肃、认真地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天书》充满矛盾”。《新英文书法》则是徐冰出国之后的创作,这件作品也让徐冰获得了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艺术最高奖——迈克·阿瑟奖,即通常所说的天才奖。该作品将英文字母以汉字的方式书写出来,阅读顺序是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从外到里,这样一来英文在其书写方式、阅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对新英文书法方块字的形式、西方人对组成方块字的字母都会产生兴趣而得以参与,将中国的书写方式融入到西方文化中,徐冰的作品充满着东方哲学的神秘与智慧。
回国后徐冰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其历时两年之久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凤凰》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广场首度亮相,而后在上海世博会的宝钢大舞台室内落脚。《凤凰》本是为北京CBD的某座大楼设计的,使用的全部是废弃的建筑材料,凤冠由安全帽构成,羽毛是铁锨组装的,凤爪则是挖掘机的挖斗,还安装了LED灯,点亮后有贵州刺绣的特点,其形象接近汉代画像描绘的形象。这件作品受到诸多的批评。就造型而言,有人认为它造型太过柔美,有人认为它太过丑陋;就观念而言,也有人认为它没有创造性。在《回到艺术本体》的演讲中,徐冰对《凤凰》进行了阐释,认为凤凰代表了中国人对物质的尊重态度,物尽其用,这一点也是媒体和徐冰本人对《凤凰》一再强调的方面,即变废为宝,可能也是徐冰本人最为得意的地方。但艺术作品除了其材料值得关注,其意义更为重要。徐冰强调《凤凰》创作的难度,但这些并不重要。《凤凰》变废为宝,又同样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创作难度大是因为其巨大的体型,并非因为观念的价值。《凤凰》可以说是一件趋炎附势的作品,没有任何创意,也没有难度可言。任何一个懂得相关知识的人都可以画出这样的草稿,至于是汉朝的还是清朝的形象,则依据设计人员的想法而定。一只体型庞大讨好卖乖的吉祥鸟而已,如此令人肉麻的歌功颂德,如此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看不出有何对物质的尊重。
和徐冰不同,蔡国强的创作以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火药作为作品载体,成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中国艺术家之一。1993年蔡国强在嘉峪关实施了其爆炸作品《为长城延长一万米——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作品规模非常巨大。19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当天,蔡国强做了一件名为《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的行为艺术,他驾驶着一条从家乡泉州起航的中国渔船驶入了爱尔兰大运河,渔船上还有一个装有中草药的自动贩卖机,展览期间,渔船一直停靠在威尼斯。1999年蔡国强应邀复制《收租院》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获得金狮奖,与《收租院》的原创者——四川美术学院因版权问题几乎引发一场官司。其频繁的活动、数量众多的作品及规模巨大的展出,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焰火《历史足迹》——29个巨大焰火脚印的设计以及60周年国庆焰火晚会总设计师的身份,让蔡国强作为艺术家越来越明星化。中国文化传统符号一直是蔡国强作品中的主旋律,他还将中药、风水、历史故事等引入自己的创作中。他是一位十分懂得艺术操作和操作艺术的艺术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焰火设计进一步强化了蔡国强的明星化身份,29个大脚印也让蔡国强与西安艺术家牧源开始了另一场版权官司。蔡国强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创作与其后来为奥运会、国庆等设计的焰火相比,尚有艺术创作的独立意义,而后者不过是政府盛典的一个业务而已,这种毫无价值取向的利益共谋,除了证明艺术家的堕落,没有任何意义。
海归艺术家不仅作为新兴的力量影响着国内美术界,同时也正成为一种独特艺术现象值得研究。对以上提到的徐冰、蔡国强等人的创作争议较多,反对者认为此等艺术家滥用中国传统文化,迎合西方批评界的口味,有“贩卖中国”之嫌。也有批评家认为海归艺术家创作较出国之前,批判性有所减弱,过于受利益驱动,而忽视了艺术本身的价值。
谷文达是水墨领域的代表,曾是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创作了不少的水墨装置艺术。80年代早期,谷文达将汉字加以拆解,用毛笔书写故意的错字、倒字并在文字上画满巨大的红色圆圈和十字符号,来反思和挑战正统体制,这种破坏性和挑战性是八五新潮美术的特点。1987年移居美国后,谷文达在创作材料方面发生了改变,开始收集人体上的材质进行创作,他曾经利用婴儿的胎盘粉末做成名为《生之谜》的作品。在装置作品《联合国》中,他利用从各地收集到的头发编成汉字和国旗,再粘贴到木板和布帘上,以探讨全球化的问题。其代表性作品当属《碑林:唐诗后著》,是由50块巨大的石碑组成,涉及到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与再翻译。即将50首唐诗进行中英文对译,将古典汉语唐诗意译成英语唐诗,再将英文唐诗音译成现代汉语唐诗,再将现代汉语唐诗意译成英语唐诗,最后将上述四种唐诗文本用50块巨大的中国碑石刻成石碑。而“诗歌就是翻译中损失掉的部分”,谷文达的这件作品也说明了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误读。

王承云作品·第一时间 200×300cm 布面丙烯 2010
黄永砯是观念艺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中,是“厦门达达”的核心人物,其代表作品是1987年创作的《中国绘画史和西方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洗两分钟》,将浙江美术学院学生认为是艺术圣经《现代绘画史》及《中国绘画史》放在洗衣机中搅拌,将搅拌出的纸浆置于木箱上的破玻璃上。这也体现出八五美术新潮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性。1989年移居法国之后,黄永砯艺术创作出现转折,对各种文化冲突的探索成为黄永砯创作的出发点。如《蝙蝠计划》按实际大小复制了坠毁在中国领土的美国侦察机局部,两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等微妙关系都蕴含在这件作品中。《非表达性绘画》用转盘来编码,并通过转盘的旋转来决定使用什么颜色、如何构图及何时完成作品,作品中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弱化了创作的主体性。黄永砯的作品并不限于视觉美感的表现,其魅力在于对文化及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挑战传统的艺术创作和观念,他曾说“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像鸦片对于人,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其前卫和反叛精神一直贯穿在艺术创作中。
除了以上提到的四位艺术家之外,还有诸如陈箴、张大力、杨千等海归艺术家,他们在西方优越条件的吸引下走向国际,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同时也开始让西方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不难理解,海归艺术家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作,以“中国艺术家”身份出现于国际艺术展览中。这一方面是接受西方文化、理论、技术的影响,融合中国元素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个体生存于异域的现实需要。
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在国际上“出场并有存在感”的艺术家,在运用中国符号进行创作时应该如何把握。将中国文化符号转换为迎合西方消费文化和心态的作品屡见不鲜,因此必然会提及后殖民文化身份问题。后殖民主义曾在学术界形成一股文化旋风,不少批评家都以此来分析现当代艺术问题,用以说明西方文化权力对中国艺术发展的“戕害”。但海归艺术家并不完全同于那些仅仅是在国外生存的艺术家。就身份而言,他们是文化游牧者,其创作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复杂过程;就语境而言,相对本土艺术家而言,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文化历练,对中国当代艺术自有其独特的推动作用。我们应该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认真的讨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回国的海归艺术家中,陈箴的创作极具代表性。他是较早做装置且极有才华的艺术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法国深造,九十年代已经非常重要,受到极高评价。他经常使用日常物品,如桌子、椅子、床等进行创作,试图对社会、个人、生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借此分析东西方文化生活的差异。人类处境、民族文化等问题的思考一直是他作品的中心思想。2000年陈箴因癌症去世,2005年上海举办“文化的无家可归者”展览,展出陈箴14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绝唱——舞身擂魂》在国内首次亮相。此件作品是陈箴在癌症折磨中,打算去印度和非洲寻找西医之外的治疗方法时突然想到的。该作品由10个床鼓和55只椅鼓组成,以人击鼓为隐喻,相互治疗,治愈自身的同时也治愈了他者,谭盾为此谱曲并创作击鼓法,中国舞蹈家黄豆豆及一名日本鼓手和美国鼓手在其间舞身擂魂,其磅礴的气势使作品的表现既深刻独特又具有启发性,让观众感动而震撼。2010年法国吉美博物馆也为陈箴举办了回顾展,有5件重要作品参展。陈箴将理性、睿智融入创作中,在面对生活的真实时,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探索,以生命的激情书写了他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其重要的代表作品还有《联合国》(1997)、《佛倒——福到》(1997)等,都是通过日常生活用品简单而智慧的组合,表达出个人对文化、生命的体悟。
张大力以涂鸦人头像《对话》系列著名,早期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关注城市发展状况,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他在城市角落的废墟及待拆的墙面上凿出或喷绘出简单的人物侧面头像,这些头像都是匿名的且随着被拆的墙面永远消失。《第二历史》是张大力的又一代表作品,历时五年完成,是一件纯档案形式的作品。艺术家利用特殊的人脉关系从档案馆中搜集整理出来,这些作品都是人们所熟悉的照片,但有着不同形态的对比。经过技术处理过的,比如抹掉一些人物、背景,人们通常看到的照片并非当时拍摄的东西。用张大力的话来说,我们目前看到的和知道的,实际上都是“第二历史”,“第一历史”则被有意地遮蔽了。由此,张大力的创作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历史的反思性。
杨千曾在美国深造,其代表作品有《浴室绘画》、《活动绘画》、《双重绘画》等系列,最近他开始使用碎纸屑创作绘画装置作品,所针对的是当今消费社会中被物质异化的人。此系列作品采用的是现成的报纸、杂志作为原材料,将其碾成碎屑,漫天飞舞,表达今日社会的迷狂状态,以抨击媒体的功利化态度。与此同时,艺术家又将这些碎屑重新转换塑造出新的艺术形象,表达出艺术家对历史文化进行超越与转化的理想。
另外像艾未未、朱金石、王功新、林田苗、王度、王承云等都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有影响的海归艺术家,其作品涉及装置、绘画、行为、雕塑等众多领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现在,一大批海外艺术家回国,自有其原因。首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其次,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家很难引起足够的重视,西方的艺术界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中国本土艺术家的创作;再次,政府开始重视当代艺术的品牌效应,接纳海外艺术家,推动政府的文化策略,以艺术明星达到宣传目的。其实海归艺术家所面临的文化语境是复杂的,他们不仅面临西方文化的他者化,同时也面临官方意识形态的他者化,海归艺术家在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之后,如何保持问题意识和个体意识,使得创作更有针对性,是他们在以后创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王承云作品·Joseph Beu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