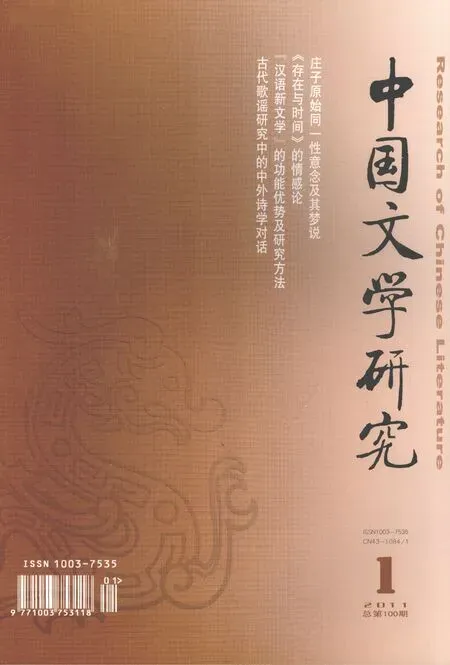论张洁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以《沉重的翅膀》和《无字》为例
2011-11-19任美衡
任美衡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湖南 衡阳 421008)
自新时期走上文坛以来,张洁确实表现得复杂多变,总是以不同的面目示人,特别是对于她在世纪末的转型,更是引起了超乎寻常的关注。王绯认为,“很难相信一个曾经写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而给人以强烈的古典主义印象的张洁,一个曾经写了《谁生活得更美好》、《方舟》、《沉重的翅膀》而给人以正统的现实主义印象的张洁,竟然那么彻底地反叛自己骨子里的诗情与崇高,如此迅捷地从古典理想主义跌入冷峻的现实主义,继而企向现代主义,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当代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像张洁这样从唯美走向审丑,在极其明快的风格变换中显示出自己的文学年龄,仿佛从文学的少女时代一下子跨入到成年时代,又迎来了文学的更年期。”〔1〕“以《无字》为界,张洁成功地完成了她由唯美、神奇到超脱平凡的创作转型。”〔2〕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这种比较却“误解”了她的转型的基体内涵及其历史性,尤其对于《沉重的翅膀》与《无字》,学术界仿佛有意识地遮蔽了、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不自觉地空缺了张洁不断突破局限、实现自我的努力。鉴于此,笔者以之为对象,力图无限地接近并找到张洁转型的深在因素与文学创作的根本路径。
一、转型的表征
审视张洁在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它们都聚焦了不同的核心特征和本质化的趋向,而且各自“呈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文本,尤为突出的无疑是80年代初的《沉重的翅膀》与新世纪以来的《无字》,在它们的背后,是张洁不同的审美理念、趣味及价值取向,同时也融入了她的全部思考及其实践。因此,从《沉重的翅膀》到《无字》的视点置换,实际上蕴含了张洁本身的创作转向,也概略地反映了个体、民族、时代及文化全球化对于当今中国文学的独特作用及复杂效果。
(一)叙述主题由“国家”向“个人”位移。新时期以来,随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文学也积极地参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是“对于那些从‘文革’的劫难中归来的作家来说,他们创作的一个共同主题便是复现过去的追求,复现理想的真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上,作家的整体写作都是为了给民族再生构筑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寓言(或历史神话)。”〔3〕
张洁也不例外,在这种共同的社会氛围中,张洁的小说创作无疑也广泛地指向这种社会的共同期待,无论是涉及改革、爱情的探索、人物命运还是其它题材,都有意识地烙上了中国想象的质素,特别是《沉重的翅膀》,胡德培曾激情洋溢地评论道:“小说有力地歌颂和肯定今天推动‘四化’建设和民族振兴的最可宝贵的精神和品格,同时无情地鞭挞和抨击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势力,作家对民族兴衰竭尽心力,满腔热情、满怀期望,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现象和问题也直抒胸臆,从而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现出了丰富多样、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画面。”〔4〕这种评价道出了文学对历史的担当,并显示出了国家成为了文学的主体,具备了强势的话语权,人作为国家的符号附着在国家的光环与规律之下,成为“影子”,并形成了以国家兴衰来表现个体命运的深在结构。当然,作家并未将之程式化,在肯定文学对国家的担当之时,作家也并不否认由之而来的疑虑和质询,在继后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尤其是《无字》的创作中,张洁逐渐地褪去了对国家的理想化期待,转向了对个体哲学的探究,并使之背景化,让个体的内面世界浮出历史的地表。如“内容简介”所指出的,尽管作者的笔墨还描摹了百年中国的风云际会,并通过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对人的与世浮沉和坎坷遭遇进行了独特的记录与审视,写出了一个说不尽的时代。然而,作者是清醒的,并将“重心”转换到对人的个体存在的开辟上来。在作品中,尽管吴为们是由特殊的国情所造就的,然而却逐渐淡化了指向“中国”的象征色彩;以此为舞台,彻底地展开了吴为们的全部实在性,既避免只强调“历史、唯物、实践、时代、阶级、集团的要素、职能的广阔”于不顾,避免把个人工具化,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实现人的价值、自由及其限度,个体存在的悲剧性和希望等等问题,从而照亮新的个体存在的合理性并为之辩护。〔5〕
张洁把历史与个人杂糅,即凸显了人的相对于历史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贯穿了人的物质遭遇,并延伸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的躯体是有限的,但在无数的集合中,个体成为了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成了国家唯一的真实存在,后者不过是为之提供某种依据而已,正是人的有声有色的参与才使得它有了丰厚的基础,因之个体是根本的。这种叙述立场由“想象中国”到“个体哲学”的位移,使得张洁不断地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并形成了最后的高度现象:她的创作依托于宏阔的背景知识,总是最前沿地追求着人的最后本质。
(二)叙述对象由“想象男性”转向“发现女性”。《沉重的翅膀》无疑寄托了张洁对男人的潜在期待,当然也浓缩了在灾难之后对男性英雄主义的呼唤:男人应该是顶天立地的强者。英雄的遭遇也许各有不同,但英雄的很多品质一定是相同的:他们善良、勇敢、正直和坚强。他们用心倾听苦难人的苦难,他们用爱和悲悯拯救不幸人的不幸!他们有宽广的胸怀,哪怕遭遇误解也始终坚守!他们有划破黑暗的力量,哪怕回报给自己的是更黑的黑暗!〔6〕也许他们还会体现出敢于反抗、热衷冒险,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总是指向宏大、总体的社会目标,处处都显示了理想主义的特点。张洁通过郑子云们,表现了对男人无限的崇敬,他们的人生表现几乎完美无缺,尽管他们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惶惑和信心丧失的时候,但这恰好地展示了他们的百折不挠,验证了一个男人必须经过无数的磨难和痛苦,才能把他锻造成为一个坚强的不会被社会的风浪所湮没的人,他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同时,作者还塑造了田守成的老谋深算,纪恒的察言观色,宋克、孔祥的思想僵化、惯唱高调、上下首耳,夏竹筠的空虚与势利,丰满了英雄人物颠倒的镜象;还通过叶知秋、郑圆圆等人的知性与无奈,敞开了英雄人物被粗砺所包裹的最柔软的人性。
《沉重的翅膀》充满了张洁的男人想象,寄托了她对爱情深在的思考及其期待,与之相比,《无字》则表现了对女性无尽的开掘与发现:张洁剔除了男性庞大的阴影和理想神话,在其形象的支离破碎之中重构了女性的本体存在。在她看来,女性应该是坚强、柔顺、富于牺牲,特别是在最艰难的环境和最绝望的遭遇中,更能显示女性的真实性及其友谊,吴为、墨荷、莲子三代人恰恰就是女性的原始底片。
张洁恢复了女性的历史主体性,以前女性总是生活在男人的庇护之中,因之,她甘愿地喑哑、沉默,历史上也就消失了女人的身影,她只不过成了男人的附属物,成为男性实现自身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为此张洁不仅通过吴为的自强、自立、自尊,展示了女性的独立性,而且还从历史的缝隙中放大她们的参与精神;甚至还显示了“正是女性才粘合了历史的断裂,扭转了历史的偏差”;历史本身就是女人的,她们繁衍子孙才创造了历史的波澜壮阔,她们主宰着权力之棒,不断地驱动着社会的变革,孕育着生活的内涵,从而彻底地展开了人类的物质史、文化史、风俗史、斗争史、生产史,等等。张洁尖锐地指出了女人的不幸之源。如她所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她把男权文化当作天然的敌人,也从性别差异中寻找解放的通道,对于无形的贞操、守节等镣铐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和置于绝地的摧毁,对于自古以来的“出嫁”意识进行了根本性的抵拒,从心理、精神、行为、存在等各方面重构女性的本质,由“第二性”形成“女人”。张洁还以被颠覆的男性作为镜子,镀亮了女性的全部光彩;因此,女人首先是主体化的,她不依赖于他人而存在,她所有的特点都指向自身;女人也是个体化的,她永远不重复;女性还是性别化的,正是与生俱来的躯体差异造就了她无法替代的痛苦与毁灭,正是不断强加的男权话语,才剥夺了她的性的基本权利,只有打倒男人的特权,才能给予她们的合法性;女人是悲剧性的,她们是世界的母体,但历史却遗弃了她们;女人是精神化的,她们永远在自我的审视里才能留下生存的依据。
张洁的这种转型移植了她对生活的根本看法,也构成了张洁深在的性别哲学。如果我们割裂地看待《沉重的翅膀》和《无字》的话,会认为张洁正在走向思想的暴力与偏执;但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发现张洁对爱、性、社会、历史、自我、他者等建构的苦心。因之,无论是对郑子云们的最大期望还是对吴为们的最大绝望的审视,都潜在地包含了张洁对于男、女双性关系的困惑,但无疑也深刻地指向了如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所由衷希望的,要在既定的世界当中建立一个自由领域,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且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
(三)叙述思维由“趋同”转向“求异”。如果从思维角度考察《沉重的翅膀》与《无字》的差异,会发现《沉重的翅膀》更多地表现为趋同思维,广义地说,“这是人们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观察和思考时,总是力求想以已有的结论、规范认同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7〕因之,这种思维具有权威性、主流性、延续性等特点,具体到《沉重的翅膀》的实现形式,可以发现由此带来的诸多“后遗症”。如把小说的“改革叙事”模式化了,基本未脱离流行的窠臼,从而展现为主题表现的概念化、形象塑造的类型化、情节发展的公式化;这些又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的总模式,普遍地表现了两个营垒、两股势力、两类人物、两种观念的对立,虽然造成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尖锐地表现了改革大潮中的矛盾、冲突,但也造成了对改革部署和改革过程的投影式的图解,〔8〕虽然不乏创新的冲动,但却缺少了艺术颠覆的魄力和勇气。
淡化了矛盾的冲突及悲剧性,由于立意在“必然性”之下,《沉重的翅膀》洋溢着这样乐观的信念而欠缺了深刻的批判性:因为有党的正确领导,有郑子云等英雄人物的艰巨努力,有拥护改革开放的基本群众,一定会在时代大潮中扫除异心人、蛀虫、腐败分子等改革开放的负极因素,从而在更高的程度上促使改革走向和谐。
还由于对社会伦理生活无条件地认同与服从,导致了人之个性泯灭,如陈咏明、叶知秋等人尽管不断地面临着新的人生选择,然而他们都循规蹈矩,压抑住所有的痛苦与不幸,使自己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从而在巨大的社会力量面前不自觉地降低了自身的欲望性和其它冲动。总之,“趋同”倾向使《沉重的翅膀》因符合各方所需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在时间的流逝中也因集体“失忆”而逐渐淡化了它的影响。《无字》则倾向于“求异”思维,不规训于传统的规范和权威的是非观,而是在对人生、自然、社会的独立思考中自由思维,探求“陌生化”效应。如人物描写的非偶像化。通过深入地剖析胡秉承内心的卑鄙、龌龊,显示了他性格中的阴暗角落,也还原了他的“凡人”面目,前所未有地敲碎了革命干部的神圣光环。同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予以诋毁,而是把崇高的信仰与他对女性的占有糅合起来,斑驳地显示了历史中某类个体的真实存在;吴为们骨子里仍然持守传统女人的准则,但也不断地质疑、反叛男人们带给她的幸与不幸,显示了被历史隐蔽的各面的人性。价值取向的差异化。作者在对美好的赞扬之时也毫不隐瞒对它的憎恶,看到了它在社会中的软弱与无能,看到了它的易碎;对于恶的一面,作者在对它表示鄙弃之时也审视了它的无尽的摧毁力;对于被历史平均化的“中间值”,如宽容、平和、淡定,作者既肯定了这些成分的粘合作用,也毫不隐瞒其中的负累和羁绊因素。总之,在不同的境遇中,作者体现了各种价值的影响力,以移形换影的方式指出了它们的流动性及其变异。深在的批判性。作者对现实总是以一种不合理的态度质疑之,也潜在地批判着。20世纪历史风云的潮流性,发酵了人性中的虚伪、贪欲及霸权主义;吴为们逆现实生活的虚幻性,对理想过度地纯洁化带来的绝望感,都使张洁意识到,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这种观念潜在地左右了她的写作情绪和主体精神,现实的残缺、人性的丑恶以及吴为的发疯,都是张洁特殊的自我审判。以及想象的丰富性,上至国家,下至世人最隐蔽的心底,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经济、军事、物质文化、正常/非正常、真/假、丑/恶、理想/信念、欲望/贞洁,无不奔涌而来,作者灵活地运用安插,在民众的、政治的与其它想象力的狂欢中找到了极大的宣泄。
总之,由于“趋同”与“求异”的不同的思维形式,使得《无字》和《沉重的翅膀》有着质的差别;然而,按照辩证法所言,这种思维形式的参差又是相对的,它们也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烙印了张洁独特的个人风格,显示了张洁在艺术与精神方面的延续性。其实,从《沉重的翅膀》到《无字》,这种转型还包括创作观念、过程、审美经验等因素的变化。不过,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张洁本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否认它们的血缘性,《无字》是《沉重的翅膀》的成熟与超越。
二、转型的原因
从《沉重的翅膀》到《无字》所发生的多样的、复杂的、多层次的转型还可从其它作品得到广泛的印证,张洁为应对时势追求最后的高度变换不已又难以把握,成为当代文学史上难以定位的另类,也显示了她的未来性,造成这种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社会变革的原因。1978年的改革开放,无疑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扭转了社会的航向。作为时代敏感的神经,文学无疑也随着它的脉搏而跳动着、变革着。处身其中的人,无论是作为何种角色,都以自己的意志参与到这种潮流中来。这也为他们提供了个体选择的自由、机会和条件,以沸腾的时代气氛促使人与时俱进,并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它们综合地形成了文学创新的总体背景及其文学传统,主要体现在:作者挣脱了“唯现实主义”的束缚,从“一体化”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开始了源自本体的文学选择,没有强迫,没有号召,没有任务,作家实现了自己的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市场经济使文学不得不面对读者的趣味、不同层次人们的审美需求以及无情的淘汰法则,读者的接受力得到了爆发,从而实现了对文学创作潜在的多元化的“召唤”;文学走向边缘化,褪去了它在政治光环下的重负与虚饰,恢复了它的本质,能够自主地担当自身与社会的职责和使命。社会变革形成了多个力的四边形,最终都作用到文学变革中来,形成了张洁现代转型的文学场,也使她的创新冲动发酵并成为现实。
(二)世界多种文学思潮相互冲撞、交融所产生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此起彼伏,不断冲击着共和国文学的版图,甚至改变着它们的基因,也给予了张洁及其他作家有力的冲击,他们惊讶于文学万花筒般的声色,并从自己的趣味、爱好和已有的艺术修养出发,不断地汲取着源源不断的艺术营养,并被裹挟着走进了新的艺术园地。
先锋文学思潮使她不再囿于已有的艺术范式,而是主动地融入到与它的对话当中,实践着自我蜕变;尤其是先锋文学对宏大叙事的解构,退出了与意识形态的合谋,寻找暴力与欲望的终极性,使得张洁有意识地打碎了国家书写的梦幻性,回落到文学的永恒主题,这就是超越了时空、民族、语言等障碍的公共经验领域。如“先锋派文学注重发掘人物内心世界,细腻描写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联想、意象、通感和自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拉开与固有经验的距离”。〔9〕张洁不再刻意追求意义的大众化,而是努力突出词语的主体性和朦胧性。
女权主义思潮使张洁仔细探讨性别在文学创作中的“程控”作用,借助于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凯特·米里特的《性政治》、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以及玛丽·埃尔曼的《想想妇女们》等著作,张洁首先萌生了清醒的女性意识,并把它置放在整个男权文化的背景上进行积极地建构,清算了“菲勒斯”崇拜对女性创作的负面作用,以性为中介,重新定义文学创作的合理性;在反对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男权思想之时,探讨妇女文学创作的形成历史及现状,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实践和净化,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女性主义,以此为标准来评判男性存在的合法性;在张洁看来,妇女“必须写她自己,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10〕
新历史主义打破了文本与历史的界限,使张洁开始深刻地怀疑历史的真实性,从而也促使她重新审视“过去”。她巧妙地避开了意识形态机器对于历史的“制造”,而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去解读历史;新历史主义的诗性也使张洁不再局限于现实的平面性和整体性,而是努力去探索现象之下的本质性。
个人化写作潮流所借重的个人记忆、经验表达也极大的拓展了张洁的视野,使她把从群体意识所获得普遍的伦理法则所抑制、所排斥、所遮蔽的私人性充分地展示出来;私人写作的躯体化也使张洁找到了语言和意义的原点,从而使之无限丰富地呈现了文学创作的巨大魔力;她也有意识地规避了“躯体写作”,当她不是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用自己的肉体展现自己思想的“陷阱”,而是驾驭着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并将它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那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11〕人化写作也显在地使之努力摆脱始自《沉重的翅膀》的“普遍写作”而努力体现出自己的特立独行,甚至不惜以极端的方式来表现。总之,各种文学思潮从多个方面充实了张洁的艺术库存,使她能够各取所需,糅合成自身的优势,从而实现了艰难的转变。
(三)影响的焦虑。英国批评家布鲁姆认为,那些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天赋较逊者把前人理想化,而具有较丰富想象力者则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然而,不付出代价者终无所获。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会引起由于受人恩惠而产生的负债之焦虑。于是,后人为了能够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不断地想尽办法努力克服对影响的焦虑的力量。也就是说,以不断的反抗来体现自己的存在。〔12〕陈忠实也这样说过:“作家重复别人是悲哀,重复自己则是悲剧。”张洁也不例外,她信奉的上帝与她努力超越自身的极限所做的努力,使张洁在艺术之途永不停歇,不断地实践着审美革命,终于在十年探索之后殚精竭虑地跨到了《无字》境界:既新颖又生动、既诗意化又复杂多变的无边的现实主义。
总之,这些因素不仅表征了她的转型的主动性,也表征了她的艺术之途的必然性;这种转型不仅实现了她个人创作的飞跃,也实现了当代文学对于过去传统的超越、面对未来的可能性与自信心,以及没有“最后”的高度。
三、转型的意义
在一篇文章中,谢有顺曾这样说过:“文坛上活跃的作家是有不同类别的,有些人一眼就让人洞穿了自己隐秘的写作深度,往往让一句先锋派或传统派就可为他盖棺论定,可见他的文字中有着某种个性的烙印,而少让人揣摩回旋的余地,这样的作家并非少数,他们是在同一条路上把文字给写死了。”因此,他更看重的是“另外一些作家,他们一直以自己的文字事实在文坛中存在着,你却很难给他规定,他们的写作好像是仅仅为了自己躁动的灵魂,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悲哀,他们是在与写作的斗争中,赋予文字坚韧的美、力量和精神的”。〔13〕张洁无疑属于后者。
(一)从70年代末走上文坛,张洁不断地流变着、冲突着,既踏着新时期以来不同文学思潮的浪花又始终坚持艺术的超越,几乎形成了自己万花筒般的艺术色彩,转型犹如一根杠杆,把这种效应基本地表现出来了。在转型的过程中,她剥落了某些根深蒂固的艺术因素,出现了不成熟造成的生涩,由此也带来了不少时代的遗憾。总体来看,她首先拓宽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在人生观上,由积极的“入世”走向悲观的“审世”再到超然的“出世”;在世界观上,由前述的“民族主义”走向忧患的批判性的“人道主义”;在文艺观上,从经典的“现实主义”走向现实审美的“综合化”,即多情节、多线索、多种艺术手法,使之显得复杂、混成和多元化;在内容上,由对情感、改革、家庭、民族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社会呈现转向对它们深度的精神拷问;在形式上,则博取各家所长以求新创作、新突破;在价值取向上,由对“审美”的追求到对“审丑”的哲理性和美学性的开掘。
(二)深化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在叙事精神上,由女作家的情绪性的宣泄到寻找自我的价值乃至超越;反驳了女性在突破经济负担之后的性迷失,避开了所谓的自恋、自慰、同性恋等属于女性的独特经验的陷阱,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女性生存史的探究,并赋予文字符号象征意义的解读,从而强化了女性文学关于现代文学女性主体性的构想;张洁的转型还表征了女性文学在表现真实自我的同时,怀着深在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深层的自醒意识,不再囿于女性个人的得失,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表现了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自觉地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张洁的转型也使女性文学在阐述诸如语境、性别、身份、身体写作、人文关怀、两性对话等社会热点问题时,重新渗透了批判的视角和理性的精神,使之不再拘泥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而是充满了重新建构的主动精神。
(三)打破了现实主义的传统界限,熔铸和提升了(后)现代派文学的中国经验,使现实主义思潮得到了阐发。张洁不但打破了现实主义向内开掘的底线,并延伸至非理性领域,使现实主义变得更为主观化,能够在不确定性与虚幻性之中聚焦、贯通现实的原色,使它的基本内核能够爆发出最强的辐射与冲击作用;强化了现实主义的文本性,即对荒诞、意识流、黑色幽默等现代主义技术进行“拿来主义”,推动了象征、寓言、比喻等手法不断地冲击着现实主义的固有秩序并打乱了它们本身适应的逻辑性,使之在面对现实之时能够产生神奇的效果和变幻莫测的气氛;促进了现实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拓展,培育了文学的当代观念与全球意识,并力促它与世界文学的循环更新;重新净化了现实主义的使命意识和问题意识,使之在批判中不断地脱胎换骨;深化了社会主义的审美意识,使之充满了中国特色及“此岸性”,也促进了它的活力。
正是由于积极迎合现实生活的变化,顺应时代的潮流的发展方向,弘扬自身的传统优势,汲取现代主义的成功经验和实验技巧,不断开拓新的艺术途径和表现空间,才使新时期以来的张洁的现实主义诗学及其转型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呈现了与现代主义彼此渗透、相辉映共生的独特艺术风貌。〔14〕
〔1〕王绯.张洁:转型与世界感——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J〕.文学评论,1989(5).
〔2〕张丽.无字我心——从《无字》看张洁的创作转型〔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5).
〔3〕郭晓莹.男性神话的解构——女性文学视角中的张洁早期小说〔J〕.福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4〕胡德培.艺术命运的魅力——《沉重的翅膀》为何受欢迎〔J〕.文学评论,2003(3).
〔5〕耿开君.个体哲学的建构及其中国文化背景——评王晓华的《个体哲学》〔J〕.当代作家评论,2002(12).
〔6〕《平民英雄的尴尬》片尾评论,见 http://tieba.baidu.com/f?kz=308792330.
〔7〕金刚、张喜阳.求异思维与观念更新〔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8(6).
〔8〕李新.模式的坚固与观念的障碍——关于改革题材小说的思考〔J〕.文艺争鸣,1987(3).
〔9〕参见百度百科的先锋文学史条,http:///baikebaidu.com/view/770059htp.
〔10〕〔11〕〔阿尔及利亚〕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4,195.
〔12〕〔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5-6.
〔13〕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J〕.当代作家评论,2005(5).
〔14〕刘卫国.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扭结——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深层特征〔M〕.天津社会科学,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