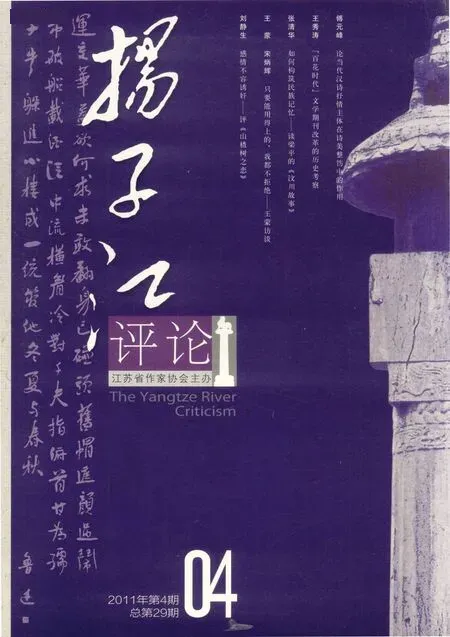只要能用得上的,我都不拒绝——王蒙访谈
2011-11-19宋炳辉
王 蒙 宋炳辉
宋炳辉:王蒙先生,我最近读过您的《我的自传》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也快问世了吧。不过,从前两部中我就已经感受到,这不仅是一部您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创作历程的历史,同时也将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见证史。我想,这不仅在于您的文学实践所产生的持久而重大的影响,更取决于您在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所处的特殊经历。关于您的三部自传,一定会引起文坛和读者们的极大兴趣,一定会引出许多话题来。
我首先注意到一点,您对于自己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创作,用了一个特别的表达词,就是“青春期的写作”,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间隔了那么多年,直到70年代末回归文坛时,进入了“中年写作”。我想,您的这种创作历程是比较特殊的,在中国同代作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这样的曲折起伏的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王蒙:上世纪50年代的写作,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上了一个底色,这个底色是比较阳光、比较光明的,因为它正处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当然,现在看来,这里面也有很多幼稚,有很多理想和现实的脱节,甚至也有某种简单、片面和“极左”倾向的东西。譬如说在小说《青春万岁》里,我曾批评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叫做李春的中学生。现在已有评论家提出,李春是不该被批评的,她无非是自己做自己的功课,不想参加班里的活动,她有权利做出这样的选择,说不定这种选择恰恰是正确的,至少她算不上一个落后的、转变的典型。现在看来,也是一个角度的说法。而我当年的义正辞严,可能就是我当初简单和幼稚的某种表现吧。
然后呢,20多年间我处于被封杀的情境中,不过,我的写作虽被封杀,但我的生活和从实际中学习的劲头并没有减少。这期间,我在北京郊区、在新疆地区参加劳动,尤其是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一下子跑到边远的新疆,对地方工作的特色、对广大农民,还有那种异质文化,也就是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等等,对我也有很大的充实。但我有一个特点是,在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改变之后,我不会就把过去完全否定,我并不认为我到新疆农村劳动了,回想起50年代初期对革命、对新中国的向往,就认为那时候像梦幻一样。我知道,它确确实实存在着,不管历史怎么变动,我们用不着以今天来否定昨天,再用明天来否定今天。
到了后“文革”时代,我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甚至是充满激情的写作新阶段。我消化了那种青春的写作,也消化了被封杀的、沉默的状态,但同时,也认真地思考着自己这样一种生活经验。我觉得我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对我的经历,我并不是一种近乎纯然地怀念、歌唱,也不纯然是牢骚、怨恨,而更从一个历史的和人生的必然性上来看待这一切变化。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他有青春的经验,有被折磨的、碰壁的经验,有被封杀的经验,有被打入社会底层的经验,也有恢复了自己原来的社会地位等等具有很多可能性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可贵的,都值得认真记取,认真回顾和反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虽然我也读书,但更多的是靠我人生的经验,靠我所读的人生这本大书。
宋炳辉:我记得80年代初我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您刚从新疆回到北京不久,当时您用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复杂经历和创作立足点和视野。我觉得您是想在这样广阔的空间和时间里,集中表现这样一种经历、感受和思考。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您集中推出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它们所叙述的故事,它们包含的激情和理性,包括艺术手法上的探索,在当时反响极大。
沿着刚才所说的问题,我在考虑您的创作与同时代其他作家还有一个不完全一样的地方:一般作家的写作,在文体的驾驭上是从“小”到“大”,先从篇幅较小的诗歌或者短篇小说入手,然后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而您给一般读者的印象是,一开始就是大部头,您是从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始自己的写作旅程的,然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确立您在文坛地位的倒是一批中短篇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王蒙:从小到大是一般规律,但也有很多特殊的个案。我当时一上来就选择长篇,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有一个具体原因。因为我的写法比较特别,我的风格和50年代中国的作家相比也不一样。我的作品中,贯穿了一种情绪。具体地说,如果我的作品没有一定的规模,我认为它可能就是站不住的,如果我用那种方式写一个短篇的话,可能很快就被否定掉了,或者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我的作品故事性不强,情节也并不吸引人。
宋炳辉:在您的自传中,您曾用了一个词是“情绪”,来说明您早期的写作。
王蒙:是的。在写作中,我所倾吐的,最最激动作者本人的莫过于情绪的表达了,说成书写激情也行。所以陆文夫一直喜欢说王蒙首先是诗人。你刚才说的一开始就写长篇作品,我觉得就和这个原因有关。
比较有趣的是《青春万岁》,从文艺界对它的评价来说,并不特别高,但我从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到1979年才正式出书,历时25年。而从问世以来,至今每隔两、三年都会重印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书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许多50年代曾受到非常高评价的书,现在可能只有研究者因为研究才去读它,一般读者不会再去买了。现在也更不会每隔两年印一次《红岩》,或每隔三年印一次《青春之歌》,或每隔三年印那些认为写得比较好的,比如赵树理的、孙犁的小说。但《青春万岁》确实是到今天为止,仍然在不断的印行过程中,哪怕是印上2000册、1500册,但它隔几年就需要印一次,说明它总还是有相当的读者群,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而我真正所谓成名,造成影响的则是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发表,弄出很大的动静来(笑)。至于“文革”后,这段写作没有停止过,一直还都是延续下来了。
宋炳辉:我记得我读小说《青春万岁》和看电影《青春万岁》几乎是同时的,那时刚刚步入大学校园。这样的阅读经验也许混同了电影和小说两种不同的文类,但对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却使您小说的人物一个个都有了具体可感的容貌特征,也更直接地激发了我的审美情感。我觉得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里面都贯注了一种理想和激情,而且对我这一代在60年代出生、70年代初开始上学读书的正在成长阶段的青年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我实在是流着泪看完《青春万岁》的,里面有很多台词,比如序诗的开头几句:“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珞,编织你们。”那个时候很容易激发起我的情感。现在可能会带着一些理性的东西去读这个作品,但当时是非常地投入,所以我想它能够不断地重印,一直拥有它的读者,还是和这个有关系,青春总是充满蓬勃的热情和希望,年少的一代需要这样的情感释放。
我记得您在和郜元宝的对话中用了一对名词,就是“前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我觉得“前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后者中,理想因素被正面描述、叙说、陈述可能比较少了,一般人都不大愿意这样做,这可能和这个社会的复杂多元的现状有关,那种理想的正面表述容易导致某种伤害,常常被称作“冒傻气”,所以人们不大敢正面说,正面表现。但事实上我觉得,不管社会和文化环境有怎样的变化,理想和激情的正面叙述还是人性中健康的、自然的一部分,它应该受到起码的尊重。
另外,我还有一些问题,因为我是做比较文学研究的,我平时考虑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作家的创作资源,而外来资源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翼。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外来文学和文化资源是异常丰富的,特别是20世纪初期以来,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各个时期的诸多思想和文学都有大量的介绍,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一个西风东渐的高峰时代,之外还有来自日本、俄国和印度等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总之,历时几个世纪的外国文化思潮同时被推倒在一个平面上,加以引进,这是一笔令人眼花缭乱的精神财富。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本来丰富的资源趋于相对单一,发展到“文革”时期,几近于封闭,直到70年代末,对外之门才重新次第开启,而您的创作实践和人生经历,正见证了自50年代以来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的重大变迁。像您这样一位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我们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里,您一步一步地展开创作,取得了今天这样的重大成就。那么对您来说,那些外国的文学、文化、思想资源,肯定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又是较为特殊的作用吧?
王蒙:我接触外国文学,曾经也非常投入。譬如说俄苏文学,包括那个俄罗斯文学最辉煌的年代,像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前夜》,我读的是如醉如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契诃夫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戏剧,我十分沉迷。我说过,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在我处境最坏的时候,我没完没了地读狄更斯的作品,我从他笔下人物命运的大沉大浮、大开大阖中,多少获得一些人生的启示。古典的当然像巴尔扎克、雨果,像梅里美、惠特曼,像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等等,这些都使我曾经激动过。后来,我读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就特别能够扭住一个人的灵魂,他的那种滔滔不绝……,我后来看过他妻子写的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好赌,欠了债,当出版商要起诉他的时候,他就没日没夜地口述,像疯了一样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口述,他老婆本来就是他的速记员,飞快地打出来,太可怕了,像疯了一样,所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有时候一连二十页不分段,就像连珠炮、机关枪,像山洪泛滥一样,给我特别深的印象。现在我接触的比较多了,我觉得美国的约翰·契弗、杜鲁门·卡波特,还有约翰·厄普代克,他们的作品风格相对简练一点,他们擅长用一种非正规的比喻,脱离了我们过去在修辞上所能理解的那种比喻和语言的表达方式,对我的影响也还是有的。但是,说老实话,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比不上中国古典唐诗、宋词。
宋炳辉:对于创作来说,我也是这么考虑的,文学资源只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对于一个中国作家而言,你不可能用他所阅读和了解的外国文学作品来解释他的创作,这是做不到的,勉强做出一些解释也不充分,只能说明是他的一部分创作资源。而且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像您这一代作家,因为共和国成立以后,整个文化和政治的特殊性,中外文化的交往体现出一个明显的阶段性。解放初期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边倒”,文学的交往也是这样的;然后,中间的“文革”时期几乎可以说是相对封闭的;再到开放以后达成比较正常的一种对外文化和文学交往。阶段性比较明显。这种阶段性,在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中国现当代作家身上,在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审美倾向等方面,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代际和群体差异。所以,对您的同时代作家,包括年纪比您还大一点的作家来说,只要是在解放区,不是在30年代或者20年代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在对外来文化和文学的知识结构上,多多少少都会有某种限制,所以这个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当然个人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后来不断地拓展自己,获得了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比如您。
80年代,您从新疆回到北京以后,先后在作家协会、文化部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您在一开始也谈到您的生活阅历,我想这一部分工作实践也是一种重要阅历,因为从我主观来考虑,您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您所做的事情,所接触的事务,包括整个国家的、世界的、国际间的资讯是不一样的,您获得这样的资讯,对社会、对现实的判断就会和别的作家不一样。这个问题,您在其它地方也说到过,我想请您再说说,在这样一个双重身份的情况之下,您觉得行政方面的工作与您的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所,您的行政方面的经历对创作有什么帮助?
王蒙: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通常作家和官员之间往往有较大的隔膜,也很难做到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但是,我从小、从少年时代起就选择了政治,现在想再回过头去,想重新选择是不可能的,我就这样介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同时,我又确实是用一种文学的激情来从事创作,我不但用文学的激情来从事创作,而且也用文学的激情来接受、理解、批评我们的政治生活。你看了我的第一部自传《半生多事》,就会体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也是我在50年代受挫的原因之一。当你用文学化的眼光来看待政治的时候,你肯定会倒霉;如果你就事论事,我当时其实已经是一个挺有经验的干部了,我根本不会犯林震那种错误,可是当把他文学化以后呢,我就变成林震了,但实际生活中我并不是林震,我也不是一个到处爱提意见的人,我甚至是相反的一种人。可是,我也没有反过来,用文学的观点把政治生活、把领导事务、把那种官员的生活全盘否定,因为我接触到的官员和我接触到的作家一样,都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不是神仙,没有那么伟大,但也不是妖魔鬼怪,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为很不起眼的一点人事生半天气,他们也有口误、笔误,突然发发脾气,等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以一种文人的心态来接受这些经验的。对于文学来说,譬如我参与的这些领导工作的经验,不但是政治的经验、社会的经验,同样也是文学的经验,它是一种心灵的经验,内心的经验。当你看到人们用另一种语言,高高在上的或者居高临下的,或者他首先考虑到政治的利益、政治的稳定性,考虑到权力运作的那种语言在研究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同样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去体会他,观察他。我相信胡风的那句话:“到处有生活”,生活和生活不一样,当妓女和当警察是两种不同的经验,但这都是生活,这是事实。
宋炳辉:您在《半生多事》中回忆写作《青春万岁》的时候说到您当年的一个感觉,您说,“写一个长篇,需要的是一种类似当‘领导人’的品质:胸襟、境界、才能和手段。”
王蒙:对,就是这个意思吧。我说这个话仅限于指对于作品的组织结构,无他意。另外,我和别人稍微有点不同呢,就是我考虑一个问题,往往从这个角度说完以后,又从另一个角度说一说,譬如某件事,那些作家都很高兴,都很兴奋,但我又从另一方面看到这里面埋伏的一些问题,我把两面、三面的话都说到了,这并不是我生性圆滑,面面俱到,而是我本身有这个条件,我既从这方面考虑到,也从那方面考虑到,这样我对生活的感受就比较立体,我觉得,就这些方面来说,我完全承认,我的政治经验,我担任各种社会职务的经验,同样是我写作的重要资源,既是精神的资源,又是生活经验的资源。
宋炳辉:刚才说到外国文化和文学资源。我看过您的《苏联祭》一书,其实当年在读您80年代的几个中短篇,包括《布礼》、《蝴蝶》、《如歌的行板》、《相见时难》等作品的时候,有个感受非常强烈,那就是您对苏联文化的情结非常深。而且我的感觉是,在你的同代作家中间,在当时对外来文化接受过程中,这种外国文化的养料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情况。但是在您的作品中,包括作品之外您的其它文字中间,这么坦率地、密度比较高地表达这种“苏联情结”,倒是不多见。
王蒙:我在《苏联祭》中曾说过,青春、爱情、文学和苏联对我来说是四而一,一而四的东西,这里头也有决定着我命运的东西。因为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和苏联从文化传统,一直到政治运作,它并不完全一样。一个人太钟情于苏联的话,他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容易受挫,所以最好是不要进一步去研究,去解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真实的苏联我其实并不了解,我所说的苏联也不是一个真实的苏联,而是经过了一个年轻的、才十几岁的小革命者所美化的、大大文学化了的那个苏联。那个苏联是王蒙的苏联、是文学的苏联,并不是具体的那个北方大国。
宋炳辉:后来自斯大林时代过去之后,中苏关系逐渐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作为两个国家实体,其在国际关系上的摩擦、冲突及其负面影响,一直到政治上的对立都相继反映出来了。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所理解和表达的苏联,只是一个个体所面对的一个国家形象,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学形象。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不同文化的接触和碰撞,确实可以激发起某种表达和表现的冲动。对您而言,您除了有苏联文化的体验和想象之外,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出访体验,还有长期在新疆维吾尔族生活的经验。我想,这些经验都是您创作的宝贵资源。我读您的第二部自传《大块文章》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这在我做研究时也注意到了。那就是,您在美国依阿华访问期间,在依阿华河畔的五月花公寓里,写作《杂色》的经过,您用的标题也很有意思,叫做《在美国思念新疆草原》。一种看起来纯粹是中国经验,或者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生存经验,却在完全异域的文化场景中被激发出来,这是颇值得注意的一种想象。这个写作情景,好像当年的评论家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倒令我想起另外一个类似的情景,就是王安忆的《小鲍庄》,那个曾经被批评家当做寻根小说代表作之一的作品,同样是她第一次出访美国之后才突然找到表达的感觉的。我认为这种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王蒙先生,据说您的维吾尔语是非常好的,是吧?
王蒙:是。
宋炳辉:这在当代汉族作家中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您维语的听、读、写都没问题吧?
王蒙:我自己要用维语写文章呢,有点困难,因为有时候它的拼写记不太清。
宋炳辉:英文呢?
王蒙:英文后来学过,可以写一点,也翻译过一些东西。
宋炳辉:这对您来说,又多了一种文化视野。我是考虑到这个情况,总体而言,当代作家和现代作家在这点上是有一些不同的。现代作家的外文底子相对都比较好,他们一般都能够读懂一二种原文作品,甚至,有许多人比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都是翻译家。现当代作家在总体上的这一差异,多少也反映在他们的创作风格的差异中。那么,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个问题呢,其中的特殊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新时期作家,特别是比您更年轻的这一辈作家,外国文学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对他们来说,曾经是最最投入的、浸润非常深的一种资源。对他们来说,往往那些一开始确立其文坛地位的作品,都和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和熟悉,恰恰又是通过翻译文本来读的,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也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在讨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时候,往往简单地用“影响”去概括和描述,但事实上,仅就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而言,直接阅读原文和借助于翻译文本是两种不同的方式,特别是假如一个作家主要是通过翻译去了解外国文学,这里涉及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一些。
而您与外国文学的接触则同时包含了两种方式,借您的说法,是比别人多出一条“命”来。我看您在传记里提到,在读翻译文本的时候,您说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语法、构词和造句的方式等等,包括您提到您的小说《风筝飘带》的写作和杜鲁门·卡波特的《灾星》之间的关联,这也不能简单地用“影响”这个词来概括,它只能说像一种催化剂促发了您的某种创作冲动。您能不能简单谈谈,如果具体地说,外国文学的作品在哪些层面上可能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王蒙:我有一个观点就是,翻译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的语言资源之一。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文学语言资源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古文,包括文言文。譬如鲁迅的文章中有很多语汇是从文言文那儿来的,李敖认为这是鲁迅的一个很大的缺欠,我认为这是鲁迅的一个特色,这同样是一种资源。第二个就是古代的白话,我觉得这也非常多,譬如很多研究者认为《儿女英雄传》虽然内容写得并不很精彩,但与北京话运用得非常好的《红楼梦》里的语言,与《儒林外史》的语言、《三言二拍》的语言,都是古代白话的一种优秀文本,这也是一个资源。第三个资源就是当代的口语。比如王朔都用当代的口语写作。第四个就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亦文亦白、亦中亦西的那种语言,尤其是那些比较典型的写散文的作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比如朱自清、徐志摩、落华生、刘半农等等。最后一个资源就是翻译语言,翻译语言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在编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我是主编,我就建议这个《新文学大系》起码要包括翻译文学作品的目录,你可能不收入具体的文本,但起码要在目录上反映出来。因为在这一个时期所翻译的大量作品,比如《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曾经很热,这些对中国本身的文学是起了作用的。王小波就很强调自己是受翻译文学影响的。而且,有些翻译家,他们的语言也很漂亮,有自己的魅力。就我个人来说,当然也受这方面影响。比如我现在注意到,有时候我写的文字中,常有“……的”的结构,用的也比较多,这都是受翻译作品影响的一种表现吧。
宋炳辉:现在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倒是已经引起重视了。因为我做比较文学研究,对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两个领域,多少都会涉足一点。到目前为止,中国近代以来的翻译文学史,外国文学的学者在做,中国文学研究者——比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杨义教授等等,他们也在做,都在重视这一领域。因此,不管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大家都开始认真地涉及这一领域了。其实一般所谓的“外国文学”,说到底,是外国人并不认可的“外国文学”,而是由中国人用汉语转述和翻译的“外国文学”,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的莎士比亚,是朱生豪的莎士比亚,不是英文背景之下的莎士比亚,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莎士比亚。现在,这些问题及其背后所包含的诸多问题的研究,在比较文学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王蒙: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宋炳辉:您刚才提到您主编的《新文学大系》的编辑方针,使我想起90年代初,施蛰存先生和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他们在当时的编辑中,就已专门设立了“翻译卷”,施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序文,其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翻译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朱自清先生在最早的“新文学讲稿”里头——这可能是现在看得到的最早的关于新文学的讲稿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其中有一讲就是关于翻译文学的,可惜当时很多作家和学者对之都不够重视。后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种对苏联的看法一样,把它看成是一个本体,而不是去追究我们所看到的真实内容。
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作家的创作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您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一方面通过阅读,阅读外国作家的创作文本,通过文字性的信息,获得一种资源、受到一种启发;另外一个方面,如您在工作中,在文化交往活动中,直接和外国的接触,包括您去外国旅行、访问等等,同样是一种资源,一种重要的激发机制。我觉得对当代作家来说,这些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前段时间在讨论王安忆的创作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王安忆第一次和她母亲出国的经历,和她创作上的明显转变实际上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这与阅读外国文学文本还不一样,它是给作家一个完整的、经验上的变化,您在《大块文章》中也提到您第一次去德国的感受。
王蒙:我和郜元宝通信的时候,他就提到过一点,他说我写的游记特别多,实际上数量确实非常多,写美国,写苏联,写墨西哥,写非洲,写印度,还有最近写伊朗的等等。但我个人看法是,我其实不是在写游记,我写的是一种对世界的观点,中国人长期的处境使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都和他在地球上的生存经验有关。
譬如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为什么在当时我形成了相对孤立的、和多数“文友”不一致的观点呢?这就和我在国外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在第三部自传《九命七羊》里有写到,因为我在80年代后期去过波兰和匈牙利,这是东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我还去过摩洛哥,摩洛哥是一个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对这三个国家文化的了解,都与我对批评西方发达国家人文精神的缺失的理解有关。所以我对世界的了解,对世界的观念,对人的现代性的表现的理解是,你不光要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土地,同时,你也应从世界上得到另外一些信息。所以说《灾星》、《多雪的冬天》和《蝴蝶》的某些相似,这些都比较简单,某一情节有类似,或者受某种启发,或者是巧合,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关系,用不着下大功夫去分析它,值得注意的倒是,它更多地表现了我认识问题的一种角度,一种胸襟,为什么我和有些人的看法不一样,就因为我知道许多其它的情况,包括一些看起来很小、很琐屑的事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中国民航局所搞的飞机误点赔偿,我就觉得不易行通,它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中国乘客在法国闹事,造成了很多不良后果。因为我坐过许多国家的飞机航线,加在一块的话非常多,各种误点的情形都碰到过,最严重的是在美国,有误过一天的,有误过两天的,哪可能赔偿呀,顶多给你提供一个10美元的饭卡,还有一个住宿的地方而已,美国相对更周到一些,它还给你提供一笔打长途电话的费用,别的就再没有赔偿了。所以,我就认为,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的误点赔偿,你只会挑起民航乘客和机场,和航空公司闹矛盾。
宋炳辉:文本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确不能等同。另外,我再问一个关于写作的具体问题。您在您的传记里提到您的写作状态,我也颇感兴趣。你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写作生活的时候,您用一个很幽默的词,说您的创作是“不摆谱”的,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定地坐下来,您在写作中还喜欢站起来捅捅煤炉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写作状态比较特殊,至少与一般读者的想象差异较大,这是一点。另外,我在读您的自传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您在回顾和描述半个多世纪的写作和生活时,里面有许多细节都非常清楚,非常具体。虽然我想,作家一般都有非同常人的记忆力,但有的作家同时通过日记来保存和磨砺他对生活细节的记忆。因此我还是很好奇,您平时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王蒙:我在90年代以前从来不写日记,这和政治运动有关,在政治运动里边,日记和书信都是危险的东西。再一个,我太迷信自己的记忆了,但是后来事实也证明,我现在也有许多记错的地方。我的自传里面,我故意说假话是没有的,但是有些也的确是记错了,比如把某一年的事儿记成另一年了,或者把张三的事儿记到李四身上,这都有可能。但是,即使这样,我还得不谦虚地说我的记忆力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那些给我印象深的东西,我永远能够想起他(她)的音容笑貌等等。至于我写作的状态,我曾自己给自己开玩笑说,这和我20多年的复杂经历也有关,所以你没权利一定要求一个书房,不能被打扰,你家里的事儿,你不管谁管呢?我妻子每天要去上课,她有很多的课,那是很紧张的。冬天的时候,那有蒸锅,我在这边写东西,写着写着我还得去管那个蒸锅,所以我自称我自己是“全天候”的写作人。
宋炳辉:这种状态其实是挺好的,把写作和生活融为一体了。我再问您一个大一些的问题,刚才也已经提到过,就是关于写作资源的问题。您写过许多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包括《红楼梦》,包括李商隐的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您还是李商隐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吧?您能不能谈谈您的写作资源中古典的、传统的部分?
王蒙:我受古典文学的影响最深的是古典诗词。对中国古典诗词,我当然没有什么深厚的研究,我这是讲老实话,别人笑我也不要紧。我对唐诗的理解基本上就是唐诗三百首的水平,但唐诗三百首却是多次读过,而且其中大量的诗我都能够背诵,我觉得从里面得到很多的滋养。宋词里头读得最多的是苏轼和辛弃疾的词,相反,柳咏的词就没有特别地感动我。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李商隐,从一个创作人的心态看,我觉得李商隐的东西特别值得去咀嚼,而我们如果想从“本事”上加以考证地解说,有时是徒劳的,或者是排他性的。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某个诗句、某个意象应该是这样,就不许解释成那样,可我恰恰认为这些解说都可以成立,但都不够成所谓“本事”,因为“本事”不是一个文学评论的范畴,而是一个史学的考证的东西,你不能用考证和史学来代替对诗的理解。李商隐的许多东西对我作品的情调是起作用的,比如我的《蝴蝶》,既和庄子有某种关系,也和李商隐的那种“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情调有关。《相见时难》那个中篇小说,就连题目用的都是李商隐的诗。还有李白……等等。我最投入、最称颂不已的还是《红楼梦》,可是我写的小说和《红楼梦》的写法是不一样的,我缺少那种非常生动的大场面的描写。所以,我想这种影响有时候不是最直接的,它是对你的情绪、情调或者对人生的体会都有某种影响。有人还说我的《青春万岁》,里头有一段写杨蔷云在春夜的晚上,去公园里去玩,回来晚了,就跳过院墙进来……,说这里头都有《红楼梦》的影子,我觉得这个太牵强了。我觉得所谓的影响,就和你吃了牛奶变成了营养一样,不是说你吃了牛奶就一定长牛肉。
宋炳辉:对,即便是对作家创作资源的合理分析,只不过有助于我们对其创作整体的理解,但并不足以说明他的独创性内涵。不过,如果从您自己的感受而言,除了您说的情绪或者情调之外,您在创作语言的运用上和古典资源之间,有哪些比较突出的关联呢?比如意境,比如修辞方式或者语汇等等?
王蒙:我觉得我在语言上总的来说是不拘一格的。有少量的翻译文体的味道,尤其是在写论文的时候。里头同样也不拒绝北京话,你看了我的作品,发现我这里头既有比较幽默的、比较荒诞的,好像在那儿胡侃的文章、文体也是有的;也有相对比较抒情的、比较矜持的。我尽量做到不拘一格,只要是能用得上的,我都不拒绝。
宋炳辉:王蒙先生,您从1953年十九岁开始写作《青春万岁》至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至今还保持着这么充沛的创作激情,最近刚刚完成了一百几十万字的长篇自传,听说马上又有关于《老子》的著作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你的写作和文学活动贯穿和见证了整个当代文学史。您不仅有如此大量的创作文字,而且还深深地参与了新中国的政治生活。即便仅从您的写作实践来看,除了小说写作之外,您还广泛涉猎了散文、自由体诗和旧体诗、文学和文化批评、文学翻译甚至是古典文化和文学经典的研究等领域,为此您获得了无数的读者,也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绕过去的,具有标志性的作家。回顾这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您一定有许多感慨,这些您在自传中当然已经有非常系统的表述了。在这里,您是否还有进一步的表述?或者某种概述?
王蒙:我已多次讲过,每条狗都有自己的时间段(英谚:every dog has it’s period),从五三年到现在,我写作的时间跨度已经超过了五十五年,从二十一年前,就不断有人宣告王某的过时或江郎才尽,早该尽啦,那是当然。这让我想起一些哥们儿对于瓦尔德内尔何时退休的着迷与关怀。急什么,这位杰出的运动员不是歇了吗?着急的朋友可以安慰自己,老王秋后的蚂蚱,跳跶不多久了,该歇菜就歇菜,该咯儿屁就咯儿屁,何足道哉?
宋炳辉:谢谢您,谢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