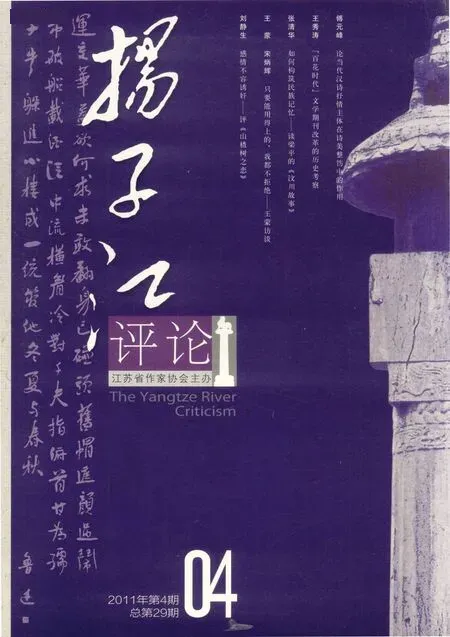不彻底地挣脱:《河岸》与《风和日丽》中的“革命”书写
2011-11-19李旺
李 旺
对于革命的讲述,包括讲述革命发生和革命如何走向胜利是新的政权建立后对自身进行合法性论证的题中之意。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就是这一时代意志的产物。“以革命之名与为了革命”成为一九四九年之后文学话语的“钦定”诉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对负载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强烈拒斥的“先锋文学”首先开刀的对象却也是革命史讲述的标本,这可以看做是一个革命高悬的国家的文学实验者的先天基因。《罂粟之家》和《迷舟》搅动了革命发生史讲述的方向。前者给革命史讲述中农民的纯洁性打上了问号,后者则对革命者的私生活发生了持久的兴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影响颇大的《白鹿原》也试图写出历史的偶然,但它浓烈的道德含量终于使它只能置入那些布满家国史诗冲动的作品序列中。革命的刻板面孔去日未远,却又挟着怀旧的装置再次登场,近年大量由关乎革命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的畅销一再使我们置身于红色的汪洋。革命的高压性竟成为在破碎的现实中的人们征询到的唯一精神逃路,而这种向革命的回归又无意中与主旋律倡导暗符契节。以反刍革命激情来解脱精神危机是充斥着政治的人的国家的悲哀。出现在零零年代的《河岸》(2009)与《风和日丽》(2010)是对于笼罩的这种革命氛围的一次有力地挣脱,虽然它们挣脱得并不彻底。
革命起源与个人史
把个人命运镶嵌在革命历史轨辙中是革命讲述文本的经典表达,个人历史淹没在革命史中也是此种表述的必然取向。这些成规作为《河岸》与《风和日丽》叙事方式的潜文本而存在。邓少香与尹泽桂都是处于革命源头这一革命叙述要害部位的人物。然而,革命与个人的力图缝合与不断游离成为小说的叙事核心,曾经的毋庸置疑的革命史讲述成为两部小说一再质询的对象。在《河岸》中,邓少香投身与献身革命的事迹几经修正,身份由棺材小姐到逃荒女子,后代库文轩的革命血统遭到质疑被逐出革命队伍。“邓少香烈士生平鉴定小组”在形塑烈士形象时动用武力,彻底删除革命者个人史的私密性质。《风和日丽》中有一个颇堪玩味的对照:在为革命正名的年代,尹泽桂的革命史与个人情史彼此缠绕是个关乎革命者生死存亡的禁忌,然而当时代取譬于革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的时候,革命被投注了新的话语色泽。尹泽桂的个人情史被大肆涂抹渲染以吸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游客。如果说革命文学起步之时,情爱与革命二者趋同的狂热为徘徊于十字街头的时代青年注入了最初的激情,而当革命历史的激情讲述日显乏力,借重革命者私生活的玫瑰色成为当下主流革命叙述的流行策略。《风和日丽》对这种暧昧的时代氛围的微妙表达道出了当下中国的精神境遇。那些红色消费产品中的草莽英雄/平民英雄的塑造奉献的依然是革命的亲和力,《河岸》与《风和日丽》剥落革命之神的点点漆金却无意于表现革命的亲民性,而是暴露了革命、革命讲述的种种乖谬。
《河岸》中的纪念碑与《风和日丽》中的附录可以看做是小说主体叙事的互文本。二者都以历史的证物/证词形式试图还原历史,纪念碑刻写了邓少香烈士的丰功伟绩,是革命者的命名式与纪念式。然而这一命名与纪念却是包括了驱除与放逐的暴力。附录是尹泽桂成为将军之前以诗人之笔满怀诗情的一腔誓言,是弱国子民的铁血豪情。尹泽桂否认了这篇“少作”,后来诗中的一句又出现在了尹泽桂为伍天安立放的墓碑上。一碑一纸这两个一直以来的“历史”的“同名物”在这里变得面目模糊。碑和纸以及碑和纸上的历史都是对过去文本化而留下的痕迹。库文轩的肩碑投水是保存历史命名的徒劳,杨小翼的历史研究是剥离历史权力的一次冒险尝试。库文轩成为革命命名的祭品,杨小翼对革命命名的突围遭遇到的是革命亲历者的三缄其口。《河岸》与《风和日丽》以碑文和墨迹在铭刻与淹没之间的混乱揭开了革命历史的暴力和迷离。
血缘与阴影
纯正革命血统是书写革命谱系至为关健的一环,它关涉着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烈士邓少香的革命履历就是革命历史讲述提纯过程的产物,而身份含糊的库文轩和库东亮成为了阶级异己分子。同样,遮蔽尹泽桂的浪漫史和贬抑革命私生子杨小翼也是对革命路上的坏女人的惩罚与警戒。《河岸》与《风和日丽》都讲述了革命接班人序列中极为独特的群体:烈士遗孤与革命者的私生子。由革命者而执政者的革命之父让杨小翼在民间日常伦理中区别于革命群众,(升学与招工的便利)但她的革命之私的暧昧气息又断然剪掉了她的革命脐带,邓少香为革命捐躯的故事形态经历了由真人真事到传说的演义过程,革命谱系初拟阶段库文轩以形象实证,而当革命偶像在革命群众的精神视域中已然生成,对革命烈士的认同与崇拜与日俱增,库文轩形象的存在与否已经无足轻重,他的被抽取便也不难理解。
《河岸》和《风和日丽》写到了库文轩与杨小翼对革命之母的固守和革命之父的追认,这可看做是对锲进革命文本的行为的书写。当革命以旁逸斜出的姿势幻化成历史,革命的后代只能以回顾的形式重写自己的革命来路。库文轩在金雀河上十三年都在为自己的烈士遗孤身份的丢弃而申诉,而极有意味的是,库文轩一再地向革命正史回归,最终回归到那个被塑造的传说的源头。他再也无法进入成型的历史文本,只能负载它而去。被排除在革命行列之外的恐惧(亦或是如库东亮所言,对一张烈属证的可盼而不可得)使得库文轩被阉割的焦虑围困,最终剪掉了自己的阴茎。革命提纯系统对历史文本进行修改以重述历史,而试图跻身革命历史的库文轩只能通过阉割获得彻底的纯洁。这种阉割的焦虑使得库东亮也笼罩在情爱的原罪之中。这可谓是革命修辞最露骨的隐喻。
库东亮的成长史就是在一个历史谜团中展开的。由于历史阴影的笼罩,他的个人史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他将承受比库文轩更为惨烈的人生,库文轩对他的监视是他承受历史之刃的最沉重处,他无法逃避,被判处不得归岸,成为无名的历史的浪者。江慧仙是又一个无历史的历史孤女,她是邓少香的化身,然而这是一个被装扮成的邓少香,李铁梅是革命英雄偶像中的新的一位,江慧仙却没有识别扮演这一行为的虚构性,舞台之上与舞台之下之间的身份翻转再一次泄露了历史的编码形式之一种,江慧仙对李铁梅的误认将遭受不服从历史命名(作为一个革命戏剧演员)的罪与罚。
杨小翼的一生都是在试图辨认自己的身份,而终究无果。在革命的正册里是不可能有杨小翼的,她是革命者疗伤路上的副产品,成为一个革命激情的剩余物而存留,会被作为革命史的删改对象。于是杨小翼的生命史竟然是一则混乱而迷狂终于形单影只的故事。她以僭越之举窥视革命来历而不得,而由亲历者转换为访问者才可接触到对革命史的生成过程。她的研究也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叙述。革命本身成为一个虚妄和空洞的符码,她以革命史的参与者之身成为革命史的研究者,被遗弃在革命行列之外。可对这一革命激情的汲取并未完结,伍天安对广场集会的巨大热情不仅由于一份革命血统被盗走的急切,也是由于一个浸淫了数十年革命激情的国家的民众的无意识眷恋和向往。
寻革命之父不得的杨小翼却在一个患有革命后遗症的年代里感受到革命的诗意与温暖,因为革命之父的压抑的刘世军则希望再次革命,而失去了具体革命之父对象的伍天安则渴望被一种革命之父的精神所抚慰。当革命已然胜利,革命遗孤将不仅仅指那些日常伦理中的革命者的嫡系,而是整个国家的民众也成为一个巨无霸的革命后裔。当寻父冲动变为一种广场情结,这不仅是从杨小翼到伍天安的转移(对尹泽桂的指认由父亲到外公),而伍思岷的缺席与还原亦与革命有关,从“文革”的造反派领袖到“文革”结束后的人民的罪人,再到走上学生集会的演讲台,在伍思岷那里,权力欲与清君侧的正义感共同赋予了他革命的激情,而伍天安的爱情挫折则在父亲于学生集会的一呼百应中终于治愈。
革命起始处的尹泽桂因爱情而革命,革命后年代的伍天安因爱情而依靠革命的激情,这表面相似的场景是一段貌合神离的历史误会,这一误会的指证者是作为革命者私生子的杨小翼。这一旁观的位置的获得受益于她被区隔在革命历史之外。在革命血统已经确定的历史中,任何革命举动都将被判处罚刑,而革命血统的散布史长久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之子,这漫漶的革命冲动归宿于同一个源头,而革命的形式的释放本身却又成为弑父之举。在境外的伍思岷的生存方式更富意味:“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不仅是他个人际遇的一个象征,更是他所寄托的翻身闹革命的理想的一个必然结局。在舆论形态上共产主义定于一尊实则极权思想无处不在的国家,现实中的藏污纳垢与意识形态的空前纯洁的截然对比每每为革命和斗争这种暴力行为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可以在思维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致它们不再能看清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可能消弱它们的支配感。在‘意识形态’一词中内含着一种洞悉,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既对其本身,也对其他方面遮掩了真实的社会状况,从而使集体无意识得到稳定。”①伍思岷在“文革”中的举动就是这种扭曲着的社会形态再形象不过的注脚,同时他也是一个牺牲品,权力施暴之后的道德抚慰往往在征用民众的道德正义中完成,循环往复的政治斗争及与之相随的忠奸好恶的简单指认让这个久经裁制的民族变得嗜血。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让尝到过夺权甜头的伍思岷再次掀起革命的激情,然而换来的却是儿子的尸体和自己的逃离。“个人心理和统治组织已经形成悲剧性的结合”②;革命意识形态灌输的唯一性与解释权利的专制性让浸淫于其间的民众只能沦为国家机器的被豢养者,由英雄到小丑成为一个革命国家的子民最终的结局。这不仅关联一部革命经典文本,更关乎一种革命后年代的现实指涉。
说出来的可能性
不论《河岸》还是《风和日丽》都怀着说出来的隐秘愿望。这份不得已在后者那里尤其耀眼。这是文学和历史的双重悲伤。革命、“文革”以及众多的革命的孪生体成为文学讲述的精神枷锁。我承认这样的观点:“历史文件所揭示的世界也不是那么易于接近的。历史文件和文学本文均是不已知的。”③可是,对于当代小说而言,在杂乱的历史荆棘丛中,文学本文的历史文件冲动或许有着另一种可能性,在对禁忌的冲撞中洗涤言说行为的污秽。
《河岸》在一个革命斗争不断的情境中无限制地延宕展开,在一个曾经把革命作为一种全民行为的国家,命名的暴力与驱逐的刑罚,历史与记忆的彼此镌刻与修改,都是革命历史谱系制造中的浓墨重彩之处。历史与文本的合谋也是必然的书写奇观。《河岸》在一个并不新鲜的历史与水的比喻中展示了这个存在于文本化历史中的个人的精神窘境。“在一厘米的窗缝间,我看见了历史的金色光束,金色的历史降落在河面上,半个世纪之前的金雀河水向我奔涌而来,苍苍茫茫,我看见浩荡的河水淹没了婴孩,一条鱼跳出了箩筐。鱼。一条鱼。是一条鱼。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恐惧,那是历史的谜底吗?我父亲如果不是那个箩筐里的婴孩,是那条鱼吗?”④历史回归为一个传说,回归为一个子虚乌有。革命印记的携带者逸出历史之页进入一片苍茫水域。《河岸》在这里陷入了并不能由优美的比喻缓解的迷惘。正如有研究者表达的遗憾那样:作品“忽略了对‘文革’这个有着巨大场域历史空间的表达,只注意了个体性格的表现”⑤,小说意从革命历史塑形中的种种荒诞处揭开塑形境遇中人的伤与痛,继而以革命之手的无处不在隐喻人生漂流的困境,然而后者这一急躁的意图让二者都失去了落脚之地,对阴郁混乱的青春受难的聚焦掩盖了对生成“空屁”命运的荒诞革命的追击。
与《河岸》闭合在一个革命依然继续、斗争远没有完结的框架中不同,《风和日丽》是一部膨胀和压抑混合着的历史编年。在指涉了诸多历史本文之后,以一个历史亲历者/疲惫者的身份表达了历史之感。这个回观的观察位置获得了一份松动历史关口的可能,它提到了一些极为关键的时间: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一九六二、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千禧年。它指向具体事件又虚化事件本身,历史的轮廓在谅解和疲惫的态度中呈现,它以回忆者和过来人的姿态对历史做了解压缩。
“多年以后,杨小翼回忆这段时光,有一种太阳重生的感觉。这种感觉同刘伯伯有关,也同‘革命’这个词语有关。‘革命’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过去的叫做旧社会,现在是新中国。时间开始了。新这个词让眼前的一切明亮起来,让世界放射出光芒来。”⑥
“杨小翼去现场看望天安,在她接触到的学生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嘉年华会的感觉,一种在人群中的浪漫情怀,一种不受束缚、受人注目的光荣之感。杨小翼认识到这种感觉来日已久,并不新鲜,它和革命息息相关,是革命特有的浪漫和爱意的延续。”⑦
以置身事外的位置对置身其间的历史的“精神”分析绕开了激情讲述的泥沼,泄露出浸泡在革命语境中的词语意识形态的杀伤力。可仅仅着眼于词语的规训却容易和革命的宰治达成和解。杨小翼人到中年的温吞目光把小说前半部分的言说激情大面积地灼伤,叙事者把一个颠踬在革命阴霾中的历史的受害者轻易地送入人到中年与世事言和的窄门中。
“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总是着手分析他们文化历史中的‘精神创伤’性质的事件,例如革命,内战。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类的大规模程序,以及丧失原有社会功能却继续在当前社会中起作用的制度。”⑧这样把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等同的行为不至于遭到诟病的前提是:“历史编写和小说被视为具有相同的重塑外形的行为,通过情节的形态重新确定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两者是互补行为。”⑨《河岸》与《风和日丽》在揭开革命的锋利与疯狂之刃之际流露出徘徊之态,书写着革命历史的晦暗遗迹时又悄悄远遁。革命/历史的惊悚面孔悄然乍现终于又隐没在重重的话语帷帐之中,从两部小说走向飘忽可以读解到革命讲述依然面临诸多可能折戟的窘境与险境这一讯息。
【注释】
①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页。
②[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兰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0页。
③⑧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67页。
④苏童:《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⑤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生成》,《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⑥⑦艾伟:《风和日丽》,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40页。
⑨[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