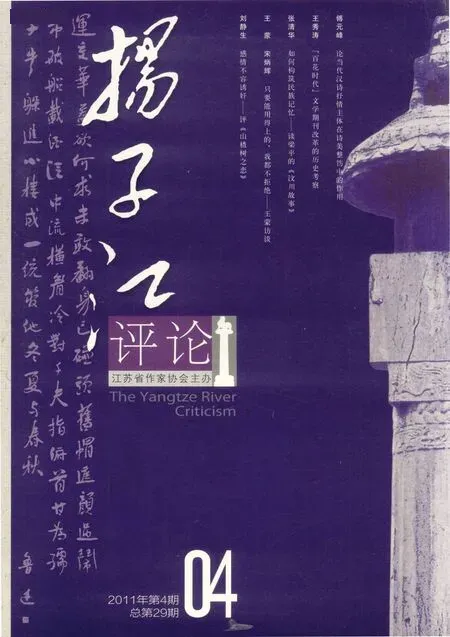嘎代才让与属于他的西藏——嘎代才让诗歌创作论
2011-11-19邱婧
邱 婧
“暮色:在大夏河上安睡的桥
像一匹马,更像一串大昭寺醒着的风铃”
——《拉卜楞·旧桥》,2002
“这些来历不明的花朵和马匹
都挤在这个夏天的湖边干吗呢”
——《青海湖》,2005
“我很早就说了,鹰翅上的文字
早已荡然无存。
庭院的莲花如同天空,迟迟未能在
寂静的领空里喊出春天”
——《七月的幻术》,2010
嘎代才让是一位藏族青年诗人,八零后出生的他活跃于当代汉语诗坛,亦是藏族第三代诗人的领军人物。①单纯就创作而言,藏区是他的“精神高地”,其诗歌中的地景描写、宗教传统、对身份的感知无不与藏族的宗教、社会、文化传统相关,他的生活轨迹在青海与甘南之间游走,也正是由于他较为纯粹的藏族身份,他的写作才更加具有民族志的参考意义。
嘎代才让擅长用炉火纯青的汉语来表达藏人天然的虔诚、明澈、质朴与厚重感,说到这里,我拒绝同意其他评论者对嘎代才让所作出的“异域”的标签。此词源于《楚辞·九章·抽思》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②。此时“异域”意指地理空间的变换,然而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异域”通常是一种粗暴地看待他者的表达。而论者把自我视为主体,将嘎代才让的诗歌视为“异域”表达,就等于将藏地与藏诗指向一个异质性的文化语境,或者将它们“博物馆化”,并且当做人类学考察中的“他者”来看待,这样无疑是偏颇的。不可否认,嘎代才让的诗歌贯穿了藏人神秘的宗教与文化传统,但是,他诗歌的言说亦是当下的(当然也不乏先锋诗歌的痕迹),这些在他的《西藏志》、《北京手记》等长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本文希望通过对其作品的细读深入语言内部,并以此探讨嘎代才让汉语写作中的抒情、语言与修辞,如果艾略特所言“诗歌在未被理解之前就会传达自身意义”成立的话③,那么,我们对嘎代才让写作的考察倾向于语言和修辞就更加无可争辩了。
本文除了对嘎代才让的诗歌做出整体观察之外,还着重讲述与阐释他的两首组诗《甘南印象》、《青海大地》与一首《七月的幻术》,它们分别写于2002年、2005年和2010年。这些诗歌中的地景描写、对隐秘的宗教色彩话语空间的渲染、对历史感的强调都与诗歌语言的陈述完美地结合起来。
一、地景、时间与言语的幻术
从诗人最初的写作《甘南组诗》谈起。本组诗歌共有七首,在《甘南冬日的寒风》中,他写道:“一声马蹄踏过甘南冬日的寂静/它的蹄声沉默/是一望千里的草原”④,如果说在品读这段诗句时单单有意关注“寂静”、“沉默”和“草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意境的所有迷人之处就会因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幅静物画。实质上,嘎代才让将动态的观感以未知的方式呈现在既定的地景空间——草原上。例如“这奔跑而去的寒风,只向着甘南/草原之半个冬天半个夏天:只有空虚的丰收/只有不朽的阴影。/寒风大地,羊群扔下了绳索/酥油灯下谛听心脏的姑娘被亲切唤醒”。
嘎代才让的诗歌包含或体现了一种矛盾的现实。在诗歌的尾句,诗人将未知揭开,“在一粒阳光中我看见:一个是寒风,一个是化身于传说的甘南。”“寒风”与“甘南”——某种气候与一个地理空间几乎成为并置的两个意象,诗人不愿意它们构成貌似真实的修饰关系,而是极力将可感知到的空间的延展性推到读者面前。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时刻是在场的,并且因其在场而引起的隐形的对话关系由此展开——姑娘、羊群、酥油灯与草原等地景描写间接地填充了这个对话关系——诗人瓦解了真实的现场,这样,嘎代才让的语言效果通过断裂、重组等修辞方式而丰满起来。
《甘南组诗》作为其早期的诗作,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特点,譬如对时间的重视,在《素描:草原上出现一匹白马》里,诗人这样写道:“草原的胃,怎么能嚼得动那些游荡在时间之外的马/再次,寒冷紧紧拥抱的风中/那匹白马奔走了。”时间性在抒情诗中起到反向的作用,它不是用来呈现真实的,而是反向地推动了诗歌的陌生化,白马与草原的关系原本是一种固定的生态景观,在诗人嘎代才让这里,白马与其说是自在之物,不如说是被制造出来的,况且是一个带有闯入者气质的符号,另外,在此诗的前几节,诗人亦引用了昌耀的诗作《命运之书》中提及的“跛行的瘦马”,这种悲凉的马的形象和最后一节“奔走”的白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么样的美学关系?这又是一个时间的断裂,“游荡在时间之外”与在场的叙事之外的马并置在文本之中,成为被强化的未知的地景表征。事实上,在组诗的另外一首《荒原,想起宁静的夜晚》中,时间性愈加明显了,“冬日将尽,如果我的步伐不能抵达/沉醉于这座城市的尘埃时”,“之后,黎明出现在渐渐衰老的容颜中/我似乎接近零点的钟声”,“在这样宁静的夜晚,还闻见四周传来的稻香/——踏过荒草,绕过河山后/我想起远方:母亲睡梦中的呼吸声。”诗人大量运用“冬日”、“黎明”、“零点”、“夜晚”、“睡梦”这种直接或者间接富有时间意味的名词,给予诗作以疏离的语言潜能,疏离感和孤独被拉近到绝对的近处,而真实本身则被推到远处并且模糊不清。
到了2005年的诗作《青海大地》,地景描写又一次被诗人发挥到极致——尤其是《青海湖》里的两句——精简亦充满暗示意味的少数语词构建出了无限的话语空间:“这些来历不明的花朵和马匹/都挤在这个夏天的湖边干吗呢”,这样的图像很能够给人以指向自我的幻觉,在场感和明晰与作者的缺席同样令人感觉新奇。由此,花朵和马匹的表面意义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意义从实物游离,如同一场风暴打开了一个缺口,展开全新的观感世界。在《天峻的黄昏》中,“我只瞩目于那无法守住的太阳/先是风,然后是遍布大地的忧伤/天地大开大合。”这首诗的地景描写很精妙,首先,在视觉上渐进的效果产生了,“先”和“然后”明显地穿插在一个动态的时间流动中,寻常的世界忽然因为词语的奇妙排列而被抬升到无论从含义和观感上都极为陌生的地步,这种陌生化的效果刚好暗合了诗歌的魔力。其次,诗人施加给语言以反常的效果,太阳、风和天地通过微妙的隐喻移植在地景描写中,建构了具有画面意义的言语:纯粹的实物、触感和张力。
我们来看一首嘎代才让的近作《七月的幻术》(写于2010年):“我很早就说了,鹰翅上的文字/早已荡然无存。/庭院的莲花如同天空,迟迟未能在/寂静的领空里喊出春天/春天如同我的爱人/泣哭的念唱之后,命运所能给我的/也就剩下一片废墟。”
乍一看,诗人用难以拆解的紧密的书写形式在编制几个美学向度的在场——庭院与人,鹰与春天,废墟与哭泣。正如杜夫海纳所言:“美是被感知的存在在被感知时直接被感受到的完满。”⑤事实上,此诗作的美学存在于理念的母题之上而并非实物的母题,或者说,美存在于这个去实物化的过程。表面上“庭院”、“我”、“鹰”都是实物的呈现,实际上是某种实物的游离。“抒情诗向来具有的优先权就是让词语以其多义性震荡。”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诗歌的修辞,嘎代才让对言语幻术的擅长——如同他的语言一样——是有着无穷潜能的。
二、圣俗、寺院与宗教空间
嘎代才让常居甘南,在他的居所不远处,就是拉卜楞寺。他写于2002年的《甘南印象》组诗中,涉及到许多次拉卜楞寺的意象⑦。
正如20世纪欧洲的抒情诗一般,现实世界被诗人分割为单独的显像,“我赶上用额头走路的朝圣者”、“一对红衣僧人穿过旧桥”、“一对爬满旧桥的眼睛”,表面上来看,这是对日常生活的抒情诗化,但是他是“以宗教的名义来祷告着写诗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⑧,宗教的介入使得嘎代才让的抒情诗进入了一个新的向度。在《甘南组诗》中,甘南与拉卜楞寺、僧人意象的多次出现是内置在一种隐秘的宗教传统之中的(诗人言说的首要前提是其对藏传佛教的虔诚)。寺院是宗教的表征,然而寺院又是以实体与图像的形式存在的,诗人将寺院为主体的各类神秘的瞬间性的图像予以整合,以达到诗歌空间的稳固性。
于是,一场颇有梦幻特质的隐喻产生了:譬如《去年冬天在拉卜楞寺》,“在那里我可以听见:大夏河的流水声/小喇嘛的法号声/甚至,落在大经堂中央的尘埃都能看见”,“风吹着,经幡在大山的背后开始摇晃/这时我在寺院的藏经楼里/可以读到红衣僧人的古体诗,以及相关的历史传言/我想:这应该是土门关近内的一种精神遗址”。在这里,图像的魔力与话语的魔力同时以宗教的名义交织在一起。
如果向上追溯藏族汉语诗歌的传统,几乎每个藏族诗人都曾为寺院和宗教传统言说过,或许是因为“居住地的神圣化和神圣建筑物,具有把人的居住从此世转换到彼世的功能。它是人间与天堂的结合,今生与来世的合一。”⑨在嘎代才让那里,这种写作的关注点延续了下去,并且作为一个隐秘的话语中心,将外在之物和内心世界起伏的角度联接,并且推移开来。“我”与“红衣僧人”之间的界限是不清晰的,一个是真实的自我,另一个是投射的自我,一种“完美的精神自由境界”⑩,亦有论者认为,藏族诗歌的写作将居住地变成了“自在的地理——文化——心灵空间”,⑪那么,诗人嘎代才让的叙事、忧伤、观察与激情都归为隐秘的宗教主题,这些隐秘以词语的方式从世界本身放射出来,“经幡”、“法号”、“藏经楼”这些带有藏族宗教灵氛的仪式性符号为语义的放射带路,从而指向了超验的世界。
在我看来,嘎代才让作于2005年的《青海大地》组诗中传递的宗教主题更加密集与成熟。譬如《塔尔寺·如来八塔》,“菩提树,究竟为谁而开?/甚至最后的灯塔被我秘密地遗忘/大鹰睡在了天上,/如来八塔呢,如宗喀巴丢失的嘛呢石堆。/拐过石窟,就能想象出传唱中的半个塔尔寺/日光清晰——/今夜的黑暗中发现:三卷壁画,/一座破败的羊圈。/塔尔寺:熄灭也是一道光/这卷世界的旧书,持有静止、神圣。正义和隐灵的辞藻。”
塔尔寺得名于为纪念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银塔,确实,从这首诗中可以发现,太多的细节被诗人有意地丢弃了,譬如一个实物、一处地景、一个建筑空间的整体性都陷入无形的隐秘体验之中。是读者作为闯入者的姿态去阅读这个空间吗?我们甚至无法界定这个对话关系——这是诗歌的常态——或者存在更广阔的对话关系。“菩提树”、“灯塔”、“石堆”、“壁画”、“羊圈”、“旧书”,这些意象的堆积并非是一场真相,毕竟,它们被“遗忘”、“丢失”、“想象”、“熄灭”等否定性存在的词语所修饰,这岂不是没有真相的真相?时间与宗教传统一样,获得了在场的功能——亦如组诗中的另外一首:《路过玉树》,诗歌的最后一句耐人寻味:“这里如果仅是一个地名/我毫无疑问地早就把它忘了”。这句诗直接指向了信仰本身,寺院、宗教传统赋予一个地理空间别样的光芒与隐喻。
既然前面提到没有“真相”的真相,那么,再来看诗人的近作《七月的幻术》,“那一阵风吹乱的头发,与草尖上的/马匹在作舞。我在早晨的/诵经声中,辨认清楚一个面目全非的地方/符合于现在的情绪/也许,谁都不愿拾起自己的骨堆/秘密地建造一座城堡”。他的诗歌语言更加倾向于一种不予化解的张力,“诵经声”同时讲述了两重含义:经文与声音——前者是藏传佛教的经文,后者是信徒们虔诚的功课,这种貌似客观的空间结构里,现实被急剧抽离出来,“我”的头发是被“吹乱”的、“作舞”的,这种私人化的体验与前面所讲的客观式空间结构更倾向于对立、矛盾而不是相互依附。这样,就牵涉到了嘎代才让诗歌中的另一个特征——历史感与修辞的超越。
三、历史、修辞与话语传统
在诗人早期的诗作《颂辞:拉卜楞寺十月法会》中,有这么一节:“一切从正午开始——/随后,几位红衣僧人穿过午风掠过的寺院/然后扛着属于拉卜楞寺的天空。/日暮:一对乌鸦从我的头顶飞过/无际的蓝天是它背后风景/在此之前,僧人是否忙于搬运:尘埃。浮云。/后来,我就这么断定咳嗽不止的人群。”
诗人在表述一种不可见的动力,即“扛着属于拉卜楞寺的天空”与“搬运:尘埃。浮云。”这个动力虽然在民族神话中习以为常,然而按照事实的一般秩序,这简直无法想象——语言艰难有力地给我们提供了隐喻和现实的联通。几个时间节点——“正午”、“随后”、“然后”、“日暮”、“在此之前”以及未知的“后来”——统统为了展开一道绝对化的以寺院为主的空间,历时性得以确认,“我”所处的空间是未知的,这种空间的错位,恰恰形成了一个可供窥视的角度,“僧人”的一切举动都是可视的,并且随着时间节点的变动而变化。“我”看待“僧人”如同看待一部流动的历史。这可以在《去年冬天在拉卜楞寺》找到一个回应:“一种感伤的言辞,或者在一群人/冰冷的骨髓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渐渐退去的信仰。”毫无疑问,空间是不曾改变的,“一群人”和前者的“人群”互相呼应,诗人意图指出“人群”所呈现的“冰冷”、“咳嗽”的一种非常态的表征,并且对信仰(历史、宗教传统等文化因素)产生了某种困惑。
同样的主题可以在《青海大地》组诗中看到,比如《9月18日晨于塔尔寺见鹰》:“鲁沙尔镇的阳光总是新鲜/此际,附近居民的屋顶上充满了宗教气息/——远离红尘。/晨于大金瓦寺跪拜时分/彻夜坐在青石上苦修的僧人/穿过一条白塔和壁画装饰的长廊/走远了,然则又是一个寂静的早晨/然后,我在想象早晨见到的鹰/是否成为被风吹散的骨头/——四下早已稗遍顾无人。”“鹰”是藏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僧人”走远了,而在“我”的思维之中,“鹰”也成为“被风吹散的骨头”,颇有幻灭之感。时间在这首抒情诗里亦是流动的,早晨与深夜、阳光、跪拜时分与寂静,这些有历时性指向的语词,安插在宗教的神圣与世俗之间,界限似乎不是那么明显,直到诗歌的结尾:四下无人,静寂之后,抵达者走向何处?结尾处的画面是一个突然的断裂——对于开始宁静的圣俗之间的生活而言。
作为一个擅长写作抒情诗的诗人,嘎代才让书写的历史感随处可见,在他的诗作《恰卜恰草原》中,有着这样的诗句:“我闭上眼睛,恰卜恰草原就呈现在眼前/我闭上眼睛,记忆中隐隐作痛的往事和细节/就会迎面走来”。这是诗歌的首句。没有起因,没有目的,这首诗的内涵完全依靠“回忆”而存在,诗人笔下的“我”是抵达者,亦是面向历史产生思索和保持沉默的在场者。弗里德里希对翁加雷蒂诗歌的断片特征这样概括:“词语是一个断片,它颤抖着立于被匆匆触及却层层掩隔的世界和立刻又在这世界之上合拢的宁静之间。”⑫对于嘎代才让诗歌来说,这种断裂之感亦是明晰的,充满了令人惊异的对历史的认知——尽管诗歌的结构简洁到极致。
如果说我在前文列举的两个组诗都牵涉到了以修辞超越历史的技巧,那么嘎代才让在《七月的幻术》中,对传统的反思显得愈加明显,“顺着风的意思,/安睡在惨然的微笑中,你将会明白/这是一册焚毁的经卷,是诗人嘎代才让诗中的/挖潜与呈现;/词根的哀伤,轰然坍塌的/一棵菩提树的故乡。”
诗人冷静地感知到传统的断裂——“经卷”是被焚毁的,“菩提树的故乡”轰然坍塌,意即一个族群的精神支撑的颓败,这是历史的断裂感与个体在场之间的隐秘关联,这不仅仅是诗人非现实的感性,并且也是族裔诗歌对文化传统的敬畏与反思。不难发现,与其早期创作的诗歌倾向于大量的地景描写和时间性不同,在嘎代才让近期的诗歌中,历史感大量介入到诗歌内部,例如《藏獒之死》(2009)、《祷词:诞生的迹象》(2009)、《我是藏人》(2010)等等,语言直接而锐利地切割空间,并且用修辞的强力来言说隐秘的话语传统。
我又一次想要称赞诗人运用汉语的能力——精准而不失偏颇,我仿佛看到,在绛红色的黄昏之中,他在书写——隐秘的传统、自我的地理学、以及令人兴奋的绝望。
2011.5.15 广州
【注释】
①作为80后藏族诗人,他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绿风》、《扬子江》、《诗选刊》、《民族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②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9页。
③参考[美]Eliot,T.S.,From Poe to Valery.New York.1949(也就是 1948 年他在国会图书馆所做的题为《从爱伦·坡到瓦莱里》的学术报告)。
④本文引用的嘎代才让诗歌均来自诗人嘎代才让本人提供的电子版本,故在此说明。
⑤[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⑥[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⑦就词语统计而言,仅仅在《甘南组诗》中,就出现了六次“拉卜楞寺”、五次“寺院”。
⑧哈森:《嘎代才让和他的诗歌》,《文艺报》2010年6月2日。
⑨耿占春:《藏族诗人如是说——当代藏族诗歌及其诗学主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
⑩[英]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
⑪姚新勇:《朝圣之旅:诗歌、民族与文化冲突——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论》,《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⑫[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译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