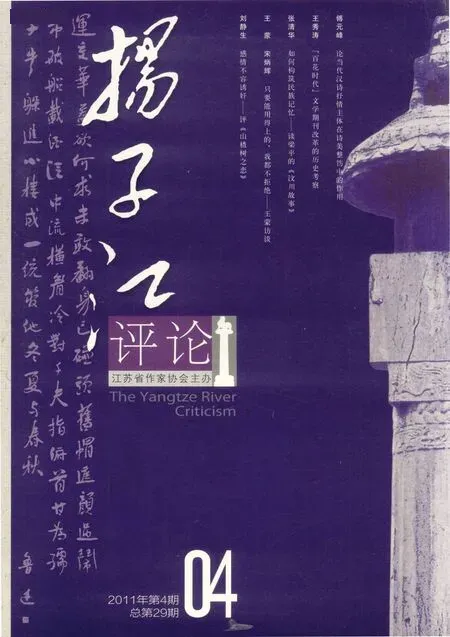探求一代人的艺术密码——读徐则臣的三部长篇
2011-11-19张永禄
张永禄
对徐则臣这样一个产量高、气场大的青年作家,现有的任何文字评论都可能是冒险的叙述。自然,笔者的论述恐怕也难以幸免。鉴于他在中短篇上取得的成绩和评论界的如潮好评,我想避开热闹的“大场面”,把目光投向他已出版的三个长篇《天上人间》、《午夜之门》和《夜火车》,试图通过探讨他在长篇艺术上的得失,借此打探70后长篇书写存在的可能“窄门”。
“70后”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作家,比如田耳、朱文颖、魏微、周洁茹、棉棉、卫慧、陈家桥、盛可以、戴来、乔叶、丁天、李师江、金仁顺等(自然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给当代文坛奉献了很多优秀的篇什。在这一点上,不仅“80后”尚无法比拟,就连新生代作家也不可小视。但,整体上“70后”作家在长篇创作上不免显得沉默且困窘。几年前,朱家雄想编一套“70后”作家群的长篇小说文库,连10部都凑不出,好生遗憾。即使在今天,情况估计也不会好多少。
在长篇小说年产量过3000部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的文坛基本步入了长篇时代,这就像小说取代诗歌成为文类霸主一般,是必然趋势。诸多嗅觉敏锐的“80后”作家基本跨越了中短篇创作的历练期,直接用小长篇、长篇对着文坛吼“芝麻开门”。“70后”们迟早也要遭遇大长篇的诱惑与挑战,他们最后的较量,估计还是要靠长篇这样的重文体作为杀手锏。吴义勤说:“长篇小说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是对作家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考验。”①对很多作家来说,长篇之于他们,就像五项全能金牌之于田径运动员一般,意义非凡。经过10年的中短篇写作锻炼后,徐则臣开始尝试大长篇,这既可以看做是接受了长篇的挑战和诱惑,也可以视为作家本人进行艺术生命的攀爬,寻求新的更生和绽放。把他最近的三个长篇排列起来,很明显感到这一点。尽管缺陷不少,但,体现了较好的长篇创作潜质,给人徐徐进步之感。在我看来,这些潜质(至少是和同龄人相比)主要体现在结构把握的技与道、题材选择的贴身性和精神气质的养护等三个方面。
一
结构是中国叙事学中最具有智慧和文化内涵的范畴之一。杨义认为,叙事文学有三把尺子——结构、时间、视角,结构则居于首位。如果把作家的写作行为看成是生命之旅的话,那写作结果就是生命结晶,而作为沟通写作行为和目标之间的模样和体制的“结构”,其实就是一种生命过程和生命形态。所以说,叙事文学结构第一,长篇小说尤其如此。总体看来,徐则臣对小说结构的把握是从结构之“技”向结构之“道”迈进。其中短篇的结构似乎注重对结构之技的追求,特别体现在对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苦心经营上。人物姿态和形象从低姿态起步,然后偏执地向高处拉升,似乎要脱胎换骨走向成功了,突然,作家让他们折翅掉下来,用欧·亨利式的结尾让人唏嘘不已。这种努力在几个长篇细部上依然可以看到影子,但整体而言,这对于长篇而言还是“雕虫小技”,基本处于修辞学阶段。如果过分炫技的话,只能损害整体之大美,违背结构之大道。在《天上人间》中,作家是用了古典的类似《一千零一夜》讲故事的方法(或者说《儒林外史》)、《水浒传》的故事连缀法),“我”一边喝酒,一边向表弟讲述红旗、孟一明、纱秀、周子平、陈子午和姑父们这群外来者、边缘人的北漂故事,来回答表弟的父亲(文中的姑父)为何宁愿在北京做底层,过着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进去”甚至死掉的冒险生活,也离不开北京的困惑,以此探讨现代社会城市和人的关系,暗示从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开放流动的市场社会,都市流民的生存境遇及其可能。就艺术形式上讲,它采用的是连缀式的小说结构,由于人物性格及其关系基本不变,但四个块状的叙事生硬地把他们分开,使得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不一致,情节和事理上的贯通性被粗暴破坏。到了《午夜之门》,这种结构的格局得到修正,虽然也基本是由《石码头》、《紫米》、《午夜之门》、《水边书》这四个部分组成。但这四部中篇小说分之独立成篇,合之前后连贯,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有机体。这个有机性靠“木鱼”这个人物穿起来,采用漫游式结构,通过走出—归来(看与被看)模式,展示了一个整体上混乱和失范的堕落世界:花街下层家庭的近乎原始的混乱与冷漠(《石码头》),大户人家的迷乱和毁灭(《紫米》),土匪窝子的战争暴力、性爱和欲望(《午夜之门》,水上人家的自然平淡的新生活(《在水边》)。除了以木鱼的成长经历(获得人生阅历和认识世道人心作为叙事的动力)来推动故事整体情节和事态的发展外,整个叙事笼罩充溢着原欲的氤氲氛围,丝毫不让人感到它们是几个中篇的连缀。从通过故事人的讲述连缀同质故事的方法让位于类似现代作家福克纳和奈保尔们设置一个人物来讲述和体验(窥视)一个世界,以此隐喻这一代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对自我位于其中的体认。可以说,这部小说的结构比上一部的进步在于作者用阴冷忧伤的情绪笼罩全部,保证了小说的文气。
到了《夜火车》,作家则直接让“自我”入场,呈现一个70后知识分子迷茫、漂泊的命运。中规中矩的陈木年有文学研究天赋,但他的人生是被父亲和老师规划好了的。在老师和父亲的心中,陈木年是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和理想的替代品。父母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洗掉自己一辈子登三轮车、被人瞧不起的底层命运。父亲对儿子的控制就是通过生活费(钱)不让他出轨,而沈教授看中了陈木年的天赋,希望通过自己的栽培,向学术界证明小城市、三流院校也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从而移植自己的学术梦想。为达到目的,他不让陈木年考研到外校,借故让学校扣发陈木年的毕业证,安排他到学校后勤做临时工,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作为陈木年本人呢?摇摆在默默忍受、本能逃避、莫名地反抗中。小说设计了一个具有隐喻性的物象:火车,作为他出走和反抗的欲望物。但是,他的每一次说“不”,都给他带来更大的不幸和灾难。“种种不幸”(在陈木年看来)给他无比的压抑,外在的极度压抑和由此而来的莫名反抗构成了整部小说叙事的基本势力,人物性格的分裂和行为的失常则是造成情节突转的动力。因为长期的受压抑,整个人处于迷茫和彷徨的半空中,上不够顶,下不着地,对一切失去信心和耐心,包括工作、爱情和生活,像一个“零余者”。内在的空虚又让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理性组织自己的反抗,只能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展开反抗和出逃。尽管小说采用出逃—归来—再出逃的形式,但这仅仅是结构之技。在结构之道上,无论陈木年是真杀人,还是假杀人,他的命运是先在的。他已经深深地被时代环境套牢,无论他是主动,抑或被动,都得付出自由和尊严,属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那一类。徐则臣多次称自己是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或者,他的内心深处和陈木年一样充满恐惧和无奈挣扎。
二
很多研究者习惯把徐则臣的创作整体上做三类划分:其一是关于外乡人在北京漂泊的“京漂”小说;其二是对于远去故乡回顾的“花街”系列小说;其三是从小说创作形式上进行探索的“谜团”系列。研究的重点自然落在“花街”系列和“京漂”系列上。不能否认这种视角很有效,既有助于归纳和概括其创作实际,也很容易把故乡和都市题材对比起来研究,进而纳入传统的研究模式中去。固然,有前人做参照系,这样评价既有便捷的操作性,又显出系统知识的魅力。但,成谱系地把作家拉入一个队伍或阵营,在求同思维下,往往会忽视作家的个体性。笔者的困惑是,这种研究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切合了徐则臣本人的意愿,又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其精神气质。原因在于这种研究很容易把徐则臣“现实主义化”。显然,这两个系列的故事大多是外在于作家本人的。由于时空转换和身份变迁,即使他再熟悉这些故乡人和京漂者,熟悉仅止步于熟悉,不会是作家和作品中人的合一,这种熟悉不得不教唆他用现实主义写实的手法来达到客观和真实。或许,越客观、越真实,越袒露了作家无法抵达人物内心的无奈。因为“无我”的写作,作家难以抵达人物世界的内心海洋。事实上,小说除了给予温情主义式的同情外,根本不能回答京漂们和北京这座现实城市的真实关系及意义。于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既不能成为批判现实主义,也不能成为理想的现实主义,只能是“混沌的写实主义”。渐渐地,在没有新的“亮点”发现之前,其写作和故事难免重复。事实上,重复写作趋向已经在徐则臣近年的小说中开始出现,无论是写“京漂”,还是写“花街”,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这种迹象。没有相同风格的作品系列不足以显示作家的创作个性,但,恰如吴俊指出的,“如果没有自觉的转型发展,创作也就会停滞,艺术的阶段性高峰就会成为发展的瓶颈;而一味大同小异的复制,实际宣告的就是创作生命的枯竭。作家写作就是在耗自己的精神生命。如果没有新的精神滋养的接续,这种生命的延续也就难以为继了。我以为这已经是徐则臣现在需要警惕的重要问题。”②作家本人也自觉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10年4月份上海的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上,徐则臣谈到了自己的这种困境:“我对北京的一些认识、感受和想法在过去的那些小说里差不多已经用完了,再用一次也未尝不可,但很容易重复。在一段时间内,你对生活和这个世界的看法不可能日新月异,你不可能每天都有一个好发现。不仅在你纵向的写作中写作有难度,在横向的,整个当下的写作中,你依然会发现难度,甚至是更大的难度。那么多人在做同一种工作,那么多人和你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过的是同一种生活,平面和趋同的生活又培养了大家趋同的看法,写出来很可能就是同一篇小说,我就不得不怀疑这个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怀疑同时又无能为力,你就可能绝望。”③
不仅如此,最大的问题是这种写作难以抵达作家的内心。作家写一篇小说就是在内心展示一个困惑或者解决一个问题,否则的话,写作于他是没有意义的。徐则臣反省他以前的小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我”,反省被大家称道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危险”。他在一次对话中谈到:“我逐渐找到了小说接近历史的有效路径,就是用个人化的‘我’,当然未必非要第一人称,介入历史,让小说成为个人化的、当代化的历史。”④是的,无论用不用第一人称,只要有个人化的“我”在,小说就能进入历史,个人化的、当代化的历史。对于真正的小说家来说,小说是他们的精神史,是他们的思想史和人格外传。这样的小说在取材上天然地要求具有内在性和贴身性,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乡题材或者京漂题材能解决的。这也是我们看好《夜火车》和《苍老》这样有“我”的小说的原因所在。它们可能在小说技术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们的本质是独特的,有个体生命的质感。让我们想一想鲁迅的《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和茅盾后期的《虹》系列那些小说吧,近一个世纪以来,如此牵动后来者的衷肠,被反复地诵读和研究,说不尽道不完,想必,和这些小说有“我”在有关联吧。当下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均质化,我们的吃穿住行,我们的用耍玩乐,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想象方式和意象,乃至我们的说话、语词运用、信息的接受和发送都可以无限制复制和山寨。均质化不仅让作家们彼此重复,作家也自己重复自己,生活场景相似,美学理念一致,生活感受雷同,日常生活的经验重叠。在没有差异环境和没有异质声音的写作中,作家的个性在死掉,作家的创造生命早已委顿。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都是没有“我”在的写作,自然难以激发作家创作的热情、意志和精神,即使文字功夫再好,技术再高明,这样的写作除了文字游戏,别无他意。抵抗均质化,坚守个体的异质性,让个体真正像徐则臣那样通过不断地反省回到内心的写作中去,是“70后”长篇创作首要解决的问题。
三
一旦作家彻底回归内心的自我,向浸淫其生命形式的切身性领域开掘,终究会形成自己独有的精神气质,这是作家的人格魅力所在,是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在徐则臣小说的字里行间,隐隐散发着缕缕特别的味道,使他区别于其他同代作家。这来自南方的味道,是构成其精神气质的因子。他的大部分小说,背景相对模糊,暮霭沉沉,水雾弥漫,人物行为单调松弛,充斥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散乱,行为缓慢,结构简单,行文绵密而缠绕,充溢着现实而又虚无、现世而又超离、悲观而又自负、理想而又绝望的情绪。在苏童的笔下,在韩东的笔下,在葛红兵的笔下,在朱文颖的笔下,在很多南方作家笔下都若有若无地散发着这种难以捉摸的气息。我强烈感到,徐则臣写作的文化底色根本上来自南方,得江南文化的地气和文风的滋养。这种迥异于北方文化、中原文化等主导性文化的南方文化极具艺术精神,可以最大限度地表征作家的自由精神和艺术才情。
和其他南方作家比较,徐则臣的南方味道是有其个性的,他有放纵,有体认,还有挣扎,甚至还有追问和困惑。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新生代们虚无式的抵抗,看不到彻底的放纵,也看不到一些“80后”笔下无意义的颓废状、自我炫耀式的腐烂以及为叛逆的叛逆等。他的主人公经常处于矛盾和身不由己的状态,执着又气馁、绝望中有希冀、屈从中带反抗。特别是最后这些社会和时代的边缘人把命运交给偶然事件来主宰,让先在命运做解释,这恐怕也泄露了作家本人情绪的孱弱和思想的缺氧。《天上人间》中那些伪证制造者们就是希望与绝望、确信与疑难、卑微与正大、阳光与阴影等一系列矛盾的混合体。而《夜火车》中的陈木年则始终处于抗争与屈从、爱与不爱、虚构杀人与激情杀人的悲剧性痛苦折磨中。这些余零者、边缘人在我们大众一方看来是“奇观”,而于他们则是日常的生活流,或者事件中,若无其事的当事人。这样的人物展示,只能采用与之相应的小叙事。比如《天上人间》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的事儿,文字俗白晓畅,行云流水般自然,人物对话简洁干脆,既无京片子的儿化和丫调,也无拖音,表面上看来有普通白话的款型,但底子上还是南方的。这样的精神气质带给他的写作以阴柔之美,阴柔中略带苍伤,偏执中暗含无奈,加上被控制的激情,有节制的叙述,人物没有大起大落,情节无大开大合,属于大时代个体的小叙述之美。但这种小,却自有其大美所在。
当然,这种精神气质也有要警惕的地方,搞得不好,很容易让作家的写作“躲进小楼成一统”,把自我无限放大,以至于没有了时代的背景,和大多数人绝缘。没有时代和同代人作为背景和参照的写作,往往让作家的情趣、思考缺少普世价值。怎样把大时代的背景和元素融进去,打破小说自身的封闭性,是作家需要警惕和思考的。自然,这不仅仅是徐则臣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70后”作家都要面对和克服的难题。徐则臣很欣赏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的一句话:“我的每一木书都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澄清一个疑问,理清一种想法,表明我是如何在这个世界存立的,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抑或我是如何对这个世界感到不解的。”那么,作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优秀青年作家,怎样在自己的精神气质中,展示一代人当下的基本生活场域和根本的精神处境,深层触摸中国当代的基本问题,表达对当代社会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困惑、理解和见解。这是时代赋予像徐则臣这一代作家的使命。
“70后”作家该如何写作反映这一代人水平,代表这一代人的思想深广度和艺术能量的大长篇?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徐则臣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孜孜不倦地磨刀,在反复地尝试,在暗暗地较劲。或许,他们酿造的时间愈长,这“酒”才愈醇愈香;或许,他们被压抑得愈久,爆发起来才更有威力。我们只能用耐心、宽容和信念,期待徐则臣们在这场由不同代际作家共同参与的新世纪文学马拉松比赛中,赢得长久的掌声和鲜花。
【注释】
①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新华文摘》2002年第11期。
②吴俊:《徐则臣小说简论》,《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③徐则臣:《零距离想象世界》,中国作家网http://ww w.chinaw riter.com.cn。
③马季:《访谈: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徐则臣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