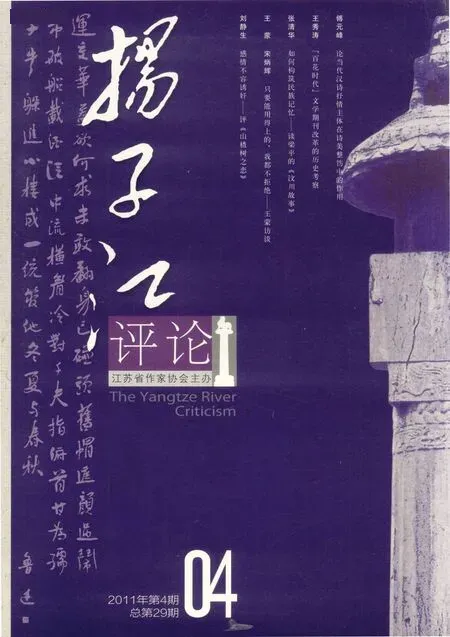如何构筑民族记忆——读梁平的《汶川故事》
2011-11-19张清华
张清华
一
废墟上正在开满鲜花,
历经劫难的那些脸庞上绽放笑容。
然而同世界上所有的灾难一样,
还有多少生离死别的阴影,
多少恐惧,多少心理余震四面埋伏,
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抚平?
这是比废墟上的援救,
比重整河山更沉重的叩问……
荷马在他的诗篇中曾构造了古代希腊人的记忆,他的讲述使希腊的历史和文明得到了一个载体,或者说是“集体记忆”。严格地说,《荷马史诗》也是一种“创伤记忆”或“创伤叙事”。因为希腊和特洛伊的战争,首先是由希腊人的“耻辱”而起的,特洛伊的花花公子帕里斯拐走了全希腊最美丽的女人海伦,使他们蒙羞,故而发动了这场既可歌可泣又全无厘头的战争。虽然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敌人生灵涂炭,他们自己也牺牲了太多——阿喀琉斯死了,阿伽门农胜利归来却被他与人通奸的妻子杀死,另一个英雄奥德修斯则是受尽磨难,在海上漂泊了十年,方才回到他几近荒芜的家园。
人类所有的史诗,迄今所记录的,要么是战争,要么就是灾难。当然,在这灾难中最闪光的,仍是人性与人的精神。《圣经》中关于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故事,同样是关于灾难或牺牲的民族记忆,但其中也包含了拯救和再生的主题——它们强调了种族或人类“最终得救”的结果。所以,正像拜伦在他的《唐·璜》中所感慨的,“战争、爱情、风暴,这是史诗的主题”。确乎如此,如同一个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是苦难一样,一个民族也是靠这样的叙事来凝聚人心、构造价值,以此来创造民族神话和提升族群精神的。
法国人莫里斯·哈布瓦赫在他的《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曾讨论了人类集体记忆的各种方式,他认为宗教在早期社会的出现,即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实现认同的一种文化记忆的形式,他说,“每一种宗教都多少以象征的形式,再现了种族和部落迁徙融合、重大事件、战争、既定体制、新的发现以及改革的历史。”①无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叙事”,正是上述人类最古老和最原始的那些“英雄史诗”或“创世神话”的现代形式,一种“宗教故事”或“史诗叙事”的当代变体。只是因为各种因素,它无法不染上现代的政治色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现的“革命史诗”式的作品——如今被称作“红色叙事”的——便是它的变体之一,它们是这个年代中国人“现代民族国家记忆”的一种构造形式。因为这些作品,现代中国关于革命的历史叙述,关于民族从遭受异族侵凌的衰败历史到独立和复兴的过程,便获得了一个形象的载体,并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革命文化”,以及一般公众都普遍认同的“集体记忆”。在最近的若干年中,这种政治化的和革命的集体叙事渐渐被重新模糊化了,嬗变为一种更具宽度的“民族文化记忆”,它包含了政治,但又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所以其思想性的含量、艺术上的复杂程度,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提高。这便是一种新的国家叙事,或集体记忆的形式了。
假如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竟然使得中国爆发了一个诗歌写作的热潮。有人对此不解,为什么一向沉寂的诗歌忽然“热闹”了起来?为什么如此短的瞬间,在网络和其它媒体上便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地震诗歌”?这其实就像一个人受伤了总要喊疼一样,一个民族受伤了也同样需要宣泄和呐喊。地裂山崩,家园遭毁,将近十万人的死亡,财产的巨大损失,如此大的创痛当然会催生一种共同性的讲述或倾诉,以作为疗伤的一种方式。最终,这些讲述会和伤痛的医治和创伤的修复过程一起,混合生成一个共同的永久性记忆。
二
然而,如何构造和升华这一记忆的过程?只讲出悲剧和苦难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将悲剧和不幸转化为“史诗”,或至少是“史诗性”的叙述,要使之充满拯救与自新的力量,这同样是集体记忆和公共叙事的必要因素。如同个体对灾难或创痛的反应是从疼痛到回味、再到思考与“遗忘”一样,族群的反应过程也同样是必须要处理伤痛之后所面临的现实,思考在悲伤之后的奋起,而不是永远沉湎于体味创伤。因此,这“重建”便不止是城市和房屋意义上的工程,同时还意味着文化和精神上的涅槃和重生,这是“比重整河山更沉重的叩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平的长诗《汶川故事》便显得不止是可能,而且是非常必要了。尽管他将这部作品定位为“灾后重建诗报告”,但从处理方式与高度看,却不止是“报告”,他通过全景的描画和上升至文化的思索,将对于灾难的理解和认识置于人类的共同命题之上,完成了这个“叙事的转换”——由毁灭转向再生的悲壮故事。
这也许会重新引出一个“写作伦理”的问题。地震之初,人们曾痛彻地反感和厌恶那些单纯的颂歌式写作,将哀痛的主题简单地转化为丰功伟绩的赞颂,甚至在那一时刻关于一切“写作”的反思也是令人警醒的,如那首影响广泛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所启示的一样,对创伤的感同身受的理解与默默抚慰成为最高的伦理。不过,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于民族来说,没有永久的悲伤,必须要在毁灭之后重生,在伤痛之余奋起,这也同样是最高的伦理。时间将会推动这一伦理的自动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汶川故事》的出现正逢其时。很显然,在对抗人类的共同灾难、关怀共同的创伤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家主义的还是个体性与人文性的叙事,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甚至它们还可以交融和纠结于一起。这是必须的,也是现实和忠实的转换。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不论我们的时代和现实中有多少问题,仅就救灾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人民和国家都显示了自立于世界的力量,显示了自尊、自信、互助和创造的力量,实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罕见的效率奇迹。在这一点上,歌颂重建和新生,便不止是颂扬国家政治,更是颂扬整个的民族和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伟大个体,这是一个全新的和坚实可靠的叙事伦理。如今,仅仅三年过去,我们就看到了总体规划清晰壮观、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新汶川、新北川、新青川、新什邡、新茂县,原本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重灾区,早已矗立起一丛丛、一幢幢的崭新楼宇与美丽家园。而且论建筑的规格、设计的讲究,论传统元素、现代气息以及地方风情的结合,都可谓令人瞠目和赞叹。毫无疑问,这便是对于灾区人民最真实、最现实的疗救和最感人的慰藉。《汶川故事》的作者从一个全景式的高度上,按照“应急——自救——援建——新生”这样的四部曲结构,完整地描绘了这一历程,复合而清晰地完成了这一文化与政治相统一的重大命题。他的尺度和分寸感是合适的——
汶川是四川的汶川。
汶川是中国的汶川。
汶川是世界的汶川。
灾难已经过去。生与死、毁灭与重生,
以及废墟上的精神涅槃,
不可置疑地陈列在世界灾难史上。
驰援,哪个国家能够如此迅捷和浩荡?
众志成城,这里的每一次托举,
都是人性的高度、生命的高度、世界的高度。
比生死驰援更加复杂和繁巨的山河重整,
同样是一份精彩答卷,难以复制。
人性、生命、世界、国家、人类,这是诗人思考地震和震后重建的几个基本维度,也由此搭建了他广阔的思考空间。而其中时间的跨度、历史的容量、哲理的运用、政论的气势、大开大合的笔法、壮阔的想象与意境,都使他的叙事充满了丰沛的激情、纵横捭阖的气韵以及上下求索的深度,充满了文化的思索与哲学的探求。他从远古传说中的大禹导江、鳖灵治水,讲到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从三星堆“太阳神鸟”的文物奇迹,说到李白笔下的“蜀道难”,蜀地的历史文化、人文风物,成为他展开叙事的广阔背景,先民的遗迹与文明也成为今天川人不屈意志与坚强品质的精神源头;他从西方哲人的警句名言中得到启示,将对灾难的思考置于人类的普遍处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的二元命题之上;将现代西方人的政治偏见与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误解与责难,同地震中中国人所显示出来的反应能力、国家意志相对照,客观并且有说服力地讨论了救灾与重建奇迹的文化与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诗中还辅以必要的背景资料、数据统计,使所有这些叙述和讨论都建立的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这种笔法,是构成长诗“全景性”宽度与纵深的条件,也是生成其宏大叙事结构与气象的根基。
比如这样的征引:
远在15世纪中叶,远在大不列颠,
那个叫培根的哲学家给人类留下一句话:
“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
然而,不是所有厄运都能征服,
奇迹也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出现,
——奇迹终归是奇迹。
几百年以后的中国,一次灾难,
一场震撼世界的救援与重建的战争,
为这个伟大论断写下辉煌的注脚。
再比如这样的举隅:
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
曾经陈尸百里、遍地哀鸿,
野狗群出吃人,灾情惨不忍睹。
1927年甘肃古浪地震,曾经土地开裂,
发绿的黑水、硫磺毒气横溢,
人畜几近无一生还。
1933年四川茂县叠溪地震,
曾经地吐黄雾、城郭无存,
巨大山崩使岷江断流,壅坝成湖,
洪水倾湖溃出,山披霹雳,天罩尘雾,
鱼在天上飞,人在水面漂。
后来邢台。后来唐山。
每一次劫后,灾与难,都不堪回首……
……血腥、漫长的地震断裂带,把受灾面积
展开成相当于整个西班牙的国土,
受灾人数超过北欧五国人口的总和。
这就是他“全景式”的叙述维度。虽然不能将之与古代的史诗笔法做简单的类比,但是它场景的展开确乎实现了“实”与“虚”之间、“现场”与“非现场”内容的穿梭搭配,这样就大大扩展了叙事的空间、内容与气度。因此,“全景式”可以认为是古今叙事中最典型的一种“史诗笔法”。它不是将所有时间流程和空间事件尽收眼底,而是取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部分,然后穿插上其它事件、人物、材料、背景等等相关的内容。这正如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荷马的赞美,他认为荷马的“出类拔萃”之处正是在于,“他只取了战争的一部分,而把其它许多内容用作穿插,比如用‘船目表’和其它穿插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他强调说,“史诗因穿插而加长”,而“内容不同的穿插”会增加史诗作品的容量,“有了容量就能表现气势。”②从这个角度看,《汶川故事》中的“穿插式修辞”和“全景式的叙述”也类似于这种典范的史诗笔法,其中大量的非现场和非线性内容的引述与插叙,使它更带有了思考性、论辩性、哲理意味与丰沛的“气势”。而这也是它作为“诗报告”这样一个文体在形式方面的自觉体现。
三
然而作品中最为感人的,还是他深入到每一个场景和细节中的人物描写,一个个感人的生命故事,这是使作品真正获得饱满情愫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写到了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里众多真实的人物,他们在大灾面前的反应:其中有泪流满面、俯身在瓦砾之上“轻轻拍打书上的尘土,擦拭血迹”的温总理,他所显示的不是一个国家的软弱,而是一个人最真实的悲伤,和自己的人民一起感同身受的悲伤和坚强;他写到了一位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乳房的女警官,她为众多嗷嗷待哺的幸存婴儿哺乳,她所袒露的是神圣而庄严的母性力量;他写到一位八十多岁身患癌症、刚刚失去了老伴的退休军医,在第一时间报名奔赴救灾前线,用他高超的医术为一位伤势严重的姑娘留住了双腿;他写到那个被从废墟中挖出的三岁的男孩郎铮,在看到救援的解放军叔叔的第一时间,竟懂事地举起手行了一个庄严的敬礼……这些感人的场景和故事所展示出的人性庄严与美丽,凝成了作品中丰满的血肉。
细节的书写还体现在对重建过程的叙述中,他写了众多坚强自救的人物:断手成杵的农民石光武,双腿残疾却在瓦砾堆上开设了第一个缝纫小摊的李万柏老夫妇,还有为护佑五个失去单亲的孩子而重组家庭的于再勇和罗兴蓉,有同样走到一起,“小叔子终于把嫂子娶进了家”的张云和李泽凤,他们相濡以沫的感情令人动容;当然,他也写了难以走出伤痛和阴影最终自缢身亡的北川人冯翔,他在震后一周年时选择了随亲人而去,但作为政府的职员,生前,“他能够承受的每一天都尽职尽责,/他把生的最后的日子,/全部给了这块饱经创伤的土地。”不过,他写得更多的还是不屈的人们,他们生存和重建美好生活的意志,他还写了重组家庭后“再做一次妈妈”的怀孕妇女的喜悦……这些生活的细节和画面,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的故事,同作品宏大的结构与集体性场景之间,构成了互为血肉的关系。比如在描写山东、广东、浙江等省市分别援建北川、汶川、青川等重灾县市的工程的巨大场景中,他疏密有致地插入了许多细节性的感人故事,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对来自山东的一位援建者,潍坊人崔学选的描写:身为北川新县城第一任的建设组长,他像“拼命三郎”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奔忙,终于积劳成疾,在长时间发烧、晕眩、腹泻不止的病痛中,仍坚守在工地上,最后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而这时候他所惦记的,仍然只有无家可归的灾民,“直到倒下,昏迷不醒”。
妻子从潍坊赶来,丈夫又黑又瘦,
原来75公斤的身体已经不足50公斤,
差一点认不出自己的丈夫。
医生说,“太可惜了,晚来了一个月……”
一直不醒人事的崔学选在弥留之际,
看见年逾八旬的老娘,喃喃地开口了,
“娘,等我病好了,
我一定陪你去看一看新北川。”
或许这是一个最适合山东援建者的例子了。它是真实的,但同时又具有文化性格上的象征性——彰显出一位“山东汉子”性格中最感人的道德情愫。
感人的力量来源于真实和立体,如果只看到崛起的楼群和山川外观的修复,而没有深入人的内心和灵魂的震颤,那样的诗意只能是肤浅和表皮的。《汶川故事》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它将重建中的包括心理创伤与记忆阴影等在内的诸多问题,都摆上了桌面,这些在以往宏大题材的“国家叙事”中是不可想象的,而这就是进步,就是新的社会伦理与价值观的必要体现。只有真正关注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状况,才会有这样的眼光,这样毫不避讳的坦诚和真实的描写——
幸存者潜伏的绝望,
救援者不能释放的精神压力,
灾后自我无法转换和消减的复制记忆,
灾难阴影步步逼近,挥之不去……
这也同样是震区人民所经历的深刻记忆。唯有伤痛之深,方显工程之巨、重建之艰,也才更加凸显生命之强与人性之美。
四
最后,还要谈一谈《汶川故事》的笔法。令人吃惊的当然首先是它舒张有度的叙述节奏,以及总体风格的把握,顿挫而又酣畅,庄重而又抒情,大气磅礴而又细腻灵动,还有以浅白口语所完成的一个沉重叙述,这些都显示了作者驾轻就熟的功力。庞杂的材料和内容经过他看似轻巧的处理,得以繁简得当、疏密有致地组织起来,整体结构的严谨和整饬,与局部描写的跳跃与松弛,构成了老练和恰当的统一。细节场景上的横向展开和时间上的跨越式处置,在他那里可谓应付自如。视野既宽,同时又从容拿捏着纵向的叙述逻辑,如果没有老道的笔法,恐很难做到这一点。三年,虽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算长,但放在抗震救灾和震后重建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便是漫长和完整的一个时间流程。必须要以合理的“叙述的转换”,来体现和完成“历史的转换”,同时以巨大的宽度体现出“时间壮观的流动”。因此,这样的处理便可以看出它的笔力:
三年,没有人统计有多少奠基?
而每一次奠基,
曾经历历在目的废墟和瓦砾重新集结,
集结成一片感恩的海,奋进的海,
海的汪洋填平了所有的沟壑。
那些挥汗如雨的额头和脊梁,
在曾经撕裂的土地上站成坚硬的铜雕……
这是“刚性”的过渡式处理,还有比较“柔性的修辞”,这类笔法在书中也起到了舒展、粘合、修饰和抒情的作用。同时也能够将叙述的速度不时地减缓下来,盘桓片刻,完成一种间隔、调整或者过渡。
岷的江把她最美的一段舞蹈,
还原成少女的梦,然后感染所有的水,
所有与水有关的记忆和生长。
鱼回到水里,在水里飞翔、水里繁衍,
水草上挂满的鱼籽,
在春天来临的时候悄悄破裂,
亿万颗黑色的星星在水里摇曳,
摇曳成新的生命。
无疑,作为一种探索体的长诗叙事,《汶川故事》显现了它的特色和优长;作为一个重大题材的国家叙事,它比较成功地超越了此类作品容易陷入的窠臼和局限,达到了新的高度。相信它会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文本,在记录民族苦难与重生、自强与复兴的历史记忆的书写中,留下独具特色的一笔。
2011年5月22日,北京清河居
【注释】
①[法]莫里斯·哈布瓦赫:《社会如何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②[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分见第23、17、24 章,第 163、125、1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