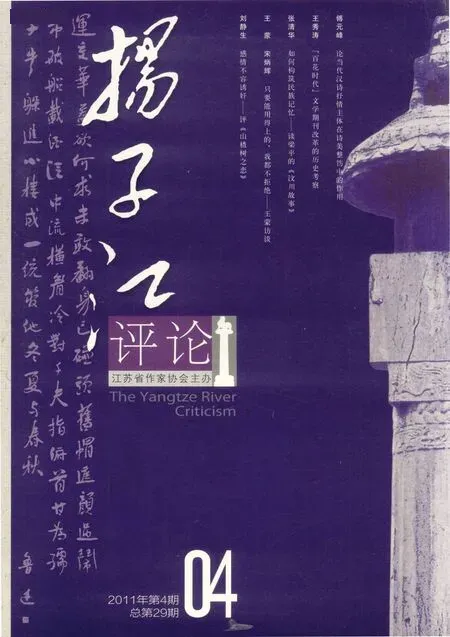新世纪中国现实的审美想象——2010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扫描
2011-11-19张丽军
张丽军
六六的长篇新作《心术》(《收获》2010年第4期),依旧是直面有“热度”、有“难度”的社会问题——“医患矛盾”。小说以一家上海三甲医院里颅外科医生们的工作情状、生活困惑、情感纠葛、医患纷争为艺术表现内容,详尽披露了医生与病人、医生与社会、医生和医生、医生和护士之间的鲜为人知而又复杂难言的多元关系。小说的艺术形式新颖独到,六六用“网络论坛”、“私人日记”、六六“自述”等各类文学表现形态,写出了医生不为人知的苦衷:“医闹”蛮横的报复,病人对医生的无奈“防备”,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医生自身的精神危机,价值抉择间的思想较量,医德高风的艰难维护。正如小说中颅外科的老主任所言,不光要有精湛完美的医术技巧,更要有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高风“心术”,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小说精心刻画了几个医生形象,他们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感立体鲜明、生动可感,富含生活气息和现实维度。老主任的高尚医德让人敬仰赞许,大师兄虽然医术高超,但面对女儿的命悬一线却无能为力。二师兄出身“名门”却没有架子,他的爱憎分明能逞一时之快也为他带来不少麻烦,他对少年病人赖月金的一腔关怀显示了他内心的温柔和敏感。“美小护”体贴入微、善解人意,她和二师兄最后的喜结良缘,证明了他们终究“逃不出”医生和护士间的微妙、暧昧的情感“关系”。传奇人物李主任的“安抚病人”的病患理论,平凡简洁却让普通医生难以望其项背。性格高傲的“孤美人”在身患绝症之后茅塞顿开,从孤傲、阴冷的阴影里走出,笑对最后人生,医生李刚对病人女儿的“自作多情”使读者在捧腹之余也有一丝苦涩。《心术》的文学表述虽然立足医院,却没有为这方寸之地所局限。贯穿小说始终的是那一句话:信仰、希望和爱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或许因为有了坚贞不渝的精神信仰,人才能在挫折、困难、打击、不幸、失败面前屡败屡战,高蹈前行;或许心存爱和希望,社会的文明进步、精神提升才会不至于如“空中楼阁”那样虚妄飘渺。
谢湘宁的中篇小说《记者》(《小说林》2010年第4期)所直接言说的内容,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性、批判性。小说描写了作为报社的“头牌记者”刘依然,在去采访昊天集团——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时的内心挣扎、思想斗争、情感困惑,把一个信奉职业道德、恪守记者信仰的女性形象,逼真细腻地展现了出来。对于昊天集团以及它的“老总”李大中,是正面报道企业的扭亏为盈、蒸蒸日上,是负面揭露集团内部管理人员的贪污腐败、集团领导的奢华淫逸、国有资产的无形流失,还是鼓起勇气报道集团职工的生活困难、下岗上访?面对报社总编以退为进的“高压姿态”,李大中周到妥帖的行程安排和顺理成章的隐秘行贿,办公室主任周龙的“美男计”,加上刘依然家庭矛盾的愈演愈烈,整个小说在极小的叙述空间里,把社会现实问题、感情问题、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人性问题、良知问题都以高超的艺术表达,理性、客观、条分缕析地予以观察予以展开。小说的人文批判和良知洞察真有“四两拨千斤”的不凡气魄。故事结尾出人意料:采访稿件被周龙力阻退回,李大中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报社没有“虚假报道”因祸得福,刘依然又有了一次“出差采访”的机会。小说可谓直击社会现实痼疾,直面当下诸种不正之风,立意尖锐犀利,价值判断鲜明有力,叙述视角也称得上别出心裁。此外,在艺术人物的营造上也是可圈可点:精明能干的周龙、颇有铁腕手段的李大中、庸俗透顶的丈夫马杰、深谋远虑的报社总编、一身正气的退休老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赵竹青的《火车头》(《当代》2010年第4期)对“群众性事件”的艺术展示不仅需要精湛高超的艺术匠心,也是对作家写作使命、写作良知、写作勇气的某种考验。《火车头》不仅机智灵活地表现了“群众性事件”这样敏感的甚至有禁忌色彩的特殊题材,而且没有简单地止于道德义愤的渲染和空疏的议论呐喊。而是从一个隐蔽侧面入手,围绕秋老八这样一个有些“地痞”色彩的人物,以他追求下岗女工尤碧华为故事主线,用丝丝入扣的叙事探索编织起了严谨合理的情节框架。秋老八本是塔山钨矿的一名火车司机,与尤碧华还有她的丈夫是同事,更是好朋友。然而尤碧华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中不幸地死于秋老八之手,两家的关系走向冷淡。随着塔山钨矿的改制、企业效益的下滑、国企改革的失败,尤碧华下岗了,秋老八的妻子也弃他而去。秋老八和尤碧华这一对“冤家”,在灰色的、艰难的生活里,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秋老八想娶尤碧华好好地照顾母女二人,尤碧华却因为丈夫之死心里的创伤始终未能痊愈。直到秋老八开着“火车头”为了钨矿工人的利益鼓动群众“闹事”,他们之间的情感坚冰才慢慢消融。此时,秋老八却被公安人员带走了。在情感表达上,小说既有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又有冷峻甚至痛苦的人文反思。作者的追求正义的人文诉求、渴望公平的呢喃絮语、审视黑暗的严厉姿态、书写底层的炽热抱负,让人肃然,也使人动容。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窄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的艺术追求和人文探索都极为成功。小说在舒缓有致、平静无波的叙述背后,逐渐地掩藏、酝酿、积累高密度的叙事势能,直到最后的瞬间“爆发”,真可谓惊心动魄,精彩不凡,让读者的心灵受到较为密集的强烈震撼之后,也暗暗赞叹作者新颖独到的叙事才具。小数内在纹理构造得精致丰厚,几近天衣无缝。鳏夫林光华在儿女事业有成之后,以独守矿山为乐事,怡然自得地与山水树木相依为伴。孰料在一帮牌友的挑唆带动之下,他渐渐地迷上了茶馆喝茶、打牌的消遣日子,阴差阳错般地爱上了名为茶馆服务员实为“暗娼”的张庆秋。然而,一个是年近花甲的鳏夫老人,一个是不满三十的青春少妇,生理和年龄的错位、生活方式的隔阂、情感沟通的代沟,使两人渐生怨隙。随着儿媳张纹的出轨、儿子林川精神的崩溃,林光华的心理在失控后,为给儿子报仇,也为给自己泄恨,在一个山洞“温柔”地杀死了“暗娼”张庆秋。小说背后思考的社会问题极为严肃深沉,作者探寻孤寡老人因为生活孤独、苦闷、亲情缺席、交流贫乏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和灰色现实。小说的叙述内容立意鲜明,社会担当深广明确,艺术细节真实生动,人物形象立体复杂,值得大家一睹为快。
魏微作为七零后作家中较具特色的、代表性作家,近几年来的创作探索一直呈现着扎实、平稳的艺术发展势头,《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化妆》、《大老郑的女人》这些代表性文本都能折射魏微细腻、敏感、飘逸、唯美、诗性的内心体悟,温情默默的文字性格也让她的小说更具独特的气质。相对而言,中篇小说《沿河村纪事》(《收获》2010年第4期)之于魏微以往的小说创作,有明显的“断裂”、“转型”之迹。魏微的凝视、观察的文学视野亦显得开阔、丰满起来,表现、思考的文学中心亦发生了由“内到外”的飞跃。小说以曾经僻远贫困的南方小村——“沿河村”为审视点,以见证人、记录人、参与者的多重文化身份,用浪漫、豪放、粗犷的新鲜笔致摹写了沿河村人从穷变富、由弱到强、从“军人”到“商人”、从保守闭塞走向改革新潮的多维性的社会转变。作者也敏锐地嗅到了改革带来的悄然“历史遗忘”,曾经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已经荡然无存,没有丝毫踪影;原先的“逃税军车”也已锈迹斑斑,成为没有人理睬的寂寞“文物”。沿河村的人们也从一种“疯狂”进入了另一种“疯狂”,村民的“集体癔症”仍然惊心动魄地上演着、燃烧着。这到底是历史的巨大倒退,还是时代的痛苦进步?魏微的文学关怀、社会审视以小见大,气度不凡,小说叙事跳跃起伏又疏密得当,作者对人心善恶的变迁考察,对理想主义的人文挽歌式的凭吊留恋,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别致拷问,富有较高的情感深度和卓越的思想力量。
铁凝的短篇小说《春风夜》(《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有着对卑微底层纯真情感的由衷赞叹和深情理解,也有对城市文明规则的严厉审视。小说把叙事镜头对准一对农民工夫妇——俞小荷和王大学,他们两人,一位是为人洗衣做饭、恪尽职守的保姆,一个是常年“以车为家”的长途司机。虽然夫妇俩彼此谋面相互“温存”的机会少得可怜,但他们依然彼此以朴实本真、温暖感人的情感方式关怀着对方挂念着彼此,依然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爱着。某种程度上,“春风旅馆”象征着森严的城市文明秩序,对夫妻二人有些许排斥和拒绝,他们反而用纯一感人的情感力量,温暖着冷漠无情的都市伦理。铁凝在有意无意间用轻盈从容的文学书写思考厚重严苛的社会真实,在孜孜以求地构建着温馨动人的情感王国,达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审美标高,营造了一座温润社会的精神之塔。
阿袁的《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十月》2010年第4期)写出了大学校园诸位高校教师的复杂人际之争,也道尽了“儒林世界”里多样的人情百态。小说从顾博士夫妇来师大试讲,夫妻间的差别让其他教授浮想联翩写起,细细道来,顾博士跌宕起伏、妙趣百般的几段情事传闻,在几近讽刺调侃之余,也有苦涩无奈的轻微叹息。顾博士先后与外语系的系花沈南、小师妹姜绯绯“拍拖”恋爱,两位美女几乎都“招架不住”顾博士“婚姻经济学”的精打细算,无果而终。而“丑小鸭”陈小美没有爱逛街购物、吃零食的“恶嗜”,让顾言的钱包不再“胆战心惊”,而她的一双巧手里的厨艺更是让顾博士眼界大开叹为观止,陈小美完美地符合顾博士的实惠、世俗、经济的“婚姻经济学”。小说叙事轻盈飘逸,人物形象的刻画饱满生动,顾博士、陈小美、中文系主任陈季子、孤傲刻薄的教授俞非、爱嚼舌头的姚丽绢、落魄可笑的卜教授、自作多情的学生鲍敏,都在支撑着小说探索现实的力度深度。小说最后,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竟“风靡”师大。博士、教授这些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们,本应该安心从容地扎根学术献身教育。然而,在阿袁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偷窥别人隐私、飞短流长于小道消息、精于投机专营的不学无术之徒,小说颇有几丝《围城》嬉笑怒骂的美学遗风。
虽然的《何氏眼科》(《黄河文学》2010年第8期)中的何大夫经营眼科门诊,擅长做双眼皮手术,收价合理,对真正的病人,手术费可以让步。小说讲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二的女子做双眼皮的故事,这个面容娇好的女子气质高雅,从容淡定,脸上布满光辉,甚至让何大夫心神荡漾。普通人追求美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个残疾女子获得美丽后感激的道谢意义更为深重,结尾处尤其耐人寻味。美丽并非表面而是生存的状态,卑微还是崇高都是自我的选择,唯有心胸开阔,从容淡定而又不盲从时尚,才会拥有美丽的人生。小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张力,饱含温情。戴善奎的《劫后人家》(《四川文学》2010年第9期)是一篇对震后生活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小说没有大幅描写震后那满目疮痍的场景,而着眼于灾区人民积极开展自救的过程。他们不仅在废墟上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在内心重筑起一片愈加澄澈和坚固的精神家园。郭震海的《一株庄稼》(《山西文学》2010年第9期)从生活中取材,描写现实,揭露弊端,将村子中最好的土地修建避暑山庄,年轻人积极支持,而老憨在村里成为孤独者,郁郁而终。山庄建成后,村民们不用种地,女人们可以成为服务生、清洁工,男人们则成为保安,原来明晃晃的锄头生锈了,犁铧成了山庄的展览品,又一个金秋时,老憨低矮的坟头上长了一株庄稼,孤独而健壮,传说中最后的一株庄稼,表现了作家对当今生活的深切关注和深刻洞察。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素来有着较高的文学特色,他本人也有中国当代的“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刘庆邦《丹青索》(《北京文学》2010年第9期)以类似白描般的细节刻画,为读者精彩地描绘了一位落魄艺术家的黯淡面影。主人公索国欣年轻时是一名美术教师,退休后他的画兴不减,以“画什么都行”当起了业余画家。机缘巧合间,画商老桂的无意中建议,使他以专画打鬼的“钟馗”谋得了一丝自信。索国欣甚至还以每张画一百元的“高价”,批给画商老桂,竟也利润不菲。然而“事业”的“成功”,无法维持支离破碎的家庭生活:他妻子整日以“筑长城”为“主业”,女儿索晓明则成了吸毒的“瘾君子”。他最后也在妻子、女儿的蛊惑下由“艺术家”堕落成了“艺术生产者”,最终“把钟馗这个打鬼的神仙,画成了被打的鬼”,他的“生意”也随之没了市场。索国欣的“杰作”——钟馗画像,颇有强烈丰富的隐喻之意,它既喻示着“人不人鬼不鬼”的世道社会,也暗示出鬼魅丛生的人心镜像。小说的叙述语言冷静理性,故事结构清晰晓畅,情节构思精妙新颖,文章到处涌动着刘庆邦深刻浓郁的文学忧虑和道德拷问。邓学义的《生意经》(《山西文学》2010年第9期)讲述的是新时代的支书兼村长关兴林,面对村里经济条件提升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远的新农村的典型问题而烦恼,小说围绕村里的一尊关公仗刀立像由闹鬼到闹神展开故事情节。作者从现实中取材,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神仙崇拜、大仙下凡的图画,没有曲折动人的情节,没有慷慨激昂的格调,小智慧隐藏在平凡的生活中,发人深省。陈纸的《刚果的羊》(《四川文学》2010年第9期)中,来自刚果的种羊“望旺”未如期使身边的母羊怀上羊仔,于是开始了它的治病之旅。非科班出身,有着杂七杂八背景和荒唐见解的几位“专家”在这一过程中丑态百出,最后却歪打正着……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带有鲜明的批判和讽刺意味,充满了智慧和幽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诞性和悲剧性。
邱华栋的《交叉跑动》(《延河》2010年第8期)讲述的是两个故事,两个主人公,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人最后相遇。故事情节交叉进行,而他们心灵深处对复仇的渴望和压抑却不期然间相遇。彭克强的童年从“文革”开始,他的父亲有着如火的革命激情,白日将毛主席像章别在额头上,鲜血直流却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骄傲地走着,夜晚激情无处宣泄,彭克强母亲的身体便成了他父亲最好的宣泄品。哥哥彭克威是个小混混头领,九岁时就可以为吃鸡肉,卡住鸡脖子将鸡残忍的杀死。妹妹生下来便身体弱,皮肤透明般。“文革”后,父亲过着平凡的生活,不久便意外死去,之后,母亲便有些疯癫,哥哥成为彭克强的老师,在夜晚带他翻上房檐教会他如何才是真正的成长为一个男人。第二个主人公名叫韦克坚,从农村考上大学,成绩优异却依然无法融入大学的生活。他决心走政治“红道”得到组织的认可。他前后遇到三个女孩子,却无一例外遭到嘲笑愚弄和轻视,惨痛的经历让他面对招摇过市的恋人们心生怨恨,内心压抑渴望释放。在新疆的一个夜总会,受过伤的韦志坚希望会有好运气,他发现了美丽的热娜古丽,此时,心中积蓄了满满复仇之火的彭克强向他们走来,命运就这样交叉,为了美丽的热娜古丽,彭克强杀死了韦志坚,杀死了木胡塔尔。小说的叙事手法独特,语言表达精准,深刻揭示了“文革”前后被时代压抑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所谓交叉跑动,并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交叉进行,更重要的是主人公精神压抑和人性扭曲的相似性造成一种交叉。小说自始至终被一种悲凉的基调所包围,主人公的成长是一种被动的成长,一种由父及兄,由兄及弟的暴虐相传,又或是一种由被玩弄后种下的仇恨继而畸形的成长过程。作者塑造了极端个性化的主人公,向现实发出深沉的拷问,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
朱山坡《逃亡路上的坏天气》中(《上海文学》第10期),“我”、黑狗、臭卵,一个“贪污犯”、一个“犯了命案”、一个“得罪黑社会”,三个人逃亡去缅甸。小说开篇便设置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活动环境,中间时隐约已经出现了政治阴谋,在逃亡过程中遇到大风雪,司徒市长对装着一百万箱子百般重视,后被两个同伴抢去,在小女孩格桑冒着生命危险的帮助下夺回箱子,竟然发现箱子里装的是妻子给自己准备的衣物。这种突然的变化让小说在跌宕起伏中给人以深思。小女孩格桑的出现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别样的味道,丑恶中增添了美和纯洁的爱,使小说有了人性的温暖,小说由此得到升华。最后作者笔锋一转,整个故事竟然是荒唐的阴谋。人物逃亡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忏悔和悔恨,纠结到释然,一切顺理成章,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既是荒唐的阴谋,更是温柔的讽刺。
王祥夫《三坊》(《天涯》第5期)。三坊,一个因盛产麻糖而泛着甜味儿的小镇,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吞没的牺牲品。拉麻糖的小人物糖五那原本悠闲恬静的生活消隐在钢筋、水泥之中。小说极其简短,却足以将这种家园的变迁、人物命运的起伏和人物心灵的嬗变刻画的淋漓尽致。乡村传统的文化和生存方式在城市化的冲击下消隐、瓦解、崩溃,而依附于传统家园生存的底层小民的失落感也昭然若揭。这其中的郁闷和纠结是不言而喻的。
葛芳的《枯鱼泣》(《朔方》第 10期),开篇写“那鱼真是疯了”。鱼的意象贯穿全文,三哥身体之外有另一个自己,作者将锦鲤鱼附在另一个三哥身上,用鱼最初的冲动象征三哥内心的膨胀和骚动,自己畅游在精神世界中,在一方阁楼里练书法、作画,在漫天星斗下听风的吟唱、花的蒂落,听见孤独的落叶飞时灵魂不安的苦涩声,夜深人静时,寂寞的流泪。这样一个精神的唯美主义者,像鲤鱼跳跃式的奔跑,很不安分,一方面是文学熏陶下的高洁,一方面是夜总会小姐的迷情。三哥是个矛盾复合体,老实的让人听不出撒谎,衣冠楚楚却隐藏不了他内心对美和真的崇尚,生活的困境也不能阻止他苦中作乐,调侃人生。三哥渴望鱼死网破似的爱情,渴望惊涛骇浪,脑海中一半是洁净无尘的湖水,一半是激情和迷乱。小说整体的氛围是神秘而玄妙,用冰冷的湖水和炙热的火焰体现主人公的矛盾纠结,细腻精致的叙述让人隐隐作痛。
刘晓珍《翁婿的战争》(《北京文学》第10期)。一场岳丈与女婿之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为了钱与权展开的较量。姐夫这样一个无钱无权的小人物将升官发财寄希望于与姐姐这场功利的婚姻。在此,婚姻不再是责任与关爱,而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宿营地。作品为我们揭示了利益和欲望驱使下人与人之间那赤裸裸的功利关系,利用与被利用成为至高无上的处事法则。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性和指向性,感情随物质的贫瘠丰盛而忽高忽低,这样功利的婚恋观所带来的幸福又是怎样的幸福?
杨凤喜《一步之遥》(《星火》第10期)这篇小说,叙述城市互不相识的邻居慢慢熟识,又因为对丈夫与女邻居的猜忌而结束友谊,平静的叙述中充满着温情的力量,矛盾冲突中彰显疏远的无奈和犹疑。最后滴下的泪水表露了女主人公对友谊的不舍和留恋,但为了自己平静而安稳的生活,放弃纯真的友谊。作者截取生活的真实小片段,从爱情和友情出发,为读者阐释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封闭,人情的自私与冷暖。
当掉入现实的漩涡的时候,再也无法自拔,主人公只能任凭无形的力量摆布,使读者仿佛看到主人公的面貌一点点的扭曲、变形,最后归于魔鬼之列。王宗坤的小说《无法终止》(《百花洲》第10期)中最精致的是他的对人物心理描写的刻画,如开篇写主人公因为嫖娼被抓到公安局,走出公安局时的慌张,作者描写得很精到,“猛然跨进出租车,迅速地把车窗玻璃往上摇,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出租车内立刻就充满了一种甜兮兮的味道,这种味道让我产生了一种逃离的快感。”“再一次感受到车流人流排泄出来的声音和色彩,我的情绪不再像刚才那样外化,一股浓浊的世间气息就如同强心剂注入了我的身体。”先是心理极度恐慌、胆怯,生怕别人看穿了什么,眼神阴霾遮蔽,而后现实生活的气息赐予了他自以为是的资本,融入它们,一切罪恶仿佛都消失不见了,当权力地位仍在时,闲言碎语也不过是一场风信子的问候。同时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从逐渐掌握官场诀窍的过程,直至将自己身心交出,将羞耻心一点点剥离殆尽,人性的光芒在主人公身上变成了义无反顾和大义凛然的作恶,可悲至极。小说中现实的尔虞我诈、光怪陆离,主人公在无可奈何中醉生梦死,在鲜亮背后是浓重,是人生存的卑微和无奈。作者用痛快淋漓的叙述笔法,透射了掉入漩涡的悲戚和无法终止的人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李治邦《寻找出路》(《青岛文学》第10期)。小说塑造了鲜明的英雄人物李出路,英雄的光辉只在每次奋不顾身的救火后社会的褒扬,而在生活中英雄没有光辉,妻子埋怨,老人生病没钱交住院费,压力的背后隐藏着英雄的无奈,为现实生活所迫,最终决定转业。将小说引向高潮的是他的副队长,与李出路的转业相反,副队长试图贿赂过他好多次,他的妻子希望他成为立功的英雄,李出路厌恶地对他说,我不走,你也当不上我的队长。而现实是副队长佩服他的英雄气概,想帮他渡过金钱的难关。在李出路骂他忘恩负义时,得到副队长牺牲的消息,原因是副队长不像他一样能够找到出路,被憋死在火海中。什么是出路?转业意味着现实生活的富足,却同时意味着信仰和理想的缺失。小说对李出路梦境的描写传达了他的内心选择,梦中妻子带他走出火海,走出来后看到一片大花园,孩子在花园里玩耍。小说采用梦境和现实结合的笔法,刻画了英雄的挣扎、反抗直至顺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发人深省。
中跃的《炒地皮》(《广州文艺》第10期),以戏谑却沉重的笔调,讽刺性地道出了当今知识分子的困境和文化界的尴尬处境。身为作家的中跃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的把握游刃有余。文中那个叫中跃的主人公似乎是作者本人,又似乎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因为他也在渴望着名利;但是他却又有知识分子的那份清高:无法和朴克等热衷于“炒地皮“的牌城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彻底地同流,看不惯学生们弃讲座而观看”炒地皮“的行为。严峻的现实拷问与浓烈的警示意义交织:这种尴尬的心态与尴尬的处境鲜活的展现了当今文化界阳光背后的一些阴影,与同时刊登的那篇《三十如狼》相比,这篇小说也对当今高等教育状况起了一种警示作用。另外,作者用了牌城大学、麻将城、草鸡毛报社等戏谑性的语词使文本的寓意更加鲜明。
夏天敏的《泛满泡沫的河流》(《长城》2010年第6期)描述对财富的渴望毁掉了曾经美丽的河流,毁掉了曾经拙朴善良的少年,毁掉了曾经执著过的梦想。作者以其忧民的心态深切地关注着农民的生存和精神状况,并有着深深的焦虑感和绝望感。文中故事发生地的高原河曾经有鱼有龟,高原河畔曾经有一个拘谨沉静、纯真宽厚、重情重义、充满生活情趣的高原少年尤小伟。但是生活的困窘与世态的炎凉使尤小伟遭受了屈辱与磨难,他的心灵开始扭曲,他决计以成为富人的方式来报复给过他屈辱的人,报复这个不公的社会。尤小伟牺牲亲人,牺牲友情,牺牲曾经养活过自己的土地,不择手段地办起果汁厂,他的发财梦圆了,而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湮没在发财梦中。文中的“我”的角色是多重的,既是一个叙述者,又是看着尤小伟变化的审视者,还是尤小伟人性蜕变的参与者。作为一个审视者,“我”的理智是清醒的,对尤小伟的变化充满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痛苦与焦虑;作为一个参与者,我对清清的河流变成泛满泡沫的河流是有责任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向利益作了妥协,所以在面对尤小伟所做的一切时会迷茫。小说中的生活是凡俗化的,语言练达深邃,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作者在小说中倾注了他对地域文化的特殊感情,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特有的文化观念关照着农民艰难的生存困境,关照着困境之下人性的变异。
肖彭的《北京户口》(《星火》2010年第6期),以近乎残忍的笔法勾勒出一个有失公正的社会和生存世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外国对我们这些孩子都敞开大门欢迎,为什么北京作为我们的首都,我们居住了十几年的家,却把我们拒之门外?”小说结尾处主人公那扣人心弦的追问令人无言以对。一纸户口阻碍了升学、就业、恋爱等所有生活的方方面面。北京户口的缺失给这些“外来户”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凭空丧失,更剥夺了底层小民做人的权利和尊严。然而不公正的何止是政策,更在于那无常的人生际遇。主人公苦苦筹来的巨额“户口迁移费”换来的却是诈骗犯的落网以及警察的到来。作者将笔触对准当下的普通小民和社会热点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悲愤的情绪贯穿小说始末。作者似有意为作品安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不久的将来,政策也许会变,局面也许会扭转,但应如何去审视和安抚那些之前为一纸户口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的弱势群体?在这一点上,小说无疑具有了审视过去和拷问人心的力量。
光盘的《洞的消失》(《上海文学》2010年第11期),围绕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洞”,讲述了三个故事。前两个故事——“村民”和“摄影家”的故事围绕小说中真实出现的“洞”这样一个实体展开,而“画家”的故事题目为“洞之外”,是关于“虚”的洞的叙述。小说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最突出的是心理刻画。面对突然出现的“洞”,村民们恐慌、焦灼、逃灾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各家在屋前屋后挖地洞,以逃避灾难的来临,小说并没有批判农民的愚昧和封建,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灾难,团结一致,向祖先祈祷岁岁平安,这一切只为了描写普通人面对灾难的无力感。“摄影家”们对洞的离奇消失,得出了“不正常的现象预示着灾难的到来,这不是迷信,而是科学预测”的结论,同样突出的也是心理刻画,面对家人和同事的不理解,认为他们得了心理疾病,就如同鲁迅笔下的“狂人”与“正常人”,各执一词。一个乡村,一个城市,一个用迷信的方法解释,一个用科学解释,最后都归结于人类对灾难到来时的无助和恐慌。第三个故事,作者借由不被世人接受的画家“妖”之口,嘲讽地产开发商,更表明了艺术家应该有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职责。“站在洞口我们永远也看不到洞里的世界”,“妖”有洞察世事的眼光,不被世人接受却用心生活。三个故事紧密相连,虚与实相结合,“洞之外”看似不相关的故事却道出主题,生活的哲学既审美又审丑。突出的心理描写、巧妙的构思、新颖的结构、深层的寓意、灵魂的书写,使得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宗利华有成熟的小小说写作谋略,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方面都是一个高手。《香树街104号》(《时代文学》2010年第11期)是他香树街系列小说的一篇。小乐和小满,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诗人和小说家的身份令他们与现实世界产生一定距离,而这种距离更容易使他们看透现实并明晰丑恶的真相,两人在香树街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相的过程。小说情节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在不断跳动着的节奏中,人物命运有了曲折变化,人格的扭曲和人性火花的碰撞也展现了出来,因而可读性较强。宗利华对造成人格扭曲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原因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充满了批判性。文中对小满和小俊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别具一格的,笔端充满了悲悯和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