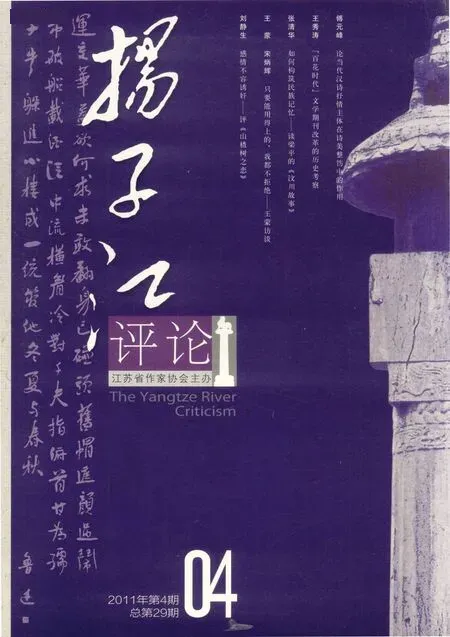论当代汉诗抒情主体在诗美整饬中的作用——以杨键、蓝蓝、潘维的诗作为例
2011-11-19傅元峰
傅元峰
抒情主体在诗歌中的言说姿态与它自我形象的塑造策略及最终效果本身就具有美学价值,而抒情主体的美学价值更重要地体现在他/她(们)对作为其对象的诗歌客体的控制过程中,这些价值体现的差异性决定了诗歌经典性的强弱分层;在20世纪现代汉诗的流变过程中,在语言、精神品格、审美趣味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抒情主体的地方性特征与国族特征,使得现代汉诗的诗学图景具有更加丰富的景深;抒情主体的语言质感实质上都体现为诗语后面的意象的质感,赋予诗语生命和灵魂的联想,从移境到移情,从语言到意象,从诗歌的内宇宙到抒情主体所处的外宇宙,这些过程皆可通过以抒情主体为线索的诗语研究表现出来;现代汉诗在抒情主体方面表现出与传统汉诗、域外诗歌的差异,探讨这些差异,并对诗歌抒情主体对文化理论的反哺进行研究,也具有重大的诗学意义。
中西方哲学对于“主体”的探讨已较为全面和深入。在黑格尔哲学及其后续谱系中,“主体”被作为人接受文化影响之后脱离身体中心所建立的另一种兼具能指和所指的两重意义的存在物,与客体建立了哲学上的对应关系。“主体”一直是哲学问题探讨的关键词。在20世纪语言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中,主体一直被作为探讨面对客体所体现出人的能动性的关键问题,得到了持续和全面的研讨: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的探讨中,在尼采、萨特等人关于存在主义的哲学研究中,在皮亚杰、拉康、荣格等带有心理指向的哲学研究中,“主体”一词被赋予了丰富的哲学意义,深化了人们对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中,“主体”也进入了文学批评话语,适用于对各种文体中具有叙述或表达能力的潜在作者的研究。而“抒情主体”则一直是诗学本体性研究的重要基础,是诗歌批评的基本概念。但在诗学研究领域,“抒情主体”作为诗歌世界里联接词与物的关键枢纽,未得到系统的研究。
简言之,“抒情主体”指在诗歌文本中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存在的控制表情达意过程的主体存在,当这种“表情达意”以叙事为主的时候,又可称为“叙事主体”,但为了研究方便,统称“抒情主体”。有时它以较为完整的形象,以各种人称外现于诗文本中,诗歌就体现为主客体共在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下,诗歌可以有多重抒情主体;有时则完全隐身于诗语之外,呈现为一个没有位格的言说主体,诗歌则体现为完全的客体形式。对于现代汉诗而言,“抒情主体”因语言、文化、国族这三方面的语境的剧烈变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应该得到诗人论层面的学术研究,以分析这些变化的写作学的根源,更应该得到基于文本细读的诗歌文体学和文本诠释学的研究,以完善新诗诞生以来关于诗歌形式研究的诗学建构,探讨现代汉诗在文体方面的自足性。只有在此基础上,现代汉诗的本土特点和母语特质才会被呈现出来。
现以三位不同诗美风格的诗人诗作为例,分析抒情主体审美个性与诗美风格的关系。
例一:带有宗教情怀的主体及其内省之美
以杨键的诗为例。杨键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具有佛性,这种佛性体现为对众生及自我灵魂的悲悯和对世事无常的感受。这自然使他的诗歌美学有浓重的禅意倾向。但在对众生与下界的悲悯所具有的哀伤意识与顿悟的禅性之间,杨键显然是以哀伤为重、禅意为辅,这样的风格构成了他诗歌美学的主要特征。
杨键对于自己灵魂家园的寻觅,与他的诗歌表达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安宁、和谐的关系。他长久观察这个尘世:“我的徐缓和平衡均来自于我对落日的长年观察。那种枯草上的落日之光,我太熟悉了,我亲眼看见江水冲上江岸时,老牛眨巴着眼睛看着江水的中国神情。我的徐缓和平衡得益于这神情,也得益于中国数千年不变如今却已经摇摇欲坠的农业制度。”他对于尘世悲哀、世事无常的洞见,不断地提升他言语的意味,这种洞见往往是在对言语甚而是对诗歌存在形式本身的质疑中进行的。这在《悲伤》一诗中有很好的体现:
没有一部作品可以把我变为恒河,
可以把这老朽的死亡平息,
可以削除一个朝代的阴湿,
我想起柏拉图与塞涅卡的演讲,
孔子的游说,与老子的无言,
我想起入暮的讲经堂,纯净的寺院,
一柄剑的沉默有如聆听圣歌的沉默。
死亡,爱情和光阴,都成了
一个个问题,但不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起曙光的无言,落日的圆满,
而没有词语,真正的清净。
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忘掉黑夜,
忘掉我的愚蠢,我的喧闹的生命。
整首诗所要表达的是对文学作品的极度失望:“没有一部作品可以把我变成恒河,/可以把这老朽的死亡平息,/可以削除一个朝代的阴湿。”整首诗只有十三行,在十三行中利用三行篇幅进行语气、语调十分急促的申诉。所植入的宗教意识、死亡哲学和历史因素表达了它们对于文学存在的一种失望。接下来,依然是对孱弱的言语功能举例:柏拉图与塞涅卡的演讲,孔子、老子言简意赅的思想。在这样的哲学境界中,诗人又引领、控诉,迈入了宗教境界:“入暮的讲经堂”、“纯净的寺院”、“圣歌的沉默”。杨键试图证明一些带有终极关怀性质的问题,对于言语都有一种普泛的蔑视,作品并不可以为之代言。他看到在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死亡、爱情和光阴因素都是人类生存中的问题,但都不是能够形成为终极关怀的最后一个问题。与此相对应,在这些问题周边,一直存在的自然景象也处于一种圆满而无言的状态。由此,诗人直接宣告没有词语的境界是一种真正清静的境界,而作品不可以促成一个沉静、清白的主体对黑夜的忘记,对自我根性的忘记,和对生命中喧闹而无意义成份的忘记。对于语言的失望,至此被渲染到极致,它构成了诗人最大的哀伤。但诗人在这一连串的诉说中,又仿佛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言语和作品本身。诗歌也可以理解成杨键对一部作品出现的渴望和祈求,也可以看做是对自身以往写作的反思。这种反思呈现出一个既骄傲又自卑的书写主体,让他具有格外的人性魅力。整首诗的写作是对一种语境下母语文学悲剧的叹息,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宗教也无法完成最后的拯救,只能形成某种悲剧性的主体意识。这首诗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现状和文化格局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描绘,是一首振聋发聩的语言反思之诗。
杨键的诗歌具有自我省察意识,他的控诉往往将自述和对于另外一种非我存在的控诉相互结合,使诗歌具有感人至深的内省力量。在多首诗中,杨键都从宗教信仰角度呈现出他对灵魂存在家园的深思,但这种思考从来没有逼迫诗歌描写的笔触从现实生活、日常生命体验的表述中脱离。《啊,国度!》、《暮晚》等诗中田园风光的迹象十分明显,甚而有风俗画、风情画的介入。河边放牛的赤条条的小男孩、拾煤炭的邋遢妇女、工厂里偷铁的乡下女孩,这些都是活灵活现的中国乡镇生活的经验。杨键一直葆有对现实说话的能力和权利,他对商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具有十分简约及富有穿透力的言说能力。他在诗歌中十分节制地动用了一些具有佛教特色的语词,如拂拭、地藏菩萨、无常等。在他的诗歌中,即使是最深度的困惑和最具魅力的蛊惑,诗人也能在诗中或文字之外保持清醒而并不点破,只是暗示和意会,就像在《陌生人家墙上的喇叭花》中所写的那样:“我心里有什么倒塌了。/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挽救。/清寒之家,/庭院冷落。/谁也不知道我从这里汲取了什么神奇的力量。”这种不为人知的挽救和我从中汲取的神奇力量,都是一些不确定的、虚妄的词语,但与非常具象的题目——《陌生人家上的喇叭花》相互映证,便具有了十足的诗歌意味。
杨键的诗中贯穿了一个对世间充满悲悯之心的抒情主体,这个抒情主体的变更、书写的语调,并没有随着意象和修辞的变化而变化,这与他的诗歌中中心词和定语间无法穷尽的、忽然性的连接相一致,它们是稳定的,有固定的操守。当代汉语诗歌所缺少的恰恰是诗人风格型的品质。很多诗人在不同诗歌中呈现出乖戾、变化的主体情绪,这造就了当代汉语写作多有佳作而少有诗人的诗歌现状。杨键是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人的诗人”的作家。他的主体修养、自我文化感知和审美境界,已经在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中被固形化,而言语的载体和观感在他的表述中永远居于下方。他的每次诗歌历程的完成,都是对言语主体经验的点燃过程。
杨键在诗歌中并不用奇诡的词汇,甚而意象也是简单平实的,但杨键能够让修饰语对中心词形成新奇的干预。这种干预也是平实的,在诗歌终结的最后一个乐章,潜藏在诗歌背后的诗人情绪必然会荡开,并弥漫在整首诗的书写过程中,成为一种氛围和背景。杨键在一个喧闹时代所选取的独特生活方式,和他沉静舒缓的的书写语调,证明在灵魂家园的寻觅方面,他是已经有自己答案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较少进入世俗视野,以至于较长时间为文学史所忽略。但是,读过他的诗歌的读者,会被其中安然宁静的情绪,以及入世的大乘佛教的胸怀和干预感所震撼。杨键并没有将宣教的意识弥漫在诗歌中,他较好地处理了灵魂家园与诗歌美学之间的关系,使二者保持着极为恰当的艺术间距,这使他的诗歌有着无限的书写空间。
但杨键抒情的固定姿态使得他在诗歌文体上创新较少,他非常审慎地对待自己抒情的节奏,避免因节奏混乱而引起诗语混乱,进而影响到一个较为安然娴静存在的灵魂核心。杨键的诗歌要想提升一个境界,必然要打破主体的僵化,使诗人在诗歌中的存在更加富有动态,去进行诗歌的文体冒险,从而探索出更加多元的表达,挖掘潜藏于生命中还未被开掘的美学原质。
例二:抒情主体依附生活并纵容一场“语言的意外”
以蓝蓝的诗为例。北方乡村生活经验是蓝蓝诗歌美学形成的基础。作为一名女诗人,她有非常敏感的审美触觉和较为鲜明的语言意识,在她将诗歌思维幻化为诗行的过程中,这两方面得到了较好的融合。蓝蓝掌握了属于自己的抒情节奏和方式,她的诗歌有较为集中的表达意象,但并不单一化。诗人那种纯粹而耐读的诗歌,明晰、简约,在连缀和转换中,以诗人的情绪和对世界的认知为粘合剂,常有出人意料的意绪的起承转合。蓝蓝善于写抒情短诗,习惯于两行一节的短句,这种单一的体式在她的笔下成为能够包含复杂感情与体现多变节奏的诗歌结构。
蓝蓝是一位具有乡村、田园审美趣味的诗人。但她的书写中包含着乡村苦难和人性深度表现之下所掩藏的世界的多义性。蓝蓝追求在每首诗中对世界都有一个新鲜的表达。她不允许似曾相识的意象和情绪在诗歌中庸俗地呈现,因此,她的诗歌给人以清新之感。她的诗观也竭力表达了这种创新意识:“诗歌是语言的意外。诗歌带来的想象力使得人与人,人与万物同为一个整体的生存体验成为可能。杰出的诗歌却使用最朴素的话语也能解决诗歌的技巧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诗歌中创造出不用词语就能使事物呈现的东西,对于诗人来说,几乎是智力的最高活动。”
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蓝蓝刷新了自己在上一代诗歌经验中所获得的一些僵化的抒情。在她现有的诗作中,能够表现她的诗歌特色并引人注意的是她朝向社会和历史的书写,但她主要的诗歌的代表作所书写的却是内心的体验,是从女性角度表达对世界的体验。另外有一些写景的诗歌,占据了她诗歌的大部分。在她的诗歌中,能够看到家庭生活、社会历史活动和自然万象,蓝蓝是一个亲近现实和自然的诗人,并对自我有非常出色的表达能力,这得益于她独特的诗歌语言。
在《真实——献给石漫滩75·8垮坝数十万死难者》中,蓝蓝对石漫滩垮坝数十万死难者的命运进行了富有女性感知的特色表达。在这首诗中,能够见到她诗歌中显见的愤怒和刚性的意味。蓝蓝体验到历史猛兽的车轮在蘸着数十万亡灵的生命润滑剂,感受到其间巨大的历史的荒谬性,她召唤着真实。在蓝蓝的诗歌中,标点符号对诗歌意境和节奏的参与程度很高,她对标点符号的表意性能有着最大化的利用,感叹号、破折号、省略号直接成为诗歌形象的象形表达。“这不只是诗人寻求个人化的语调所致,而是与其总体的诗歌本体自觉、心理完型、经验图式、认知方式、结构意识等密切相关的。”在这首诗的结语中,“……黑暗从那里来”,一个来自历史隐身之处令人惊悚的黑暗向现实蔓延的情境,被得以象形化表达。另外,在《火车,火车》、《纬四路口》中,也能够看到蓝蓝对社会现实的冷峻思考。诗歌充满痛感,这种痛感的介入打破了蓝蓝委婉舒缓的田园诗节奏,但并不显得混乱。这一切都结构成为诗人介入生活和历史的通道,从而使她的风景、风情书写与江南诗歌的美学特质相区别。
蓝蓝的诗歌由物语和情语组成,她对意象的质地和潜在于一首诗中的音色和韵质都相当敏感,有自觉意识。在《我的笔》中,她对于诗歌写作的思考有着深入准确的表达:“蘸满肮脏的泥水,我的笔/有着直立的影子。一棵陡峭的树/从那里生长。我的笔//钻进垃圾箱翻检……”,在这样的一些断行和节与节的连缀方式上,附着了富有陌生感的日常经验。这种连缀赋予蓝蓝诗语以独特的意义。蓝蓝竭力避免圆圈式的抒情,但每首诗的节奏都是圆满的、有序的,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的系统,在诗歌意旨的设置上都具有多维和开放的特征。蓝蓝避免在读者预设的向度上落笔,因此,她的诗歌充满着语言的冒险。这种对诗语的控制使她能够成功模仿一些著名诗人的语言风格,如她在《仿策兰》中完成了对策兰意象特质、书写风格的汉语再造,并熔铸进了对策兰诗歌美学系统和思想的诠释和解读,显示出她控制语言的出色能力。在诗歌《几粒沙子》中,蓝蓝再次展示了她黏结寻常诗语的天赋,表现出奇特的诗歌结构能力。这首诗充满了对宏大社会意识的深刻反思,她完成这种反思的技巧在于在这样宏大主体的细节和内部镶嵌了细致微小的女性日常经验,如第三节用两节三句诗行写道:“有时候我忽然不懂我的馒头/我的米和书架上的灰尘。//我跪下。我的自大弯曲。”这一过度环节以一个女性的在世经验很好地承接了一个世界的宏大主题,从而形成非常微妙的语调和抒情情态。蓝蓝在以下的诗节里,继续叙写她基于北方农村的生活经验和田园诗风格。这样感性的焊接使得她的诗歌有较为宽敞的平台,种植自己的主观情绪,甚而是直白的观念。在第八部分,蓝蓝用一个感叹句直接抒发了自己的情愫:“哦,命运,我在你给我的绞索上抓住了多少/可免于一死的珍宝!”在这样的诗句中,蓝蓝表明自己所领受的包括苦难与痛楚在内的在世经验,并把它看成是自己诗歌之美的最好来源。蓝蓝的诗语极其简省,有时由单个词构成,她宁愿用标点也不愿嵌入多余的汉字,诗歌至少在形式层面都留有蓝蓝抒情的空白,期待读者填充。蓝蓝是一个具有哲思能力的书写感性的诗人,《虚无》开篇就以单句写道:“虚无,最大的在之歌”,然后,她尝试在这首“在之歌”中,嵌入爱情、孩子和苹果中所附着的感性因素。蓝蓝具有记录自己稍纵即逝的感性细节的能力,她的诗歌为当代汉诗世界增添了许多丰富、细腻的感官隐蔽处的细节。她对于一个时刻、一种条件、一个季节、一种简单的人类行为、一个社会角色、一个生灵、一阵风、一种日常生活的状语或补语的诗歌阐发都相当精彩。这让人觉得她是为被大多数人所丢弃的细节而存在的诗人,她是在捡取被历史和现实表述中所丢下的下脚料。诗人用自己的视角去重新观照和雕琢这个时代的力量,并将它写意性地拓展到对更加宏大的人性情感表述之中。
作为一个诗人,面向世界蓝蓝体现出比其他同代诗人更加开放的接受姿态。她不因自己的观念取舍、审美取向,而丢弃一些被他人看来可能不属于诗歌系统的信息。蓝蓝诗歌中通常会出现对隶属于两种类型的审美元素的混合。这种宏大与细微、美与丑、明与暗、连续性和横断面不拘一格的诗行交织,使她的诗歌在表达任何主题时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在《教育》、《艾滋病村》等诗中,蓝蓝关注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和底层生存情状,即使是这样新闻记录式的诗歌表达,主体的感知在诗歌中依然起到有机连缀的重要作用。蓝蓝不再清晰划分自我书写和他人书写、心灵书写和世界书写之间的界限。她的短句最适合表达一个女性对环聚在她周围景象的言说,从中一种表象的深度已经达到某种哲学思维的状态。
在长篇诗作《诗篇》里,蓝蓝以驾轻就熟的新鲜意象为基础,勇敢地让奔放的主体情绪在抒情的不同阶段奔流。这是一首表达之诗。诗歌由十四个段落组成,其中有些段落用单句一节的方式构成。蓝蓝善于用留白的方式控制诗歌情绪的流淌节奏。只有写到充满情欲意味的一部分时,诗人才情布于诗歌,反复絮语,呈现语言的混乱状态,而在其它部分则保持语言的内敛和冰冷的简省。蓝蓝在肉体和宏大的人类聚落意象描写中表达了一种渴望,比如在城市之间进行大胆地穿连,在人的身体上进行物象的种种譬喻,从而编织成一种关于情欲关系的崭新理解。这首感性成份流溢的诗歌,似乎拒绝读者将阐释局限于儿女情爱和性爱之中。诗歌确乎在写一场惊心动魄的性爱,但又将整个世界的轮回都嵌入其中,表达一种牝牡双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体悟,又在其中投注对生存的悲悯和主体自我在精神困厄中的深度痛感。在十四节中,她写道:“只有痛苦的爱那泪水的光芒是热的”,“受苦的爱”与“那泪水的光芒”之间的连接较为突兀。但在此前十三部分诗歌节奏的惯性之下,理解这样的句子已经没有难度。蓝蓝成功地将诗歌节奏、韵律等音乐特质征引为一种表意结构,或者一些只具有语言特性的东西都被激活,从而生成营造意境的能力。在这样的写作中,看不到主体观念的表达,或主体情绪力量所构成的类型化抒情。蓝蓝充分表达了她对于诗语的尊重。正是这样的尊重,使得诗语能够承载她对复杂世界的多向性、多维度的感知经验,诗语和主体经验形成了良好互补。但蓝蓝抒情的基础在哲学和文化上都较为薄弱,其语言的审美特质还没有通向更加深邃的精神境界。因而,她的诗歌具有较为显明的随感特征,显得不够厚重。
例三:主体强大的自我观念及其美学
以潘维的诗为例。潘维在诗歌中追求抒情主体的精神贵族感受和语言的雕琢之美,他的“那些混杂着精致的颤动与疲倦的个人化语境,已然成为当代中国诗歌的一处名胜”。《苏小小墓前——给宋楠》一诗,是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美与责任之间沉思的诗作。诗歌描述一位中年诗人在妓女苏小小墓前关于自我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深思,是对一个人生的转捩点、一次自我深埋意识的苏醒,和自己经过痛苦选择后所选取的一个人生姿态的细描。
诗歌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写就。由此建立了三个乐章:其一为忏悔的表白;其二为凭吊情形的客观陈述;其三在忏悔中重新获取自己的灵魂支撑,完成自我灵魂的贵族化处理。在第一部分的第一节,诗人就将全诗的主旨用简练的视域交待处理,描述一种向有责任、美的人生转换的中年心态,诗语在开篇就用“交待”、“罪与罚”搭建了一个自我审判的法庭。第二节中“用它中年的苍白沉思,一抔小小的泥土。那里面,层层收紧的黑暗在酿酒”交代了生命中变故的发生过程。沉思是苍白的,带有一种病态的美感,但诗人非常自豪地为它选择了“泥土”这一喻体,并用“小小的”作为“泥土”的定语,显示了抒情主体对这一迟到而苍白的沉思的珍爱。但诗人并不在泥土所具有的指向生长的方向上延伸他的抒情,而是对喻体进行了再次譬喻,他将这样一个可以作为思想生长营养剂的存在物,描述为发生着更加不可思议的酝酿过程的空间,而参与这一酝酿和发酵过程的是“黑暗”,黑暗是活的、动态的、有灵性的,它以内敛的方式“层层收紧”,并最终形成生命的佳酿。接下来诗歌有沉缓的、诗意的荡开:“而逐渐浑圆、饱满的冬日,停泊在麻雀冻僵的五脏内,尚有磨难,也尚有一丝温暖。”从泥土的狭小时空到浑圆、饱满的冬日,形成第一次荡开,但荡开没有继续进行,诗人将它收束在“麻雀冻僵的五脏内”。在这样的情态中,磨难与温暖共存。接着用连续两节讲述了两次内化过程,即发生在抒情主人公沉思之内的一种情思发酵过程,和季节景观的因素在冬日的麻雀体内的一种情态,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镜像关系。在这样奇妙的时空中,第一部分的情感落点在描述西湖上的降雪过程,从而迎来对于西湖的具有强烈情绪渲染的譬喻,即“我”发生这样的一次人生转向,实现自我与美结合的婚床。第二部分,以第三人称对在第一节中完成的情境及主体进行复写:“现在苏堤一带已被寒冷梳理,桂花的门幽闭着,忧郁的钉子也生着锈。”对苏堤冬景的书写,是对一种美的类型的表述,是抒情主体情绪的蔓延或对周围环境的感染。桂花和钉子之间再次出现两重譬喻,桂花的冬季被想象成一个幽闭的空间,并用门上生锈而忧郁的钉子。本已经过想象的空间再度加工,让处于奇异想象中的情景非常鲜活地环聚在诗人周围,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氛围。
第二部分第二节诗人面对自己所钟爱的苏小小,她终生特立独行,以自己的身份宣告道德范式的失效和审美存在的永恒,苏小小成为一个美的类型和观念的象征。由于是第三人称的表述视角,诗人能够以“恋尸癖”来进行沉痛的指责,表述诗人与苏小小之间十分亲密的联系。愤怒里有赞叹,这在接下来的诗句中被勾勒得很清晰,“越来越清晰,行为举止/清狂、艳俗。衣着,像婚礼。”诗人在墓前的凭吊行为继续获得具有强烈倾向的形容词:“青黄”、“艳俗”,用这些词汇对一种美的认知继续进行细描。当然,诗人对于苏小小的审美象征的痴迷也得以同时进行:“他置身于精雕细琢的嗅觉/如一个被悲剧抓住的鬼魂”。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节,诗人与墓中苏小小的审美观念遇合的婚礼得以隆重地举行,在他驰骋的想象力下,墓前的中年知识分子穿透了时间厚重的墓碑,回归民间的大红大绿。直到这时,诗人才屈从于时间,用一种与之共老、九死未悔的心态,将其迷恋写到极致。第三部分回归于第一人称的书写,这种书写是对一个静止场景的再次复写,诗人没有迷失在一个痴恋的审美象征物里,他重新走回自己的主体存在,这种回撤是通过对西湖景致的再次描绘完成的。
在第二、第三部分之间,诗人快速完成婚丧、生死的转换:“陪葬的钟声在西冷桥畔”。诗人的反向是通过对历史和责任的抛弃完成的,在这个审美世界里,它的节奏和本质在这一节里得到描述。持有权柄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爱情。诗人假想在这一新的审美王国,以自己“在风月中习剑,并得到孤独,太多纵容的丝绸才子”,凭着这样的新生得到赦免。于是得到赦免后的诗人,对接下来的情状得到了非常细致的书写,他用了三节,其中两节作为状语服务于抒情主体所处环境的书写,第三节才浓墨重笔地写贵族意识重新获得的过程,这时诗人有足够的勇气从苏小小的祭奠时空返归尘世。
当,断桥上的残雪
消融雷峰塔危险的眺望;
当,一座准备宴会的城市
把锚抛在轻烟里;
我并不在意裹紧人性的欲望,
踏着积雪,穿过被赞美、被诅咒的喜悦;
恍若初次找到一块稀有晶体,
在尘世的寂静深处,
在陪审团的眼睛里。
人性的欲望是对这一审美观念的最后的注脚,表明他对于美的认知是与尘世和生命的本质、本相相联系的,并对这样的行走进行了譬喻,用两个“在”表明的处所与前两个诗节中两个“在”构筑了一个在尘世中获得尊贵的精神存留的情态。虽然整首诗中用了责任、美、罪与罚、虚无、悲剧等抽象语词,但并未损伤整首诗给人的实境描写。一个冬日墓前的沉思事件,一个简单静止的凭吊动作,这同一情景进行了三番表述,但并无重复之感。整首诗在表达审美认知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是作为中心词得到专门描述,而是作为凭吊中情境的修饰语逐渐渗透于一个抒情过程。三个阶段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并未留下非常明显的复写痕迹,仿佛是三个经过若干梯级的抒情的持续,而最终打开了情感的隐秘,一个心灵的境界。整首诗在这样的阅读中,读起来像是获得了一句话一样的整体感。每一诗节都作为这一句子的成分,而又非常独立的语言角色。就像一个合唱团的不同声部,有非常和谐的配合,它们音质、音色不同,唱词甚至也有差异,但它们听从于同一节奏、服务于同一韵致。诗中交织着自我反思、自我审判的痛楚,与向过去宣判、向尘世和虚无宣言的豪迈,形成了特有的既哀婉又悲壮的抒情语调。这种观念的明晰化和感受的细腻,与主题精神壮美与忧伤交织的审美情状成为潘维诗歌的主要美学特征。
在另一首诗《那无限的援军从不抵达》中,也可以读到相类的情绪、抒情节奏。在诗中,诗人已经走到了腹背受敌的绝境,但对绝境却有非常从容而细腻的书写,这构成诗歌最动人的部分:
没有一片树叶抬头
光线的钉子钉入我们的器官
我家乡的风光被缝织在茅屋与阴湿的冻土上
而透过丝绸轻柔的压迫
那些乳房,少女们的乳房
正和根须一道喘息
用疲倦、雨声、山谷哺育着一片醉酒的和谐
潘维从江南氤氲的风物中获得了灵魂和精神的营养,诗人在物我之间进行了颇为深邃的同一化,形成自我主体与带有地域风物特征的环境之间的同位关系。潘维舍弃了家乡风物的言语载体,而将其本质浸没在自己的话语之中。主体情绪和江南风物互为背景,并共同抽取出宏阔与细腻相交织的忧伤,壮美相映照的美学,潘维做到了极致。每一抒情流程都不会让观念流失:“而我在秋天的怀里哭泣/我松开火焰的缰绳,水的马蹄/让骄傲把人类的第三只眼睛踩瞎//我保存了最后一滴贵族的血”。诗人最后将自我存在的姿态和自己描述的绝境统一为一个贵族品质获得的结局。但同时也令人遗憾地证明,他的写作因主体意识的过分强大而成为观念先行的书写。他的感官的丰富性在每一抒情流程中,都倾向于被强大的主体观念和信念戕害和分解,成为意图的工具。这样的书写形态也是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因自己的文化遭际而形成的共同审美症候。他们在观念的牢笼内、在颤叫的阵列内、在慷慨的宣言里,与上一时代为意识形态所俘虏的诗人共同持有一种单调的诗歌形式。这导致了潘维的诗歌对于主体姿态的描绘形成了相当奇异的修辞景象,却走向空虚和单调的观念。语调的复活并没有为诗人拓开一个无限的抒情向度,只能走向不断重复的狭仄而贫瘠的抒情。这使得这一代诗人成为终生只为写一首诗而存在的诗人。实际上,没有与墓中的苏小小的生存状态达到一种本质上的结合,而对自己的灵魂和观念有重新的孕育,达到自我的审美品格的重生。这一批已经意识到象征、颓废、唯美的诗学价值的诗人,将只能“向美做一个交待”,而无法成为美本身。
以上例析表明,诗人诗中的主体存在形态和诗歌审美格局之间,存有十分微妙的关联。20世纪中期,德国的G.穆勒和H.欧佩尔是率先在文学领域中进行形态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类型被界定为“形态文艺学”。他们认为诗是“构形的整体”,是一种有机体。而诗歌作为构形整体的有机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抒情主体的有机性。因而对诗歌抒情主体的形态研究具有格外的诗学意义。在现代汉诗中,诗歌抒情主体的不同构形以及在构形之后的“变型”,可以通过对百年汉诗具有经典品质的文本进行分析和归纳,从显性和隐性主体、单一和多重主体、主体的人称和视角、主体对作为客体的诗歌世界的干预方式、对话型主体和独语型主体、主体的文化性格与审美品位以及情感取向等方面,对现代汉诗的抒情主体的形态进行分类。在此分类的基础上,探讨现代汉诗的经典文本在各种分类上的比重,提取抒情主体的形态与现代汉诗经典性关联的规律,对此进行诗学评估。结合历史时间中的诗歌编年,从抒情主体存在形态及其对应的经典性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规律,以求达到对现代汉诗诗美特征的更准确的认知。
抒情主体的形态学研究和诗歌形态学研究之间存在一个有机的文化、情感、语言、心理的中介,抒情主体的形态与诗歌形态的特性之间,具有亲和力。在传统诗学中,抒情主体被纳入“诗人”、“抒情者”或“抒情主人公”等概念之中,作为一个未被命名的诗学元素,边界较为模糊,已经难以适应对富有诗美现代性的现代汉诗的研究需求。抒情主体与诗人之间存有复杂的多变的关联。诗人作为最潜在的抒情主体,对于抒情主体有支配和塑造的能力。诗人所感受的地理、时代、国族的影响,必然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抒情主体中。有时以顺向的方式,在抒情主体与诗人之间建立影响的同一关系;有时则表现出抒情主体与诗人的逆向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于诗人,抒情主体会发生分裂与变形;有时两方面的因素会在同一文本中显现,二者的关系会更加错综复杂。
抒情主体作为诗歌之外的诗人在文本当中的代言者,体现出深受现代文化熏陶的现代汉诗诗人在结构、意象、意境、节奏、韵律、诗语等方面的控制力。现代语言哲学和形式美学理念的介入使得抒情主体有能力以个性化的方式干预诗歌形式,让表意结构充满变化,甚至富有戏剧性。这种由抒情主体施加于现代汉诗形式层面的作用,改变了汉诗以意象、意境或童心、性灵为主要方式的审美接受理念,让形式和结构本身富有诗歌意味。语言文字形成了韵律与诗型的骨架,也形成了中国诗歌的抒情特征。与抒情主体紧密相连的“诗语”研究,是中国传统诗学意象论的薄弱环节。在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思潮中,曾提出过“字思维”的主张,将诗歌的思维品质归结到抒情主体的做法,颇合结构主义诗学的精髓,最起码在方法论层面,它打通了古典诗学和现代诗学的隔阂。通过对抒情主体在诗歌言说中一词一句的考察,探讨其广阔的文化、文明的背景。从诗歌修辞的时间、诗语形成的条件、诗语素材、诗语词法等多角度阐述诗语与抒情主体的关系,并以文化平行论的方式对诗语的语汇形成作基于抒情主体的诗学探讨。还可对现代汉诗诗语承传的稳固性、典型化特征进行个案分析和独特的文化解读。对抒情主体与诗语的综合考证,可显示诗歌语言学研究与心理探究的互融。从语汇史的细致入微的考察走向诗歌意象的心理探悉,在方法论上注意对比对象的差异和互训,并发掘汉语诗歌的质感。还可更细致地探讨抒情主体的言语细节,如汉语诗歌的数词和量词问题,先溯源,再理析,继而归纳,然后进行水到渠成的诗歌意象的提升。现代汉诗抒情主体对诗歌其他形式的影响,如节奏、韵律,包括换行形式等方面的研究,也可纳在这一探讨单元展开,使诗学中的结构形式研究纳入到与抒情主体的关联研究中,将形式演进中的抒情主体的因素揭示出来。
就意象、意境等传统汉诗诗学元素而言,现代汉诗的抒情主体不再因循古老的拟象、造境方式,而体现出有机的再生特点,这使拟象和造境的过程直接呈现在诗歌文本之中。同时,抒情主体作为诗人有机的再造物,它对于情境的呈现具有文化和精神的责任能力,使得潜在的抒情主体的处境更加安全。意象、意境因此而生发出不同程度的“场景”特点。其他语种的诗歌在翻译中,由汉语译者和原诗作者共同塑造的特殊抒情主体,对本土诗歌的抒情主体有诗学上的暗示,而本土抒情主体也对其有同化和其他方式的改变。此外,对现代汉诗的抒情主体进行独立的哲学、心理学、叙事学的探讨,以总结20世纪以来现代汉诗中的抒情主体形象以诗学的方式对这些学科相关理论的反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