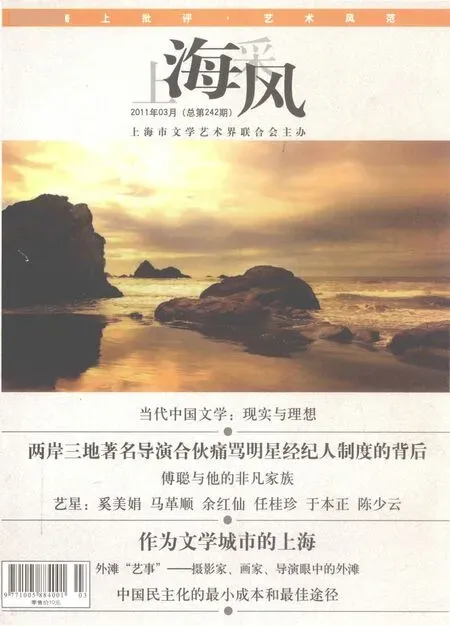外滩“艺事”
——摄影家、画家、导演眼中的外滩
2011-11-06刘莉娜
文/刘莉娜
外滩“艺事”
——摄影家、画家、导演眼中的外滩
文/刘莉娜

恐怕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外滩这样深刻地代表着上海。
它是上海都市最初的轮廓线,殖民主义的标志物,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全球化的中心,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起点。从1843年外黄浦荒芜的泥滩上出现第一座洋楼,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跨过外白渡桥,上海全境解放,外滩见证了上海无数的沧桑往事,见证了它从滨海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的曲折历程:这里是万国建筑的博览会,远东的华尔街,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是外国冒险家与华人买办的乐园。外滩是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地,是近代民族金融业兴起的开端。它被如此醒目地标识在了中国的金融地图上,却又在英国的文件内被称为英国的地方,有一座“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家花园”。
这就是外滩,一颗带动城市发展脉搏,却又悬挂于体外的奇异的心脏,一个西方现代文明与古老东方文明的猛烈碰撞中诞生的寂寞的混血儿。复杂的历史赋予了外滩宽容、开放、崇尚竞争、追求冒险的性格,而外滩造就了中国第一个现代都市,然后又培育出了第一代现代都市的市民;它是上海城市精神与海派文化的绝佳代表,透过外滩,你能触摸到上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所以,当我们探寻上海这座魅力之都的时候,总是首先将视线投向外滩。
我们怎么理解外滩的历史?外滩之于今天的意义又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也许会得出各自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我想所有人都不会否认:外滩是海派精神的源头,它一直提醒着人们,我们的现代意识与现代生活是怎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上海的中心始终都是外滩,在这里发生的许多事情,使得上海最终成为了上海。
摄影篇:
——周抗

周抗对于故乡上海最深刻的记忆,是小时候父母亲带着他,在黄浦江上坐过的那艘摆渡船。混浊的晃荡的江水,拂过脸颊的微凉的风,以及外滩建筑起伏的轮廓线下流动的都市风景——这一切如此浪漫又如此诗意,让人忍不住期望这航程永远都驶不完。周抗把他对外滩的这份感情叫做“依恋”,它根植在他的血液里,最终成为他后来选择用镜头来记录并表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最初的动因。
1998年到1999年间,周抗拍摄了以“浦江两岸”为题的一组照片,以此作为他对新千年的献礼。其中,一幅名为《百年对话》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在这幅作品中,周抗将新老上海艺术地定格在了一幅画面里:漫天红霞构成了整幅作品的时空基调,照片的前景是以外滩钟楼为代表的浦西,而它的身后,以东方明珠为象征物的浦东陆家嘴,正与金色的旭日一同冉冉升起。作品的意涵不言而喻:这既是飞速发展中的现代化的浦东,与承载着老上海兴衰记忆的浦西的一次隔江对话,更是以外滩为代表的上海,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上面向未来的一个敬礼。
“上海在将近百年的风霜雪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景线,这一点在外滩尤为明显。于是我想通过拍摄浦江两岸的风光来体现新老上海、新旧世纪的一种内在的联系。”周抗这样解释他选择并定格这个镜头的原因。见证新老上海的变迁,与新旧世纪间的内在联系。这很可以被视作周抗的上海城市摄影作品的母题。周抗喜欢“见证”这个语汇,而在他看来,他的作品不单要见证这座城市的过去,更要见证她的现在,以及她所面向的未来。
与其它摄影家略有不同,较之细节而精致地制作一个有关石库门或是苏州河的摄影专题,周抗更愿意去以更加宏大的视角,记录一个变化中的上海。他很少涉及那些阴暗败落的角落,在他的镜头下,上海总是显得那样积极蓬勃,繁华美丽。“我是一个上海本土摄影师,对于上海有种难以言喻的依恋之情,这种感情是根植于血液中的,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在自己的照片上表现上海破旧的一面的。”



说到最初为什么把镜头对准外滩,周抗提到一个小插曲:他曾经看过的一组由日本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内容是东京与上海两座城市之间的对比。这样的选题本身当然没有问题,然而日本摄影师的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的倾向性,却令周抗感觉到了极端的愤怒:“你不能以上海破落的一面去对比东京繁华的一面,既然是对比就应该公平。刻意贬损乃至歪曲上海的形象,这一点让我完全无法接受。”也正是在这一事件的触动下,他开始投入地拍摄以外滩为主题的上海大景,希望让那些从未到过上海,渴望了解上海的人,能够透过他的作品清晰地触摸到上海真实的跃动的脉搏。“我爱这座城市,这就是我全部作品的出发点。”
《百年对话》发表十年之后的2008年,周抗带来了他的另一组作品《紫气东来》,依旧是以浦江两岸为拍摄主题,依旧是全景俯瞰的表现方式,然而与前作相比,在作品意涵的表现上却又有了微妙的变化。《紫气东来》中的浦东与浦西,不再是《百年对话》那种前景与后景的关系,而是被平行地放置在了同一条水平线上。另一方面,以浦东陆家嘴地区为圆心的黄浦江流的巨大拐势,却又天然地突破了这种看似均衡的构图,巧妙地凸现出了浦东在画面上的重心地位——天际祥云,人间灯火,这样的光影色彩中显现出来的是一种属于而今上海的,雍容而大度的盛世气象。
4 查看构图。用更高的ISO来拍摄测试照片,这样曝光时间就只有几秒钟。索尼A7 III有亮屏显示功能,在实时取景模式下可以提供更好的曝光模拟效果,这样你就用不到上面的窍门了。
可以这样说,从《百年对话》到《紫气东来》,周抗以他的外滩摄影作品,完美地诠释着这十年来上海城市发展的巨大变迁。“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你需要渗透到血液中去感知,需要不断挖掘贴合上海现实生活的,有本土特质的内在意涵,你必须放缓脚步,静下心来观察它,体会它的每一个改变,并让自己也随之发生改变,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并真正传递出它背后蕴藏的城市精神。”
“照片本身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只有经过时间、文化沉淀,才会厚实起来。一百年前的摄影师所拍摄的外滩和上海总令我感到惊讶与震撼。而我所理想的,则是百年之后的人们,也能够从我所拍摄的浦江风貌之中,触摸到今天的上海。”周抗如是说。
水彩篇:
我画外滩,是因为我们上海人爱家乡,也爱洋气,外滩就是我们屋里厢最洋气的一道风景。
——陈希旦

外滩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一个沉默坚固的存在——也许因为组成它实体的那些灰色石头,也许因为组成它历史的那一百年岁月。可是在水彩画家陈希旦的笔下,外滩却是那么的轻快和通透,在明丽的天光下,我们早已看熟的那些建筑有时是浅蓝色,有时是暖橙色,有时干脆是透明到发白,好像和印象里的外滩总有那么些相异,可是看在眼睛里却又总是那么妥帖。陈希旦的水彩画真正做到了:既勾兑出了“干”与“湿”的最佳比例,又调配出了“水”与“彩”的完美结合。
外滩是陈希旦的作品中最常见的艺术地标,作为中国仅此一人的英国伯明翰水彩画学会会员,在受邀赴英参加建会100周年庆的时候,陈希旦带去的四幅作品里就有《上海外滩》。问他为什么独爱这一道风景,他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家就住在外滩附近,每天都会听到海关大楼的钟声,好像是一种召唤;又因为住得近,所以画画写生的地点也自然在外滩公园和隔江相望的滨江最多,所以,外滩自然就成了我画里最多见的风景。”可能对于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外滩那个样子铺陈在浦江之滨,一百年来都是不变的风景,可是在陈希旦的画家角度看来,外滩是多变的,它总是充满了迷人的时代感觉。“每个时代的外滩,虽然那些房子是不动的,但其他的场景总是在变化:比如本来的外滩马路上汽车很少,人也很少,能看到的是那种有轨车;之后,马路上小汽车多了,人也多了,中国人,外国人,旗袍和西服的组合全世界只有在上海在外滩才最和谐;再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又有了‘亚洲第一弯’,不论是从弯道上看外滩,还是从外滩上看这道弯,视角总是那么新鲜多样;可是这个弯现在又没有了……这些周围景致和人物的变化总是在改变着外滩的气场,让它在我不同时期的作品上都留下不同的时代印记,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这也许就是外滩吸引陈希旦的地方——面对的总是这一个外滩,可画出的每一张画都是不一样的。

外滩还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它明明在中国已经伫立了百年,每天有无数中国人穿梭于它脚下,可是不管什么时候你猛一看它,都会恍惚觉得它好像并不存在于这个时空间。对此,陈希旦说,这也是外滩对艺术家的吸引之处:“上海人看到外滩会有一种本能的家乡认同感,可是,当我把外滩的水彩画拿到法国展览的时候,法国人居然也问我,这是法国的哪儿?我说,这是外滩,这是上海。说的时候我的心里很受触动。”
采访的时候听陈希旦说,他现在把家安在了深圳,不过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还是会回到上海,青浦区政府给他在朱家角设立了一个工作室,他就住在那里画画。于是问他,现在去外滩的机会少了,还会画外滩么?电话里陈希旦笑说:“我今天就在深圳的家里画一幅新的外滩呢。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常常去外滩实地作画,那时候车少,人也少,我画画几乎没什么人会围观;可是现在的外滩已经很难具备实地绘画的条件了,人太多,打扰也太多,并且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所以他现在会用自己以前拍摄和收集的外滩照片做素材来画画——“毕竟,画了那么多年,外滩早已在我心里了。”
油画篇:
我忽然觉得,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原本心里认为只是游客观光地的外滩,居然对这个城市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我忽略了它太久,这一次作画,不能再错过它。
——沈勇

有太多的艺术作品试图描述上海。无论是来自经典影视的影象、摄影大师的照片还是知名作家的文字,在看到真实的上海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读到了太多关于上海的艺术化形象,在那些被他人总结,意象化,抽象化,又重新成形的影像或文字中,上海似乎笃定就是那个样子,也理所当然的是那个样子——它的一切风情都围绕着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老外滩形象,“十里洋场”这个专有名词俨然也来源于此。可是眼前的这幅油画却完全不是那样的,也是上海,也是外滩,可是它丝毫没有灯红酒绿的迷醉色调,相反的,它是雅致的灰色线条,带着点淡淡的褐色忧伤,它从骨子里散发出宁静温和的气息。
这就是沈勇在2000年创作的油画《上海40年代外滩》,原画现在被银行博物馆收藏在册,说起这幅画,沈勇说,创作之初,它应该算是一个“命题作业”吧。为了完成这个点名要求“三四十年代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命题作业,沈勇查阅了相当多的文字资料和图片,看地理变迁,更看人事风云,在这个过程中,他心里一条外滩发展史的脉络渐渐地清晰起来,“我忽然觉得,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原本心里认为只是游客观光地的外滩,居然对这个城市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我忽略了它太久,这一次作画,不能再错过它。”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从1847年第一家外国银行——英国丽如银行进驻外滩,到20世纪三十年代初,多达7万之众的外国人聚居在上海,十里洋场成为外滩的代名词,这些“洋面孔”带来了异域的文化,更留下了异国的建筑。100年来 ,这些来自欧洲的建筑风格正是通过外滩一条条延伸的道路不断向城市的内心辐射,从此改变了上海的城市肌理。虽然在上海的版图上,外滩只是黄浦江畔一条窄窄的弯道,北起黄浦公园,南至金陵东路;可是实地的外滩,在长约1500米的江边,鳞次栉比地矗立着24幢风格迥异的建筑——160年的历史,最终将一条“万国建筑之廊”凝固在了黄浦江的岸边。从哥特式的尖顶到古希腊的穹窿;从巴洛克的廊柱到芝加哥的楼顶,古典的、折中的、现代的,不同的立面造型,共同构成了外滩滨水建筑群优美而经典的天际线,闪耀着外滩建筑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艺术光芒。

短短的外滩浓缩了大量的艺术元素,对建筑的取舍和对角度的选择就成了沈勇最先考虑的问题。“当初给我的要求是要有中国银行这个建筑的,我到外滩去实地考察了好几个角度,最后选择了从侧面西林时报的大楼这里作为视角,这里可以最大程度地展现立体的外滩。”因为作画的主题是三四十年代的外滩,沈勇当时还找来了大量的照片资料,发现五十年代以后的照片,建筑资料比较完整,但建筑下面马路上的场景明显就不是味道了,于是他选择了拼接——大楼的资料是五十年代照片上的,街道的资料则是三十年代的。这无疑人为地增加了“命题作业”的难度,因为这样就要把两份资料上的所有小细节都统筹到一起了,比如大楼上挂的旗帜要符合年代,马路上的有轨电车方向要正确,马路边很小的人也都要穿着当时时兴的旗袍款式,细节越多越容易出错。但这个时候沈勇早已不把“画外滩”看作“作业”了,也许早在他翻阅外滩的过去时,那些粗糙的花岗岩大楼已经不动声色地摩擦到了他的灵魂。为了尽可能地还原那个时代的那个外滩,沈勇几经斟酌,选择了西班牙画家洛培斯的写实笔法——线条很素净,景物如照片般清晰,油画中常见的圆涌酣畅的笔触被长短不一、疏密有致的运笔所取代,初看之下甚至会有些潦草之嫌,可是细节处却又特别显功力,大楼上的那些玻璃窗的映像都恍若可见。还有那些花岗岩,即使在画中它们也还是那么有真实感的沉重着,蕴涵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力量感,一如外滩最初的使命——它的成形可不是为了点缀浦江的夜景,它是西方金融资本在本土落地与生根的第一个脚印。
作家陈村曾经在小说中写过——当然我们知道,小说家的语言都比较夸张——他说他愿意在外滩的石头上一头撞死,因为他觉得那种建筑太过令人惊叹。“你走过去,你摸摸花岗岩的那种大石头,你看看它的建筑理念,你就会浮想联翩地想起一整个大时代。”这是一些怎样的石头,这些石头如何营造了外滩的尺度与空间,在这些尺度空间里,又记录着一段怎样的屈辱与梦想?这些追问在作家的笔下可能就此成为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而在画家的画笔下,它们还是沉默的石头组成的建筑,然而这些建筑分明又与现实中的那些有了点不同,那点不同,便是画家自己表达感触的方式了。
影视篇
用自述的方式是因为我希望别人觉得:外滩是活的,现在依然活着,可以让它自己来讲故事。
——周兵

就像伟大的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一样,外滩这个独特的艺术符号,自然也不仅仅只吸引上海籍的艺术家,来自北京的纪录片导演周兵就是一例。执导了《故宫》《敦煌》《千年菩提路》等多部广受好评的纪录片之后,周兵的目光被外滩吸引。耗时两年,呕心沥血,当周兵拿出纪录片《外滩佚事》时,他自信地说,这是一部比《故宫》婉约,比《故宫》柔美,却和《故宫》同样深刻的力作——我们一直觉得外滩是摩登的,是洋气的,可是在一个纪录片导演的眼里,它居然也可以是和“故宫博物馆”一样深刻的。

作为一部“非典型意义上的”纪录片,《外滩佚事》使用了别出心裁的手法和语言。它没有局限于详细解释上海外滩的历史沿革,而把胶卷用在了6个在外滩生活过的人物的命运上,用人之喜怒哀乐,勾勒出当时远东第一城“冒险家乐园”的风云流变。这6个人分别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民族商业巨贾叶澄衷、流氓大亨杜月笙、金嗓子周璇、金融家法诺、日籍电影明星李香兰(均由演员扮演)。影片的旁白使用第一人称,让拟人化的外滩以一个老年男人的声音自述平生。为什么《外滩佚事》的自述是老年男人呢?在大多数人眼里,上海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阴柔、女性化的城市吗?拿这个问题问周兵,他说:“最初想让陈冲配音,外滩仿佛母亲的角色。但整个片子做完,我发现这片子很阳刚。我想人们一直以来对上海有误解,他们看到了上海精致、阴柔的一面,但这背后的本质,是经济,是权力,是资本。上海是大气、充满冒险精神的。用自述的方式是因为我希望别人觉得:外滩是活的,现在依然活着,可以让它自己来讲故事。”至于为什么选择这6个人物?周兵说,这6个人打动了他,所以用了非常个人的表达。“我们看了很多故事,做了很多史料梳理工作,粗选了20多人,从一开始就决定要用人物串联。故宫的时间跨度有1600多年,外滩只有160多年,但拍摄《外滩佚事》更难,一是空间不封闭,二是人物更复杂,人性的挣扎和矛盾冲突更大。”


作为一部纪录片,《外滩佚事》中有不少珍贵的历史素材,如1898年外滩最早的影像资料,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建成后不久的航拍影像资料,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共同出现的影像资料等,并以叶澄衷学习洋泾浜英语“来叫克姆(Come)去叫谷(Go),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爷叫发茶(Father)娘卖茶(Mother),红头阿三开泼渡(Capital)”的过程,还原了早期华洋杂处时外滩的风俗人情。周兵说:“《外滩佚事》其实是一个‘混血儿’,该片拍摄之初,剧组就专门成立团队收集史料,关于外滩金融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法国INA(国立音像研究院)以及高蒙电影公司资料部等地得到了一批拍摄于不同年代的珍贵影像资料。于是,观众才得以在大银幕上看到解放后,在赵丹家中,周璇穿着呢子套装,现场演唱《天涯歌女》。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现场歌唱,不久以后就撒手人寰,年仅37岁;‘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军轰炸上海南站后,废墟般的铁轨上留下一个无人理会、哇哇啼哭的婴儿;1942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军队踩着傲慢的步伐,踩过外滩的土地,他们终于进入了租界‘孤岛’。这些历史,也许你都知道,也许你也看过老照片,但当这些黑白影像有形有声地出现在面前时,大家会感受到,纪录的力量是无法替代的。”
作为并非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导演,周兵对自己的镜头和外滩的这一次“相遇”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说:“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我认为外滩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基地,是中国起航的地方。纪实频道找到我合作《外滩佚事》,可能正是需要我‘非上海人’这样一个‘局外’的视角。或许,只有跳脱出地域的局限,才能够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角度来审视外滩。”在他眼里,在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上海一直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和碰撞的地方。它既不完全中国化,也不完全西方化,寻找身份定位的问题贯穿了上海的历史。所以,他眼中的上海精神是包容、大气的,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
不是上海人的他在博客上这样写心中的上海:“在匆忙的人群中,人们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奔忙,这里面也有许多怀揣梦想、有热情活力和激情的年轻人。一百多年来,他们虽历经不同的时代,但追求的脚步从未停止。上海是一个美丽而精细的城市,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而外滩,是一种象征,是梦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