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及其他
2011-09-29刁斗
刁 斗
略萨及其他
刁 斗

略说略萨
近些年,好几回与人说拉美文学,我发表意见时都脖子粗脸红——替略萨吃马尔克斯的醋:就知名度说,后者比前者大太多了。我无事生非地替两个遥远的同行为虚名操心,也许显得挺小心眼,没准略马两位大人大量,从没计较过在世的拉丁美洲小说家里,他与他谁该坐头把交椅,尽管,这对曾经的好友哥们,也曾经反目成仇拳脚相加。
其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同样是好小说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好法,风韵妇人与青春少女,都可以成为美的注释,而不同看客的见仁见智,更属于上帝都无权干涉的主观评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至于我的吃醋,实属无聊,顶多在无聊之外,又添加了点我对文学价值的个人化理解。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开始,拉美文学一如那一时段畅行中国的走私汽车,驶进我们的文学生活时风驰电掣,其尖兵,正是略萨和马尔克斯。他们对中国文学界的强力冲击意义特殊,除了送来一批精品养料,更让我们找到了参照的坐标——原来,在欧美之外,好小说也可以在落后的经济禁锢的政治贫瘠的思想中脱颖而出。中国与拉丁美洲形异而质同。自那以后,对我来说,我相信对我的许多中国同行也没两样,陡然间,就长了几分写作的信心。并且经过挑挑拣拣,在或精或粗地持续领略了十数位拉美小说家的风姿以后,我约略确定,略萨、马尔克斯与博尔赫斯最吸引我。但继续掂量他们与我关系的亲与疏时,一般情况下,我会略过博氏只比较略马,原因很简单,我眼里的博尔赫斯是神的化身,略马两位才是人的英雄。我也是人。人只能挑剔人,对神光顶礼膜拜就可以了。顺便坦白一句我的偏见,我心目中的大小说家,都得写过过硬的长篇,连不过硬的长篇都没留下的博尔赫斯,大概是个唯一的例外;同样没长篇的鲁迅在我眼里,是个伟大的启蒙先知。还说略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二十世纪的辉煌收获,但一个仍在行内的在世作家,基本靠一部作品支应左右,总让我觉得,有点像对国计民生麻木不仁的体育明星当政协委员,有点像只擅长溜须拍马的贪官污吏当人大代表。我这样说不够厚道。马尔克斯作品没腰,也多系佳制,比较之下,略萨虽然佳制也多,甚至作品及胸,但毕竟少了部旗帜般的《百年孤独》——如果把他介绍给外行,我提《世界末日之战》呢,还是《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还是《酒吧长谈》或《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早年我也像别人那样,在略马之间更看重后者。我不知别人为何轻看略萨,反正我的理由很多:比如,他长得太帅了,对英俊的男人我不大信任;再比如,他那部广被传扬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几近于靠贩卖私生活夺人眼球的艺人勾当;还比如,尤其让我失望的是,作为一个以社会批判见长的好小说家,他居然去参加总统竞选,欲把自己混同于以遮掩社会疮疤为己任的无良政客——再顺便申明一句我的陋识,我不是对知识分子参政一概反对,但为党派之争,光直抒胸臆就可以了,只有为人权而战才值得身体力行。像写剧本的捷克前异议分子哈维尔,在极权政治垮台后出任总统,我就能够理解认同。其道理在于,哈维尔不“根红苗正”,是个天然的“国家公敌”,只要他想有尊严地活着,就没法不被裹挟进意识形态的漩涡之中。我的意思是,为更迭一种非法统治可以舍我其谁,为延续一个官僚体制,首当其冲则没有必要……另外,略萨以秘鲁、西班牙这个双重国籍设定身份,也让我心里挺那个的:至少这容易制造麻烦!比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黄袍终于加他身了,可秘西两国,该如何为他欢喜或郁闷呢,难道那军功章也得一家一半?
略萨在我心目中地位渐高,最终高于了马尔克斯,现在想来,大约就开始于他新户口到手的那个时候。当然了,我评价他们,主要依据艺术标准,间接参考政治态度,没考虑他们都是谁的公民。
我喜欢的小说家品质,是艺术追求的执拗与艺术表达的专一。我不极端,承认精神也像物质一样,流动与变异是允许的,更是应该的,我不认为一个人调整和修正自己的艺术观念与艺术行为就是不负责任。但我更看到,的确又有许多写作者,甘愿让精神依附于物质,像一个幼稚的社会那样动辄“转型”,以投机取巧和见风使舵为艺术伦理,模仿妓女与嫖客的关系。鉴于略萨的个性特点与生活态度,我很担心他太“与时俱进”,只当“时代的作家”“社会的作家”,而忘记小说首先是艺术,而早早成为晚年的萨特——让我一直对之兴趣浓厚的法国哲学家与文学家萨特,曾有着充满思想魅力和诗意生命的青壮年时代,可他的晚年,被政治涂抹得不三不四,而略萨,“小萨特”正是能传他神采的响亮绰号。所幸的是,“小萨特”没被自己热爱的老萨特蒙蔽双眼,他对自己热爱对象身上的优劣短长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在政治的泥淖里崴了脚后,他居然能东山再起,强势重回艺术的怀抱,回到他一以贯之的艺术探索与社会关怀双拳齐出的轨道上来,让他“结构现实主义”扛旗者的一世英名继续光芒四射。“小萨特”的老而弥坚,让我愿意对他另眼相看,一种历五十年而初衷不改的“结构”热情,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小说。
说心里话,略萨的“结构”稍嫌花哨,甚至不无生硬,不如马尔克斯的“魔幻”深厚浑然。但正因为他身后有一条由凡人而英雄的成长轨迹供我辨识,能让我看到瑕疵被光芒所照亮的过程,我才觉得他亲切可感;而马尔克斯,早已成了定型的英雄,他凝固了美也终止了美。我尊重偶像,但喜欢活人。
加缪的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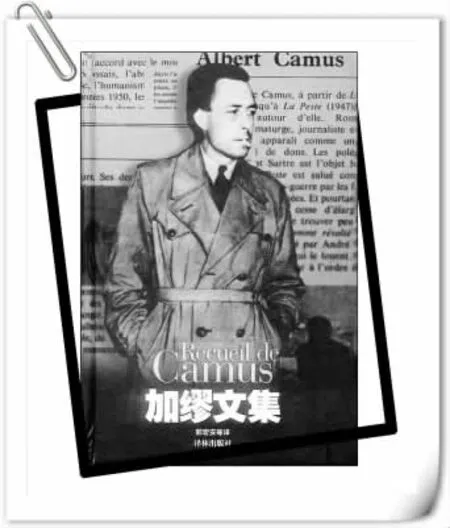
好多年前与朋友聊天,数道各自喜欢的作家,数道完,朋友对我的评价是:你喜欢的都是哲学家。这“哲学家”里就包括加缪。读大学时,加缪还真攻哲学专业。对朋友的刻薄我不以为意。兴趣使然没有办法,我喜欢的小说,的确多含理趣智性,其间飘溢着哲学的芬芳——遗憾的是,中国那种止步于形而上的道德哲学少有这芬芳。
像多数人一样,知道加缪,是读他篇幅不大的《局外人》,那时我大学刚刚毕业:“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劈面而来的第一句话,就将一种罪恶的快感注入我身体,顷刻之间,便颠覆了我的伦理观念:谈论母亲之死,怎么能用这样的口吻?我受的教育,都赞美母亲,即使母亲邪恶卑鄙,也得把她伪造成圣人——中国文化里,好像母亲也不邪恶卑鄙,邪恶卑鄙的只能是继母。加缪把神圣还原为凡俗,让我因他对母亲的态度而喜欢他。我喜欢一切思想意识层面的冒犯与挑衅。当然,《局外人》的表达重心不在母子关系或神圣与凡俗,它以顺脖梗子灌凉水的方式征服我的,是虚无感。那时候,年轻的我思考问题很中国特色:怎么活?误以为应世哲学的烂泥塘就是永不干涸的大江大河。可同龄人加缪(写作《局外人》时他二十多岁)的适时点拨,惊出了我的一身冷汗,沿着他细长的手指向远方望去,我方发现,原来生命哲学的瀚海才广阔无涯且万世荡漾。为什么活?生命的终极问题跃出了海面,它像一部现代派小说,有点别扭,有点晦涩,但经得住多角度的品咂琢磨。
不久之后,加缪的另一本书又摆到我面前,《西西弗斯神话》,这是本暗地里呼应《局外人》的哲学随笔。那时我已接触过康德黑格尔们的佶屈聱牙,比较之下,加缪这一类型的生猛鲜活更打动我。“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又是劈面而来的冒犯狂言与挑衅妄语,比贬抑孝道还让我惊骇。他在哗众取宠吗,还是在故作高深?
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得罪了领导,受贬天天做无用功:推巨石上山。山尖尖上留不住巨石,巨石旋即会滚落山脚,他得弯腰撅腚地重新来过,周而复始无止无休。加缪借用西西弗斯,更清晰地,让我看到了我的处境。他太狠了!他以薄薄的两本小书,结结实实地动摇了我此前建立的人生信条:过有希望的生活。
“过有希望的生活”有什么错吗?没错,假如你把希望视为生活的根据,有办法让“明天会更好”与某些具体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希望的确能暂时壮阳。可是,究竟什么算“希望”呢?寒窗苦读的希望是念大学吗?好好写小说的希望是当厅局级作家吗?以灵肉为柴燃烧爱情的希望是煮熟婚姻这锅糊糊粥吗……如果是这样,那求知的满足感、创造的欣快感、男欢女爱的愉悦感,是否会因其难以量化、不生成结果、无从建立目的性价值,而不再是人性中更值得把玩的奇珍异宝呢?秋波流转间,希望的媚眼的确顾盼生辉,可那辉,却怎么看怎么像陷阱上的迷彩伪装。
希望是对未来的关怀,其姿态高蹈,不容易让人也留意到,它身后的阴影会遮蔽当下,会忽视或者冷落当下,甚至干脆摧毁当下。但生活的常识是,未来永远始于当下,即使未来并不存在,当下的门槛也绕不过去,而通往未来的曲折台阶,再光洁齐整高入云端,也得由无数级当下依次铺就,哪怕当下的砖石残损破碎,尚堆在沟壑深深的底部。可人们更喜欢张扬希望贬抑当下,这原因多多,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点,是有时候,许多时候,当下的同义词也叫及时行乐。强调当下要冒风险。在希望被标举为端庄神圣的堂皇语境,及时行乐低俗猥亵,它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尤其那个赋予了生命全部意义的“乐”的概念,总被简化为生理满足,几乎等同于粗鄙可耻。这种别有用心的词义缩水,是以谎言强奸诚实,就如同如今的公共声音,也色情场所般浑浊下流,皆以“妓女”强奸“小姐”。表面看,这种强奸彬彬有礼,毕竟,这很像“高雅”理想对“庸俗”现实的超越与提升,可事实是,任何理想都起飞于现实的跑道,没有现实的地面导航,理想的飞翔就不真实,如果对之不敢承认,卸磨杀驴或言不由衷,只能证明,那超越与提升伪善且功利。首先,人作为一坨血肉之躯,践行生理满足之乐不仅不粗鄙可耻,还是对天赋人权的积极回应,对于大自然的造化和赠予,谁都没资格否定拒绝;其次,只要思想和情感没被彻底格式化,任何人都不难明白,及时之“时”也好,行乐之“乐”也罢,都弹性巨大边际广阔,狂欢于一场以九十分钟为时段的足球比赛,与陶醉于一次以一生为期限的爱情甜美,同样是对“时”与“乐”的恰当把握与深刻应用。固然,也有些人,甚至为数众多的人,由于思想和情感接受格式化的程度比较彻底,便很难理解,为什么“希望”只有转化为“及时行乐”,才能真正地体面健康。是势利让他们一叶障目,只识“成功”为生活的砝码,不认生命系“过程”的享受,于是,在他们那里,只有金牌叮当的奥运“希望”才叫幸福,而平日里升华身心完美技艺的卓绝之“时”与磨砺之“乐”,只算囚犯的刑期与苦役的劳作。
社会性对人性的异化无所不在,但人性对社会性的反抗也没有穷期,能够找到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滚石上山的“局外人”身份,我必须承认我运气好。借助于加缪的隆隆滚石,我碾碎曾让我无比信赖的希望时干脆利落——当然,我没必要也碾碎“希望”中那个动词的部分——否则,继续与“希望”中那个名词的部分勾肩搭背,在亦步亦趋中枯萎活泼的生命可能,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生命是生活的宿主,一任生活在标识明晰的轨道上按图索骥,只等于在了无意趣的苍白时空中堆积和繁衍僵化的事物,与人其实关系不大。要让生活与人有关,必得通过生命的摆渡,告别此岸向彼岸进发,即通过爬出“希望”之类美丽然而阴险的陷阱,创造属于独特个体的“时”刻与快“乐”。没人否认,生命只是存在的过程,它的诞生只为湮灭,面对死亡这一常胜杀手,它上阵之前就败局已定。但恰恰是它的绝望属性,能从反抗的徒劳中昭示人性的尊严,能在失败的悲壮里彰显精神的高贵,从而让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洗礼生活,让只有经历的贫瘠却没有经验的丰饶的匆促人生得到拯救……
看来,“哲学家”加缪没哗众取宠,没故作高深,他负责任的一针见血,只表明他有着指认皇帝裸体的清醒与率真。现在,好多年过去了,推着加缪这块哲学的巨石暗夜行路,我的踉踉跄跄竟越来越像优美的舞蹈,并且,我的膂力也得到了锻炼,能让我抱紧心爱的姑娘。
卡夫卡退婚

译成汉语的卡夫卡作品,我大多读过,包括他的日记和书信,包括别人写他的传记。如果文如其人这话准确,那么,文也就应该能说明人。卡夫卡的文基本能说明他。他悲观,忧郁,严谨,自律,是个诚恳的君子温情的绅士,柔弱腼腆却意志坚定,焦虑其里而安详其表。但在有一点上他让我困惑,他在四十一年的短暂生命里,在并无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曾三度订婚又三度退婚,以“甩”未婚妻的方式,涉嫌羞辱了爱他的女人。倒没人规定,订立的婚约不能毁弃,每一桩风流韵事的曲折后路,都必须通往婚姻的殿堂或者地狱。问题是,他不是卡萨诺瓦型的花花公子,也不是叔本华式的厌恶女性者,还与每个恋爱对象间都没什么障碍——比如,与他最情投意合的蜜伦娜虽系有夫之妇,也甘愿为他“牺牲一切”。既然如此,他为何要出尔反尔、左顾右盼、朝令夕改、自欺欺人呢?我相信,当他一次次让爱他的女人情伤心碎时,他心头那种自责的疼痛,几乎会长过他的生命。
好多年里,我一直想解开卡夫卡的退婚之谜,如同为蒙冤的好友找回公道,尽管我知道,欲撬开别人的心底密室,远难于在文明世界搞强制拆迁。是的,卡夫卡有他的夫子自道:婚姻生活会影响写作,会让他平庸,“生活方式的千篇一律,规律性,舒适和依赖性”会毁了他。可如果是这样,像他这等睿智之人,矛盾一把也就够了,哪还用三番五次地百般纠结,况且,在他熟读的前辈同行中,并不缺少现成的楷模:因了同样的理由,福楼拜就拒绝结婚,克尔凯郭尔虽有过动摇,也只订婚退婚各折腾一次。显然,是卡夫卡不肯就事论事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把俗常的婚姻之事,解成了一道旷世难题。
卡夫卡天性敏感多思,质疑追问时,喜欢起步于极端个人化的具体经验,甚至也只止步于此,并不涉足观念领域。熟悉他作品的人都很清楚,他对身体、对家庭、对日常生活与社会机制、包括对他视若生命柱石的小说写作都不信任,他的全部文字,只为诉说同一件事:他置身其间的人类世界,是为加害于他而存在的。他构建匪夷所思的滑稽故事,记叙来路不明的怪诞人物,使用因无助而沾沾自喜、因无奈而津津有味的诡异笔调,孤注一掷地从自我消耗中榨取每一滴渗血的浆汁,以喂养这世间绝望的果实。不难看出,卡夫卡的旷世难题就是绝望,是他那种无可救药的绝望感,以及他对那绝望感的失败的救治。
作为旁观者,我们咀嚼卡夫卡能以苦为甜,可卡夫卡每每自食其果,我猜他一定苦不堪言。一般来讲,再冷酷的质疑者,再决绝的追问者,否定也是为了肯定,粉碎也是为了再造,即使那肯定与再造漏洞百出,多数人也会收了贿赂般含糊验收。毕竟,生命和生活都是缺陷的原型,经不起推敲。可卡夫卡偏执,对自我检点有病态的热情,喜欢将世间缺陷都栽赃给自己,再擘肌分理地加以推敲,任推敲出的疼痛深入骨髓。他没兴趣大约也没有能力,像卡萨诺瓦那类玩世者一样,像叔本华那类厌世者一样,一边以抽离自身的理念谶语去诅咒世界,一边用接纳世界的感官体验去丰腴自身。他的特长是通过自虐缓解紧张,头破血流也要以身试法。
卡夫卡的绝望,由遍布于他生活中的恐惧感受抽象而出,他欲调和与绝望的关系,首先必须克服恐惧,而摆脱孤独,是克服恐惧的通行手段——具体来说,多数人把婚姻视为抵抗孤独的第一道防线与最后的堡垒。于是,有时候,一向与多数人格格不入的卡夫卡也会失去主见,以为婚姻也是能帮他逃离孤独之海的救命绳索。只是,每次伸手,还未抓牢绳索,他便能够及时发现:前方的热闹并不是安全岛,而是一道无底深渊。与孤独之海的令人窒息比,热闹之渊的非我化洗劫更为可怕:热闹意味着侵蚀、剥夺、占有、控制,意味着荒芜的集体习俗对妖娆的个人脾性的覆盖与毁损,意味着自由独立的终将丧失……看来,要么溺毙孤独,要么坠落热闹,卡夫卡面前唯死路一条。
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卡夫卡的首鼠两端,虽然表现为针对某一条或某几条确然死路的判断与选择,但那判断与选择的切片样本,透露出的,却是他玩味失败时的痴迷与执著,甚至喜悦。作为一个内心冲突永远优先于外在行动的人,放弃并非就是否定,他在肯定与否定间广阔的灰色地带艰辛跋涉,只能是他甘心臣服于寻觅与求索本身的一个结果。就此,我愿意以为,他反复无常的订婚退婚,其实是他陷身于另一个千古谜题时的下意识挣扎:爱情与婚姻是什么关系?
爱情是一种愉悦灵肉的人性体验,比较脆弱,但也不无顽强,出之于爱与被爱的本能需要。可许多时候,多数情况下,它和虽然顽强但也脆弱的婚姻,是拴在一起的两只蚂蚱。大部分人,只能看到它们形似,却懒得计较神是否通,把常常落户于物质世界的婚姻大厦,与更多扎根于精神领域的爱情茅屋规划建筑在同一小区,盲目草率或居心叵测地,在它们间画上等号,再出于种种社会化需要,只为婚姻强制保险,不为爱情颁发驾照。可卡夫卡属于小部分人,他相信太阳能带来光明,但不承认带来光明的都是太阳,他不肯忽略爱情与婚姻的根本差异:茅屋必为秋风所破,大厦才支持亮化工程。这令人沮丧,但没办法,主宰生活的不是心因,而是物象。爱情主要通往灵肉的愉悦,是单纯的审美活动,不论多顽强,其“无用”性都决定了它的核心只能脆弱;而婚姻主要指向繁育后代与经济合作,有实际的功能价值,再脆弱,其“有用”性也注定了它的骨干必然顽强。这是审美只能归顺于功能的理由,亦是功能必然蚕食审美的原因。进退两难的卡夫卡,正是在这个关口上没了主见:他冀望于以审美摆脱孤独,但对功能的清醒认识,又让他在更强大的恐惧威慑下瑟瑟发抖。
当然,在卡夫卡笔下,爱情是种稀缺物质,他这个不信任一切的人,未必会将其视为例外。也许我在强加于他。我相信爱情。但我比相信爱情更加相信,某一存在之所以价值巨大,正在于它可供误读与曲解的阐释空间格外广阔。那么,对卡夫卡磨磨叽叽的退婚行为,我继续解读为那是他在诀别爱情,不算牵强也说得通吧:他退掉爱情,其实是退掉了生活中萌芽的希望,退掉了生命里残存的可能,退掉了对于绝望的救治。
责任编辑/鲁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