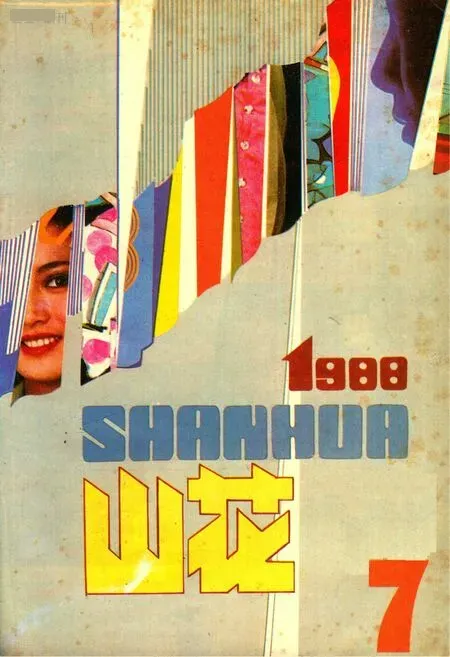世纪末的焦虑与渴望
——回望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
2011-09-27王光明
王光明
世纪末的焦虑与渴望
——回望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
王光明
结束,还是开始?
是否由于“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缘故,近代人类史每个百年的结束与开始都是那样让人充满焦虑与渴望?
在19世纪末,那蔓延于整个欧洲的“世纪末”氛围,是那样地让罗曼·罗兰不堪忍受,认为整个“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以至于决定写作贝多芬、弥盖朗琪罗、托尔斯泰等人的“名人传”,让世界“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1]
而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个人静月黑之夜,“少年悬弧四方志”的中国青年梁启超,则夜不能寐,在横渡太平洋的船上写下了壮怀激烈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
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
………………
海云极目何茫茫,涛声彻耳逾激昂。
一百年后20世纪的世纪末,人类的焦虑与渴望不是降低了,而是变得更加强烈。虽然苏联的解体意味着近半个世纪冷战时代的终结,保守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热情逐渐降温,利益主义和技术主义成了行动的主宰。然而世界似乎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安宁与和谐,相反,它面临着更为错综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变得更为尖锐复杂,另一方面,积弱贫穷的第三世界既盼望着发展变革,同时也对大国霸权和经济、文化侵略忧心忡忡。东方与西方、边缘与中心、贫穷与富有、经济增长与精神危机,各种矛盾纠结缠绕。
而中国,一百年前开始的现代转型,也面临着新的历史性的调整:既是从高度集中的政治社会,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变化的结构性调整;也是由把现代化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到把现代性作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的认识上的改变。一方面是,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参与世界;另一方面,必须在后冷战时代重建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才能在混乱的世界和发展的焦虑中获得强大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焦虑与渴望,这种纠结缠绕,并没有随着一个世纪的结束画上句号。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文化生活的边缘化与市场化
处在世纪末的焦虑与渴望,以及社会转型矛盾双重背景中的90年代中国,面临的改变不仅是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也是思想和价值观念。处在这种改变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矛盾和心理冲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紧张强烈。在政治上,冷战时代的政治思维和两极对抗的思维方式面临着重大调整。在经济上,越来越开放的资本与市场,表面看来是削弱了传统的权力,给人们带来了公平、平等和自由竞争的机会,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这仍然是强者的公平与自由,而不是弱者的公平自由:浮沉在生活海洋中的普通人只能被迫承受国际资本或权力与资本合谋的市场“规律”,而无法与市场产生有互动意义的对话。
而文化与文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是面临着边缘化和市场化的巨大压力。90年代初的传媒随处可见作家经商、文人下海的报道,所谓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所谓穷的是教授、傻的是博士,虽然只是社会一时的价值失重,但连某个著名作家都站出来鼓吹“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从事科技开发、三流人才搞行政、做文人不是白痴就是天才”的时候,人们就不难理解,一些活跃于80年代的年青学者,为什么如此深切地感到“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作家、批评家卷入这场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戏剧性转型实际上突出了精神问题的重要性:没有文化的凝聚力,没有精神归属,没有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功利主义就会一统天下,人就将失去作为人的尊严。
但市场还是以它金色的媚眼改变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和想像方式。过去把女人漂亮比喻成一朵花,但90年代的一本小说却说“她的脸像人民币一样可爱”。过去人们说诗言志,歌缘情,把文学写作当作安顿灵魂、在创造性想像中获得满足的一种精神方式,而现在许多作家却在揣想市场的卖点,不仅出现了文稿竟拍、作家稿酬年收入上百万元的现象,还有大腕导演出价征集一部武则天题材的小说。更不用说性题材和“成功人士”的自传横行市场了,《废都》因庄之蝶与多个女人的关系成为禁书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白鹿原》的开头被理解为白嘉轩“一上场就干倒七个女人”,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一些名星的自叙传发行量远远高于质量很高的纯文学作品。

张帆作品·灵宫活石 之一 三联水墨 180×288cm 2009
这是一个被市场主导的时代,创造性想像的满足不再是创作与阅读的原动力,而是变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关系。这是既面向国内也面向世界的生产消费关系:一方面,在向世界开放的趋势中,国内市场需要更新鲜的故事和异域情调,因此新移民文学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也要吸引西方北美等老外的眼球,让中国故事占领世界市场,得外国人设的奖项。《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代新移民奋斗过程的辛酸血泪,不仅展览了异国风情,也强化了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论述;而《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霸王别姬》等都是当时给西方观众留下过印象的中国电影。当然,就像新移民文学要满足中国读者对异域的猎奇心理一样,向西方人讲中国故事也要顺应西方人的趣味,因此在那些电影中,既杂糅了西方观众对神秘东方的风俗、性与政治的传统兴趣,也加入了诸如同性恋之类的新时尚。有观众不满电影《霸王别姬》中同性恋情的表演,责怪演段小楼的张丰毅的没有接好演程蝶衣的张国荣的出色表演。实际上怪不得张丰毅,因为那是导演对“同志”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入理解。
文化生活的边缘化与市场化改变了人们的文学态度和阅读期待,文学观念、价值尺度受到了挑战,文学趣味、经典的神圣感和权威性也受到了质疑。这是一个似是而非、话语泛滥的年代,又是一个失重、失范和失语的年代。文学正在疏离五四以来在兹念兹的历史抱负和重大题材,形形色色的“个人化写作”成了文学舞台的主角。在这个时代,一方面,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写什么和怎么写已经没有什么禁区和禁令;另一方面,人们发现市场又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具有把一切“格式化”、货币化的力量。一方面,“个人化”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但另一方面,在天使和魔鬼都远离文学的时候,文学也变得无家可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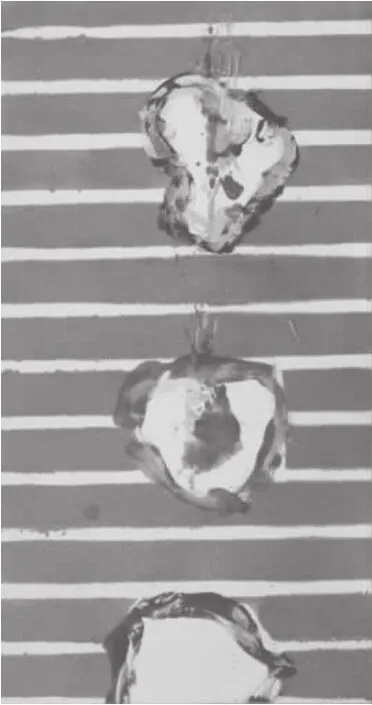
张帆作品·灵宫活石 之二(上) 二联水墨 360×96cm
在90年代的门槛上
海子是不是较早就有无家可归的预感的诗人?在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中,曾想像过这样一个“春天”的情境:那时候十个海子全部在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着沉浸于冬天的“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村庄
此诗的写作离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不到两个星期。在这首诗中,作者为什么要把作为诗中说话者的这一个“海子”和在春天复活的十个海子作鲜明对照,为什么站在春天这边、守望村庄的“海子”变成了“冬天”的遗民,“野蛮而悲伤”?联想海子另一首名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中说话者对今天与明天的划分,感受其渴望“明天”却只能站立在“今天”的忧伤,我们不难体会海子对于即将到来的时代的渴望与恐惧:作为一个热爱土地、村庄而“不能自拔”的诗人,海子比谁都更强烈地预感到一个“光明的黑夜”的来临。这是海子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在上一个世纪就揭示过的现代之夜,后来被这个时代的小说家称之为“华丽的世纪末”,许多诗人都恐惧它华丽的荒凉,身心被它所撕裂。海子自杀于1989年3月26日,他谢绝跨入90年代的门槛,而进入90年代后自杀的诗人则有戈麦、顾城、徐迟、昌耀等。
我们不必讳言诗人的自杀有着不同的个人原因,但作为某种文化与精神症侯,却正是敏感的诗歌(与文学)与时代紧张关系的见证。在20世纪末,许多诗人(作家)的自杀或象征性自杀(文人下海、弃文经商),醒目地放大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通过荷尔德林的诗歌所提出的问题: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而这个世界性的现代问题在90年代中国语境中又显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它是“幸存者”的心理与精神压力,正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劫难时所说的那样:“在奥辛维兹(Auschwitz)集中营大屠杀之后,诗不再成为可能。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对今天为什么不能写诗的理由的认识。”[2]死亡之后,诗歌如何说话?毕竟任何“事后”的书写,都不足以形容“事发”的情形,幸存者不能代替受难者承受死亡与伤痛,诗歌怎能补偿历史的错误?另一方面是,灯光转暗,垂幕放下,剧情已新,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中国进一步的市场化,使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在财经挂帅和大众传媒的引导下,谁还会上演堂·吉诃德的剧情,你又上演给谁看?90年代有多少诗人与读者在移情别恋,有多少“写诗的人比读诗的还多”、“诗歌成了小圈子里的东西”的议论!而关于文学的议论,对事件的兴趣也远胜于对文本的兴趣,就像许多人对90年代的诗人自杀津津乐道,却对那些诗人的作品知之甚少一样。消费意识进入了文艺的阅读与观赏领域,普通读者更愿意消费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故事,而不愿认真品味故事里面的感觉与情趣。
因此,如果说海子的自杀象征了80年代文学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主体精神的终结的话,电视连续剧《渴望》则是当代文艺向世俗位移的一个拐点。《渴望》的主题是歌颂勤劳、善良和忍耐的传统美德,给人们提供了“好人一生平安”的道德承诺和精神抚慰,但它同时也强烈地表现出了某种逢迎与媚俗的倾向,为市民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提供了既有政治安全感又有丰厚市场回报的文化生产模式。
当然,不是只有对市场的逢迎,也有悲壮的抵抗。这是跨进90年代门槛的另一种文学倾向,有人试图给它以“抵抗投降”的命名。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以笔为旗”,保卫“念想”,抗衡物质主义时代的来临。与那种顺应市场、取悦读者的写作倾向不同,张承志写到90年代“总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拒绝读者的冲动”,通过《心灵史》向人们展示了与物质主义相对的另一种生存逻辑:在那丧失了世俗经济文化的起码生机的土地上,也有人追随“念想”,通过主观精神对自己生活环境的“场地净化”,营造一块精神的净土……

张帆作品·灵宫活石 之二(下) 二联水墨 360×96cm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伴随着电视剧《渴望》、王朔的小说、汪国真的诗与《心灵史》为代表的“抵抗”文学进入90年代的,它们代表着当时文学的两个侧面或两种极端,典型体现了转型时代文学立场和观念上的冲突。而后出现的以贾平凹的《废都》、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为标志的“个人化写作”现象,则是转型市场经济后的衍生物,它是90年代文学困境与可能的体现:这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但这也正是一个拥有新的可能性的时代;写作,不只是为了肩负某种历史或时代的使命,更是出于表达内心和想像世界的需要。
注 释:
[1] 傅雷:《傅译传记五种》,1995年版,第121-123页。
[2]见《否定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后来阿多诺在《许诺》(Commitment,1962)一文中又说:“我不想淡化我过去的立论——‘在奥斯维辛后写抒情诗乃野蛮之举’……然而艾森柏格的反驳也确为真切:‘文学必须抵制这个宣判’……实际上现在只有在艺术中,苦难尚能找到它的声音与慰藉……艺术作品无言地承担政治所无法负荷的责任。”(The Essential Frankf urt School R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