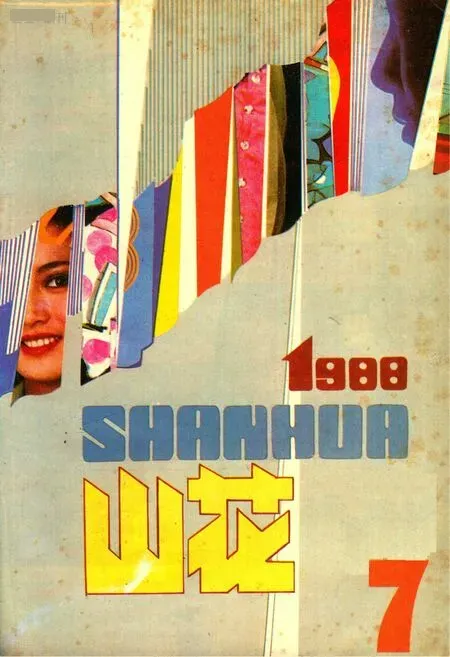鲁院:文学的现场(外一篇)
2011-09-27宁肯
宁 肯
鲁院:文学的现场(外一篇)
宁 肯
鲁院:文学的现场
诗,戏剧,文学艺术古老皇冠上两颗古老的明珠,鲁十三以自己的方式实验了摘取了。似乎与教学无关,与要求无关,好像完全是自发的,是生命的丰富性与实验性达到秘密的熔点自然的爆发。但说到底,又怎么能说无关呢?在鲁院,没有不相关的事物,一切都是相关的,因为一切都与创造相关。只是某种相关是建立在氛围中的更深层意义上的:即鲁院不仅仅是课堂,是五楼的教室,它同时还提供了更为重要的生命与文学交互的场域:文学生活化,生活文学化,在生活中体味文学,在文学中体味生活;生活与文学几乎共生同一,如同一种行为艺术,一个机位固定的长镜头――是真实,又具一定程度的表演自己的性质。这是任何一所大学甚至艺术院校都不可能实现的,但在鲁院却成为了四个月的可能。四个月,来自不同省份的五十个一线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编辑(主编)、批评家,一届又一届,在这个抽离的场域成为最活跃的文学现场。还有哪里或什么地方、哪一家杂志或出版机构能称得文学现场?现场三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鲁院可谓条件齐全。当然,毫无疑问,就意识形态的初衷而言,这个现场的存在是有规约性的,但就像这个过渡性时代(后极权时代)的许多事物一样,主体与客体乖离,正如股市常见的乖离。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律令性与自反性,而奇妙的是它又必须以被它拒绝的东西为其存在的前提。这在我们这个诡异的时代并不荒诞,相反很正常。而文学的真谛爱,同情,自由,独立,思考,抵抗,批判,真,善…这一切来于自身又怎么可能脱离自身?这里的一切都可以说与此相关,包括课程设置,教师选择,比如何光沪的课,牛宏宝的课,王瑞芸的课,王小鹰的课,这些课都直指人的核心,时代的核心,文学的核心。在这样一个复杂吊诡的时代,任何简单的或单向度的价值判断人只能反映简单的大脑。凡是喜欢断言的人、一言以蔽之什么的人,不是内心充满暴力就是头脑简单,或二者兼而有之。温和,理性,明辨——总是被甚嚣尘上的简单所遮蔽,所蒙尘,以至难以清晰的面貌立于当世。
事物总是相辅相承,相映成趣。前面,许多小节,我竭力回避严肃地谈论了四个月鲁院场域的丰富性、暂时性与实验性,现在我谈及了鲁院严肃的教学。这时候谈鲁院的严肃性,即只有在丰富性与实验性的基础上谈鲁院的严肃性,才有严肃性的完全意义。失去前者,鲁院的严肃性将大打折扣,缺少根基,而有了后者前者的丰富性与实验性才有所附丽,二者共生,不可缺一。我的意思是,作为文学的现场鲁院,它除了提供了一个文学发生学意义的“舞台”,一种精神与生活双重的维度,其另一特征便是提供理性与知性。然而,鲁院并不是一张传统的经院的面孔。经院扼杀生命,扼杀创造,让灵感甚或灵魂消失。经院与“现场”正好相反,经院通常指的是过去的静态的东西,指的是与创造性生命无太大关系的知识的积累,而现场是“用学”共生,是与过去和未来都相关的正在发生中的事情,是“前台”而非无边无际的“后台”。因此,这里设置的课程不是漫长的教科书式的,而是高速的讲座式的。讲座具有现场性,交互性,富于启迪,生发,对写作者而言,还有什么比角度多变的讲座式教学更适合的呢?每天都是不同的老师,不同内容的讲座,每个老师讲得再精彩也只讲一次,没有第二次机会,因此每个老师讲的都是自身研究领域的精华,都是知识节点,同时带着各自的体温。体温很重要,没体温的知识是死知识,有体温的知识是活知识。试想一个教师讲一本教科书会有体温吗?会传感生命吗?而讲座是可能的。讲座看起来是孤立的,但一系列的讲座却构成了一个跨跃的极为广阔的知识网,今天是欧阳自远的宇宙星空,明天就可能是叶舒宪的中心与边缘的文化人类学,今天是电影,明天是后现代音乐,今天是舞蹈,明天就是军事,今天是绘画,明天就是宗教,四个月大体有四十个跨学科跨领域的顶尖高手来讲座,简直让人眼花瞭乱,应接不暇。文学创作不就需要海阔天空眼花瞭乱吗?没有海阔天空眼花瞭乱怎么可能有活跃的迸发的文学现场?四个月——我们仅仅经历的不同体温与面孔的老师就已打开我们的生活空间与想象空间,而非单纯的知识空间。在这里一切都针对着特殊的写作者群体,一切都为了创造而设,这种教学思想应该说煞费苦心。这样的教学(竟然是规约性意识形态的产物——事物之复杂吊诡可见一斑)怎不唤起最易感群体的激情?怎么可能不发生诗歌事件,戏剧事件,心灵事件?怎可能没有面对古老西子湖的口占?怎么可能没有向传统向文化的致敬?没有向文学的边界与可能性的冲击?
经常性的学员作品研讨会,是教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且形成了某种文学批评风格。这种风格最大特点就是批评的现场性,写作的内部性。没有语言的空转、意义的滑动、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大而不当,这个场域的批评不存在这个。这里的批评植根于现场、作家、作品,针对的是文学内部,创作内部。这里的批评形式也完全不同社会上的研讨会,要立体得多,有效得多,及物得多。首先是作家之间的直觉性的批评:或争论,或对话,或交锋,甚至常常面红耳赤;然后是佳宾的专业批评(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庸常,让人感到没有进入文学创作内部,没进入文学现场语境,还是社会上那一套)。最后,是郭艳老师颇具理论背景的评点梳理、施院长感性精准的点穴式批评。
施郭两驾批评马车构顾了鲁院特有的批评风格,或许将来在文学批评界可称为鲁院学派——当然要有鲁院学派,特别鲁院提供了如此丰富独特的可能——他们的风格体现在学员作家身上。他们发现并确认作品价值,指出局限与可能性,厘清理论背景,针对写作内部发言。这当中我当然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对我在鲁院期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藏》的评点,虽风格不同,却都同样洞幽。比如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郭艳从后现代理论背景上发现了《天·藏》的“启蒙”价值,一般认为后现代是对启蒙的质疑与解构,郭老师看到问题的复杂性,看到了《天·藏》中“某些类似启蒙时代的理性之声,”“因为作者本身对现代后现代社会文化较为深入透彻的理解,这种启蒙在去魅的同时又完成了复魅。”“去魅即是重新唤醒理性思考、冥思和精神对话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性,复魅则是在这种理性的精神对话中,不再认为科学的、哲学的、思辨的甚至怀疑论者的精英和超验地位,反而赋予神性更加超拔的精神意味。”(以上引自郭艳博客)由此可以看出郭老师的思辨与洞幽达到了怎样的维度。而施院那天同样清晰、准确地谈到了《天·藏》的巨大理性(与盛可以巨大的感性相对照)、作品场域的普适性、超地域性——即《天·藏》这样的小说放在世界任何一地都适合,以及《天·藏》所含的“天机”——因此也可读“天藏(cang)”,这些都让我叹服,深思,时时回味,觉得头上有一片天空。
鲁院是价值发现之地,对于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还有什么比对其价值的发现与辨晰更为重要的?而来到鲁院你就等于来到价值发现之地。很多时候你已写出相当出色或有个人特点的作品,如果你还没被发现或被同行认可(相当多学员没得到真正的发现),那么到了鲁院这个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现场,你不被同行发现就被老师发现,反之亦然。总之,任何发现都会成为鲁院的发现。比如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已有相当境界的王宝忠、李进祥两个人,在文坛上一直默默无闻,说实话,过去我完全不知道这俩兄弟,而当我读到他们的作品我是那么的惊讶,感叹,他们的品质、心态、技艺以及所透露出来的精神背景和支撑,读过之后久久挥之不去。在鲁院研讨会上他们价值凸显,一下成了明星。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学的深水层(他们代表了一批人),其价值会慢慢显露,迟早会水落石出、显示出这个时代曾经有过的伟大的存在。

张家瑞作品·树不子——怒江 木炭油画150×180cm 2009
代表鲁院风格的还有那些年轻的领课教师,他们朝气、儒雅、风度翩翩,一代年轻学人,让人想入非非,他们引进老师,开始和结束的介绍与简评虽然短暂但完整精当,颇富形式感。形式有时就是内容,形式意味着一种自信,甚至一种未来风范也未可知。还有,我不能不再次提及十三的沙龙,我主持多次,我曾讲过的“症候式写作”,前面我不愿谈,曾说自己因此加重了十三的模范与严肃,现在讲情况已全不同,不仅不再觉得自己是一张模范如同桌椅的面孔,事实上因为有了那些沙龙,讲座,研讨会,我的点评,我的面孔已变得更加丰富,不仅仅与周朴园、诗歌朗诵、西湖三叠、世博园有关,也与整个鲁院之维有关。我的面孔,或者十三的面孔,应该由毕加索或达利设计,它们具有立体与梦幻性质(当然,十三的面孔是难以复制的)。那么鲁院的面孔又是什么样的呢?场域,作家,教学,批评,四位一体,一届一届,已历十三,构成了时间中的文学的现场与鲁院的面孔。
现场相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是历史。
酒 会
酒会,当然要有酒会,毕业酒会,最后的晚餐,然后离开,历届如此。但是今年似乎有所不同,因为有了最后的戏剧成功,有了意外的高潮与落幕,一切与往昔有所不同。本来,酒会并非安排今天,而是明天毕业典礼之后,院方根据情况及时做了调整,将联欢会与酒会连在一起,如同导演做了最后的调整。
而且,鲁院本身是一个舞台,是四个月的一幕大戏,角色基本相同,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每次演员不同。有趣的是,演员的不同使相同的戏每每十分不同,每每都有或大或小的意外与溢出。
鲁院传统的毕业酒会一般都在贵州饭店,到十三改为了华都饭店。这也说明对十三而言一切都充满了变数、神秘与戏剧性。带着对自身的惊异、挥之不去的戏剧精神、高潮即落幕离场的复杂心情,谢幕的十三步入最后的金碧辉煌的华都饭店宴会厅。饭店坐落在东部酒店区域,灯红酒绿,奢华大气,对比鲁院周边的民间气息,烧烤摊的烟火,污水,光膀子喝酒,一切都有登堂入室的极致之感,一切都仿佛告诉十三:这是最后的日子,笑,哭,狂饮,倾诉,离别,随便吧,一齐来吧,尽兴吧。即使一贯的对一切都满腹狐疑的顾飞也在后来的博客里稍稍放下了解构的姿态写道:“临散伙的前一晚,学校把大家拉出去聚,说放开来喝。同学们果然很放得开,喝着喝着,有人唱歌了,有人跳舞了,有人拥抱了,还有人哭了,主要是女生哭了。这是一次类似春晚的大聚会,有人模仿杰克逊,有人跳着维吾尔;左边是慢三,右边在蹦迪。那边还有排着队伴奏的,唱爱江山更爱美人,唱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这个场面非亲历不能想象,欢乐,离愁中的欢乐。我和小胖子当忠实的观众,抱头大笑。小胖子说我爱死我的同学们了。这家伙说到底还是爱十三。是,那个晚上每个人都放下了最后的矜持,最后的底线,不喝酒的人也开始喝酒,少喝的开始多喝,笑哭两股混乱又快意的力量在身体里乱窜。我来鲁院后已喝多过多回,这一次当然、毫无疑问要喝多。但即使我喝多了也没忘记“西湖三叠”,三叠今天没能进入戏剧联欢演出的空档让我觉得有点遗憾,我认为它会给戏剧联欢增色。但自三叠发生以来,似乎它总是不能被接纳到十三的整体,好像只属于几个人。的确,三叠太出离集体,太让人不可企及。遗憾也不算什么,遗憾自有动人之处。但现在,是时候了,必须重现三叠。今天放开一切,做想做的。我们重现了,排成一排,就像当初在湖边。没多少人听我们的,大家都多了,都在执着地展示着自己,都在那么真地敬酒。
我当然多了。有人在哭。好像有人在告诉我说杨帆在哭。我立刻有种醒酒的感觉,回头找杨帆,感觉又回到戏中。是,一切仿佛并没结束,只不过一切看上去都有些重影儿,戏与现实重叠,自己与另一个自己重叠。杨帆显然已经哭了多时,显然还喝了酒,而她平时是不喝酒的。她的高脚杯中有着红色残液,一如脸上残存的泪迹,并且是双重的泪痕。那么我是谁?也有些重影儿?时而对得上自己,时而对不上。现在,就在我写这篇文字时,我已回想不起来我当时对杨帆说了什么,但我记得一到她身边就开始跟她喋喋不休地说,现在我还能清晰地看到我当初的情景:我端着杯子,认真,特认真,滔滔不绝,完全是醉态。我想我在谈戏中情景?戏外生活?周朴园如此关心繁漪,戏中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到底是戏里还是戏外?我记得她一直不说话,一直听我说,听得很认真,简直是在谛听,或者什么也没听。说着说着又想起侍萍,对了,侍萍呢?想侍萍就有了侍萍,同样就像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去找侍萍,我们三个人不知怎么仿佛就像云一样聚在了一起。我们都已离开了座位,怎么离开的记不得了,总之我们好像是在舞会上,我们在途中相遇,一下都把手伸出来,头碰头,搂在一起。我们喁喁而谈,还是主要是我说,对繁漪说完对侍萍说,对侍萍说完对繁漪说,完全是醉态。不过偶尔也会醒了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一下抬头一看,看到大庭广众,看到众目睽睽,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又好像有人在哄我们。
音乐响起,舞曲响起,或者早就响起刚刚听到,我邀繁漪跳舞,她不跳,我拉她起来,边跳边滔滔不绝。后来又跳了迪,与同桌的娜娜跳,后来如何结束的已完全记不清,也不知怎么就上了大轿车,不知怎么回的鲁院。能记得的就是又在鲁院烧烤摊上接着喝酒,啤酒,白酒,完全乱了。虽然已完全不醒人事了,但神奇的是居然就是不倒,而且,居然有一刻知道自己手机丢了,记得有人帮我打我的手机,是关机,说明真丢了。丢就丢了。接着喝,说了许多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后来有人问我,知道我那晚都说了什么,我说不知道。
喝到什么不记得了,记忆一鳞半爪,残缺不全,记得最后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和烧烤老板喝,不知怎么和老板喝上了,记得后来突然意识到不对才起身回家。没有倒下,几次要倒,没有,坚持,天旋地转。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突然发现天亮了,酒就有些醒了,而且突然发现自己就站在自己家门口。
手机丢了,似乎是个隐喻。九点钟急起,参加毕业典礼,代表学员发言,念《鲁院的意义》,仍不是特别清醒。这一天是七月九号,全天告别的一天,我的手机丢了,和所有人失去联系。那一天,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告别的信息。只能在家里看虚拟的班博,看到安昌河,那么大脸,哭得那么灿烂,那么难看,那么崩溃,那么震撼,我觉得安昌河的脸也是我的脸,所有人的脸,眼睛禁不住一片模糊,崩溃,大哭,如此快意,笑,在泪中大笑,在笑中飞……结束了,鲁院,十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