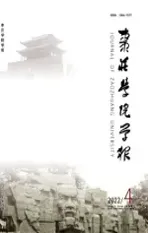世变缘常——试论林斤澜80年代小城镇小说
2011-08-15耿艳艳
耿艳艳
(陇东学院 文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近年来,对于小城镇文学的研究,成为饶有意味的话题。研究者们认为:在中国近代,随着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到来,小城镇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文化上居于新与旧、变与常、西与中、现代与传统的过渡带,因而,产生了独具个性的小城镇文化。所谓都市与乡村的碰撞交流,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争斗融合,在某种意义上都间接地通过小城镇发生,都较集中地体现在小城镇身上。小城镇成为了中西两种文化和文明交汇或碰撞的合适空间,上演了一幕幕人生与文明的悲喜剧。于是,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物的近现代文学,开始将小城镇纳入视野,小城镇文学由此应运而生。[1](P3)
的确,从鲁迅的“鲁镇叙事”开始,无论是茅盾、叶圣陶、沈从文、萧红、沙汀,还是汪曾祺、古华、张炜、贾平凹、李杭育、何立伟等人,无不在创作中对于小城镇人的生活予以关注与描写。因此,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众多的以小城镇为背景甚至为文学角色的小说创作,其中不乏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古华的《芙蓉镇》、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张炜的《古船》等等。以此归类,林斤澜也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矮凳桥风情》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作家用他一贯微笑的眼神,宽容的心态,写下了那份独具的“感受”。
一
1983年,林斤澜将个人对家乡人事的惊异感受以“印象”的笔触写了出来,成就了《矮凳桥风情》。正如他在《后记》中谈到的感觉:故乡“好比埋藏了几千年的能源忽然暴露”,“这些人自己都说不清楚碰着了哪一根筋,怎样踩着了哪个点子,如何如何就爆发起来了,钞票成捆成捆地塞到床底下,店面一间接一间打开,三层楼四层楼一座比一座造得讲究,把旗号打到天边,把全国走遍,如果香港也随便去得。”[2]故乡人们的龙腾虎跃、勃勃生机造就了《矮凳桥风情》中欣欣向荣的改革镜像:
新经济政策下来的几年里,江南神秘的小镇“矮凳桥”暴发了起来,来不及造店面、挂招牌,先摆摊子,老街上挤着六百家纽扣商店和摊子,开着三十多家饮食店,寸土必争。什么车辆也开不进去,人也走不开。一条街一天的营业额,论两位数的万。汽车公司特别为这个乡镇加班,经常加到五班。“邮电局、银行、电话局、税务所,连带着派出所和医院,都不能不到这个乡镇来设点设站,不断添人、造房子”,“摊子上是纽扣,店堂里是纽扣,后院作坊里也是纽扣”,“常年有成千的供销员,走遍了城市乡镇,走草地走戈壁滩。走到国门边卡,人回来,纽扣走出去了。”[3](P75~76)
矮凳桥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靠着小小的纽扣,给社会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和旺盛的活力。这种变化和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80年代一大批小城镇的发展状况。
作者在表现家乡小镇改革开放之后整体生活欣欣向荣的同时,更在意的是居住其中的小人物生活及其感情的发展变化,这更能揭示时代风雷,更能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城镇经济的发展变化。《溪鳗》里,溪鳗对女儿说,你赶上好时候了,妈妈有权开店了,不用再担心受改造、割尾巴了。仅仅几句话,反映了经济政策的利国利民,小镇居民的欢欣鼓舞。《丫头她妈》里,从小种田的丫头她妈,到现在才觉得种出来的东西珍贵、旺俏,才觉得自己的劳动值钱了,就连人都值钱了。经济搞活为小镇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笑杉》里,车钻身上的衬衣长裤,是日本式的剪裁,头发也服服帖帖地“巴”着头皮,还有花露水的香味。因为只有穿上这样一身现代派,出门才吃得开,才能代表矮凳桥的形象。小镇人也懂得了包装,懂得了形象的重要。同时,新兴的方言更暗示了人们生活的变迁。早先只说顶条扁担——百字,就不得了了,后来说甩一撇——千字,也吓人,哪像现在,车钻会说出去随随便便捉个把猴子——万字回来。还有,以往连“中文也难得用”[3](P70)的小镇,却正经用起了英文,车钻开始用英文来介绍纽扣,推销员们也会用简单的英文同客商交流。这是多么令人可喜的变化。
二
然而,正如孟悦所说的,“作为一个饱领大半生社会沧桑的作家,一个在时代变幻中‘写东西写老了’的人,势必会将他独有的那一份源自历史、源自人世沉浮、源自生命本身的彻悟与睿智、信念与希冀灌注在自己的作品里。我也因此相信,《矮凳桥风情》正在不仅以它明确说出的东西,而且以它未曾出口的东西,以它的全部存在,把作者半世思索感受的精华馈献于当今。”[4](P24)作者不会仅仅陶醉于故乡经济发展变化的欣喜当中,他“未曾出口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故老乡亲的根底精魂,就是我们民族普遍的品性,汪曾祺曾认为那是“生命的韧性”,而用林斤澜的小说语言来说,就是人的“皮实”。作者用他微笑的眼神,注视着“矮凳桥”人的过去,更关注着“矮凳桥”人的现在,在欣喜于家乡风情的同时,寄托的却是对于推动这种变化产生的内驱力的肯定,即对于人的生命韧性的肯定。
《溪鳗》里,正派、勤快、像一个魅人的水妖似的溪鳗无论小镇饮食业怎样的起起落落,总是从容地做着她的鱼面、鱼丸,淡定自若。《袁相舟》里,袁相舟在任何环境中都能适应和生存,用那只“不闲着,又安闲;不争不抢,又固执”[3](P26)的手,显示着自己生命的“旺俏”。《李地》中,别人因为莫须有的“尾巴”无故自惊,炸了营的时候,李地却在感受着自己肚里那块肉的“一拱一拱”,猜想着“这圆轮轮的是脑袋还是屁股?”[3](P231)她的一生,无论遭遇什么,都能融化在一杯“静定”的茶水中,一个衣柜的角落里。就连《章范和章小范》里,被叫做“老张谎儿”的章范,在困苦卑微的生活中,也能用吹牛扯谎来“开胸化气,消愁解闷,舒筋活血”。[3](P103)这群人抛开了所有不堪回首的记忆,埋葬了所有的刀光血痕,留下的是仍然“天真”的童心。他们没有眼泪,有的便是历史和人生锤炼而成的超然与淡泊。正如汪曾祺说的那样: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中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得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
老一辈靠着皮实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在改革年代,继续着他们生命的旺俏;而小一辈则靠着皮实在改革的风浪里纵横驰骋。或许,这一切都是由于温州小镇的地理人文、人情世故所构成的独特“风情”,渗透在人们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憨憨》里,供销员憨憨,面对着生存和竞争的压力,独有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憨气”。身着一身单衣,在大雪里,硬是走到了最后一个工厂,回到南方后,笑翼看到的是两只“真正黑了”的脚。用这双脚,他走遍了“天南海北”,成为了矮凳桥第一个起楼的供销员。《蚱蜢舟》里,从小以“皮市”出名的笑耳与小周,在新时期到来后,放开手脚,做出了可以是领扣、是帽花、是装饰的小蚱蜢船儿,赚了大钱。《车钻》里,小时侯专做刁钻、古怪事情的车钻,在变革年代,钻出了矮凳桥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生意经,办起了一个纽扣资料公司,且发了财,闹的人心浮动不已。可见,矮凳桥的新一代人,有着他们克服生活艰难的决心,也有追求事业和幸福的毅力,当然,更有在新时期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创造新生活的无限生命力。
三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小城镇在中国当代和未来社会格局中重要性的日益加强,秉着现代小城镇文学的传统和精神,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小城镇小说。如古华的《芙蓉镇》、柯云路的《新星》、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张炜的《古船》、李杭育的《沙灶遗风》、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等。这些小城镇小说,充分地展示着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特殊状态,“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5](P339)呈现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作家们特殊的心理状态与思考角度。赵冬梅认为这些小城镇小说中,虽然多多少少反映了历史变革、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冲突、眷恋或批判”,“但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期待、肯定和认同,更多的是对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一历史时期的反思和批判,对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在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生活观念等方面的思考、探讨和批判等。”[6](P56)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未来突飞猛进地发展,人类历史在“第三次浪潮”中进入了信息革命时代。中国人民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以后,面对飞速发展变化着的世界变得目瞪口呆,开始了冷静的民族自省。如何使中华民族赶上当代世界发展的步伐,屹立在世界的民族之林,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中共中央适应时代的要求,代表了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因而,作为关心祖国前途与人民命运的中国人的一分子,林斤澜说,“面临一场大改革,关系着民族的振兴,我也要研究研究”[2]。但是,作者看到的不仅是现实中的火热与变化,而是旺盛的活力下推动历史前进的内在魂灵,即我们民族普遍的品性。这才是我们的恒常,我们民族屹立不倒的基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斤澜并没有用一种悲怆的或是嘲弄的感情来看矮凳桥,我们时时从林斤澜的眼睛里看到一点温暖的微笑。《矮凳桥风情》不仅“描写了处在时代变革中的小城自身所不可避免的变化”[6](P56),而且完成了“对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积淀的挖掘和表现”[6](P56),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成为80年代小城镇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逄增玉.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5).
[2]林斤澜.矮凳桥风情后记[A].矮凳桥风情[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3]林斤澜.矮凳桥风情.林斤澜文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孟悦.一个不可多得的寓言——《矮凳桥风情》试析[J].当代作家评论,1987,(6).
[5]沈从文.长河题记[A].沈从文小说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6]赵冬梅.20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J].南都学坛,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