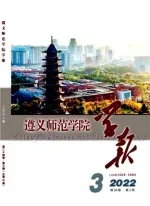新启蒙主义语境下的萨特在中国的译介
2011-08-15刘大涛
刘大涛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2)
70年代末,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上“拨乱反正”,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同时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激发了学术思想界对新中国历史现实的全面反思与批判,以清算“文革”乃至整个极“左”思潮对人的“非人化”、“异化”的践踏,这被学界称为新启蒙运动。在“重返五四”的启蒙现代性语境中,人道主义话语再一次成为各种思想论争的聚焦点,并成为新启蒙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一时期,为了满足人道主义需求的现实迫切性,人道主义犹如一个万花筒,什么理论都可以装在里面。不仅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是人道主义,而且现代西方一些人本主义哲学家,如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等人的理论,也被看作是人道主义理论。加上萨特还发表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新启蒙知识分子在宣传他的理论时,就显得更为理直气壮。由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是被新启蒙知识分子借用来启蒙大众的思想文化资源。于是,对萨特的译介就比较迫切,并被迅速提上了日程,曾一度掀起过译介萨特的热潮。
在80年代,译介者不仅翻译了萨特的大部分著作,还翻译了一些西方学者专门研究萨特和存在主义的专著。即使有些著作一时还没有被译介,他们也在努力地撰文加以介绍,并且积极关注世界各国研究萨特的最新动态。萨特的译介,对启蒙现代性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复旦大学林青教授翻译、发表在《外国文艺》1978年7月创刊号上的《肮脏的手》,是新时期出版的萨特第一部作品。萨特最初发表这部剧作时,就被认为是一部反共的政治剧,而遭到各国共产党的封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是新时期萨特译介的第一部作品,并且在1981年被著名导演胡伟民搬上了中国的戏剧舞台,产生过很深的影响。此外,1978年10月,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的《外国哲学资料》(第四辑)上,发表了陈启伟翻译的《科学和辩证法》。在197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一书中,收录的《想象的事物》一文,摘译自萨特《想象心理学》的结论部分。70年代末翻译的萨特这一部作品和两篇文章,虽然不再是为国内学者批判“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提供“反面的教材”,但仍然是“内部读物”,也就使得它们的影响只能局限于学术界。由茅盾题词,面向广大读者开放的《外国名作家传》(1979)(中册),将萨特纳入了外国名作家的行列。主编张英伦亲自执笔撰写的《萨特》一文,对萨特的文学作品及其社会活动做了言简意赅,同时又不失中肯的评价。这表明文艺界同仁对萨特开始认同和接受。
在“新时期”,真正让萨特“进入”中国的,是被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柳鸣九先生。作为《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执行主编”,在1978年秋举行的外国文学第一届全国工作规划会议上,他作了《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学术发言。针对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把20世纪西方文化艺术痛斥为‘反动、颓废、腐朽’”[1]的“日丹诺夫论断”作为文艺批评的“准文件”,他认为有必要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价值重新进行解释。为此,他以萨特为例,认为“不论从理论上、创作上和社会活动来看,萨特都继承了过去时代资产阶级进步的思想传统”,如萨特“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存在主义理论对“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是一种积极处世态度。由此可以将之概括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个性自由论、个性解放论的一种新的形式”。[2]随后,柳先生将这次学术发言公开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和第2期上,并在他主持的《外国文学研究(季刊)》上刊载了《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的一系列文章,这就是他所说的“三箭齐发”。此后,国内书刊对萨特的正面译介蔚然成风。
1980年4 月15日,萨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萨特的逝世,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在官方报纸上发文,对他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人民日报》17日发布消息,称赞他是“法国文化界和哲学界中享有盛名的作家”,并称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萨特于19日下葬后,《人民日报》22日又发布《巴黎数万群众为名作家萨特送葬》的消息,并发布数万群众自发为萨特送葬的图片。张英伦也写了《萨特——人类进步的朋友》一文,发表在5月5日发行的《人民日报》上。来自官方报纸的这些信息,让人民看到了思想解放的政治气候的真正来临,也是这一年在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萨特译介的繁荣景象。
在1980年6月创刊的《当代外国文学》第1期上,集中发表了萨特的《禁闭》(张月楠译)、《可尊敬的妓女》(杨剑译)和《墙》(远岫译),并且三位译者都写了相当详细的“译后记”,如张月楠在“译后记”中引入了萨特在1965年灌制该剧唱片时的“前言”,这有助于人们对该剧本的理解。在第1期上,还登载了两篇介绍萨特和存在主义的文章:冯汉津的《萨特和存在主义》长文,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原则和文学的创作方法都逐一作了介绍;在《法国作家萨特逝世》的报道中,引用了法国总统斯坦福的悼词,“让-保尔·萨特的逝世使我觉得当代的一盏伟大的智慧明灯熄灭了”。在《文艺理论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萨特的文论专著《什么是文学?》中的第二章《为何写作?》(薛诗绮译)。在《外国文学》第5期上,发表了方文翻译的《萨特言论选》(包括《什么是意识形态?》和《忠诚与怀疑精神》)。在《外国文艺》第5期上,发表了周煦良翻译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译者前言中,周煦良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是入世哲学,而不是出世哲学;即使不能有力地树立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观,至少可以使‘顽夫廉,儒夫有立志’”。周煦良给予萨特哲学的高度评价,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所在,无疑具有很强的导引作用。
在编著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福克纳评论集》,收录了萨特的文论《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嚣与骚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第5辑)上,收录了《七十岁的自传—让-保尔·萨特尔谈他的一生》,《让-保罗·萨特尔访问记—“恐怖主义可认为是正当的”》和《可怕的处境—关于访问巴德尔问题与萨特尔的谈话》等萨特访谈录。
在这一年里,还翻译了大量国外纪念和研究萨特的文章。在《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上刊发的有:第3期上“简讯”栏目下发表的《“今日萨特”国际座谈会》和《英国出版研究萨特的新著》,第6期上发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逝世》、《萨特关于哲学问题的最后一次谈话》以及《萨特生平大事记》,第7期上发表的《美英学者评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一位为了未来的哲学家》。在《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第6期上发表的“萨特生平三则”:《访让-保尔·萨特》、《纪念让-保罗·萨特》和《萨特传(1905—1980)》。分别在《世界哲学》第4、5和6期上发表的《萨特尔与马克思主义》、《让-保罗·萨特尔》和阿隆的《我的老同学——萨特尔》。
让罗大冈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等待,他于1947年全文直译萨特的剧本《恭顺的妓女》,终于发表在《春风译丛》1981第4期上。根据1948年发表于天津《益世报》上的《义妓译序》来看,他当时认为萨特并不是要替“有色人种”打抱不平,自己翻译萨特该剧本,也不是为了批判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而是为了对弱者“奴隶根性”的批判。时过境迁,译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认为萨特写这部剧本,是为了“揭发、控诉美国的种族歧视,反对美国残酷迫害黑人”,并进一步加以阐发,“种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他将改编本《丽瑟》和原版《恭顺的妓女》加以比较,认为剧本结局的改写,在批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确实大快人心,但是那样的情节似乎理想主义的成分多于现实主义”,而原版中妓女丽瑟向统治势力的屈服,则更能激发观众的义愤,“对于群众也能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因为它“更强烈、更沉痛地揭发和控诉了美国,这个以‘人道主义’自诩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现实”。[3]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2册),收录了郑克鲁翻译的萨特的《一个厂主的童年生活》和剧本《死无葬身之地》。译者前言说:“萨特同情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侵越战争,这些观点在他的作品中都有鲜明的反映。因此,他的作品拥有更广泛的影响。”
1981年10 月,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的出版,在“新时期”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如何编选萨特的资料方面,从“编选原则和内容”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编者柳鸣九的精心策划:
选择一部分萨特的文论,以提供萨特本人对他的政治、哲学、文学思想所作的阐释和解释;选择一部分萨特的文学作品,以提供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或典型章节;编选萨特的年表、萨特全部文学作品的内容提要以及与萨特有特殊关系的作家的材料,以提供萨特的生平和创作等情况;刊载一部分萨特进行文学活动时期的文学背景材料,以提供萨特与当时文艺创作状况的材料。[4]
在“萨特文论选”栏目下,收录了施康强翻译的《为什么写作?》和《七十岁自画像》,以及郭宏安翻译的《答加缪书》。施康强在《七十岁自画像》“译后记”中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在现实社会中受到异化,人只有在实现自由的同时创造他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在“萨特文学作品选”栏目下,收录了郑永慧翻译的《恶心》,谭立德、郑其行翻译的《苍蝇》和李恒基翻译的《间隔》(即《禁闭》)。在“作家批评家论萨特”栏目下,收录了《论让-保尔·萨特》(莫洛亚著,齐彦芬、葛雷译)和《萨特的戏剧与小说是我们时代的见证》(加洛蒂著,徐家顺译)。在“关于萨特戏剧创造的文学背景资料”栏目下,收录了《战后法国戏剧》(布阿德福尔著,吴岳添、郭宏安译)。在“萨特生平与文学创作资料”栏目下,收录了罗新璋编译的《萨特年表》,谭立德、施康强、杨志棠等撰写的《萨特文学作品提要》,郭宏安和金德全分别对“与萨特有关的两位作家”加缪和波伏瓦的介绍,以及罗芃写的《萨特逝世后的反应与评论》。另外,在《附录》中,罗芃和赵家鹤介绍了法国的最新文艺动态。柳鸣九对编选的各部分内容都进行了介绍。在今天看来,他的介绍似有许多可商榷的地方,但他对国内萨特译介和研究所做的贡献,仍然是别人无法超越的。
从1982至1984年,萨特作品的翻译仍然比较零散,主要刊载在一些杂志和选集中。发表在《外国文学报道》1982年第6期上的文章有两篇:《当代评论和萨特》(黄慧珍选译)和《萨特谈他的戏剧创作》(张连奎选译)。前一篇文章包括萨特对自己作品的某些评论:“萨特论萨特”,“论《肮脏的手》”和“论《墙》”;以及波伏瓦所写的“1929年的萨特”和“1946年的萨特”等部分。后一篇文章节译自波伏瓦的《告别仪式》一书第二部分“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74年8-9月间的谈话”。对于萨特和波伏瓦的这次谈话,张连奎认识到它们对于了解萨特的思想和创作的重要性,于是全文翻译了两人在“1974年8-9月间的谈话”,发表在《外国文学动态》1982年第6期上。在《外国文学动态》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法〈文艺报〉载萨特一篇未发表的谈话》(陈力川译),这篇文章是萨特于1975年5月就自己的哲学和文学生涯与米歇尔等人的对话录《献给哲学的一生——同让-保尔·萨特的谈话》的节译文。
“收编”在一些选集中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剧作家论剧作》(1982),发表了杨知翻译的《制造神话的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评论选(下)》(1983),发表了俞石文翻译的《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嚣与骚动〉》。三联书店出版的《法国作家论文学》(1984),摘录了萨特创办的《〈现代〉杂志纲领宣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文艺理论译丛2》(1984),设立了“让-保尔·萨特哲学文学论文选”专栏。在专栏中,选收了萨特八篇文学论文和两篇哲学论文,其中作家评论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活着的纪德》、《阿尔贝·加缪》,作品评论有《加缪的〈局外人〉》、《〈一个陌生人的肖像〉序》、《〈艺术家和他的良心〉序》,文论《什么是文学?》中《为谁写作?》(节选)和《一九四七年作家的处境》(节选),哲学论文《与他人的具体关系》(节选自《存在与虚无》第三卷第三章)和《唯物主义与革命》。另外,还有外国学者对萨特的评论性文章:斯特劳斯的《存在主义》,安德烈耶夫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德桑的《萨特》。“编者前言”说:“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个体的人是真正的存在,而作为集体和社会中的成员的人则是非真的存在。因为集体或社会限制了人,使他划一化,失去个性,使之异化,而他又非得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加之生命无常,死亡难免,因此,他既感到孤立无援,又感到世界与人为敌。”
萨特写于战争时期的《奇怪的战争日记》和战后的《道德手册》这两部遗作的发现并在法国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共有八篇文章在不同的刊物上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萨特的遗作:〈奇怪的战争记事本〉和〈道德手册〉首次在法国出版》介绍了《记事本》是萨特对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及思想活动的记述和一些哲学问题的探讨,而《道德手册》则是他对伦理观念的研究成果;《萨特养女发表两部萨特笔记并答〈快报〉记者问》一文认为,两部重要笔记作品的问世让人们看清了萨特的思想演变,弥补了他前后期思想的裂痕,从而证实了萨特所说“我不认为我的思想发生过断裂”的正确性,并翻译了发表在《快报》上的萨特养女答记者问;还有《萨特的未发表作品遗稿大量发现》、《萨特的两部遗著》、《萨特两部未发表过的作品出版》、《新发表的萨特著作》、《法国出版萨特遗稿》和《萨特的再发现》①这八篇文章分别见于《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6期、《外国文学动态》1983年第6期、《外国文艺》1983年第4期、《世界图书》1983年第3期、《译林》1983年第4期、《读书》1983年第10期、《国外社学动态》1984年第3期、《外国文学欣赏》1984年第4期。等文章都介绍了这一对萨特研究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事件。
萨特的作品被大规模、系统化地翻译出版,始于1985年。在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萨特作品,不管是文学、文论,还是哲学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文学作品方面的有: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萨特戏剧集》(共两册),收录了萨特的八部主要剧作和附录(作者本人为这些剧作发表的谈话或文章摘要)。在“出版说明”中,编者认为萨特的理论“标志着一种忠于个人信念的独立不羁的精神,因而具有格外强烈的吸引力”,他的戏剧“既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某些进步倾向,也处处渗透着以个人主观意志论为基础的存在主义哲理”。1986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魔鬼与上帝》,收录了最能体现萨特思想的《苍蝇》、《间隔》和《魔鬼与上帝》三部名剧,书前有本丛书主编柳鸣九的长篇译本序《历史唯物主义的度量与萨特的存在》,书后附有《萨特简介》。柳鸣九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死灰复燃的“日丹诺夫论断”而发的,并指出了萨特所提倡的“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价值所在。198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理智之年》(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的第一部),译者亚丁在其序言《关于萨特的小说》中说:萨特“用作品让读者自己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句读后感式的话,却道出了萨特小说的魅力所在。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郑永慧翻译的《厌恶及其他》,与196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同一作品比较,它删掉了“内部读物”的字样和批判性的后记。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潘培庆翻译的萨特自传体小说《词语》,译者还将长达160页的米歇尔等编的《萨特著作目录及提要》收录在此书中,这份资料对于从事萨特研究的人尤为重要。198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斌、江政华等翻译的《萨特自述》,由两个独立成篇的作品组成:《萨特自传》和《萨特自述》(这是一部拍摄于70年代的访谈记录电影片的声迹全抄本)。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沈志明翻译的萨特自传体小说,取名为《文字生涯》,“译本序”说:“上帝不存在的假设使萨特处于窘迫的境况,但也使他获得‘人是注定是自由的’这个立足点。上帝不存在,人的价值失去了终极的依据、尺度和目的。”由此可见,“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味着‘痛苦’、‘苦恼’”,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给人们提供了“自我选择”和“自我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在译者看来,萨特所说的人,不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而是指“千差万别的某个现实的个体”,他写自传的目的,是“力图破除一种神话”。在今天看来,沈志明对萨特的中肯评价,都可以作为我们认识萨特的标尺。
美学与文论方面的有: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魏金声翻译的萨特第一部论想象的著作《影象论》(现译为《想象》,并以《萨特〈影象论〉述评》一文作为译者前言。198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禇朔维翻译的《想象心理学》,是萨特论想象的第二部著作。为了有助于读者对萨特这部著作的理解,译者在前面加了《译者前言》和玛丽·华尔诺克写的《英文版导言》。198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萨特论艺术》,该书是冯黎明、阳友权译自美国韦德·巴斯金编选并英译的《萨特美学论文选》,书前有《英译者序》,书后有《译后记》,“译后记”说:萨特的“美学是一种‘行动美学’”,并“十分注重主体在一定环境中的选择活动。”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施康强翻译的《七十述怀》,收入这个集子的著作是:一篇政论《占领下的巴黎》,两篇文论《被捆绑的人》和《〈局外人〉的诠释》与一篇谈话记录《七十述怀》。
哲学方面的有: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宣良等翻译的萨特前期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并附有“萨特生平、著作年表”。陈宣良对这本长达800页的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始于1980年,用了六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可见其翻译的难度。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包括周煦良翻译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汤用宽翻译的《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萨特与本尼·莱维的对话录),汤用宽在序言《萨特,一位“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学家》中说:“萨特的哲学不是‘悲观’的哲学。他认为他的学说是‘乐观’的、‘行动’的学说。”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当时国内一些学者视萨特为“一位绝望者”的言论。
“收编”在一些选集中的有: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国二十世纪中短篇小说选(下)》,收录了萨特的《卧室》,另附有张迪安的《作者与作品简介》。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小说派研究》,收录了萨特为法国作家萨洛特的作品《陌生人肖像》写的序言。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纪实文学》(第2辑),收录了尚智超翻译的萨特散文《枪声中欢庆胜利——记巴黎解放的战斗》。1987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作家论现代小说艺术(下)》,收录了萨特和米歇尔等有关萨特哲学和文学的谈话。198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谈创作》,收录了萨特的《为什么写作?》和《谈谈我的戏剧创作》,还有王宁写的《让-保罗·萨特》。1987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专题作品选》,收录了萨特的《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和《恭敬的妓女》。198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木已成舟》,收录了张燕如翻译的萨特写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木已成舟》。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收录了萨特的《为何写作?》和《加缪的〈局外人〉》,在附录中有苏联学者安德烈耶夫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一文。1989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神分析》,收录了薛载斌、高岭翻译的萨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
80年代中后期,大量国外学者研究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专著,作为我国萨特研究的第二手资料,被大量翻译出版。1986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安延明翻译的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A·丹图教授的著作《萨特》,译者并增加了《萨特生平年表》和《萨特主要著作目录》两份有价值的附录。198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袁树仁翻译的法国著名小说家安德烈·莫洛亚的第一部作家专论《从普鲁斯特到萨特》。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顾嘉琛翻译的法国洛朗·加涅宾的著作《认识萨特》。1988年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阳等翻译的美国著名作家阿·马德森的著作《萨特和波伏瓦的共同道路》,由于作者是萨特和波伏瓦的好友,其创作所利用的资料主要由他们本人所提供,这对于我们继续研究萨特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让人遗憾的是,译著被贴上了“内部发行”的标签,并且只印了4500册。1988年大连出版社出版了郭晓红等翻译的印度汉吉的著作《弗洛伊德,萨特与美学》,并为之写了长达47页的译者前言《存在主义美学思想述评》。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崔相录、王生平翻译的日本今友道信的著作《存在主义美学》。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翁绍军翻译的法国让·华尔的著作《存在哲学》。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鼓应、孟祥森、刘崎翻译的美国W·考夫曼的著作《存在主义》,陈鼓应还翻译了考卜莱斯顿的《存在主义导论》和《无神论存在主义》两篇论文作为本书的附录。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潘培庆、郝珉翻译的法国保罗·富尔基埃的著作《存在主义》,译者介绍说:“本书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十八版译出。”可见其在法国受欢迎的程度。198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沈华进翻译的美国戴维斯·麦克罗伊的著作《存在主义与文学》。198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彭镜禧翻译的美国威廉·白瑞德的著作《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探源》。198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赵汇翻译的英国莱斯利·史蒂文森的著作《人性七论》,其中有一章《萨特:无神论的存在主义》。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廷龄、金玲翻译的法国波夫娃的著作《少女的心——我与萨特》。随着萨特大部分著作中译本的问世和国外萨特研究的专著出版,为90年代和21世纪的萨特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带来了萨特研究的真正繁荣。
[1] 柳鸣九.我让萨特“进入”中国[J].书摘,2009,(1).
[2] 柳鸣九.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J].外国文学研究,1979,(1).
[3] 罗大冈.关于《恭顺的妓女》[J].春风译丛,1981,(4).
[4] 柳鸣九.萨特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