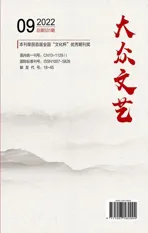阿尔比剧作《美国梦》中的社会批判
2011-08-15楚合江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楚合江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阿尔比剧作《美国梦》中的社会批判
楚合江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许多评论家将阿尔比简单地归为荒诞派。然而,本文作者认为,阿尔比只是借鉴了荒诞派戏剧的表现手法,他以此所揭示的仍旧是美国现实主义戏剧永不枯竭的主题,即社会批判。本文以《美国梦》为例,分析了剧作家是如何对当代美国社会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的。
爱德华•阿尔比;《美国梦》;社会批判
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1928- )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剧坛上最重要的剧作家,在美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可与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和阿瑟•米勒三位大师相提并论,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两次获得纽约剧评奖。他的许多作品,如《动物园的故事》(1958)、《美国梦》《谁害怕弗吉妮亚•沃尔夫?》(1962),已成为美国戏剧的经典。作为一位戏剧家,阿尔比为美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1996年荣获了肯尼迪中心终生艺术成就奖,并在1997年由克林顿总统授予国家艺术金质奖章。
深受欧洲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阿尔比的剧作表现出了明显的荒诞派特点,如反逻辑的情节、非个性的人物、贬值了的语言、象征和悲喜剧等。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一位美国本土的剧作家,阿尔比是继承着奥尼尔、威廉斯和米勒建立起来严肃传统步入剧坛的,他的多数作品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现实主义的,表现出了对当代美国社会问题的现实性思考和批判。正如阿尔比自己所说的:“作家的责任应该是一种尖刻的社会批评——把世界和人按照他所看到的样子反映出来,并说:‘你喜欢它吗?如果你不喜欢那就改变它吧。’”(1:16)
《美国梦》是阿尔比1960年创作的一部独幕剧。在该的前言中剧作者曾这样写道:“这部剧只是对美国形象的一个考察,它抨击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虚假价值代替了真正价值这一现象,谴责自鸣得意、冷酷无情,谴责软弱无能和精神空虚。它当众捅破了在我们这块每况愈下的土地上一切都是无比美好的神话。这部剧冒犯人吗?但愿如此。……我要说,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画像。”(2:53-54)
中产阶级,作为美国社会的主流阶层,代表了广泛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而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特质。《美国梦》正是通过对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剖析,影射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千疮百孔、满目狼藉——冰箱坏了,门铃坏了,厕所的水箱不停地漏水。戏剧一开始,爸爸妈妈分别坐在起居室的两把扶手椅上,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人的到来。夫妇俩结婚多年却没有孩子,彼此之间早已是心照不宣的貌合神离。继而,姥姥抱着一些大大小小包扎精致的盒子上场,母女之间很快表现出了一种敌意,甚至暴发了激烈的争吵。随后,一位自称是“职业女性”的巴克尔太太突然来访,但她又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在巴克尔太太与姥姥的交谈中,一些有事情才渐显明了,原来二十年前爸爸、妈妈通过巴克尔太太领养了一个男婴,但后来又将其虐待致死。接下来,一位年轻人上门找工作,他体态健美、相貌英俊,姥姥称之为“美国梦”,而事实上他正是领养儿的孪生兄弟。结尾外,这位年轻人成了这个家庭新的一员,而自我放逐了的姥姥正冷眼旁观着他们举杯欢庆所谓的大团圆。
总的来说,在这个“富裕”的家庭里,人与人的关系是畸形的、异化的,纯粹是一种商品买卖关系、金钱交易关系。(3:172)首先,妈妈与爸爸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妈妈完全是因为看中了爸爸的财产才跟他结婚的。其次,爸爸、妈妈领养的孩子也是他们花钱买来的,而且他们只把他当作一个玩偶,叫他“一堆欢乐似的东西”(2:97-98)。当日后发现这个孩子不尽如人意时,爸爸、妈妈又将其折磨致死,更为滑稽的是他们居然还要向领养机构索要退款,以获得“满足”。再有,最后加入这个家庭的年轻人,作为巴克尔太太向爸爸、妈妈提供的“售后赔偿”,本身就是个交易的产物。而且,这位年轻人原本是来找工作的,并一开始就声称:“干什么都行……能挣钱的活儿什么都行,为了钱我什么都能干。”(2:109)通过对这样一种家庭成员关系的戏剧化处理,阿尔比无情地戏谑了当代美国社会普遍盛行的物质主义、拜金行径,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独立宣言》中提到的“幸福生活”已被人们简单地理解为物质享受,“钱能通神”已被人们奉为颠扑不破的金科玉律,财富积累的多少已成为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
剧中,爸爸和妈妈构成了这个家庭的中坚,他们陷入物欲与功利之中,是当代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而在这里要特别分析的是妈妈这一形象,这一形象集虚伪欺骗、独裁专断、凶狠残暴、庸俗愚蠢与金钱异化于一身,集中体现了一种虚假价值观念对个人的荼毒与戕害。(4:114)妈妈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在那时她就很虚伪,善于欺骗,并有着一双向钱看的势利眼。上学期间,妈妈每天带着姥姥为其精心打点的饭盒去学校,但午饭时总是装作舍不得打开它,“噢,瞧瞧我这漂亮的午饭盒,包得是那么漂亮,打开了我的心就碎了。”(2:66)而事实上,是因为她太虚荣,羞于在同学面前吃自己粗糙廉价,但却是姥姥苦心为其筹办到的食物,而宁愿厚着脸皮去“品尝”同学们的鸡腿与巧克力。剧中姥姥曾这样对爸爸说:“她还不到八岁,就老是爬到我身上细声细气地跟我说,‘我长大了要嫁个有钱的老头。我要把我的小屁股放在全是黄油的浴缸里,这就是我要做的。’我警告过你,孩子他爸。我告诉过你离她这种人远点儿。”(2:69)终于凭借着一位有钱的男人,妈妈从社会的底层爬了出来。她直截了当地对爸爸说:“我有资格靠你过日子,因为我嫁给了你,因为我允许你跟我睡觉。将来你死了,我也有权得到你所有的钱。”(2:67)在家庭生活中,妈妈完全是一个独裁统治者。妈妈总是随心所欲地指使爸爸,训斥爸爸。而在妈妈的威慑下爸爸驯服得像一个孩子,一个应声虫,甚至连爸爸自己都曾有过这样的怀疑:“男子汉?我真是个男子汉吗?”(2:74)当然,爸爸的顺从、软弱与缺乏活力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美国社会的腐朽堕落。妈妈不仅对爸爸颐指气使,对姥姥也时常出言不逊,甚至两次气急败坏地让爸爸去砸了姥姥的电视机,并多次表示要把姥姥送到养老院去。在对待领养的孩子上,妈妈则把自己凶狠、歹毒、残暴的“恶魔”本质暴露得无遗:只因为婴儿长得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便心存芥蒂,有所怀恨;只因为孩子只看爸爸不看妈妈,便将其眼睛挖掉;只因为孩子对自己的性器有了本能的反应,便将其阉割,不足以惩戒,又将其双手砍掉;只因为孩子对妈妈说了脏话,便将其舌头割掉。如此这般,在妈妈的一系列酷刑之下,孩子成了一个没有脑袋,没有内脏,没有脊梁骨,脚是泥做的怪物,并最终悲惨地死去。(2: 99-101)另外,妈妈这个人物也是一个十足庸俗、愚蠢、无聊的家伙。一开始妈妈就讲述了她买帽子,大闹商店的奇遇:原本是米色的帽子,却被人说成是微黄色的,于是她返回店里,大吵大闹要换帽子。营业员拿着帽子到后边转了一圈,把同一顶帽子又交给了她,而妈妈却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真是不折不扣的阿Q精神。物质生活的富足无法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且精神上的空虚很可能比物质上匮乏更令人难以忍受,这在当代美国社会已是一种普遍现象。(5:69)作为阔太太的妈妈只好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总而言之,剧作者在这里塑造了妈妈这一具有“破坏性”的形象,一方面可能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多少投射出了其养母的身影。另一方面,这也很有可能与当时女权主义猖獗,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有关,知识界对其多有声讨,恐怕剧作者本人也是按捺不住。但从根本上来讲,作者的意图在于说明:“美国梦”的虚假价值对美国人社会理想、道德素养的误导与荼毒。那么这个虚假的“美国梦”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且进入对下一个人物的分析。
剧中的年轻人出场比较晚,戏份不多,但却是体现主旨的核心人物。他筋骨分明、肌肉结实、体态健美、相貌英俊,俨然一个电影杂志的封面人物。年轻人这样评价自己:“挺漂亮,是不是?刮得干干净净的中西部农场小伙子的脸,而且是典型的美国气派,漂亮得都让人感到无地自容。侧影也不错,直挺的鼻子,诚实的眼睛,迷人的笑容……”(2:107)这样一个外表出众的美男子,难怪姥姥连声称赞,并矢口称他为“美国梦”。然而,在姥姥与年轻人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们发现了年轻人只是金玉其外,并不完美:“除了你看到的这些……我这个人,我的身体,我的脸孔。但在所有其它方面,我不那么完全。”(2:113)他非但没有什么才能,而且也“没有感觉能力,没有感情”,“不能去爱……不能用怜悯、用深情去看所有的事情,有的只是冷冷的漠不关心……不能用我的身体去爱任何人……不能去触摸另一个人并且感受到爱”。(2:114-115)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次,就好像突然一下,我的心变得麻木了……几乎就好像……心被人从驱体里摘走了;有一次……我正在睡觉……我的眼睛就像着了火……;还有我的下身……;就连我的这双手……我被抽干了,扯烂了,掏空了。”(2:114-115)不难看出,年轻人先前提到的被人与之拆散的孪生兄弟就是被肢解了的领养儿,因为他们有着心灵感应,所以年轻人在精神上承受了弟弟在身体上遭受的巨大“损失”。无论如何年轻人解释了他择业的要求:能挣钱的活儿什么都行,为了钱我什么都能干。仅到这里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得出,剧作者借姥姥之口把年轻人称为“美国梦”的妙处所在——外表华丽、内心空虚的年轻人正是虚假“美国梦”的化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美国人所追逐的“美国梦”的物化本质与欺骗性。
在资本主义文化形成初期,在启蒙者们的构想之中,追求物质富足的工具理性(或功利动机)和追求道德进步的人文理性(或价值动机)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携手并肩,共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最终建立起一座必然王国。但这种设想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伴随着现代机器的隆隆轰响,对精神的追求淹没在了物欲横流的海洋中,资本主义的理想只剩下一个物质的外壳,而缺少了内在的灵魂。(6)很明显,剧中年轻人形象便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工具理性的象征。这一象征充满着悲剧和反讽,然而造成这一现实的恰恰是爸爸妈妈,是他们亲手杀死了人文理性——那个被肢解了的孩子。与代表“美国梦”的年轻人相比,我们且不空泛地说这个孩子有一种性灵中的精髓血脉,是温情与理想的寓居之所,能跟自然和谐并存。最起码地来讲,他有感觉,有思想,有其独立的爱憎情感,有其倔强的精神追求。拒绝自己的存在被忽视,他“把心给哭出来了”;敢于挑战权威,他无视妈妈,“眼里只有爸爸”;在反抗非人的虐待中他曾“高高地翘起鼻子”,甚至愤怒地骂了妈妈。(2:99-100)最后他的死,可以说也是有尊严的,不像孪生哥哥一样,虽躯体一息尚存,但灵魂早已不复存在,行尸走肉,虽生犹死。然而,爸爸和妈妈却毁灭了弟弟,接受了哥哥,让哥哥顶替了弟弟的位置,这也就预示了当代美国无可避免的精神危机、发展悲剧。
年轻人加入了这个“富裕”的家庭,是取代了领养儿原本应有的位置,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置换了姥姥在这个家庭里的归属。(7:248)姥姥是剧本中唯一的正面人物,代表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她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某些传统的美德。首先,姥姥是一个极勤忍的人。在妈妈小的时候,家道艰难,姥姥一个人苦心勤俭,维持生计,每天都把妈妈带去上学的午饭盒装得满满的,包扎得漂漂亮亮的。而现在妈妈傍了大款,成了富婆,年迈的姥姥还在为女儿一家人辛勤操劳,“做饭,擦拭餐具,搬动家具”(2:67)。同时姥姥也非常真诚,富有同情心。正是在姥姥的暗示下,巴克尔太太才弄清楚了自己为什么被爸爸妈妈找来了,也正是有了姥姥的“妙注意”,巴克尔太太才“解决了所有问题”,为自己解了围。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畸形的时代”(2:86)的叹息中,姥姥选择了让位给新的一代,选择了自我放逐,传统价值观念随之消亡。作为美国民族历史的开拓者和见证人,姥姥见证了“美国梦”在历史的传承中已被偷梁换柱,原本的璞玉浑金,如今的污泥浊水。于是上演了这一出“怀金悼玉”的悲喜剧。
[1]McCarthy,Gerry.Edward Albee [M].Hampshire: Macmillan Publishers,1987.
[2]Albee,Edward.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Zoo Story [M].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61.
[3]汪义群.当代美国戏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4]周维培.当代美国戏剧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郭继德.当代美国戏剧发展趋势[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6]张晓峰.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深化与危机[J].国外理论动态,2008,(10).
[7]Gussow,Mel.Edward Albee: A Singular Journey: A Biography [M].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9.
Many critics recognize Albee as one of the dramatists of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However,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Albee’s themes these techniques help to expose are typically of American realistic drama-to criticize the society.Taking The American Dream as an example,the writer of the thesis will analyze Albee’s ruthless exposure and demonic criticism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ociety in his works.
Edward Albee; The American Dream; social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