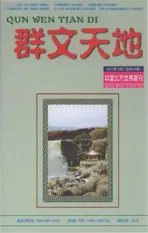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读余华
2011-07-12王宁
■王宁
对传统文学的颠覆和彻底的反叛性构成了后现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在余华小说中,对“红色经典”的颠覆,小说中灰暗的人生图式,还有黑色幽默都是深受后现代主的影响。
1983年开始创作的余华,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4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关卖血记》、《兄弟》),中篇小说集6部,随笔3部,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多国出版,并且多次获得国外大奖。余华的火热使多种评论纷至沓来,对他的评价也有多种声音,人们给他冠以“先锋小说家”的称谓,认为他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评价余华:“1986年以前的所有思考都只是在无数常识之间游荡,直到1987年的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和1988年的中篇《现实一种》,才寻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思考脱离了常识的围困。在这些作品(连同《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中,对于暴力和死亡的精确而冷静的叙述,和在冷静后面的巨大的愤怒,让当时的许多读者感到惊讶。”“在他(余华——笔者)看来,为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以及现实的世界的混乱,并未得到认真的审视。他坚持以一个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语言和结构的独创性发现出发。来建立对于真实的信仰和探索。”“90年代的几部长篇(《活着》、《许三关卖血记》),日常经验(实在的经验)不再被置于与他所追求的本质的真实相对立的地位上。他的叙述依旧是冷静,朴素,极有控制力的,但更加入了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透过现实的混乱、险恶、丑陋,从普通人的类乎灾难的经历和内心中,发现生活的简单而完整的理由,是这些作品的重心。”洪先生的评价中肯而到位,但是他没有说出余华的成长经历中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但它又是与现代主义显然有别的新的文化倾向和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小说不是一个内涵确定、清晰的概念,它还包括许多不同的小说流派,诸如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等。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人们已放弃对意义的解释和追求,深度模式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消失。对传统文学的颠覆和彻底的反叛性构成了后现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在余华小说中对“红色经典”的颠覆,小说中灰暗的人生图式,还有黑色幽默都是深受后现代主的影响。
文论界大多数人认为,红色经典是20世纪40至70年代(40年代的创作主要指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带有明显"革命"色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红岩》等。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景的“亲历者”,他们能够用文字来回顾一下自己光荣的历史,也可以进一步使革命神圣化、经典化,所以此类作品的真实性遭受到很大的质疑。现在拿起《青春之歌》可以再读的也许也只有林道静与几个男人的感情纠葛值得玩味了,而与之同时期的《红豆》以其“哀而不伤”的风格在当下还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这些广为人知的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精神追求和理想,人们全部的生命热情就在于此。儿女情长算的了什么,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献身才是最光荣的人生目标。人们顶礼膜拜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崇尚的是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和为革命牺牲性命的英雄,要求自己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一心为公,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精神追求大大地超过了物质追求。
在余华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潜在的“文革”气氛以及对“红色经典”二元对立等级秩序的拆解,作者有意无意地运用解构主义的颠覆性和颠覆力量。《活着》是余华的一部叙述家庭历史的小说,是社会风云大变革在一个家庭中引起的悲欢离合。“红色经典”中原本相对立的两种正义与邪恶的力量在《活着》中彻底被颠覆了,作者倾注于人物身上的是自己个性鲜明的历史观。首先,是福贵和龙二。福贵是一个有“一百多亩地”家产、“远近文明的阔少爷”;“龙二说话是南腔北调,光听他的口译,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是个闯荡过很多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但是他的家当就只有“两个大柳箱子”。这分明就是一个地主阶级,一个无产阶级流浪者。福贵从小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长大后更是吃喝嫖赌,最终荡尽家产,把全部家产输给了龙二。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地主变成了佃户。龙二却从一个流浪者变成了新一轮的地主恶霸。后来,在“打土豪分田地”中,龙二被拉去枪毙了,福贵觉得龙二是替他去死的。历史的必然发展在余华的笔下成为“纯属偶然”,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身份的转换是这样地带有戏剧性,这对“红色经典”宣扬的“历史的必然选择”不能不说是一种颠覆。其次,是福贵和春生。这两个曾经在战场上同生共死的好朋友在从炮灰里爬出来之后,农民身份和干部身份的对立却使福贵失去了儿子。主流意识中干部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但是为了救县长夫人就要抽干一名群众所谓血,这就又陷入到了一个悖论之中。这就对“红色经典”中至高无上的人民公仆的形象进行了颠覆。
另外,余华对“红色经典”的宏大叙事也提出了质疑。千百年来,英雄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等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余华通过人在战争中的心态表达对战争、献身、正义等等宏大主题的认识,他只是在小说中穿插一些战争片段表达对英雄正义理想的认识。《活着》中福贵以一个国民党兵身份和视角叙述了国民党包围以后的情景:“国军的阵地一天比一天少……每天都有几千缺胳膊少腿的伤号被抬下来……我们连的阵地在后方,成了伤号的天下。伤号越来越多,只要前面枪炮声还在响,就有担架往这里来,地上的伤号起先是一堆一堆,没多久就连成一片,在那里痛得嗷嗷直叫……那是痛得受不了的声音,一大片一大片……天亮时,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昨天还在喊叫的几千伤号全死了……”这里没有解放军的英勇作战、所向披靡,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几千几千生命的消亡,在这一刻,读者被触动的已经不是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政治身份,而是对生命的关怀。历史的发展与其说是不同力量间斗争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人性的展示和保持的结果。
存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存在主义文学的题材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神话的、虚构的但是无论如何,他总表现出对人生状态的深切关注。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是揭露世界和人存在的荒诞肯定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表现人在荒诞、绝望的境况中的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这是存在主义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最突出的特点。《活着》中的福贵经历了一般人都难以承受的人生,一一送走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直到最后只剩一头叫做福贵的老牛,他说:“为了活着而活着”。福贵人生的传奇性就像一个神话,可是当他遭受了一切不幸之后,他还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福贵活着,但是没有自己的意志、思想,也不可能有自己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他麻木地等待死亡事件的不断降临。他表面的乐观和风趣,只能理解为面对宿命时的自我排解,理解为为了“活着”而自我麻醉、自我补偿。《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以不断地出卖宝贵的血来维持自己苦难的生存,他以走向死亡的代价维持着灰暗的生命;虽然每次也会用“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来调剂一下艰难的生存,但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其生命的灰暗色彩。余华笔下的这些人物,都经历着艰难、险恶的人生,他们如木偶一般忍受着生活中的厄运,没有欢乐,没有温情,没有理想和希望,也没有避让、选择,甚至也没有哀怨,这里没有人生的亮色,也没有人们企盼的幸福。人,就只是为了存在而存在。
[1]余华.兄弟(上)[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余华.活着[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