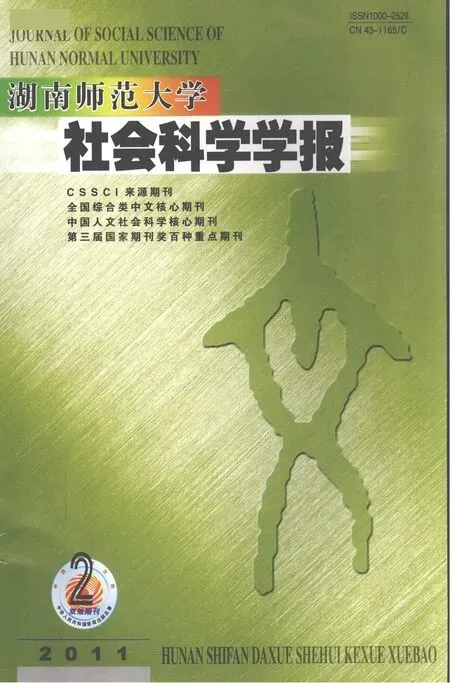康有为“虚君共和”论浅析
2011-04-13朱忆天
朱忆天
(华东理工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 2 00237)
康有为“虚君共和”论浅析
朱忆天
(华东理工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 2 00237)
通过对辛亥革命之后的时代背景、康有为个人文化与思想背景,以及明治日本天皇制度对康有为的启发等多个侧面的剖析,揭示了康有为从“君主立宪”构想转向“虚君共和”制度设计的思想轨迹。并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康有为在共和民主的潮流之下依然固执于“天下”观念,但他希冀借助体制内“虚君”的凝聚求心力,实现民国社会在帝国崩溃后的统合,并最大限度汇集有效的社会资源,实现国家的富强,这种价值取向,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康有为;虚君共和;明治日本;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前,康有为一直希望在温存清王朝支配体制的前提之下,通过颁布宪法和确立君主立宪制,逐步实现向大同社会的平稳过渡。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崩溃,彻底打乱了康有为原初的政治构想,逼迫他做出新的抉择。
在日本迎来辛亥革命的康有为,接连写下《救亡论》和《共和政体论》,倡导“虚君共和”之说,力推类似“共和帝国”一般的过渡政治体制。这一主张,在1917年他写下的《共和平议》中得以延续,且终身未变。
变法运动之际,康有为热情颂唱君主立宪制,为何在辛亥革命之后迅速转向“虚君共和”论呢?“虚君共和”的设想,与君主立宪制有哪些不同呢?同时,康有为这种思想转换的背后,究竟又隐藏了些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解明,构成康有为后期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一、“虚君共和”论的基本观点
“虚君共和”论的构想,主要体现于康有为《共和政体论》和《救亡论》这二篇论文之中。康有为认为,国外的经验教训证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目前阶段不宜采用共和政体,而君主立宪政体最为适宜,但考虑到辛亥革命后中国国内的实际状况,又不能过于死板,需针对形势的变化灵活应对。为此,康有为主张汲取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的各自优点,创造一种新的整体模式,也就是所谓的“虚君共和”体制。
康有为强调,“虚君共和”是他独自的造语,它以共和为主体,以虚君为从体,是虚君在位与共和政治的完美合体。康有为是这样描述“虚君”的:
虚君者无可为比,只能比于冷庙之土偶而已。名之曰皇帝,不过尊土木偶为神而已,为神而不为人,故与人世无预,故不负责任不为恶也。今虚立帝号乎,则主祭守府,拱手画诺而已,所谓无为之治也。[1](P677)
这种“虚君”,无事无权,无需特别的才能。与此同时,“虚君”又是一座“神”,具有极高的资格地位,必须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因此,环顾宇内,康有为认为唯有末代清帝溥仪或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孔令贻能够荣任此位。溥仪是清王朝正统权威的象征,而孔令贻则连接孔圣人的血脉,从某种象征意义上而言,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传人。在康有为的这一设计当中,专制政体下皇帝的立法权、行政权、人事权和军权都已有名无实,“虚君”说到底就是一种“名誉总裁”,即便是“神圣不可侵犯”,但依旧只是一个“土木偶”。那么,康有为为何非要树立这样一个“土木偶”呢?他是这样说明的:
且夫立宪之君主,至无用也,然欧土立宪国,乃皆若至愚谬,而必立一君主国,盖立一无权之君主,人不争之,于是驱其国人,只以心力财力,运动政党,只以笔墨口舌,争总理大臣,而一国可长治久安矣,无复岁易总统以兵争乱之患,不陷于无政府之祸,则君主者无用之用至大矣。故欧土各国,宁备极敬礼,岁糜巨俸,鞠躬以事之,甚至迎于外国异族而立之,盖有大用者在也。[1](P688)
在康有为那里,“虚君”的存在,确切地说,只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效用。“虚君”能免去共和政体下为争夺总统职位而产生的混乱,而且,由于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就是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民众的文化素质水准较低,为了防止争夺政权产生的动乱,需要有这样一位“土木偶”式的“虚君”压住阵脚。康有为坦率地承认,“虚君”的存在,不过是一种维持社会、政治安定的暂时性措施,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中国的文明程度向前迈进,到一定历史阶段,“虚君共和”制必定要让位于民主共和制。
在共和概念深入人心、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主流的背景之下,康有为为什么对“土木偶”的“虚君”抱有如此异样的执著呢?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源自康有为内心深处强烈的“尊皇”冲动。
逃往海外后的康有为,自觉受到光绪皇帝的厚爱,自始自终打着“保皇”的旗号,展开其政治活动,并表示出全力救助光绪帝的强烈愿望,这些均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康有为真的是出于纯粹的“尊皇”之心,那么,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他肯定会将“虚君”的头衔授予清王室成员。但问题是,从康有为的相关表述来看,不仅仅是清朝的遗族,只要是能够获得中国民众广泛认可的人,谁都可以戴上“虚君”这顶帽子。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论的动机,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尊皇”之心。
二、时代背景之下的“虚君共和”论
要探寻康有为倡导“虚君共和”论的真实动机,不能绕开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
在康有为看来,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方式实现共和政体之举,弊远大于利,革命派所谓的“跨越”愿望,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革命派设计的共和制度,脱离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现实,在推行中必然面临巨大的困难,并且,还会带来思想、文化上可怕的真空状态。
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对当时社会上不顾中国国情、一切盲目照搬西方的思潮进行了严厉抨击。他在1913年撰写的《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一文中,明确指出:“今自共和以来,民主之政既师法美,议院政党,蓬勃并出,官制改于朝,律师编于地,西衣满于道,西食满于堂,鞠躬握手接于室。……凡欧美之政治风俗法律,殆无不力追极模,如影之随形,如弟之从师矣。凡中国数千年所留之政教风俗法度典章,不论得失,不分是非,扫之弃之,芟之除之,惟恐其易种于新邑矣”。[1](P890)
康有为要强调的是,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政体,只能带来混乱和社会的无序。康有为在《废省论》中,从军队、民众与自治的分离、中央政府的财税征收、地方的平民政治、民政的分权自立、妨碍民生的稳定等方面,指出了军阀割据的七大危害。[1](P745-750)康有为发出警告,当时的中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军阀割据的无序状态。这种军阀割据,是酿成中国分离、崩溃的根源,而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探讨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军阀形成的可能性,可视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的一大动机。
变法运动之际,康有为企图以光绪帝为权力核心,推动政治的全面变革。可是,其结局是敕令乱发,不见效果,反而进一步导致了政局的混乱。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帝的敕令,丧失了让地方诸侯严格遵从的绝对权威。康有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中央权威失落的苦痛。
1900年6月,英美等列强与清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公然声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之下的“矫诏、乱命”,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不予执行。“东南互保”是清王朝建立以来首次地方势力与中央的公开对抗,反衬出清王朝支配体制的严重弱化,加速了晚清中央集权崩溃的步伐。[2]
康有为认为,辛亥革命带来的,是更为严峻的中心权威空洞化。在清末,虽然普通民众已经很难真正吸引到王朝体制中去,但毕竟还是存在着皇帝的权威,在金字塔型的传统政治框架之下,勉强维持着大一统的格局。而一旦迈入共和的时代,则作为最后一道“防卫线”的皇帝的凝聚力资源也丧失殆尽,这只能导致中国的分崩离析。由此,在康有为那里,国家政治的运营,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否的理论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国家安定与统一的生死攸关的至上命题。康有为推出“虚君”,就是要树立一种让人产生敬畏感的神圣存在,创出一种精神的统合权威,并以此为基础或核心,制约日益膨胀的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回避革命后的内乱,进而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局面。
另外,康有为的这种主张,亦可获得一部分担心革命会导致社会秩序崩溃的保守乡绅的支持。对这些传统士大夫来说,如果失去了君臣、上下的伦常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将难以续存,因此,即便是礼仪性的存在,“虚君”这一君临统治中心的权威,依旧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支撑。从这一点来分析,康有为的“虚君”主张,也隐含着确保自身的支持基盘,并与革命派的主张相对抗的政治算计。
三、康有为个人的文化、思想背景
除了上述现实政治的考虑之外,康有为如此拘泥于“虚君”,也与他作为传统士大夫的文化、思想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是这样分析的:
对出生在清末、生活于以科举制度为象征性标志世界中的学者、官僚、士大夫等来说,毫无疑问,“天下”的世界,已构成他们赖以存在基底的最根本条件。可是,当国家采用共和政体、确立总统制,在一瞬间,当人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赤裸裸的武力独裁之外其他一无所有时,时代揭示的课题,就不仅仅是单纯导入制度的是非问题,或者说是如何面对“世界”解体这一事实及如何采取各种措施应对的问题,而是必须要从正面去追问这种解体所蕴含的深层意味。
在中华帝国悠久的历史中,“天下”的世界,长期以来一直是知识阶层最为看重的东西。简单而言,“天下”的世界,是由天子——皇帝为核心、并以“君臣大义”为基轴运作和展开的。辛亥革命之后,王朝体制被彻底否定,并以民主的名义直接进入“共和”的时代。这个“天下”中心的消亡,对中国传统知识阶层而言,已远远超越了现实政治的意义,它唤起他们一种感觉——面对“天下”解体的异常危机感,或者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楚感。曾经拥有的中华帝国文明的自信和荣耀,毁于一旦,其巨大的冲击波,绝非言语所能表达。
“天下”中心的丧失,在康有为看来,这只能意味着天下之“乱”。正是这个“天下”中心的存在,才保证了世界的稳定和安宁。面对清王朝的崩溃、“天下”的解体,康有为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在“共和”的世界中,是否还存在着维系世界安定与安宁的最终、最后的保障?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究竟是什么?
稍微考察一下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可以发现,面对这一难题的,不仅仅是康有为等文化保守派,也包括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只不过陈独秀开出的“药方”,与康有为截然不同。陈独秀认为,政治世界“天下”的解体,是以固有价值为基盘的旧文化体系全盘崩溃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如果想要再建“天下”,那也只能是在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新的文明创造。共和民主体制,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带来些许“乱”,但这绝不是什么坏事,只要能够提升国民的地位,促进国民能力的提高,那么,这种代价是值得的。
陈独秀将“天下”之“乱”看作是新文明创造的前提和宿命,是一种必然的、正常的现象,表明了他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勇气和决心。与陈独秀的这种“向前看”的乐观主义相比,康有为则更多地背负历史重压,最终依旧希望通过崇拜、归依“圣上”,再建君主体制下神圣、权威的“天下”秩序。
康有为建立在儒学普遍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认同”,决定了他必然选择在传统“天下”的框架之内、以皇权为中心来推进国家的变革,康有为提出的“虚君共和”论,可以说是这一构思的具体体现。康有为推崇的以“天下”为顶点的儒教金字塔型或同心圆的精神构造,对应在政治体制之上,就必然要设计出一位“虚君”来,这位“虚君”,无论是宣统帝或其他相应的人物,他首先是一种统括民意的象征性存在,同时也是孔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总代表。可以说,孔教的存在,在理论论证的逻辑上,已经注定康有为必然要在政治组织构造上树立一个绝对性的神圣存在,即便这种存在是没有任何实力可言的“虚君”。
由此,“虚君共和”论和孔教运动,其思想的基盘是惊人的一致。只要提倡孔教运动,康有为的“虚君”概念就不能放弃。“木偶之虚君”的信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只是从理论一贯性的要求出发,“虚君”必然是康有为哲学最后立身安命的场所,是其展开思想活动之最后保证,绝无舍弃的可能。
四、明治日本天皇制的启发
虚君在位和共和政治合为一体,这样的构思,也是康有为考察日本、欧美各国后酝酿产生的独特思想结晶。1898年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有为被迫亡命日本,通过直接接触日本的风土人情,他对明治日本的天皇制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康有为在推动戊戌变法时,虽然积极主张模仿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理论阐述,但当时他对天皇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等,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当时的康有为,完全无视明治维新变革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过分迷信明治天皇的权威力量,认为明治维新取得的不凡成就,完全得益于明治天皇及少数大臣的英明裁断,在这种认识之下,康有为将变法的成败,也始终系于光绪皇帝一个人身上。从康有为当时的论述来看,这一时期他论述的“君主”概念,绝非“虚君”,而是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实力者。
及至逃往海外,康有为才得以近距离考察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形成,是明治政府巧妙利用拥有传统权威的天皇的必然产物。根据1889年颁布的帝国宪法,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具有立法、行政、军事等各方面的无限权力,但另一方面,天皇又要通过议会的批准才能确立法律,文武官僚以天皇的名义展开政治运作,承担各自的政治责任。由此,天皇虽然是一种尊贵的存在,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但同时又是一位“虚君”,他的作用仅仅是显示国家机构的尊严,起到统括国民的作用。
关于明治天皇的作用,日本学者安丸良夫曾这样总结:
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国民国家的编成原理的“核心”,是天皇挥舞巨大的权威,直面里里外外逼近的各种危机,一边维持权威的秩序,一边实现近代化——文明化的课题。并且,在避免此岸社会秩序崩溃的同时,实现近代化——文明化这一课题,是明治政府的指导者、神道家、国学者,乃至民间记者、民权派、地方社会各层次指导者达成的广泛的社会共识,其对照系便是作为启蒙对象的普通民众。[3](P88)
就像安丸良夫所表述的那样,明治天皇确实具有巨大的权威,可是,这种权威的根本,并不是政治营运之力,而是精神方面的统合。天皇只是国家统一的象征,是避免社会秩序崩溃的广泛社会合意的产物。也就是说,天皇这张牌,对新政权来说,是其统治正当化的象征,是汇聚支配人心的符号,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政治资源。
明治日本的天皇制度,给了康有为深刻的启发。康有为认为,比起中国原先的那种以实力来争夺皇位的做法,日本的这种“虚君”体制,显然更具积极意义,日本国家体制的安泰与战乱的减少,与这种“虚君”体制有着很大的关联。同时,明治天皇具备的传统权威的凝聚作用,又确保了近代日本在文明开化转型过程中的“举国一致”,令其在短时期内顺利蓄积能量,迅速崛起。很显然,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论,和他在流亡时期认真考察近代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五、结 语
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将“虚君”与“共和”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捏合在一起,折衷成一种奇特的矛盾统一体。“虚君”和“共和”,如何并存于一体,这里面确实存在着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点。
“虚君共和”论和孔教运动一样,在当时就不受好评。这里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康有为在共和民主的思想潮流之下,仍然固执于“天下”观念、拘泥于皇帝的君臣等级意识,这种浓厚的保守色彩,自然成为革新派最好的攻击靶子。
但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虽然反对革命派倡导的共和政体,称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他主张的“虚君共和”论的核心,归根到底还是共和制。辛亥革命前后的康有为,已经充分认识到:唯有制定宪法召开国会,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自治和财政的运作方式,并形成与欧美相似的政治组织,才能挽救中国的危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从根本上而言,并非反对共和制。
从“虚君共和”论中,还可以感受到康有为政治姿态、立场的柔软性。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告了康有为一贯主张的“君主立宪”理想的彻底幻灭。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康有为迅速调整自己的思想定位,自觉地实现了从“君主立宪”向“虚君共和”的思想转换。并且,在与革新派的理论论争之中,康有为坦承自己并不拒绝共和制本身,未来的中国必然会导入共和制。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康有为与时俱进的革新一面。
“虚君共和”论和孔教运动,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康有为对国家内部多样性、权力和文化多元性抱有的极度警戒心理。在当时混乱、分裂的政治局面下,康有为希望借助体制内“虚君”的凝聚求心力,实现民国社会在帝国崩溃后的统合,并最大限度汇集有效的社会资源,实现国家的富强。可以说,康有为对民国的政治现状,是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的。康有为是政治上的“虚君共和”与思想上的孔教运动并用,双管齐下,力图解开民国初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之难局,这种价值取向,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历史学研究室.历史と文化·十八[J].历史学研究报告,1994,(22):174.
[3]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M].东京:岩波书店,1992.
Abstract:The paper reveals Kang You-wei’s thinking path from the“Constitutional Monarchy”to“Xu Jun Republican”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Kang You-wei’s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background,and enlightenment gained from Meiji Japan emperor system and so on.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is reached:Although Kang You-wei was still entrenched in“The World”concept under the tide of democracy and republican,he wanted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collapse of empire,and optimize the social resources as effectively as possible with the cohesion in“Xu Jun”system.Such value orientation should be affirmed.
Keywords:Kang You-wei;Xu Jun Republican;Meiji Japan;Confucianism;the Revolution of 1911
(责任编校:文 心)
Analysis of Kang You-wei’s“Xu Jun Republican”Theory
ZHU Yi-tia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K249
A
1000-2529(2011)02-0121-04
2010-11-20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0100-C-0902)
朱忆天(1968-),男,上海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