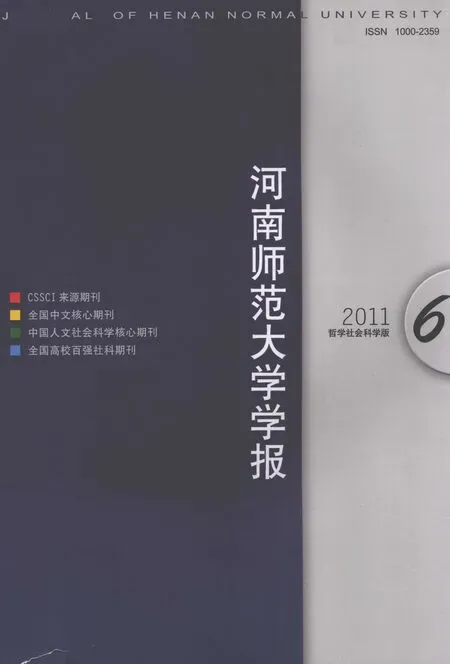论白居易的音乐思想与讽喻诗创作
2011-04-13柏红秀
柏红秀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盐城224002)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其诗歌在当时广受赞誉,传播盛况空前,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1]555白居易的许多诗歌创作本身就是歌辞或者被人们当作歌辞传唱,如刘禹锡《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来章有移家惟醉和之句)》:“制诰留台阁,歌词入管弦。”[2]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中晚唐李益、白居易为多。”[3]白居易对自己的歌辞创作水平非常自信,如“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4]478、“我有阳关君未闻,若闻亦应愁杀君”[4]472。这种自信既与他精通音乐有关,也与他独特的音乐思想密不可分。关于白居易精通音乐的记载颇多,但是对他的音乐思想以及其与歌辞创作特别是讽喻诗创作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有深入的考察,下文就此角度作详细论述。
一
白居易的音乐思想主要体现在《策林》、《与杨虞卿书》及《与元九书》上,其他则散见于诸诗篇中。总体而言,白居易的音乐思想仍然是儒家的,他承认“声音之道,与政通”,如《策林》六十二《论礼乐》曰:“臣闻序人伦,安国家,莫先於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於乐。二者所以并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也。……是以先王并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诸掌耳。”[4]1362-1363但他对“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具体解读,却与传统儒家有所不同。传统儒家认为音乐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因此特别强调音乐建制工作、古乐的地位及对古乐的传承等。白居易对此却有自己的见解,《策林》六十三《沿革礼乐》:“臣闻议者曰:‘……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于古,则乐不能和矣。’古今之论,大率如此。臣窃谓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达识也。”[4]1363白居易所谓“通儒”的音乐思想,就是认为乐的根本在于人情,音乐只是乐的外在形式。《策林》六十三《沿革礼乐》曰:“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得作乐之本情也。”“乐者,以易直子谅为心,以中和孝友为德,以律度铿锵为饰,以缀兆舒疾为文。饰与文,可损益也;心与德,不可斯须失也。”[4]1363白居易认为决定人情的核心要素是国家的政治,“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4]1364。“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4]71。国家的治政决定着国民的情感,而国民的情感又会以音乐的方式具体呈现出来,所以白居易认为帝王最需要关注和努力的是治政而非治乐,“故臣以为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4]1364。这样一来,白居易所理解的“声音之道,与政通”,虽然强调音乐与国家存亡有密切关系,但是却不认可音乐决定国家的存亡的观点,相反认为后者决定前者,进而指出音乐只是帝王治政的重要辅助手段。
纵观唐代音乐思想发展史,唐太宗亦不认同儒家传统的音乐决定国家存亡的观念。唐代吴兢《贞观政要·论礼乐第二十九》记载:“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5]唐太宗提出这样的音乐思想,尽管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但响应者却寥寥无几。白居易之所以能够与唐太宗遥相呼应,缘于他所处时代音乐发展的状况以及白居易对这种状况的深切认知。
唐代音乐的发展以开元后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宫廷音乐因为汇集了数量惊人的一流乐工并创作了诸多旋律精美的乐曲而成为全国音乐的主流。受此影响,雅乐观念深入人心。后一阶段,民间则逐渐发展成为音乐的重镇,《旧唐书·穆宗》载丁公著曾对穆宗言:“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则是物务多废。”[6]卷16,486故此阶段,俗乐异常活跃。唐代杜佑《通典·乐六·四方乐》记载:“又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寢。”[7]卷146,3723《通典·乐六·清乐》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7]卷146,3718此阶段俗乐兴盛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胡乐在宫廷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宫廷音乐的重要构成部分,《新唐书·礼乐十二》记载:“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8]《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记载:“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9]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雅俗、华夷等界限被彻底打破,雅乐与古乐几乎要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即便有所表演,也因为受俗乐特别是胡乐的渗透而面目全非。基于音乐发展的现实状况,白居易提出了“通儒”的音乐观念,虽然承认音乐与国家兴亡存在密切相关,但指出音乐只是帝王治政的重要辅助手段。这种音乐思想使得他对繁荣的俗乐并不断然排斥,只是主张稍稍作些抑制即可,如《策林》六十二《议礼乐》并不要求帝王完全抑制俗乐,“国家承齐、梁、陈、隋之弊,遗风未弭,故礼稍失于杀,乐稍失于奢。……防其盈放,则诏典乐者少抑郑声”[4]1363。
虽然白居易对音乐功能的认识与唐太宗大体相同,但是与后者的笼统质疑不同,白居易进一步对于音乐如何发挥它的治政辅助功能进行了深入思考,将音乐分为乐器、乐曲与歌辞三个部分,认为乐器与乐曲不能承担起这一功能。他说:“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故臣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4]1364因为歌辞反映的是人的情感,而后者与国家兴亡密切相关,所以白居易认为只有歌辞才能做到这一点。《进士策问五道·第三道》曰:“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古之君人者采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迩,无美刺,日采于下,岁闻于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4]1001受其音乐思想的影响,白居易的歌辞观念大致有三:一、歌辞应当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他在《与元九书》中指出:“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中提出了“形容盛行,实在歌诗”[4]964等观点。二、就歌辞本身而言,它的内容比形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如在《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中,白居易强调歌辞应当揭示出乐曲的深层含意:“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终稽首陈其事。”“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4]75在《和答诗十首并序》中反对歌辞在形式上的追求:“且奉新诗一轴,至于执事,凡二十章,率有兴比,淫文艳韵,无一字焉。”“言有为,章有旨,迨于宫律体裁,皆得作者风。”[4]39三、歌辞应当具有讽刺精神。白居易认为:“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4]39在《与杨虞卿书》中又指出:“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4]947总之,白居易认为歌辞应当具有现实内容和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为此,他认为《诗经》是歌辞最早的源头和最好的范本,并以恢复“诗道”精神为己任。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仆尝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4]960受此音乐思想影响,他还进行了具体的歌辞创作实践。
二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它们分别是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与杂律诗,他最在意的是讽喻诗。这些讽喻诗主要作于元和三年至五年,当时他任左拾遗,并充翰林学士,元稹《白氏长庆集》曰:“未几,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1]554据傅璇琮研究,翰林学士在此时是一个非常显赫的职位,“按翰林学士建立于唐玄宗期间,它是唐朝中期后知识分子参预政治的最高层次,对文士生活、思想及文学创作,都有较大的影响”[10]。故白居易此时拥有高涨的参政热情。当时翰林学士除了参政议政以外,还会应制进行歌辞创作,比如,白居易在《太平乐词二首》标题后注有“已下七首,在翰林时奉勅撰进”[4]397-398。基于对音乐功能的独特认识,白居易将歌辞创作也视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事务来对待,他说:“当其在近职时,自惟贱陋,非次宠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称之。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4]947又说:“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4]962他在《与元九书》中所列举的“咏歌之”的篇目主要是讽喻诗,而这些讽喻诗的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充满着现实内容与讽喻精神,与他的音乐观与歌辞观相一致,所以这些讽喻诗的实质就是歌辞。
关于这些讽喻诗是否为歌辞,历来存在着诸多争论。持否定态度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有“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1]555,一般学者认为既然“时人罕能知者”,就说明它们没有被传唱过,所以它们不是歌辞。实际上,元稹的这番评论是在比较的视野下得出来的,意指讽喻诗相对于白居易的其他类别诗歌在传播上显得寂寞。众所周知,白居易的杂律诗在当时传唱最盛,“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4]962,李忱《吊白居易》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11]50但是元稹并没有说讽喻诗在当时没有被传唱。事实上,在唐人心里诗与歌的区别并不大,当时人仅从形式上作些简单的划分,如元稹《乐府古题序》说时人只是从形式上对两者作简单的划分,“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1]254。两者的转换极容易,只要有乐人翻唱即可,如羊士谔《客有自渠州来说常谏议使君故事,怅然成咏》曰:“至今犹有东山妓,长使歌诗被管弦。”[11]3713白居易《醉戏诸妓》曰:“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4]510唐代许多诗人的诗被传唱,清代陈仅《竹林答问》曰:“大抵唐时诗人多通音乐,故其诗皆可披之管弦。”[12]白居易精通音乐,且与乐人有密切交往[13],所以他的诗更容易被传唱。《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形象地再现了他的诗瞬间转变为歌的过程:“我有乐府诗,成来人未闻。今宵醉有兴,狂咏惊四邻。”[4]105故据元稹的评论并不能得出白居易讽喻诗不为歌辞的结论。
持否定意见的另一条依据是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歌辞一》中对“新乐府”所作的解释:“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14]1263其实,所谓“未常”,即“不时时”,可见郭茂倩并没有断然否定它们是歌辞,况且其在《乐府诗集·新乐府歌辞八》又曰:“新乐府五十篇……大抵皆以讽喻为体,欲以播於乐章歌曲焉。”[14]1355事实上《乐府诗集》所收集的新乐府作品,有些在当时已经被传唱,所以据《乐府诗集》亦不能得出这些讽喻诗不是歌辞的结论。
只要仔细检索唐代相关史料,我们会发现诸多关于讽喻诗被白居易视为歌辞创作的证据。以《秦中吟》为例,白居易不但在诗序中言“直歌其事”[4]30-34,而且在《寄唐生》中亦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同时还将之称为“乐府诗”,“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4]15。白居易在其他诗作中也曾用过“乐府诗”一词,如《读张籍古乐府》赞誉张籍“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并接着曰“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4]2,从此首诗中用“播”、“内乐府”、“闻”等描述“乐府诗”来看,白居易所谓的“乐府诗”实质就是指歌辞。再以《新乐府》为例,白居易在诗序中有“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4]52之句,在组诗《城盐州》中有“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4]67等句。除这些内证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外证。如《与元九书》曰:“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4]963时人将《秦中吟》与《长恨歌》并提,而《长恨歌》在当时己经广为传唱,既然将这两者并提的还是当时诗歌传唱的主体——歌妓,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据此判断《秦中吟》在当时己经被传唱。《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6]卷150,4340所谓的“流闻”就是指口耳相传,因为唐人常常用“流”来指称音乐的传播。关于这点,唐诗中俯拾皆是。如“高殿凝阴满,雕窗艳曲流”[11]465(许敬宗《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舞集仙台上,歌流帝乐中”[11]957(张说《奉和圣制喜雪应制》)、“不知何处学新声,曲曲弹来未睹名。应是石家金谷里,流传未满洛阳城”[11]1474(王諲《夜坐看搊筝》)。由此推断,这些讽喻诗在当时有些己经被入乐传唱了,并且还被传到帝王耳中,从而部分地实现了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如《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6]卷150,4340
综上所述,白居易提出“通儒”的音乐观,即承认音乐与国家兴亡关系密切,但音乐并不是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而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在音乐诸要素中,最能发挥这种功能的是歌辞而非乐曲或乐器。白居易的这种音乐思想与唐太宗有相似之处,扎根于中唐音乐发展的现实土壤中。白居易非常重视歌辞创作,主张歌辞应当具有现实内容与讽喻精神。以《秦中吟》与《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就是这种音乐思想的具体歌辞实践。
[1]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0:500.
[3]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75.
[4]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吴兢.贞观政要集校:卷7[M].北京:中华书局,2003:417.
[6]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3.
[8]欧阳修.新唐书:卷22[M].北京:中华书局,1986:478.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8[M].北京:中华书局,2005:6993.
[10]傅璇琮.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J].文学评论,2002(2).
[11]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2]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234.
[13]柏红秀.白居易与乐人交往考[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6).
[14]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