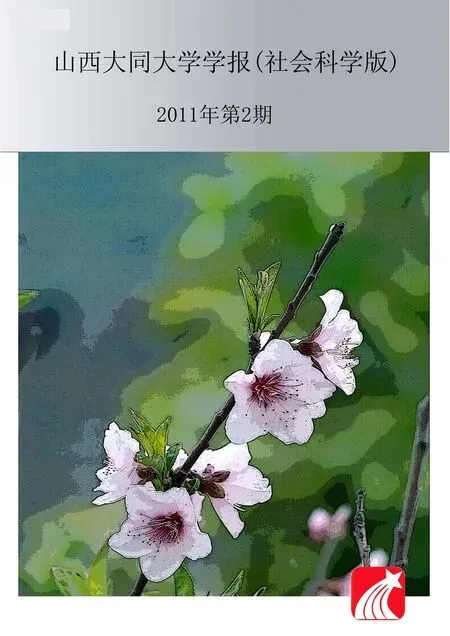浑源龙山考
2011-04-12李润民
李润民
(山西大同大学辽金文化研究所,山西 大同 037009)
浑源龙山考
李润民
(山西大同大学辽金文化研究所,山西 大同 037009)
“龙山三老”是金元之际一个著名的称号,涉及元好问、李冶、张德辉三位在金末元初声名卓著的历史人物。“龙山三老”的龙山(封龙山)又有两说,一是山西浑源,二是河北元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通过考察辨证,河北元氏封龙山固然得天独厚,为人所共知,而山西浑源龙山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元好问有诗,麻革、刘祁有记,还有不少诗文提及龙山,足见其在金元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
浑源;龙山;元好问;刘祁;麻革
一、金元名人在浑源及龙山的踪迹
山西浑源自古人杰地灵,尤其是金代斯文昌盛,人才辈出,浑源雷氏与刘氏便是享誉全国的文学世家。浑源的龙山更是代北名山,北魏时期已成为北方的佛教盛地,几经天灾人祸,经唐宋恢复,到金元时香火又盛,我们从元好问、刘祁、麻革的诗文中可见一斑。雷思、雷希颜,雷渊、刘撝、刘汲和刘从益,都是在龙山浑水的孕育中称名当世的。元好问《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说:“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乾隆《大同府志》卷四载:“龙山,一名封龙山,东北距浑源州治四十里,高三里,盘踞八里,两岭中分处建大云寺,岭西为文殊岩,危峰怪石……元初李冶、元好问、张德辉尝游此,时称‘龙山三老’。”[1](P87)卷六载:“龙山遗迹,州西南四十里封龙山,金时李冶、元好问、张德辉尝游此,号‘龙山三老’,山中有刘京叔、麻信之诸贤题咏。”“龙山诗碣,在大云寺中,金郡人雷思撰并书。”[1](P118)
《元诗选》巻一麻革《贻溪集》:“革,字信之,临晋人。父秉彝,登金皇统九年进士第,歴官兵部侍郎。革生中条王官五老之下,长侍其先人,西观太华,迤逦东□至洛,遂避地家焉。北渡后尝自雁门踰代岭之北,留滞居延。己亥夏,赴试武川,及秋归道浑水,访刘祁京叔于浑源,登龙山絶顶,自作游记。”
刘祁撰《归潜志》卷十三载麻革《游龙山记》:
“余生中条、王官、五老之下,长侍先人,西观太华,迤逦东□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乌权、白马诸峯,固已厌登,饱经穷极幽深矣。……越既留滞居延,吾友浑源刘京叔尝以诗来,盛称其乡泉石林麓之胜。浑源实居代北,余始而疑之。虽然,吾友着书立言蕲信于天下后世者,必非夸言之也。独恨未尝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试武川,归,道浑水,修谒于玉峯先生魏公……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识”因命余,余乃提笔,书凡游者名氏及游之岁月而去。……己亥岁七夕后三日,王官麻革为之记。同游者。”[2]
“作者曾饱游中原名山,又久厌塞外荒寒,因而对刘祁盛赞他家乡浑源山水之美,将信将疑。而经过两天的游赏,目睹龙山山水之奇异,深为叹服,发现龙山有他山不可或替的独特胜景,觉悟到自己陷于因循通病,‘得于此而遗于彼,用于所见而不用于所未见’,偏执己见,实乃孤陋寡闻,缺少全面的实践。本文通过龙山记游,生动具体地表现了‘始而疑之’到‘观山有得’的变化和体会。因为作者立意于此,所以写龙山胜景,不仅描绘精美,更充满惊讶、赞叹、省悟有得的感情,情随景移,意趣盎然。这是本文的显着的艺术特点。”[3](P98)麻革的《游龙山记》,写法讲究,浑然一体,颇受后人的重视与好评,多种游记选本都收录。
刘祁撰《归潜志》十三《游西山记》:
“余髫乱间,尝闻先大人言,龙山之胜甲乡山。时幼,未能往。其后在南方,北望依依,每以为歉。甲午岁还浑水。明年秋八月,释菜于先圣。越明日,拉友人河阳乔松茂寿卿、云中刘偕德升,暨弟郁同游。初出西城,日方中,望西山而行。一二里,涉水。又前七八里,至李谷。谷在永安山下……呜呼,余生山水间,故有乐山水心。然南游二十年,所居皆通都大邑,无山林,尝迫狭不自得。今因北归,得游历故山,可胜快哉!况干戈未已,栖隐为上,行当结屋山中,览天地变化之机,而又读书足以自娱,着书足以自奋,浩歌足以自适,默坐足以自观。逍遥涧谷,傲睨云林,与造化为徒,与烟霞为友,虽饭蔬饮水无愠于中。振迹宽心,可以出一世之外,又何必高车大盖、驺骑满前方为大丈夫哉?因记。”[2]
刘祁是浑源人,习惯称家乡的龙山为西山,岳神山(今北岳恒山)为南山。但今人杨镰在其《元代文学编年史》中提到:“八月,刘祁出游封龙山,作《游西山记》。元太宗六年,刘祁还归浑水。七年秋,进入封龙山游览。《游西山记》是封龙山的工笔画卷”似有理解之误。[4](P61)刘祁对龙山感情更深厚,笔端常带感情,对景物感受更真切,这是与麻革一个外乡人所不同的。当然叙写也就很随意,不太讲究章法,且议论感慨也多,这是刘祁的特色。
金刘祁撰《归潜志》卷九:“梦中作诗或得句,多清迈出尘。余先祖龙山君尝梦得句云:‘山路崭有壁,松风清无尘。’先子梦中诗云:‘落月浸天池’。余幼年梦中亦有作诗‘□猿哭处江天暮,白雁来时泽国秋’,如鬼语也。”[2]卷十四《归潜堂记》:“刘子,朔方人,生于云中之浑源山水之间。髫龄从父祖仕宦大河之南……岂知一旦时移事变,流离兵革中。生资荡然,僮仆散尽,从行惟骨肉数口,旧书一囊。由铜壶过燕山,入武川,几一载始得还乡里。乡帅髙侯为筑室以居。所居盖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见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东为柏山,代北名刹。西则玉泉、龙山,山西胜处…榜其堂曰归潜且以张横渠东西二铭书诸壁”。[2]
浑源雷氏和刘氏在金代是享誉全国的文学世家和文治能臣。到元代孙氏崛起,成为武功的代表。刘因《浑源孙公先茔碑铭》:“…昔龙之山,有晦而沦。必孙氏之先,盖有嗟其屈者。谓天道之或愆,今晔其华,贲及邱原,亦有嗟者,谓赋兴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终,而不探其源,孰驭龙山,逰万物巅。下视乎神川,…郁乎相辉,一代人闻。惟将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复与雷刘之子而骢马聨翩…”[5](卷8)王恽《孙公神道碑铭并序》:“云西风土雄硕,龙山峻极为之奠焉,浑流交贯,神川清淑资其润焉。故士生其间,有瓌竒宏杰之称,而刘雷为之冠焉。然山川炳灵奚间今昔,况河洛为帝王之里,并汾多攀附之臣。俪景风云依光日月者哉?若乃始以才技有光世绪,终则挺输忠荩作时名卿,安荣福寿庆流后裔者谁乎?故宣慰使工部尚书孙公其人也。公讳公亮,字继明,世家浑源横山里。”[6](卷58)元明善撰《大元故保定等路军器人匠提举孙君墓碑》有序:“……(山下龙)嵷龙山,锦里烂烂。菡其晖华,而大厥家。神川之封,三爵俱公。始慎择术,仁被锻镞。五世效庸,以食函功。皇矣帝图,完哉士体。保孙氏函,克受帝祉。猗嗟孙门,世载令人。允武允文,国也宝臣。繄从仕君,众子惟肖。截截才妙,风棱清峭,方期巍调,有奕它曜,云何四十一病不疗。”[7]
刘因《示孙谐》:“龙山古壮哉,郁郁盘烟岚。一读元子诗,泠然玉泉甘。江山胜景要佳客,而我不到懐应惭。雷家髯翁虎眈眈,刘氏遗爱存河南。百年乔木动秋色,篮舆谁与供竒探。昆山出美玉,楚国多楩楠。孙郎复贵种,良璞须深圅。勾萌慎培养,云霄看岩岩。野失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归休堪。传经访道可无媿,为我早办龙山庵。”[5](卷17)
刘因《孙尚书家山水卷》三首:“扁舟老树傍苍崖,好似今秋雪岭回。试问黄尘山下渡,几人曽为?山来。”“诸公乆矣笑吾贪,是处云山欲结庵。只有皇卿解赀助,画山须画静修龛。”(谓皇甫安国)“画圗题品代移文,寄谢神州老使君。欲乞龙山恐孤絶,南州隆虑且平分。”[8](卷14)
刘因、王恽、元明善都是元代诗文大家,他们与浑源孙氏多有交往,王恽还写有著名的《浑源刘氏世德碑铭》,是研究金元文学的重要文献。
二、元氏封龙山及“龙山三老”的历史事实
(一)问题的提出及“龙山三老”的出处和性质康熙《山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八载:“李冶,字仁卿,正定栾城人,登进士第,调高陵薄,未上,辟知钧州事。壬辰城溃,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聚书环堵,人所不堪,冶处之裕如也。世祖在潜邸,闻其贤,遣使召之,且曰:素闻仁卿学优才赡,潜德不耀,久欲一见,其勿他辞。及即位,欲处以清要,肯求还山。冶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而浑源志谓冶与元好问、张德辉尝游龙山,为龙山三老之一,今两存其说。”顺治《浑源州志》上卷载:“龙山,一名封龙山,在城西南四十里,暑月雨霁,山气上腾,其色如虹,顶有萱草坡,翠杉苍桧,千尺凌云,又有文殊岩,大云寺禅寺,金麻革有《游龙山记》,一统志云:金末李治、元好问、张德辉尝游此山,号‘龙山三老’。”同书下卷载:“元好问,号遗山,太原定襄人,七岁能诗,以文名世,时游神川与李治、张德辉结吟社,称‘龙山三老’。按遗山足迹遍雁代间,龙山独称三老,盖地以人重耳。”一个称谓涉及到金元之际三位名人,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事关两个地方,到底是山西浑源,还是河北元氏,为何出现这种现象?有弄清楚的必要和研究的价值。
元好问、李冶和张德辉是金末元初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政治家,虽然三人经历不同,成就各异,但一个共同的称谓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道出了三人巨大的影响和所受的尊崇,这个称号就是“龙山三老”。这一称号最早的出处应该是《元名臣事略》卷十:“宣慰张公,公名德辉,字耀卿,冀宁交城人。国初为丞相史忠武王幕官,寻召居潜邸。中统元年拜河东宣抚使,入拜翰林学士,参议中书省事,出为东平宣慰使,出佥山东行省。复召参议中书省事,表乞致仕,未几,起为侍御史,遂致仕归……与人交重然诺,不戏言笑,在尊俎间亦以礼法自持,故元遗山呼为畏友,亲旧不敢干以私恤,……与遗老敬斋游封龙山时人目为龙山三老云”。又《元史·张德辉传》载:“张德辉,字耀卿,冀宁交城人……与元裕、李冶游封龙山,时人号为‘龙山三老’。卒年八十。”[8]这让我们很容易和当时另一个群体称号“河汾诸老”联系起来。但是很明显,后者是一个纯粹的遗民诗人群落,相似的风格和经历使后人把他们当作一个流派看待,而前者则要复杂的多。“三老”都能诗能文,元好问是当之无愧的文坛盟主,而李冶更是一位科学家,张德辉又颇有治才。但真正把三人联系在一起的还是元初为了保存传统文化,弘扬儒学治道,为济世救民而做的共同努力。这一点已有多人论述,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山与人的关系问题。
(二)“龙山三老”在河北的依据 河北封龙山,虽然在县志、府志、通志中都没有明确的提到“龙山三老”或“封龙三老”,但封龙山的名字是早就确定的。乾隆《正定府志》载:“封龙山,元氏县西北五十里,在获鹿县南,旧名飞龙,唐改今名……有书院,汉李躬郭元振,宋李昉张皤叟,元李冶后先于此讲学。”民国《元氏县志·地理志·山脉》载:“封龙山,乾隆志在县西五十里范家庄村西,巍然崛起于太行之东,回环望之,四面如一,旧名飞龙,盖山势如伏龙故名飞龙,唐改今名。”《元氏县志·地理志·古迹》载:“封龙山,按山开面向南,正南中峰之下有书院,金榆枓障二山左右对峙,有龙虎环抱之势,‘封龙山’三字在山麓东南,大约二尺四五寸,旧志‘龙山耸翠’为八景之一。”《元氏县志·教育志·书院》载:“封龙书院,在县西北封龙山下,相传汉李躬授业之所,唐郭震,宋李昉、张皤叟,金李冶,元安熙皆尝讲学于此。”而且,我们在《元氏县志》中李冶《重修庙学记》一文记载中知道,李、张二人一个主讲封龙书院,一个主管真定地区的教育,关系相当密切。元王思廉在其《龙泉院营建记》中提到:“因忆甲寅九月先大夫同张丈,奉先诸君陪遗山先生会饮于此,留题石刻故在,顾怀畴昔已自不能辞。”元好问本人在其《鹿泉新居二十四韵》一诗中有“灵岩龙泉曾一到,独欠封龙展衰步”的诗句,以元好问爱山乐水的性格,封龙山不会“独欠”下去的。《元名臣事略》、《元史·张德辉传》一提到封龙山,多数人就确信无疑“龙山三老”是在河北的封龙山了。所以今人有下列论述:“龙泉寺元碑的发现,证实了元好问在封龙山活动过。”[9]“封龙三老指的是元好问、李治、张德辉,三人均为金元时期的诗人和名宦。他们都在元代真定所辖地区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晚年又归隐于此,于真定路的人民和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上的封龙山,是一个集儒、道于一体的名山,文化宗教氛围十分浓厚。元好问等人晚年归隐于此,正于这瑞安定的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封龙三老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与元朝统治阶级中的某些高层人物有广泛而密切的交往。”[10]“与张、元相比,李冶与封龙山的关系最为密切”。“龙山三老一起在封龙山活动的时期应该就是1249至1257年之间”。“真定地区之所以成为蒙元初期的人文荟萃之地,出了不少在文学创作、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人才,其中既有汉人世候史天泽的功劳,也有龙山三老的功劳。”[11]“元好问的晚年曾在封龙书院就教,与大科学家李冶、大诗人张德辉一起被称为‘龙山三老’或‘封龙三友’。”[11]“‘龙山’一词,历来颇多混淆,实则一在山西浑源,一在河北元氏。据嘉庆《一统志》载:‘龙山在浑源州西南四十里,亦名封龙山,其绝顶曰萱草坡,翠杉苍桧,千尺凌云……夏时雨过,山气上腾如龙,故名。金末李治、元好问、张德辉常游此山,时号‘龙山三老’。麻革‘游龙山记’,遗山‘龙山诗’均指此地。《全金诗》注云:‘遗山游神川,与李冶、张德辉结吟社,称龙山三老’。施国祁亦注:仁卿居浑源,惟据苏天爵名臣事略。仁卿‘居元氏之封龙山’,焦集贤撰仁卿文集序云:‘先生北渡后,隐居崞山,又之太原平定元氏,流离颠沛,未尝一日废’,均未提居浑源事。又遗山龙山诗只言‘玉峰(魏璠)有佳招’,亦未及仁卿耀卿,则三人结社吟咏之地,当以元氏之龙山为确。据一统志载:‘正定府封龙山在获鹿县南,结元氏县县界,一名飞龙山……《水经注》云,洨水东经飞龙山北,即井陉口。《旧志》:山势入伏龙欲飞状,峰峦泉石迥环错列,称为奇胜。’山上有封龙书院,《一统志》载:‘封龙书院在获鹿县南封龙山上,……元李冶安熙皆尝讲学于此’。按正定为仁卿之故乡,由崞南归,经太原、平定而至元氏,乃捷径,无北迂浑源之理。又遗山晚年常至镇州(正定),且在获鹿营‘鹿泉新居’,有定居意,耀卿则久居史天泽幕,且一度提举真定学校,三人同在一地,结伴漫游,吟咏为乐,为极自然之事。地方志附会名人,以显地灵,殊无足取。”[13]
三、正确对待和利用浑源龙山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名人效应
从以上材料我们看出,山西浑源的龙山是本名,而又名封龙山,是别名。河北元氏的封龙山是本名,只有在“龙山三老”这个称号中才叫龙山,是简称,二者都与“龙山三老”关联。不能否认河北元氏封龙山的正宗地位,但山西浑源龙山也非浪得虚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山西浑源龙山又名封龙山的来历。清光绪《山西通志·山川考》载:“又龙山,方志以为封龙,又以为龙兑。以史记赵世家核之,皆不在此。”这是史书误读误解之故,因浑源有恒山又名常山,与河北曲阳恒山多有误会,所以牵带着把龙山和封龙也弄混了。笔者曾亲自调查,按麻革《游龙山记》和刘祁《游西山记》的记述重游龙山,景色依旧,而古迹几乎荡然无存了。在新建的文殊殿中找到两块明万历年间的《千古龙山大云禅寺记》残碑,可惜字迹漫漶不清,难以卒读。在浑源龙山脚下荆庄村大云寺 (又名下寺,龙山上大云寺为上寺)发现仅存的金代大殿和其中的元明壁画,更重要的是在大院内找到仅有的一块清康熙年间的残碑《重修龙山寺碑记》,上书“按舆图志,云中有丰隆山,其形胜壮如游龙……”。龙山又名封龙山的来历,看来是同音误传之故。
其次,元好问“得交此州雷与刘”并多次逗留浑源,还留下了《浑源望湖川见百叶杏花二首》、《念奴娇》(小山招饮)、《游龙山》、《李峪园亭看雨》、《玉泉二首》、《赠玉峰魏丈邦彦》诸诗词,可见元好问与浑源缘分颇深,是“龙山三老”在浑源的最有力实证。《游龙山》:“曩予尉大梁,得交此州雷与刘,自闻两公夸南山,每恨南海北海风马牛,老龙面目今日始,一见更信造物工,……一峰一峰千百峰,虽欲一一顾揖知无由,金城偃蹇不得上,瑶瓮回合如相留,……白云相望空悠悠,异时华表见老鹤,姓字莫忘元丹丘。”《李峪园亭看雨》:“龙山右胁松十里,细路蜿蜒绕龙尾,…玉泉元自别一天,眼界廓廓无神川,金城百里纔一俯,半尖浮图插苍烟,……只知龙山之神神更神,永安亦能撼诗人,晦暝变化千万态,画出风雨元非真,夕阳展放紫翠屏,只欠松梢一轮月,山中一石回万牛,况是一壑复一丘,不如一诗招将入南州,先生兴来时卧游。”元好问写龙山的两首诗,都用得是七言古体,最适合表情达意,抒写怀抱。元好问能放浪浑源山水间,既有人的因素,再加上绝胜山水,无怪遗山要流连忘返了。
再次,两山都是境内名山,有着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河北封龙山如上所述,固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浑源龙山也不逊色,前文已述,不再赘言。
最后,崇尚名人、乡土自重的文化心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浑源州志》:“按遗山足迹遍雁代间,龙山独称‘三老’,盖地以人重耳。”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必然有它的倾向性,扬善隐恶是人之常情,何况还有元好问确凿的事例。李冶曾“流落忻、崞间”,离浑源并不遥远,虽然没有发现来过浑源龙山的证据,但既然是“尝游龙山”,游过一次就符合要求,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这种可能。张德辉本是山西交城人,在《大同府志·流寓》中载其“中统元年拜河东宣抚使”,来晋北游龙山也有可能。但这些都不影响人们把“龙山三老”拉在自家门下的自豪与执着。历史上这种并存的现象不胜枚举。还是举浑源的例子:如苏保衡和魏璠到底是不是浑源人,怎样理解浑源有苏保衡墓,有刘撝和苏保衡读书的翠屏书院;魏璠是刘祁的姑丈,长期隐居浑源南山,麻革、元好问都来拜访过。和“龙山三老”一样,都有待我们不断探求其历史、文学以及文化的价值。
浑源龙山不只景色绝佳,更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引人注目。本文只是就金元之际龙山的相关情况作了些粗浅的探究,有待进一步的考察、研究与开发。
[1](清)吴辅宏.大同府志[M].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2007年标点本.
[2](金)刘 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费振刚.古代游记精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杨 镰.元代文学编年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5](元)刘 因.静修集[A].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元)王 恽.秋涧集[A].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牛贵琥,李润民.全元文补遗二篇[J].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5-59.
[8](明)宋 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李金泉.小释鹿泉市龙泉寺元碑[J].大舞台,1999(4):58.
[10]吴秀华.封龙三老与真定元曲作家群[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4):34-37.
[11]魏崇武.封龙、苏门二山学者与蒙元时期的学术和政治[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2):74-79.
[12]东淑梅.龙泉寺发现元好问纪事碑[J].大舞台,1999(4):89.
[13]续 琨.遗山之师友渊源[J].元好问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4(6):59-60.
〔编辑 赵立人〕
A Survey of Longshan M ount in Hunyuan
LIRui-m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aojin Culture,Shanxi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Three Longshan Seniors"(Longshan Sanlao)was a famous title addressing three prestigious people,Yuan Haowen,Li Zhi,and Zhang De-hui,in Late Jin and Early Yuan dynasties.Some people say Longshan was in Hunyuan in Shanxi,and others say it referred to the Yuans in Heibei.Why was this?After investigations,it can be seen that though Fenglongshan in Hebeiwas well-known to people,the Longshan in Hunyuan of Shanxi ismore impressive,and it has beenmentioned bymany scholars in their poems,therefore,itenjoys unique importance in Jin and Yuan literary history.
Hunyun;Longshan;Yuan Haowen;Liu Qi;Ma Ge
K291.25
A
1674-0882(2011)02-0054-05
2010-11-12
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82020);山西省社科联“十一五”规划项目2009-2010年度重点课题(SSKLZDKT2009121);山西大同大学科研项目(2010K13)
李润民(1971-),男,山西灵丘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辽金元文学。
·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