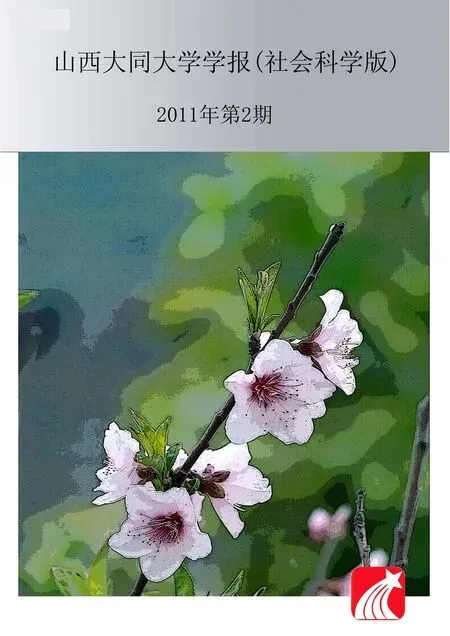“优歌”“秧干”辨
2011-04-12刘兴利
刘兴利
(1.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2.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山西 临汾 041004)
“优歌”“秧干”辨
刘兴利1,2
(1.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2.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山西 临汾 041004)
广灵秧歌,又有“优歌”、“秧干”等异称,但文献中并不见其作为“秧歌”的记载。笔者在详尽辨析之后认为,“优歌”非“秧歌”,“优歌”很可能是一个泛称;“秧干”是“秧歌”一词的读音在广灵方言中发生音变所致。此外,舞台题壁中的“洋歌”、“洋干”、“洋哥”等称呼,除方言原因外,亦与书写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书写随意,不求文字的准确性有关。
优歌;秧干;洋歌;洋干;洋哥
广灵秧歌属晋北大秧歌系统,与繁峙秧歌、朔州秧歌并称为晋北三大秧歌。但在今所见到的有关广灵秧歌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并不曾见到“秧歌”一词。按诸多研究者的理解,清康乾间《广灵县志》中所记的“优歌”,即是今日所谓的“广灵秧歌”,群众习惯把它呼为“秧干”。因此,他们多以“广灵秧歌”又名“优歌”亦或“秧干”来介绍这一剧种。对此,《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和《朔州地方戏曲音乐》(上)均解释说:由于方言的缘故,县志记作“优歌”,群众呼为“秧干”。果全是由于“方言”之故?笔者存疑。
一、“优歌”乃古代优人所唱之歌曲
“优歌”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1](P58)关于“《暇豫》”,从《国语·晋语》所叙优施事迹中即可了解。优施,《国语·晋语》云:“公(献公)之优曰施,通于骊姬。”所以优施参与了骊姬欲谋杀太子申生而拥立其子奚齐的阴谋,并受命前去威吓利诱对此事有碍的大臣里克,在他的酒席上起舞,并唱了一首《暇豫》之歌:“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已独集于枯”,用以讽喻里克不要死心眼,而要识时务。按《说文解字》:“优,饶也;一曰倡也,又曰倡乐也。”古代之优,本以乐为职,故优施假歌舞以说里克。“优”古时又训为调笑、戏谑之行为。《左传》:“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杜预注:“优,调戏也。”引申之,则从事此行为者亦称为“优”。《辞源》:“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的通称,后来亦以称戏曲演员”。由此推理,“优歌”自然是指从事这种职业的“优”所唱的歌曲了。对此,《汉语大词典》明确解释:“优歌,即优人唱的歌曲”。
既然所有的优人所唱的歌曲皆可被称之为“优歌”,那么清康乾年间流布于广灵境内的晋剧、北路梆子、弦子腔等剧种,也是有可能被记作为“优歌”的,因而不一定特指广灵秧歌。这是其一。
二、“优歌”乃古代酬神之剧种
古人祭祀,礼有常数,乐有常节,是相当郑重的。为表示对神灵的尊敬,或者说为了不冒犯神灵,他们每次为受祭神祗供献的戏曲种类和剧目内容也是极为讲究的,并非任意剧种任意剧目皆可。这也就体现出了“入流”和“不入流”的差别。所谓“入流”自然是指能登大雅之堂,可用来供奉神灵或为官僚士大夫们于正规场合所欣赏的戏曲剧种和剧目。“不入流”者即是表演粗俗、剧目充满“色情”内容的小戏剧种。清·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二载遂安洪子泉著《演戏敬神说》:
演戏敬神,为世俗之通例……若夫点演淫戏,令人丑状注目,妖惑攒心,此稍知自守而具天良者,皆欲恶此而逃,望望然去之,岂有聪明正直之谓神而耳忍闻目忍睹者乎……夫岂有敬神而反以亵神者,岂有劝世而反以惑人者,岂有祈福而反以求祸者。诚如是也,则所谓“非徒无益而又
害之”者也。[2](P309~310)
由此看来,按照古人的评判标准,是绝不敢让“不入流”者去亵渎神灵的。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广灵县志》“营建”卷“坛壝”条关于“优歌”的记载有两条:一是“雩祭坛,在壶山上,是日,置水器、柳枝,用优歌”;一是“春场,在先农坛,至日设春筵,用优歌”。[3]这两次均为重大活动,尤其是前者在广灵历史上是极为受重视的。
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因为“雩”音近吁,祭祀中有舞者、歌者、哭者,发出悲泣吁嗟之声,寄以感动神灵,及早降雨,所以谓之“雩”。“雩”分“官雩”及“民雩”两种。自西周以来,历代朝廷雩祭都要唱悲苦乐歌或者类似歌曲,再加上既定的礼仪,最终确立了可以称之为“官雩”的祈雨传统。民间祈雨则受到“官雩”的左右及影响,参伍因革,因地制宜,又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民雩”的祈雨传统,两大传统其实出自同一源头——雩。广灵历史上多旱,雩祭频频,如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广灵县志》“艺文”卷《重修社台山圣像碑记》载:
县治西关有社台山,屹然特出,环冈面水,轩敝可远眺。上有龙神庙,不知创于何时……邑人遇旱,祷雨于此,每祷辄应。去年嘉平月,余承乏是邑,值岁旱不登,黎民阻饥。今岁复骄阳为虐,自春徂夏不雨,土若焦釜,二麦不生,谷黍皆槁。余与寅属诸生斋戒虔诚,朝夕步祷,将四十日。至六月乙卯大雨,四郊沾足,禾稼勃兴,官属四民,靡不举手加额……城关士民戴天之恩,而愈弗敢没神之惠,遂各醵金钱装修神像,丹雘庙宇,以酬神德。《祀典》曰:能捍灾御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是役也,诚有合于《祀典》之谓矣……余愿与畴人父老明德荐馨,永报赛神德于勿替矣。[3]
碑文至少反映出五条信息:第一,雩祭的对象是山川、龙神;第二,雩祭的执行者是邑令及寅属诸生;第三,当时的祈雨仪节是斋戒虔诚,朝夕步祷,将四十日;第四,效果是六月乙卯大雨,四郊沾足,禾稼勃兴;第五,祈雨灵验,“遂各醵金钱装修神像,丹雘庙宇,永报赛神德于勿替矣”。雩祭的地方模式,分常雩、大雩和个人步祷暴露法三种,碑中资料显示的显然是步祷暴露法。该法源自春秋时的齐景公,主祭者多为地方官,也有平民,他们跣足露首,步祷上山,暴露于庙庭,故而一旦有应,其事遂入宦迹,受到上司的赏识和百姓的爱戴。由于该邑令雩祭之时非常虔诚,甘为黎民而受苦的精神终于使神灵为之“感动”,故其祈雨未久而天降甘霖。相较于官雩,民雩则显得较为灵活随意,其主要特点是既不定期也不寻址,一般是在持续干旱,灾情特别严重时才举行,有的甚至远到他乡更为灵验的神庙祈雨,多依附于迎神赛社一并举行。
春祈秋报,悦神庆丰,自先秦时期即已成为民间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六朝时期,这种报赛形式与佛教行像仪式结合,发展为社火游行表演。宋以后,民间杂神淫祠广为兴起,社火与庙会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迎神赛社,对于像广灵这样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地方来说,自然有着特别的意义。广灵春祈仪式一般设在先农坛举行,至日设春筵,摆供品于神前,后用“优歌”演戏酬神。出于救旱的现实需要,北方民众要以祈雨、谢雨为主,其次才是个人的其它祈求,即或面对并不以救旱名世的神灵也不例外。民众可以崇拜不同信仰中的神灵的实质,主要是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现实问题 (如干旱)的关注,相信神灵能够解决现实世界里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优歌”非秧歌
从广灵秧歌的演变历史来看,清康乾时期正是这一剧种从广场歌舞“秧歌”向“秧歌戏”的转变期,其表演仍以广场演出为主。也就是说,它尚未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可以正式登台演出的戏曲剧种。与可用来供祀神灵的戏曲剧种相较,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早期的广灵秧歌上演的剧目多以反映农民心态和民情民俗的“二小”、“三小”戏为主,如《卖饼》、《打瓦罐》、《借冠子》、《牧牛》之类。这些小戏结构简单,表演粗俗,多以情节风趣、语言生动取胜,因此颇受民间大众的喜爱,将秧歌班唤为“玩艺班”,唱秧歌的艺人则被称为“耍孩艺”,并有“胡闹三官”之说,不能敬神。又《广灵县志》“戏曲”条载:“弦子腔是本县较早的地方剧种。清朝初年由河北进入境内,后经多年辗转演唱,揉入本地口语。”[5](P559)弦子腔最大特点是多唱“敬神戏”,演出时态度严肃,动作规范,唱词文雅,无庸俗动作。表演技巧讲究“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等,脸谱讲究,且剧目繁多,内容丰富。除“三小”门的生活戏外,更多的是多行当的袍带戏,如《聚古城》、《单刀会》、《打三鞭还两锏》、《淤泥河》、《美良川》、《击金钟》、《告御状》、《审郭槐》、《乌盆告状》、《收存孝》、《五牛挣死李存孝》、《刘秀走南阳》、《夺状元》等。可见,无论是从剧种自身的成熟程度,还是从剧目内容特色方面,广灵秧歌都是无法与能唱“敬神戏”的弦子腔相提并论。
综上,大旱灾荒之年举行的雩祭,每行必“歌哭而请”,歌唱时需伴之以忧愁之乐,执行之人步祷暴露,场面是何等的悲壮谦恭!春祈又是一年之初的大祀祭,其仪式亦必是庄严肃穆的!在农耕祭祀时唱的戏,不是在农田里唱的,而是在庙里唱的;唱戏的目的不是给人开心逗乐的,而是给神焚香致礼、请求保佑的。在如此场景之下,若以诙谐风趣、谈笑风生、颇具滑稽搞笑色彩的广灵秧歌去供奉神灵,必是对神灵的大不敬!诚则动,敬则格。按古人对神灵的虔诚和敬重,既然此时广灵本地已有最适宜为神灵演出的“敬神戏”,他们是万般不敢再用有“胡闹三官”之称的秧歌戏去敷衍神灵的。由此,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优歌”非“秧歌”,“优歌”很可能是一个泛称,包含当时广灵境内所有能被正统主流思想所接受的剧种,是封建士人对当时能“入流”的戏曲表演的总的称呼。
四、“秧干”乃音变
至于“秧干”,笔者认为这只是“秧歌”一词的读音在广灵地方方言中发生音变所致。现代普通话的韵尾分为三类:没有韵尾的开韵尾、以元音为韵尾的元音韵尾和以鼻音为韵尾的鼻音韵尾。这三类韵尾古音里也都有。音韵学上依照韵尾的不同,又把古韵分为三类:一是无韵尾的韵和以元音收尾的韵归合为一类,叫做“阴声韵”;二是以鼻音收尾的韵叫做“阳声韵”。这里所谓的“阴声韵”和“阳声韵”的区别,完全是从韵尾着眼的,跟声调的分阴阳 (“阴平”和“阳平”)毫无关系。三类韵尾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音韵学上称为“阴阳入对转”,这是因为古人把入声韵归入阴声韵里。当然,这种变化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就可以互有对转的。它分两种情况:一是主要元音一般是必须相同的;二是首先主要元音发生旁转,然后韵尾阴阳对转。依此,我们分析一下“歌”和“干”。显然,二字音变属后一种情况,即两字同为见母[g],“歌”[ge]为阴声韵(属无韵尾的韵,即开韵尾),“干”[g]为阳声韵(属以鼻音收尾的韵,即鼻音韵尾)。在广灵地方方言音系中,原本是通语的 [e]发生了旁转,变成了[an],发音由舌中位转到了舌前位,读“歌”为“干”。由此可见,“秧歌”即是“秧干”,二者名异实同。
其实,除了文献中常提及的“秧干”外,在广灵境内还有多个与“秧歌”、“秧干”发音相近者,如“洋歌”、“洋干”、“洋哥”之类,被当时的艺人书于舞台而留存至今。在今广灵境内共收集到舞台题壁133条,其中有7条含有上述字样。具体如下:
同治元年(1862)广灵县东台村秧歌班在此一乐也 (抄自大湾戏台)
同治贰年(1863)三月十五日 南留庄好地方 □□□□洋哥 □□把□□唱□□□在家良(抄自南留庄戏台)
光绪十二年(1886)□月初一日牛大人□洋歌一乐也 (抄自鹿骨戏台)
光绪廿年(1894)□月十六日洋歌三天□本张 陈老本在此一乐也 李蕊在此一乐也 (抄自杨窑戏台)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初九日刘运洋干在此唱了三天 (抄自涧西戏台)
留洋干人不害羞 吃酒肉之□□□五天洋歌唱完了 此人中□□□(抄自平城北堡戏台)
蔚县城东 秧歌班人 丘家皂人吕发在此一乐也(抄自平城北堡戏台)
在这些题壁中计有“秧歌”2次、“洋歌”3次、“洋干”2次、“洋哥”1次。且有平城乡北堡村戏台一条中“洋干”与“洋歌”并存。由此可以判断,它们皆是“秧歌”之异称。造成如此之多异称共存的原因,除因方言之故发生音转之外,亦与当时秧歌班的艺人们文化水平偏低,书写随意,不求文字的准确性有极大的关联。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广灵县志办公室.(清)合订本广灵县志[M].内部出版,1989.
[4]山西省广灵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广灵县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编辑 赵立人〕
An Analysisof“You Ge”and“Yang Gan”
LIU Xin-li1,2
(1.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Shanxi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2.Research Institute of Opera and Cultural Relics,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Shanxi,041004)
Guangling Yangko has the alternative names of“优歌”and“秧干”in history,but the record of the name of“Yangko”is not seen in relevant documents.With the exhausti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as the following:“优歌”is not“Yangko,”it’s just a general term;“秧干”is only a result of the sound change of“Yangko”occurred in Guangling local dialect.In addition,in the stage wall inscription,the names of“洋歌”、“洋干”、“洋哥”and so on are the result of the low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artists in the theatrical troupe,the randomness ofwriting and the inaccurate us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优歌;秧干;洋歌;洋干;洋哥
K291.25
A
1674-0882(2011)02-0051-03
2010-11-12
刘兴利(1971-),男,山西广灵人,在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戏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