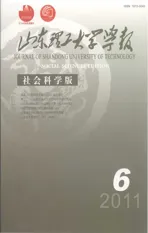五四进步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
2011-04-12李颖
李颖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五四进步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
李颖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一个经历了理想目标、改造手段、依靠力量的多重转换的复杂过程。如果以摆脱民初中国政治社会的困境而作的救国选择为线索,五四进步知识分子完成由一般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这样一种大致相同的思想发展轨迹:选择对青年群体进行文化改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选择依靠平和的民众运动推动社会改造实现社会主义;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时期。尽管五四进步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经历了不同的探索、在不同的时间确立的,但依然可以勾勒出一条总体相同的思想发展轨迹。
本文以五四进步知识分子为摆脱民初中国政治社会的困境而作的救国努力为线索,尝试勾画出进步知识分子们由一般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致相同的思想发展轨迹。
一、困境面前的第一次救国选择:对青年群体进行文化改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辛亥革命后呈现在国人面前的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主落空、封建复辟的极其纷乱的政局。残酷的现实使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不得不调适自己的理想。
(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依然是基本的社会理想
尽管屡经波折,但五四进步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矢志不渝。从1897年参加江南乡试开始,陈独秀逐渐由“康梁党”而“革命党”,直至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上海,其间陈独秀几乎尝试了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所可能采用的所有办法,但仍不得已于1914年在革命受挫、生活窘迫的双重压力下第五次东渡日本。不过陈独秀对于民主主义的向往并没有熄灭,反而更加炽烈。他激进地认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1]71陈独秀这一思想一经在《甲寅杂志》上发表,即引来“读者大病”,皆“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其实陈独秀何尝不爱国,只是此时在陈独秀的思想中民主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存在的基本价值所在。
相对于激进的陈独秀,年龄略小几岁,个性上也更加宽厚的李大钊是一个温和的民主主义者。六年的天津法政的学习奠定了他对西方政治基本价值的认识和认可。尽管袁世凯篡夺政权后,李大钊对民国也发出了与孙中山相似的感叹,“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2]552但从他在1913年前后发表的文章来看,如《弹劾用语之解纷》、《裁都督横议》、《一院制与二院制》、《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欧洲各国选举制度》、《各国议员俸给考》等,李大钊曾经希望以自己的专业学识来匡正这个变形的民主政体。1914年面对古德诺关于中国更适宜君主立宪的言论,为维护现有的民主共和政体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酣畅淋漓地驳斥其即便不是别有居心,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国国情,非吾之纯确国情也”。[2]688即便是后来对时局愈加失望,李大钊本人的激进倾向也日益增长,但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于《民彝》创刊号上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仍然坚持“惟民主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3]339为最适宜的政治。
(二)对青年群体进行文化改造成为实现社会理想的路径选择
第五次流亡日本的陈独秀痛定思痛,此时他相信“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4]221在日本期间他曾经跟好友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4]224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在其创刊号上,陈独秀直言,“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82在宣布远离政治的同时,陈独秀寄希望于那些“新鲜活泼之青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1]82希望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起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之”。[1]73
此时,正在东京留学的温和的李大钊,在国内反袁斗争的洗礼下,越来越增长了激进的倾向,终于于1916年4至5月间深感“再造中国不可缓”,决定回国投身反袁斗争。从发表于其主笔的《晨钟报》上数量众多的以唤起青年之自觉,激励青年奋发为主题的文章,以及他写于日本回国后发表于《新青年》上的《青春》一文的主旨来看,此时的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极其关注青年,寄希望于青年。但李大钊真正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是在1918年他正式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之后。此前,李大钊在反袁斗争胜利后,曾积极为制宪会议和调停府院之争建言,但制宪工作的失败以及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的段祺瑞公然解散国会、对日大举借款的政治现实使得避居上海的李大钊发出了悲凉感叹。“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5]21于是,结束了上海的流亡生活,于1918年1月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后,李大钊也开始了追求民主的新尝试,此时他的一些故交如陈独秀、高一涵等早已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
陈独秀、李大钊等师辈群体的救国选择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寄予厚望的“孩子们”。1915年当时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杨昌济老师的推荐下,开始接触《新青年》,后来毛泽东曾说:“我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6]30周恩来是在从天津赴日的旅途中开始特别关注《新青年》,从此之后《新青年》成了年轻的周恩来汲取精神食粮的重要来源,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1918年2月25日他在《旅日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新青年》“把我那从前的一切缪见打退了好多”。[7]282武昌大学中学部的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4]115《新青年》在其创刊后的短短几年时间中,确实如一盏指路明灯,培育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二、危机之下的第二次救国选择:依靠平和的民众运动推动社会改造以实现社会主义
其实,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或后来的孙中山,他们对中国民智未开的社会现实也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在救亡图存的使命面前,他们都优先选择了投入现实的社会改造之中。五四时期的这些进步知识分子能够幸运地另辟蹊径吗?历史已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一)由远离政治的文化改造回归直面政治现实的社会改造
191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场民族危机使五四进步知识分子们回归到直面政治现实、从事社会改造的行列。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东北的侵略地位,中国面临被日本独占为附属国的危险。随后,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提出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怎应该装聋作哑呢?”[1]268为便于进行政治评论,1918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另办政论性刊物《每周评论》。在紧迫的救亡危机面前,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师辈群体已经回归到了“社会改造”的立场,但此时他们还没有付诸“直接的行动”。相比较来看,由于年龄和经历的不同,学生群体显然要表现得比他们的老师更加激进。1918年,学生们掀起了反中日协定的直接斗争。1918年5月20日,北京各高校2000多人,前往新华门的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李达、张国焘、周佛海等参与其中。尤其是李达组织领导的留日学生回京请愿斗争,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据当时中国方面统计,在3548名留日学生中,归国者2506人,占总数70%以上。[8]14在湖北,由恽代英组织,刘仁静参与其中的互助社原本是一个以自助助人为宗旨、强调道德修养的组织,在全国性的爱国浪潮的推动下也投入了这一爱国斗争,从而刷新了互助社的基本面貌,开始面对迫切的社会问题。
1918年毛泽东也因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第一次来到北京,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并有机会亲身接受李大钊等学者大师们的引导和帮助,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6]34尽管这次运动从规模或效果上都不及五四运动,但它是五四运动的序曲,此后,“北京的学生界,三三五五,课余饭后,在教室、操场、公寓里,以及公园里,凡是大家游散聚坐的地方,无不争论着国事与报纸刊物上的文章”。[9]245而毛泽东回忆当年经历时也说,“我回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6]36
(二)社会主义成为回归社会改造后进步知识分子新的社会理想
回归社会改造后的进步知识分子依然需要理论的指导。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到巴黎和会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国内的五四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国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曾经被认为楷模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厌倦,一时间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了时尚。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悠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9]79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12月,陈独秀发表《新青年》的办刊宣言,明确提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427
据统计,1918年至1922年,发表社会主义文字的报刊占总数的79%,较前增加了3.5倍。[10]192-193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不仅有“科学的一派”(马克思主义),还有“互助论”、“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此时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普遍地交织着多种观念,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表现了一定的倾向性,同时对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还存有许多幻想,社会主义者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1918年7月,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八个月后,李大钊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将俄国十月革命比作是惊秋的桐叶,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从此开始了其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实质的进步知识分子。但即便是李大钊,也曾经把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当成社会主义接受,直至1919年,其思想中还渗透着互助论的杂质。如1919年7月,李大钊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还认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通法则。”[5]285陈独秀曾经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忠诚的信仰者,但巴黎和会对陈独秀是当头棒喝,以致曾经被他奉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威尔逊总统又被他讽刺为“威大炮”,他也开始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好感。他于1919年4月撰文把十月革命与法兰西革命相提并论,认为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1]381但直到1920年初,陈独秀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持论的榜样”。而邓中夏、张国焘、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还对新村主义颇有好感。1919年10月间,邓中夏、张国焘等在北京组织了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曦园”,倡导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而早在1918年夏刚刚从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就曾经和蔡和森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实践自己的新生活理想,一面自学,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与探索,一面坚持亲身参与劳动,每天赤脚草鞋,拾柴挑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1919年春夏间,毛泽东自北京回湖南,又再次提起建立新村的构想,并著有《学生之工作》一文,作为实现这一构想的计划书。1920年初在恽代英的积极筹划下,湖北的利群书社成立,这同样是一个试验半工半读生活的基地。
(三)平和的民众运动成为实现新的社会理想的首选方法
对民众力量的认可,是当时国际国内局势变化的另一个结果。吴玉章对此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经过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冲击旧制度的伟大力量”,“以前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今后一定要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9]61-62吴玉章的认识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曾经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巴黎和会都抱有极大热忱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当天,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指出人类真正幸福,“非得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1]397半年后,陈独秀更是公开宣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1]4281923年陈独秀在回顾五四运动时,曾总结五四的一大优点是“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9]136
正是在五四之后,陈独秀开始了其“平民征服政府”的政治事业。无独有偶,李大钊在后来回忆五四运动时,也认为五四是因为在这一天“中国学生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9]144而值得纪念。他们所谓的“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实力,不依赖代表”。[1]518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相信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此时在天津的周恩来在革命浪潮的洗礼下,于1919年8月发表的《讨安福的办法》中,直接表明“我们自己到底用什么法子去讨他呢?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7]315为了更好地启发民众,成立于五四之前的由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更是走出了城市,走向了乡村和工厂。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和平与暴力之间,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此时更倾向于平和的民众运动。五四后,尤其是结束了其98天的牢狱生活后,陈独秀开始注重劳动人民的力量,但此时的陈独秀还是“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致于造成阶级争斗”。[1]438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也还有“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意向。他说:民众联合起来,改造社会的方法,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很激进的办法”,其首领是马克思,另一派是“较为温和的”,其首领是克鲁泡特金,想“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有意思”。[11]341恽代英在1920年初还认为,“有些人太热心了,动不动便高呼起来,排外哪,革命哪,然而这不但附和的人少,不能成功,便令成功了,亦不见得有什么好效果。”[12]116而远在欧洲的周恩来,也正因暴力革命和温和运动各执一端而陷入困惑,他在1921年《致陈式周的信》中说,“若在吾国,则积弊即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7]490
三、比较实践后的第三次救国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需要向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向再跨出一步,但能跨出这一步的只有少数人。据统计,1918~1922年,信仰社会主义者中只有1/4转向马克思主义。[10]194笔者注意到,许多早期共产党人信仰的确立是从1920年的下半年开始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此前及当年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展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之外,有一些更加现实的助推因素值得提及,即苏联的政策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各省“自治”运动的挫折、工读互助团实践的失败。
(一)1920年苏联的对华政策以及魏经斯基来华加速了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转变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一宣言起初只是从外国通讯社和报刊传来了一些信息,并不为中国方面所全知。直到1920年3月,苏联远东外交委员会才将中文译本交中国政府,次月见诸报端。这一宣言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当时进步青年中的普遍看法是,“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13]127在此背景下,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会晤李大钊后,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与陈独秀、李汉俊等进行了几次座谈,详细介绍了苏共和苏俄的情况。之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就在上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并于1920年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4]10因此,有理由相信苏联的政策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对陈独秀等人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1920年各省自治运动的开展及其最后失败教育了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仍然对改良手段抱有幻想的进步知识分子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希图通过人民制宪、实行湖南人民自觉自治的湖南自治运动。由于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具备像俄国那样进行“全国彻底总革命”的条件,因此,尽管他认为自治运动其实只是一个“次货”,但“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如果连这个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11]470但这场运动最终在湖南督军谭延闿、赵恒惕等的破坏下宣告失败。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深受启迪,1920年11月25日,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通过近几个月来的湖南自治运动,我“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11]548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深切赞同”蔡和森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这一通信,标志着毛泽东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吴玉章也曾回忆说:“1920年底,我们开始了组织活动,1921年4月1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通过‘自治’的失败,使我又有了两个教训,第一是进一步体会到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第二是自治联合会那种地域性的临时的组织极容易为敌人破坏,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的组织,来领导革命。”[9]66
(三)1920年工读互助团实践的失败在不同程度上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抱有幻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在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王光祈于1919年12月在北京创办了工读互助团组织。他们租赁了房屋,集合了数百青年,希望通过平和的经济革命,建立一个无政府的互助的自耕自食自工自读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希望互助团的实践会成为新社会的胎儿。北京的实践极大地带动了各地的建团活动。在湖北,恽代英成立了利群书社。在上海,陈独秀等筹划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则准备在湖南建立自修大学。然而仅仅三个月后,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就因经济原因宣告解散,到1920年下半年,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基本都进入了尾声。工读互助团实践的失败证明了以平和的方式实现无政府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中楼阁,它的失败教育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从中受益,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踏上了科学社会主义之路。正如从外地赶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活动的施存统所总结的,“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不可能的”。[15]269
[1]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
[2] 李大钊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 李大钊全集(第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4]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6] 毛泽东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8] 宋镜明.李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0] 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1]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12] 恽代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3]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选编.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
[15] 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The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Ideological Track of Choosing Marxism in the May 4thPeriod
Li Ying
(The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The process of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choosing Marxism in the May 4thperiod was a complicated one going through the multiple conversion of ideal purpose,alteration measure and dependable force.If the choice of country salvation was taken as the clue to shake off the predicament of China’s political society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the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experienced their ideological track similar to that of common democrats changing into Marxists.They chose cultural alteration among the young group to realize bourgeois democracy;chose to depend moderate mass movement to promote social alteration to realize socialism;and chose class struggle guided by Marxism to realize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May 4thperiod;progressive intellectual;Marxism
G112
A
1672-0040(2011)06-0018-06
2011-09-19
李颖(1976—),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思想政治教育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 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