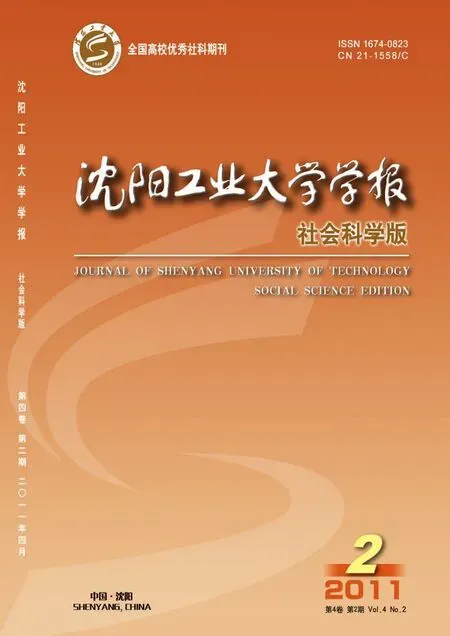综论中西文论融合之初现与儒家思想变迁
2011-04-12王影君
王影君
(1. 沈阳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 沈阳 110870; 2. 辽宁大学 文学院, 沈阳 110036)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领域出现了西论中输现象,中国现代文论随之诞生。表面看来,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具有西论中输带来的突发性,但是任何质的变化均离不开量的积累,据此,早在“五四”之前,一定存在着历史性的演进因素,积累着旧传统的新变。那么,中国文论自身到底经历着怎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具有着怎样的思想内驱动力,促使中国文论在“五四”时期出现了与西方文论的现代融合?本文首先概括中西文论的审美传统,然后通过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自宋明理学起的变迁,力图找到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转化的思想根基,再行论证这种变迁怎样导致了与西方现代文论趋同的审美特征,并最终促成了中西文论现代融合的发生。
一、中西文论不同的审美维度传统
1. 中国文化形成中国文论“求善”的审美价值判断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儒释道并存,或隐或显,共同构成了华夏文化。整体说来,儒释道均承认天地有大道。中国文化整体上对天地人和谐关系的重视与体悟,使得山水人情事理的诗性美成就了文学作品的主要审美特征,并且由于儒家思想的广泛影响,这种诗性美主要以儒家的“善”为价值判断核心。作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正统文化思想,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入世品性,表现出强烈的指导社会人生的实践性特征。儒家主要以孝道贯通于天地大道,讲究天理人伦,主张克己复礼,最终建立起囊括了天地人等众多关系的封建宗法制伦理体系。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个体人被置于人伦关系网中,成为各种关系中身份性的存在。个体的行动和意识受到理性关系的严格制约,要谨慎遵循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按照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人格上追求“内圣外王”的崇高境界。高度理性化的道德修养极大排斥了个体人性的意识自由,社会个体的人生价值必须服从家国集体利益的需要。个体人生存在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的人伦关系中,必须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①总之,家国利益远远高于个人情感,即使个人情感与家国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也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讲究“美刺时政”,恪守“温柔敦厚”的君子之道,宗法道德意识始终至高无上。对应于这样的社会思想,在文学上“文以载道”之说历经千年而不朽,人伦道德美也就是儒家的“善”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标准。
2. 西方文化形成西方文论“求真”的审美价值判断
西方文化源于两希文明,即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奠定了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哲思,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康德,均相信最高真理的存在,形成了追求事物本质的终极式思维方式,注重本质主义二元论的逻辑推理,形成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事物间的联系是逻辑推导式的线性关系,西方社会因此并不注重像中国的宗法制社会那样的网络式人际关系,其文化生存因此也不是伦理关系中的生存,而是个体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是因为具有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而发生联系的,并不是因为血缘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人性的美与善独具价值。所以,古希腊罗马戏剧通常展现的都是人性的善美愿望与理性命运的冲突。即使到后来基督教文化统治欧洲时,人也是作为自我个体而存在的,人性自我需要以自身的人生苦难来单独面对上帝的末日审判。人类因为违背上帝意志偷吃禁果而犯下的原罪,由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一代代传递下来,个体人因为出生而获得了原罪,他们必须在自我的人生中通过对人生苦难的加倍承受来赎清自己身上的原罪,以便在临终之时能够获得上帝的赦免,进入幸福的彼岸世界。西方文化因此带有挥之不去的悲观意识,个体人生也因此带有哀苦情结。在西方文学中,不管是从个体人生的苦难需要艺术发泄这个角度来讲,还是从需要获得上帝怜悯的角度来讲,社会人生真实的情状总是成为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也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价值标准。总之,西方文学传统上就注重艺术对个体人性的追求,以对个体人生和情感的真实表现为重心,个体人性的情感美以及人生的苦难美成为艺术表现的审美特征。由于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关系,西方文论形成了求真的审美价值判断。
3. 中西文化下不同的文学审美表现
在西方,人类先是遭到万神之父宙斯的嫌弃,后是遭到圣父耶和华的驱逐,所以无论是人生好梦的日神精神,还是人生纵乐的酒神精神,整个西方文化都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悲观的人生宿命。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西方文学十分注重表现个体人生的苦难,渲染俄狄浦斯式的命运劫难,企盼精神的救赎与人性的怜悯,强调个体情感淋漓尽致的真实表现。无论是希腊文明留下来的人体雕塑、角斗场以及神话传说,还是希伯来文明流传下来的基督传说和圣经故事,无不展现着一种亘古幽远的静穆、崇高、伟大、哀伤的艺术氛围。
在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建立有序的理性社会为目的,以塑造纲常完美的人格为途径,以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以圣君贤臣孝子贤孙为楷模,以圣人君子为榜样,为社会成员建构起一条指向理想境界的现实人生之路。因为对理想生存状态的追求与信仰,个体对群体性德行标准的日常操守,加上对中庸调和的价值认同,使得中国人的情感境界一直处于知足常乐的氛围里,安天顺命的态度表现在文学中,使得大多作品的意蕴虽有慷慨却没有激愤,虽有期待却没有绝望,虽有欣喜却没有放荡,虽有不羁却没有反骨。含蓄内敛、点到为止的诗意情怀,以社会理性来净化个体情感,以天地大道来规划个体人性,使得文学作品中的事理人情都有一种昂扬的理性美,这与西方文学作品中人生苦难哀伤的底蕴截然不同。对比鲜明的典型例子,就是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与西方戏剧《美狄亚》。同是亲子被杀,《赵氏孤儿》是杀子取义,纲常理性战胜了个体情感;《美狄亚》则是杀子复仇,个体情感超越了人伦理性。
可见,中国传统文学十分注重对社会群体利益的表现,相对忽略个性情感,以人情美为作品的艺术表现主旨,以求善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价值标准;西方文学传统则十分注重对个性情感的表现,以人性美为作品的艺术表现主旨,以求真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价值标准。
二、儒家思想变迁与个体人性意识觉醒
自孔孟起,儒家思想就极力追求圣贤君子式的人格魅力,强调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体修养,压制完全个性化的七情六欲,这种共性利益的追求致使人性个体逐渐成为无我的关系式存在,发展到程朱理学而达到极致。所谓物极必反,对个体情欲的高度压抑,不断引起社会人心的不满,由此返照出走向个体人性觉醒的背反道路。儒家后来的发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1. 朱熹:格万物以穷天理
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格万物以穷天理,强调社会个体对纲常伦理的绝对遵守,将个体人心与天伦大道合一,把个体情欲完全从社会理性中驱除,以道德理性充斥人心,从而将血肉之躯彻底变成理性大道支配下的木偶神雕。虽然统治阶级由于对儒学的独尊而极力倡导程朱理学,个体人心被规整到统一的理性模式,致使社会意识形态达到高度哲学化的一统,但是儒家学说也因此失去了从现实人生到理想世界的弹性距离,也就失去了社会稳定所必须的、最起码的、最低限度的心性自由。社会个体人格修养上的圣贤追求,一下子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日常操守,且这种操守高度德性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抽离了个体的心性自由,遮盖了行为主体真实的个人情感,强行神圣化、仪式化,进而产生理性虚伪和情感苦难。于是,个体人性与理性道德埋下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人性在极端的压抑下必然出现个体觉醒倾向,最终摧毁理学的理性权威。
2. 陆九渊:以人之心体去合万物之理
事实上,在朱熹强调天理至尊时,同时代的陆九渊就提出了“理在心中,心即理”的主张,突出了心的作用,主张以人之心体去合万物之理。这一观点遭到朱熹严厉的批判,他说:“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并指出这种危害是“无大无小”,“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其害甚大”[注]参见《朱子语类》第124卷。。在朱熹看来,陆九渊的主张无疑违背了儒家天地人浑然合一、心物一体无我的伦理秩序,打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群己关系。尽管陆九渊的“心”并未偏离天理道心的普遍性品格及超验性,但是他另一方面又强调“尽我之心”即达天理[1]439。不可否认“我之心”毕竟是个体之心,既可以盛满抽象的理念,又可以充斥具体的情感。从本质论的角度来讲,朱陆的心理之辩在哲学上其实是心与理何者为世界本体的争论:以理为本体,则是纯粹的形而上;以心为本体,既可以是普遍心性,又可以是个体人心。是个体人心,就有转向形而下的可能,在客观上就存在着一条个体自我解放的路径。因为一旦“心”由抽象的儒家善之本心、君子之道的良心走向社会个体情感的具体真心之时,个体人性意识也就被释放出来,必然获得觉醒了。而个体人性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人欲的重新复苏,又因为理学对人欲的极端压抑,这种复苏必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澎湃之势。
3. 王阳明:吾心之良知即天理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崛起,恣情纵欲、追钱逐利成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存天理,灭人欲”带来的道德理性与人欲情感的矛盾日益尖锐,儒家思想面临着社会生存危机。正是为了调和心与理的紧张矛盾,王阳明提出了“心性说”。王阳明的“心”是一个介于朱陆之间的概念。与陆九渊相似,他也认为心即理,具有先天性和超验性,具有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道德理性;但同时他又强调心具有实践性,心的行为个体可以通过道德实践,即“致良知”的过程成就自我,这样的主张在客观上重新拉开了心与理的距离,以心性良知支配的道德实践行为重归理的圆满境界,“致良知”的道德实践充当了个体人心与天理合一的桥梁,从而再度恢复了孔孟以来儒家道德理性与社会实践的弹性生存空间。但是对个体致良知以养善的本性之强调,客观上必须借助于个体对象具体的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心与理的统一,所以,个体人生的社会价值经王阳明的心性说开始具有了存在的合理合法性,那么个体人欲的情感状态也随之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获得自由释放。
王阳明明确表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2]45,将个体之人心与天理合一,肯定了个体自我的利益与价值。王阳明本人还明确表达了对行为个体自我意愿的肯定,他认为:“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注]参见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唐翊问:“立志是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思何去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这意味着一个达到了理的境界的良知个体是可以依照自我心愿自由行动的。王阳明的这一观点被他泰州学派的门人们进一步继承,向强调个体自由的向度发展,其中以李贽的“童心说”[注]参见李贽《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最为著名,影响也最为深远。“童心说”对自我原本真心的强调,释放了被儒家理性长期压抑的感性,充分肯定了个体的生存价值及心性自由。表现在文学上,就是“缘情说”接续发展,在晚明时期热度超越了诗言志的文以载道论。文学领域出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论”,一部《牡丹亭》为情生生死死,情动千古。更有表现市井人生的《金瓶梅》,书中人物本真的欲望和个体情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时,文论发展与文学创作相得益彰,除了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论”外,还有公安派三袁的“独抒性灵”论。在中国传统文论发展的脉络中,它们上承陆机的“缘情说”,下启袁枚的“性灵说”,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个体人性意识涌动潮流。
4. 明末清初民本思想及个体意识觉醒
自王阳明起,中国儒家文化由强调社会集体利益的无我状态,开始正式进入到有我之境。进而,在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又发生了更大的变迁。面对明朝统治的腐化颓败,儒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3]25的思想;顾炎武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注]参见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第13卷,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观点;王夫之将人心向背视为天理,反对“天命”、“道统”和“神道”,主张“不以天下私一人”[注]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5卷。,强调民权。以民为本,是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的共同主张,也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民本思想在极大程度上颠覆了封建秩序的君臣关系,因为“民”的概念内涵已经由孟子时代群体性的意指,发展成具体的所指,成为一个个血肉之躯,即顾炎武所称的“匹夫”[4]18。这样,“民”转化为一个个的“人”,国家的繁荣昌盛与社会每个个体的责任意识紧密相连,不再仅仅是靠圣君贤臣的伦理关系支撑。“民”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新的内涵,标志着作为社会生存主体的个体其自我人性意识开始了历史性觉醒。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意识和个体自由思想由此埋下了极具生命力的种子,这颗种子随后在五四运动时期凭借着西学之风生根发芽。
三、个体意识觉醒与中西文论审美维度的融合
如前所述,中国儒家思想经历了宋明理学与心学的发展后,在思想维度上出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意识的觉醒,打破了中国文论自唐宋以来长期以道统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个体必然最终脱离人伦关系的束缚,最终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社会生活主体走上社会和人生的舞台。于是,脱离了关系生存的个体面对着新的生存境遇,经历着新的生活体验,产生了新的思想感悟,这些全都成为新的审美对象。同时,因为审美对象强烈的个性审美特征,使得相应的文学艺术创造也必然带有浓厚的感性意蕴,个体情感得到充分释放和淋漓展现,“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自然再度得到普遍追寻,文学开始渐渐远离道统束缚,向文学本体回归。文学反映社会人生的真实或情感的真实,必然成为新文化思想背景下的理性要求。于是,儒家思想变迁所带来的个体意识觉醒,促使中国文论出现了由单纯求善到偏重求真的转向。而恰恰是在求真的审美维度上,中西文论出现了彼此交融的内在契机,这是中西文论能够在现代出现融合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国国情的变化又为中西文论的现代交融提供了时代契机,这是中西文论出现现代融合的外在条件。
1. 传统人伦价值崩溃,现代民主意识发展
虽然清朝建立后的强权统治以文字狱为打压手段[5]21,以尊孔复礼、八股取士为拉拢手段,以闭关锁国为安定措施,继续推行封建伦理纲常和君主统治,但是民主自由思想并没有因此泯灭。鸦片战争的失败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国门,《南京条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国家前途岌岌可危。亡国的危机和生存的苦难,最终由一个个个体的血肉身心来体悟,强国保种成为不可推卸的匹夫之责,“国家危亡,匹夫有责”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人们发现,尽管封建制度空前完备的清政府君臣谨守伦理纲常,但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坚甲利兵却是如此的节节败退,可见圣君贤臣的政治理想已经难以为继。夷狄小国入侵天朝大国,皇帝不再奉天承运,国权受辱君威渐失,面对一系列乾坤失序的“咄咄怪事”,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价值出现崩溃,人性个体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开始逐渐得到认可和尊重。于是,个体民主意识伴随着人伦价值的倾颓获得更为深远的进一步发展,何谓天道?何能强邦?何能富国?一系列追问成为时代话题。
很多知识分子,以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带着觉醒了的民主自由意识,怀着富国强邦的愿望,借助着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开始走上西学中输、变法革命的道路。西学中输是中国知识阶层在儒家思想文化发展到特定时期出现内部民主转向需求和制度危机时,面对历史和现实国情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无可否认,西学中输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现代天道论引入中国。中国文化历来以天地有容万物的“道”为核心,以万物一体的“和”为出发点,以天地人伦理有序为生存方式,但是《天演论》一举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人生态度。《天演论》所带来的“落后就要挨打,强国才能保种”的现代认识,成为国人奋发图强的动力。无疑,《天演论》一方面为人性个体的生存和人生奋斗提供了合理合法性,另一方面对儒家伦理秩序造成了致命性打击,从而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辟了思想道路,标志着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朝向民主自由发生了现代化的根本转向。
2. 中国文论由求善到求真的现代转向
伴随着人性个体意识的觉醒,中国文论的重心也发生着由求善到求真的现代转向。因为自我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使得文学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描写空间。人性觉醒的个体情感以及对社会和人生的新体验,纷纷成为文学表现的写实题材。早在明清时期,个体人生千变万化的现实样态、个性情感喜怒哀乐的真实体悟就正式进入文学表现领域,以绚烂多姿的色彩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仔细研究这一时期的诗词、戏曲、小说,就不难发现对真与情的自觉追求[注]明清时期,汤显祖的“至情论”、公安派三袁的“独抒性灵”论、李贽的“童心说”、袁枚的“性灵说”、龚自珍的“尊情说”等文论主张极大地影响了各类文学体裁的创作,情感的表现已经不再局限于诗歌中情景交融的意境,而是具有了独立表现,更加明白晓畅、曲折生动。对情感的展露和对情感真实的追求,一直发展到清末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进而经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现代文论相结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各类文学体裁在情感论的基础上正逐渐发生着古今新变,其中以小说最为明显和卓著。
小说,顾名思义,因为“小”而不登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也因此得以逃脱儒家道统的过多束缚,保留了思想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自由与活跃。小说又因其无所不包的内容、富于变化的体裁、情趣意一体的通俗性,十分适合作为新思想的文学载体。例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明清小说,无不记录着历史真实的社会图景和离经叛道的新思想。从作者的写作目的[注]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开篇明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荒唐言”划开与传统作品文以载道的界线,以“辛酸泪”点明作品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不同的悲剧结局,展现出作家求真写实的创作思想。、创作内容和时人评论来看,这些小说都明显偏离了文学道统要求。首先,人物思想和形象塑造都不尽符合儒家伦理法度的要求,从神鬼妖怪、市井村夫到豪门公子,屡屡辛讽仕途经济,常常违规越礼。其次,从人性角度出发的写实风格,很是有失儒家雅正,却颇有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的味道,可见这点在世界上也是超前的。再者,在情感表现程度上,情真意切爱恨鲜明,淋漓展现个体人生的血泪心酸、宗法社会的世态炎凉,远远超出了温柔敦厚的儒礼范围。最后,时人对这些小说的评论同样超出了传统的思想认识,如脂砚斋评点《红楼梦》、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两部在正统看来诲淫诲盗的禁书,在他们的笔下却均显现出绚丽的至情光彩,可圈可点。
总之,这些作品的诞生很好地证明了,随着个体人性的不断觉醒,因为人性个体情感的“求真”而导致的对儒家正统礼教即“求善”的蔑视和超越,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从这个趋势判断,即使没有后来鸦片战争促成的西论中输,中国传统文论也会不断发生演变,正所谓“世易时移,质文代变”[6]150-155。
但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加速了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转向的步伐,也改变了这一转向本身自然演进的发展方式。当西方以钢枪铁炮、坚甲利兵攻破国门之时,一些最先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毅然承担起富国强邦的匹夫之责[7]57-84。封建统治阶层的腐朽昏聩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唯一的希望和力量就是广大国民,而如何启蒙民众、变革图强,成为先觉者的历史使命。为此,很多人留学海外,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黄遵宪、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曹禺、巴金等人纷纷以文学作为疗救国人、启迪民智的重要途径,提倡、赞成或以实际创作支持文学革命。这一时期的文学,从表面看来继续延续其“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但是道统在内涵和性质上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道”已经由儒家的伦理大道,变成了社会革命大道;其性质也由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为了更好地唤醒民众,就要充分暴露社会的腐朽黑暗和民生的艰辛悲惨,所以真实的社会人生更加成为时代文学必须表现的主题。中国文论的审美价值标准,也因此彻底由伦理求善转向了社会人生求真,从而完成了其现代转向。
3. 中西文论以求真写实为价值标准的现代融合
中西文论虽然都在人类共同的审美天空下,但是截然不同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标准,构成了它们各有侧重的不同的审美维度。但是,20世纪初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一方面,随着中国文论审美价值标准在自身封闭发展的环境下由求善到求真的最初转向,中西文论出现了现代融合的可能,因为求真恰恰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审美标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巨变,将这种可能急速地变成了现实。五四前后,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大潮,西方现代文论涌入中国,于是,中国文论这个原本独立自传的星球产生了变轨运动,开始与西方文论交轨,经历了思想文化选择的多重碰撞融合后,开始了自身现代化的变奏[8]71-79。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提出的新文学标准“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和“人的文学”得到广泛响应[注]胡适于1917年1月在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提倡言之有物,强调情感,反对文以载道。陈独秀于1917年2月在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主张。周作人于1918年12月在第5卷第6号上发表《人的文学》,提出提倡新文学,而新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即“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各类文学作品动用了各种表现技巧和形式,充分暴露出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人生,昭示出以父权为象征的封建宗法制度吃人的本真面目。由此,中国文学在表现目的上由对封建伦理关系的讴歌转向了揭露式批判,在创作方面极力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各种表现技巧。但是,这种吸收是有选择、有目的、有改造的融合,带有中国人自己的对象化关系,而且始终未离开中国的思想文化土壤。
这一时期,各类成功的文学艺术形象无不既带有中国时代特色,又暗含着深受西方文论影响的痕迹。例如,病弱的母亲、哭泣的青年和专横暴戾的父亲成为此时小说中最为常见的文学形象,这些形象既是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又带有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表现特征,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强烈气息,是中国传统小说中难寻踪迹的新形象。但是,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人物的抽象缥缈,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环境品格,有血有肉,这与当时中国文论界强调“血与泪的文学”、“文学要表现社会人生”[注]文学研究会的批评家茅盾与郑振铎各自对此进行阐述,详见茅盾1922年7月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和郑振铎1921年6月发表于《文学旬刊》第6期的《血与泪的文学》一文。是分不开的;此外,死水、泪珠、铁皮屋、火焰等成为此时诗歌中的常见意象[9]410-418;雷、雨、电则成为此时电影戏剧中常见的场景……这些都具有中西艺术相互结合的时代气息,这些形象除了中国传统意蕴之外,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其背后所带有的西方浪漫主义色彩和意象派、直觉派、精神分析等文论特征,也同样有迹可循。
另外,即使是表面上完全舶来的西方创作技巧,在实际运用中也不免要经过中国传统文化过滤,带上中西融合的印痕。例如,心理分析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是西方社会20世纪初崭新的文论成就,心理世界的精雕细琢是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表现技巧。不可否认,正是因为引进了西方心理分析论,中国作家施蛰存才能创作出《梅雨之夕》这篇心理分析小说。但是,这篇小说在心理表现层次上远比同时代的西方作品丰富,那种患得患失的忧伤情调独具特色。作品心理表现层次的细腻丰满和情调的典雅优美,无不映衬出中国传统文化婉转细腻的思维习惯和中国古代诗歌延续下来的意境之美。中国传统诗论的意境美与西方文论的心理分析相结合,形成一种同时具有中西文化特色的文学创作意识,才有了施蛰存笔下如此优美雅丽的现代主义小说《梅雨之夕》。中西文论在这个角度上的完美结合,不妨称为心理意境创作,它融合了心理意识之真与情感含蓄之美的表现手法,融汇了中国文化的雅正之韵,剔除了弗洛伊德理论中力比多赤裸直露的刚硬,弥补了心理分析因西方文化的悲观色彩所导致的作品意蕴先天的晦暗。
在自身理论建构上,中国现代文论一方面继续沿着明末以来的“至情论”向现代发展,并且适应时代的需要把情感的表现与求真的文学目的结合起来,反对无病呻吟,高度提倡个体情感的人性真实,在五四时期借助新文化运动与西方人文思想相结合,形成“人道主义”批评标准;另一方面,主动与输入的西方现代文论相结合,积极改革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技巧,借助西方科学理性的方法改变了中国文论偏重诗性感怀的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与中国现实革命需要相结合,形成“写实主义”批评标准。新的批评标准通过各文学社团间的理论论战不断获得巩固和发展,并通过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不断促成中西文论的进一步融合,使得西方文论在现代中国的应用具有了中国化的特色品格。期间,中国文论变化的特色是大范围、大规模、高密度、高效率,即主要在20世纪初短短30年间,西方文论历经了现代社会几百年间发展的主要成就,轰轰烈烈地涌入中国,不断在中国文坛掀起惊涛骇浪,伴随着中国社会向现代演进的整体步伐,狂飙迅猛地完成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向。
四、结 论
在儒家思想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文论伴随着人性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脚步,自身历经明清之际的缓慢演进,现代转向意识初露端倪。接着,伴随着20世纪初民主启蒙的现实需要,中国文论的审美价值标准由伦理求善转向了社会人生求真,进而在真的价值标准上,因为与西方现代文论价值标准的趋同而发生了中西文论的现代融合。这种融合是从激流勇进式的西论中输开始的,因为西论引进速度的迅猛与骤变,致使中西文论的这次最初融合没能在大范围内很好地磨合,显现出很多粗粝的地方;也因此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论相对照,显现出明显的裂痕。但是不可否认,而且当时各种文学社团激烈论战的历史可以证明,西论在中国的应用始终经历着中国思想文化的选择、吸收、改造与创造,与传统文论有着无法简单割断的承继性,刻有着中国化的风骨。由此可见,中西文论融合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陆九渊.陆九渊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2卷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顾炎武.日知录正史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李贽.焚书:第3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杨国荣.杨国荣讲王阳明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李春雨,杨志.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顾祖钊,郭淑云.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杨乃桥.东西方比较诗学 [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