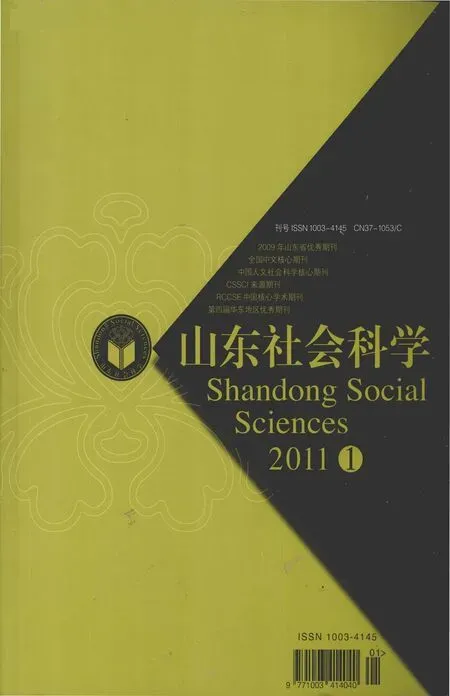鲁迅研究三题《腊叶》:为爱我者而唱的歌*
2011-04-12李玉明
李玉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鲁迅研究三题《腊叶》:为爱我者而唱的歌*
李玉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腊叶》所呈现的鲁迅心境是沉静的,这一点与《野草》其他诗篇不同。“病叶”是鲁迅身体境况的自喻,它使鲁迅再一次真切地目睹了“死”;然而,面对着“死”的却是一颗平和的、充盈着爱的心。
身体;死与爱
从一开始,《野草》的写作就是在心灵世界的大分裂、大搏斗、大震荡中进行的,鲁迅的身心一直处在一种高度绷胀而冲突的状态中,犹如荒海中的波涛一样,没有一刻停息过、平静过。然而,这篇《腊叶》的出现,其中荡漾着的柔和温润的情感,却使我们看到了鲁迅内心世界的另一种倾向、另一个侧面。虽然其中仍然夹带着一种揪心的、不易察觉的哀伤与沉潜,但是与之前的其他诗篇中大起大落、灰暗阴冷的情绪相比,毕竟有些不同了。它是鲁迅低诉的心曲,一曲为爱我者所唱的沉郁而忧伤的歌。
在《腊叶》中,鲁迅以温熙的、饱蘸情感的笔墨绘出了一幅深秋的图景:乍寒的季节、夜降的繁霜,以及在肃杀中凋零飘散的枫叶。这一切虽然给鲁迅以冷威的感觉,使其时时记起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和现实境遇,然而慢慢地聚积着浸渍着的、暖熙而润心的热情却满溢在鲁迅的四周:
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自念:这是病叶呵!
于是,鲁迅将这病叶摘下,夹在《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然而,时光流逝,又是一年的深秋的夜晚,当鲁迅在灯下忽然翻出这片病叶时,它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甚至它的旧时的颜色在鲁迅的记忆中也将消去。这使鲁迅颇感寂寞和悲哀:“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树木也早经秃尽了;枫树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罢,但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
《腊叶》是在舒缓平和的语调中展开的,但鲁迅内心的情感仍然是灼热强烈的。在散文诗中,鲁迅以罕有的笔触精心设计了“病叶”这一意象,并对其倾注了无限的深情。显然,“病叶”是鲁迅的自喻,是其自我形象的一种象征。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鲁迅说:“《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①《二心集》,《鲁迅全集》第 4卷,第 365页。许广平在《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一文中说:“在《野草》中的那篇《腊叶》,那假设被摘下来夹在《雁门集》里的斑驳的枫叶,就是自况的”①转引自《鲁迅全集》第 2卷,第 225页注释[1]。。鲁迅对“病叶”的态度及其无可奈何的心情已透露出这一倾向。综观这篇散文诗,鲁迅对“病叶”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其中呈现出如下几种趋向。
首先,从鲁迅对“病叶”的惊异、珍惜和宝贵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一种漫漫侵袭过来的温情正环绕在鲁迅的四周,这引起了鲁迅内心深处巨大的情感波澜,尤其是在这繁霜夜降、给人以凛冽感觉的深秋,它给鲁迅带来了不易察觉的热情和温暖,“爱我者”的深情在这片小小的“病叶”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我们常常说,鲁迅在同形形色色的论敌斗争时,往往容易将论敌所加予他的攻击和伤害,——哪怕是一些极微小的言论、举动——予以集中、夸大,形成严重的结论,作出强烈的情绪反应,施以果断而猛烈的反击。然而同样地,由于鲁迅对历史过程和现实人生的特殊感受和认识,他对于哪怕是一些极微小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也格外地珍惜、宝贵,而且也会将这种情感予以集中珍藏,淤积于其心灵世界的深处,从而成为他战斗事业的无穷的力量和鼓舞。这是一个心灵的两面,似乎是爱憎分明分离着的,然而却均以“爱”为前提和基础。“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②《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 8卷,第 179页。孙郁先生在这种“爱”里,甚至体味到了一种佛的胸怀和悲悯,因为他是“站在东方被压迫者的角度思考问题”③孙郁:《鲁迅与周作人》,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第 128页。。所以,珍惜“病叶”,在鲁迅这里翻滚着的是巨大的情感热流,透露出他无限的眷恋之情,对于经历了鲁迅这样人生过程而又深深地陷入绝望和孤独的灵魂而言,这是人间“大爱”、“至爱”!
其次,由于战斗和前行的需要,鲁迅有时候是摈弃所谓温情和“好意”的,他认为这些情感的负累会成为一个人的包袱,会销蚀一个战斗者的意志,妨碍他的前进和求索。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客》中,当“小女孩”献上一片裹布、“过客”流露出感激之情时,他马上意识到这种感激和好意的危害——它有可能使“过客”“酱”在这些情感里而忘却了自己的使命,会像“老翁”一样停息在人生的歧路,中止对人生的求索。鲁迅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磋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④《25041l致赵其文 》,《鲁迅全集 》第 11卷,第 477-478页。鲁迅甚至说:“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⑤《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 11卷,第 81页。由于鲁迅在现代中国特殊的位置,由于鲁迅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独特考察,由于他在现实境况中的遭际及一次次地被利用、被诋毁和被打击,鲁迅对人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怀疑人的倾向有所滋长。他甚至说:“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⑥《坟 ·写在〈坟 〉后面 》,《鲁迅全集 》第 1卷,第 300页。所以,他赞美、欣赏“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彻底摈弃无爱的人间,与“鬼”同道,把目光投向有真情的鬼魂,隐隐透露出鲁迅对现实人生的消极评价。他之所谓“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就包含着对人生的和人的怀疑倾向,以及对自我人生道路的悲剧性否定。但是,鲁迅对此又无法证实,他又怀疑自己对人生的悲剧性看法,而且认为这些看法可能与他的年龄和经历有关,是不确切的。显然,鲁迅的无法证实起因于他的终极关怀,源自于其内心深处对真诚人生的巨大渴望。换言之,鼓涌在鲁迅意识底层的是对人的巨大热情。因此,“爱我者”的爱等等人间真情的诱惑对鲁迅仍然是巨大的,他只是仅仅从一个先驱者孤身探求人生道路的角度对其加以摈弃的,在其心灵世界中,尤其在他痛感人世炎凉、孤独寂寞的时候,他对这些情感表现出趋附和吸聚的要求,从根本的意义上说,鲁迅从来都没有否定它们;因此,他渴望真诚的情感交流,渴望真诚的理解与支持。鲁迅借助于“病叶”这一象征性意象对“爱我者”的情感的沉淀、体味,充分体现了鲁迅内心世界的这一情感渴望,可以说,不断地积聚热情和力量是鲁迅写作这篇散文诗的最根本动因。这样的一个绝望而阴冷的心灵,遭遇了这样的“爱”和“热”,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味呢?!
其三,然而,自喻为“病叶”,总是展露出鲁迅思想意识中的消极情绪,至少体现了鲁迅对自我人生道路的悲观估价。这不仅关涉到鲁迅此时的心态和人生哲学,甚至与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看法和死亡的威胁也有关联。查鲁迅日记可知,《腊叶》写作和发表于鲁迅肺病病重期间:1925年 9月 23日至 1926年 1月 5日,大病,历时三月余;1925年 12月 23日,开手写作《腊叶》,发表时注明的时间为 1925年 12月 26日,非一日完成,可能有修订;1926年 1月 4日,刊发于《语丝》周刊第 60期;第二天大病初愈。就此,钱理群先生说:“在写《腊叶》的时候,鲁迅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写《腊叶》,是留给后人的遗言。所以他在文章中说,希望‘爱我者’、想要保存我的人不要再保存我。这也就是说《腊叶》是鲁迅最具个人性的一个文本,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一次生命的思考。……《腊叶》这篇文章写的正是生命的深秋的季节,但却如此的灿烂,乌黑的阴影出现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这是生和死的并置和交融”①。鲁迅也曾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料是活不久的。后来预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②又说:“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③显然,在这里有一种病态的自虐倾向,疾病和死亡的阴影同样造成了鲁迅心理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所以他才会自喻为“病叶”,这“病叶”灼灼的目光也将随时光的转移而消失,并且避免不了随众叶一同飘零的悲剧结局。——“爱我者”的爱是温馨的、诱人的、珍贵的,但它改变不了“我”的现实处境和指向死亡的悲剧命运。更何况,正因为其为“病叶”,更耐不住现实的冷威和抽打,它的结局只能是“飘零”。在这里,可以发现鲁迅对自我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命运的清醒认识和把握,而且这种认识和把握不仅是心态上的,它还包括鲁迅身体的状况。所以,《腊叶》的主旨不是有些论者所谓鲁迅对一些外在事物的感兴和抒发,“是一幅诗人夜读图”。和《野草》其他篇章一样,它同样是鲁迅对自我及其心态的一次调整,同样是鲁迅将解剖的利刃刺向自身的结果。虽然在这一重新认识的过程中,鲁迅发现自己身心两个方面都面临着尴尬而难堪的处境,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是“病叶”,不能珍藏,而且最终将在时光的长河中泯灭、消失,但是,敢于将解剖的利刃刺向自身,敢于确认并正视自己的悲剧性历史地位和难堪的现实际遇,这本身就饱含着一种罕有的勇气和向命运抗争的可贵精神。它表明,鲁迅能够跨越自我个人的悲戚,在一种悲剧性的历史承担中开始向现实从而也是向自身的挑战!
I210.97
]A
]1003—4145[2011]01—0148—03
2010-11-08
李玉明 (1961-),男,山东省牟平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人之子的绝叫”(课题编号:06FZ W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陆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