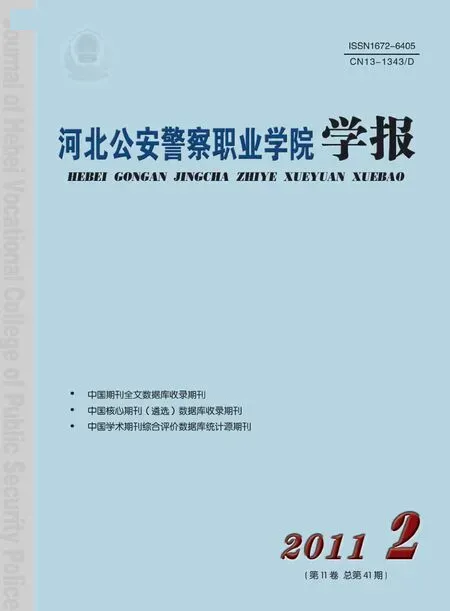品格证据及其有限可采性考量——基于刑事被告人的考察
2011-04-11顾玉彬张军平
顾玉彬 张军平
(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中油国际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38)
品格证据及其有限可采性考量
——基于刑事被告人的考察
顾玉彬1张军平2
(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中油国际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38)
品格证据十分复杂,单纯予以排除不符合事实认知与价值追求的平衡。应考虑采取品格证据的有限可采性,在二者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品格证据;理论认知;现实考量;有限可采性
一、对品格证据的理论认知
品格证据涉及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犯罪学等多学科内容,其范畴和内涵结构极其复杂,关于品格证据的界定也林林总总,视角不一。从心理学的角度,传统观点认为,“品格证据的理论根基是心理学的人格——行为理论,”该理论强调“品格证据包含在从品格到与品格一致的行为之推论中的归纳概况是:人们具有按其品格特性行事的倾向”。而今这种观点已经受到后实证主义者的质疑。质疑者认为,人格——行为理论所植根的现代心理学正面临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错误地采纳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众所周知,近代心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以实验为基本方法的实证研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一度引领心理学走向繁荣。但实证的方法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实证有一个科学的假设,即心理现象如同自然现象,以‘是’与‘否’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特性,而衡量这些特性的方法是建立在二值逻辑之上的概率论及其庞大的统计学。应该说,这种方法体系对心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也有严重的缺陷,心理不仅仅是二值,而是多值;心理不仅仅表现出不相容,更多的是相容;心理有确定的情况,更多的是不确定。现有的方法,并不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信奉唯方法论,以为一种研究采用了实验室方法就一定成为一种地道的科学研究,而不分析其指导思想和观点是不可取的。”在传统心理学受到质疑的情形下,人格——行为理论受到诘难也在所难免。
从证据法角度看,品格证据不被法庭信任主要基于事实和价值两个向度。后实证主义者对“人格——行为”理论的解构显然是不满足于从价值角度论证排除品格证据的正当性,而试图从事实上阻断个体人格与行为所具有的相关性,从而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寻找新的更有说服力的理论皈依。
事实上,心理学方法论的变革极大冲击着传统的理论成果,但同时也为进一步探寻人的心理现象、发现心理活动的规律创造条件,而且也彰显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心理活动确实复杂,无怪乎连心理学的专业人士也慨叹,融合心理学各学科并非易事,“尽管心理学家们有融合不同线索的意愿,但尚未有融合的迹象。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心理太复杂了。”反过来说,或许正是基于心理活动的复杂性,才促使研究者们绞尽脑汁地不断更新研究方法,展开一轮又一轮新的探索。
尽管在具体的人格与行为之间未必能建立必然的逻辑联系,新的心理学研究也不断地把人的内心世界描述成错综复杂、难以企及的智慧迷宫,让普通人望而生畏。但依靠传统的经验性的概率性推测未必不能为司法人员发现案件真相提供哪怕些许帮助。而且,在心理学不断“实现从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观到社会文化模式的心理科学观的转变”过程中,新的理论智慧在警醒我们不要盲从于人格与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时,也在为我们徐徐开启另一扇揭开品格证据面纱的光明之门。我们应该相信,心理学研究的多元化肯定会为刑事司法活动的顺利展开提供更为有益的帮助而不是相反。
从上述讨论中可知,品格证据的复杂性实质上源于人自身的复杂性,我们无法在人格与行为之间搭建必然的因果联系,我们也无法截然区分人格与自由意志,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一次做贼,终生为贼”,但也无法接受“一次为贼,就永远不再做贼”的提法。事实上,在发现事实的前提下,法官应谨慎对待品格证据。既不可草率承认,也不宜盲目否定,而要结合其他证据全面审查。
二、品格证据的域外发展及其启示
从历史上看,品格证据在英美法国家的发展一波三折。易延友对此进行了简略的描述。在英国发展的早期,品格证据普遍得到法庭认可。而从17世纪末开始,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得以逐步确立。至19世纪,“几乎所有英语国家都普遍确立了品格证据不具有可采性的规则”。
令人回味的是,在现代英美证据法上,品格证据排除的坚冰正在逐渐松动。尽管立法对品格证据仍然抱有十分警惕的态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品格证据的可采性普遍受到重视。在易延友看来,英美证据法将品格证据分为三个层次,并分别予以处理。“整体上看,英美证据法对于纯粹品格证据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因此原则上予以排除;对于与品格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犯罪、过错或行为,则限定其可以容许的证明目标;对于构成案件事实的品格证据、作为弹劾证人可信度的品格证据以及量刑程序中的品格证据,则原则上具有可采性。然而这仅仅是表面文字上的规定。剥除其立法表面文字上的排除规定,当可发现其实质上容许的姿态,以及实践中盛行的通例。”
与此相对应,大陆法系国家对品格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始终关注得较少。究其原因,在达马斯卡看来,“可以通过大陆法系对‘自由心证’的钟爱及其特殊的诉讼制度得到解释。”可见,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品格证据主要是通过职业法官的“自由心证”加以衡量并予以取舍的。所谓的排除规则非常少,即使有,“也主要是基于某种价值的考虑,而与确保正确认定事实无关”。
综上,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大陆法还是英美法国家,品格证据是否可采都无法摆脱认定事实与价值诉求的挣扎与矛盾。事实上,现代诉讼文明总是纠结于事实与价值的冲突漩涡而不能自拔。司法者面对激烈的社会冲突也往往踯躅于个案正义与社会公理的艰难取舍。从理性的角度,我们丝毫不怀疑归纳在实践应用中的局限,而在情感上,我们却无法面对犯罪给我们带来的伤痛和数学概率在我们内心所产生的冲动。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在品格证据的取舍之间徘徊。
三、我国品格证据及未来发展
在笔者看来,尽管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带有明显的价值意味,但它与案件事实之间所具有的或然性联系的确让我们难以割舍。
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社会条件下,应当确立适度的品格证据规则,其必要性在于,时至今日,我国鲜有关于品格证据的立法出台,这凸显出我们对品格证据的漠视,而且立法上的疏漏必然会导致司法适用上的混乱。立法缺失与司法失范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法律难题。另外,司法实践的回应也不容我们忽视。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品格证据适用的情形。极为典型的示例莫过于案发后当事人家属组织或群众自发填写并向法庭呈递的所谓“请愿书”,用来表白当事人品格的优劣,以求法庭“公正处理”。这些“请愿书”直接指向定罪的很少,更多地是作为对被告人从重或从宽处罚的情节出现的。如最近广为人们关注的药家鑫案。在不否认具体案情的情形下,药家鑫的同学向法庭提交“请愿书”试图在量刑上为被告人开脱。第三,品格证据规则的“适度”意味着既不是全面排除,也不是一概承认,而是要综合案情予以慎重考虑。具体说来就是充分发挥审判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对品格证据进行细致全面的审查核实,以确保认证的客观全面准确。
而且在我国目前条件下,适度的品格证据规则的适用也具备可行性。一方面,我国刑事司法追求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这敦促我们要对品格证据进行辩证分析,切忌草率和武断,既不能偏听偏信,也不能游移不定;另一方面,我国采取职业法官制度,完全可以综合案情对品格证据进行评判,无需担心英美法国家对陪审员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毕竟,法官兼具职业理性和专业知识,再加上中立地位,有助于对品格证据作出客观评价。
因此,对被告人可以考虑从两方面规范品格证据的适用。
(一)品格证据在刑事法律上的取舍
在规范层面,刑事法上应注意区分犯罪记录和前科,同时贯彻前科消灭制度。关于“犯罪记录”和“前科”,有学者认为,“犯罪记录是对犯罪事实及其刑事判决的纯粹客观记载,前科则是对犯罪记录的一种规范性评价。”“犯罪记录是永久存在的,而前科作为一种规范性评价结论,不一定会必然出现。”笔者认同上述观点,并认为,作为一种评价结论,前科劣迹的法规范无疑会对被告人产生不利影响,而前科消灭制度则体现了我们从实体法律上对品格“入罪”的适度克制。在刑事司法上,对品格证据宜采有限肯定态度。具体说来,就是借鉴英美法国家关于品格证据规则的规定,将品格证据进行分类,对于明显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内容,予以排除,对案件事实可能产生影响的,应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不宜盲目排除。
另外,也要注意通过规范性评价引导品格的非规范性评价,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事实上,对被告人而言,影响其回归社会的,更多的是社会的非规范性评价。我国的报应刑法律文化传统在很长时间内对具有犯罪前科的人都会有负面影响,这对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是极为不利的。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贴标签”理论就是社会非规范化评价的生动表现。其对当时美国刑事司法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二)品格证据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在定罪上,域外国家主要是通过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例外来影响定罪。我国证据规则较为粗糙,已经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品格证据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品格证据仍然可以自由出入法庭,对法官施加影响。具体在罪与非罪、轻罪重罪、事实认定、情节轻重等方面都会发挥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决定案件定性的“最后一根稻草”。确立品格证据规则,肯定会对法官定罪产生一些影响,但影响更为明显的肯定是在量刑方面。事实上,我国目前的品格证据对司法的影响也主要是从量刑上体现出来的。在我国刑法中,影响量刑的情节很多,酌定情节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品格证据。这些证据体现了社区以及他所生活的群体对被告人的基本评价,可以作为量刑的参考性指标纳入其中。另外,量刑程序的改革或许对品格证据的运用提供更为有利的程序性保障。
[1]徐昀.品格证据规则的反思与重构[J].河北法学,2009,(2).
[2]RonaldJ.Allen.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M].张保生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景怀斌.西方心理学百年发展的思路与思考[J].国外社会科学,1997,(5).
[4]高峰强.现代心理范式的困境与出路——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叶浩生.论现代心理学的三个转向[J].江海学刊,1999,(3).
[6]易延友.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易延友.英美法上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基本原理[J].清华法学,2007,(2).
[8](美)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M].吴宏耀,魏晓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9]于志刚.“犯罪记录”和“前科”混淆性认识的批判性思考[J].法学研究,2010,(3).
[10]潘菽.潘菽心理学文选[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D915
A
1672-6405(2011)02-0033-03
顾玉彬(1974- ),男,吉林镇赉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0级刑事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研究。
张军平(1977- ),男,黑龙江绥化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中油国际(曼格什套)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部经理,主要从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等研究。
2011-05-17
王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