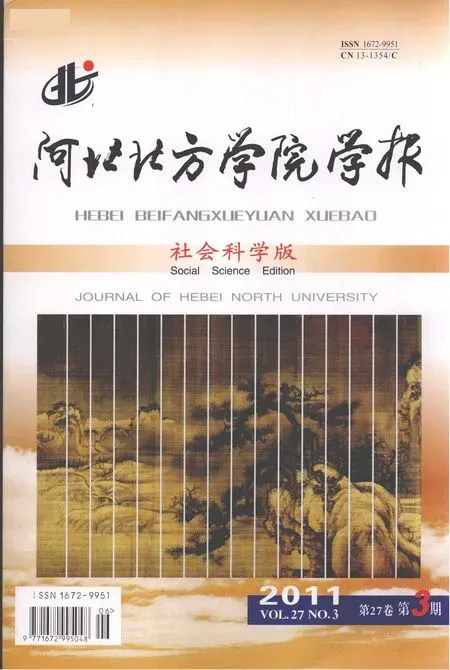格萨尔王与耶稣之人物形象研究
2011-04-11王银辉
王银辉
(1.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2.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焦作454000)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王和基督教神话故事《圣经》中的耶稣分别是东西方史诗、神话中的神性人物。虽然,史学界和文学界对二者存在的可能性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两个人物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在各自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却已根深蒂固,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两位神性人物形象虽没有任何事实上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二者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通、相似之处,而且在相同之中伴随着迥异的不同点,在这些异同之中有着许多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价值。
格萨尔与耶稣都是在各自民族的灾难时刻产生的神性人物,肩负着各自民族的历史使命和信仰使命,二者都是神人之子,有着神幻般的经历,富有极其浓厚浪漫色彩的神异性。英雄格萨尔其理想人格的突出特点是理想性和完美性。这一突出的人格特点是通过其一生的三个阶段展现,即在天界、在尘世安定三界(幼年少年、赛马称王、降妖伏魔、地狱救母救妻)、重返天界。英雄格萨尔爱国爱民,除暴安良,智勇绝伦,战无不胜。他不畏强暴,坚韧不拔。人神合一,幻变无穷。他是大梵天之子,神通广大,有超人的本领,15岁夺得王位,为铲除人间强暴驱妖降魔,他南征北战,东征西讨,雄霸四方,前后征服了十几个国家(部落),完成了人间使命后,重返天国。耶稣,上帝之子,到人间播撒福音,能用语言和触摸的力量治愈疾病,驱除妖魔,显示神迹,以警示人们上帝的天国即将来临,是上帝派遣到人世间传报天国即将来临的“救世主”。两位神性人物除了具有非凡的神性特征之外,他们也都是凡人之子,是血肉之躯。格萨尔虽然出身于王室,由于父亲僧唐惹杰年迈衰老退位,叔叔超同把持朝政,母亲被遗弃,因而他从幼年到少年,过的是打柴、放牧、揉皮子、挤奶、捡牛粪、挖地老鼠的艰苦岁月,为生计奔波在穷山荒沟之中,有时几乎靠乞讨度日,因而格萨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过的是下层贫苦人民的生活。耶稣,相传其父是木匠约瑟,其母是玛利亚,生活在一个微贱的家庭,因而属于社会低下阶级。
此外,二人在他们的显示神迹活动中,都播撒了一种宗教信仰。格萨尔所宣传的宗教是佛教,“佛教自传入西藏以后,尽管和原始宗教——本教有过几次大的较量,一旦立定脚跟,必然要与西藏固有的文化交流汇合,成为西藏封建领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藏族人民性格特征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对藏族的文化艺术,自然也会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1](P157)。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与环境,才酝酿出格萨尔这一东方藏族式的“传教徒”形象。耶稣所宣传的则是早期基督教理论,并且这两种宗教信仰在当时是“非法”的,但是他们所宣传的理念都是为下层广大人民所接受。他们“以对于崇高事物的敏感性为组成部分的内在超感觉幸福似乎是一种未来的奖赏;内心和外表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人类新觉醒的精神生活必须和外界世界情况相适应,这是会自然地逐渐地产生的,但不可能在今生完全实现,只有借助于宗教表象期待其作为神迹般的调节在来世获得实现”[2](P282)。
虽然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固有的传统道德与精神,但是,在东西方两个民族——藏族和犹太民族——这两位神性人物的相同性上,都闪现出两个不同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内在理念。他们虽各自属于不同民族,并且都是各自民族广大人民的典型化的代表,但是当各自民族都处于民族苦难(或是受压迫,或是处于分裂动乱)之中,两个民族的广大下层人民都无法解救自我的时候,便在民族心理与精神中幻化出一种神性人物来拯救民族命运,这种民族心理与精神上的形象“幻化”在民族心理机制上具有相通性。而格萨尔与耶稣便是在这种民族心理与精神的条件下被“幻化”出的神性人物,是各自民族的“救世主”,然而他们却是神、人的“复合体”:一半是神性的,一半是人性的。神性可以在民族心理上有效地证明他们本民族存在的某种“合法性”、“优越感”,不过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隐性”的,但是它却赋予了该民族应受“解放”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人性在他们幻化出来的神性人物身上则是“显性”的,表明一种作为人的个体性存在的可能性,意味着这位神性人物会是他们本民族成员中的一“分子”。因此,这种神性人物是一种个人自我意识和民族集体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民族的内在文化心理的“共享”之物,是各自民族内在文化心理积淀的外在表现。
“作为承载民族审美旨趣,表现民族精神的文艺作品,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是从民族的审美需要而创作的。”[3](P52)东方藏族的英雄人物格萨尔和西方宗教文化中的“救世主”耶稣,这两个神性人物除了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外,他们的不同性更显示出了东西方文化审美价值的巨大差异,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和审美特征。
格萨尔和耶稣这两位神性人物尽管都是天神之子,承担着相同的民族历史使命,向人民传播“福音”(基督教理念或佛教理念),拯救人民远离灾难苦海,引导他们进入“天国”,但是这两位神性人物却走了不同的道路,“目的地”也有所不同。
格萨尔凭借自己卓越智勇、能谋善战、知识渊博以及高尚的品德,赢得了王位与爱情,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懂得仅有决心不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他强调:“那危害百姓的黑色妖魔,若不用武力去讨伐,则无幸福与和平;为了把黑魔彻底来降伏,我又是武力征服的大将领。”言必信,行必果。他一生先后用武力降服了鲁赞、白帐王、萨当和辛赤等四大魔王,并征服了数十个魔国与敌国,用他那非凡的神威和超人的智慧,消灭、制服和收降了数不胜数的妖魔鬼怪,忠实地实践了他曾经立下的“降伏妖魔、造福百姓,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道德誓言。他通过战争,不但巩固了国家政权,而且使国家兵强马壮,民富国强,因此该传奇式人物实质上是以血与火的方式来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王国。与此同时,他把佛教带到人间,向岭国以及被征服国的人民撒播佛教思想,希望把天国带到人间,完成在人间的使命后,重返天国。拿撒勒的“救世主”耶稣,以和平的方式布道、传教,传布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天国即将来临,忏悔吧,并相信福音。”并召集了一群信徒,向人们传教说道。同时,耶稣也显示了不少的神迹,变水为酒,厉声喝止风暴,让聋者聪,使瞎者明,甚至让死者重生,水面上行走,以五个饼及两只鱼喂饱数千人,等等。他预言自己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及死后复活,来宣扬上帝的福音。他宣扬受苦,相信受苦是为了赎罪,是为了能够进入天堂。他还认为:“通向幸福和富裕的正确道路已不再是暴力斗争、严格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是仁慈、和平与忍耐。”[2](P281)在这方面,两位神性人物有着明显的不同。
格萨尔和耶稣虽然都是天神之子,理想中的神性人物,但是他们却在执行各自的神的使命时,选择了不同的途径和媒介物。格萨尔走出的是一条以武力开拓“天国”的道路,耶稣则踏出的是一条爱的道路,但是从某种更深层次的意蕴上,作为民族之神而存在的人的存在,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外现化形态,是一种文化存在物,是不同民族塑造自己理念的形象化载体,实质上他们是作为各自民族的人而存在的神的存在。
两位神性人物选择道路的问题,从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和个性追求方面体现了东西两个民族在文化渊源上的差异性。“耶稣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完美的人而出现的,只需从其本性做自我发展,使他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越来越坚定起来,而不必需要做任何改变成开始一种新的生活……”[2](P286)体现了以耶稣为代表的西方精神文化,从一开始就崇尚自由、个性、民主,推崇人的独立性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博爱。东方藏族——果洛藏族的祖先,以河曲为中心的党项人“俗尚武,无法令、赋役,人寿多过百岁,然好为盗,更相剽夺。尤重复仇,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颜,跣足草食,杀己乃复”[4](P6214)。藏族民族文化中的尚武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自由民主精神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尽管这两位神性人物都是神性与人性的“复合体”,但是西方的这个“复合体”式人物虽然有一些神性的色彩,人性的部分在其中占据了支配神性的地位,他从生到死,显示了人的完整过程。比较而言,神性则退居其人格化的次要地位。在东方神性人物格萨尔身上,藏族文化所孕育的这一神人复合体,则恰恰相反,人性的比例变小了,神性的比例膨胀了,“他时而从天神之子,点化为一只‘上身是黄灿灿黄金做成的,下身是绿油油的绿松儿石做成的,腰是雪白雪白的海螺做成的,四个爪子是漆黑漆黑的黑铁做成的,两只眼睛是花花的花玛瑙做成的’独一无二的小鸟儿;时而由拖着鼻涕的穷小孩,摇身一变为一个仪表堂堂的魁伟男子;时而像孙悟空那样能变出成千的人马来;时而又变化成穷老汉;他的箭能从魔鬼国射到霍尔国,象闷雷般震响,等等。”[1](P166)他在姜岭大战中,格萨尔王杀死了老姜王萨丹,降伏了姜国;在门岭大战中 ,格萨尔王杀死了辛尺王,降服了门国;在这降伏四魔的伟绩中,展现了他一生的大智大勇。他不但能够同各天神通话,收到他们的预言和指示,而且能指挥他们同各魔王作战,最后能够直接返回天国。格萨尔王是古代藏民族勇敢、智慧、力量的化身,是《格萨尔王传》史诗中智勇双全、战无不胜的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岭国君王、佛祖化身。这种浓厚的神性色彩充斥了藏民族文化心理,神性的膨胀终会导致了人性的萎缩甚至丧失,形成了英雄式人物身上应是神性的民族风格,从而忽视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形成了东方的“神性”与“人性”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范式。
东西方民族文化的这种神性与人性上的差异性,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西方文化中那种崇尚民主、自由,尊重自我、个性,推崇平等、博爱的民族文化传统,已植根于西方民族心理之中,当他们处于民族苦难中时,就唤化成为了耶稣这一“弥塞亚”的典型形象,正是由于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所产生的共鸣,才使它保持着艺术上的青春。东方藏族文化的尚武精神,对英雄人物的渴慕情怀,那种潜意识中的个体意识的淡化以及个体人性的“无意”丧失,在身处灾难中的藏族人民心中,也就自然而然地铸造出了格萨尔这一理想神性形象,在某种层次上,这一形象又能真实而艺术地再现该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这种神性艺术形象与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是“互动互应”的。
综上,东西方民族文化中的两个神性人物格萨尔和耶稣,尽管各自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却有着诸多惊人的共同之处,在共同之中也蕴涵着不同民族的相同或相似的民族文化心理与情感,这是人类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作用的产物。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塑造出来的神性人物包含着各自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则从深层次方面反映了各个民族迥异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
[1] 潜明兹.史诗探幽[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2] 〔德〕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张央.史诗格萨尔的美学精神[J].西藏艺术研究,2003,(2):52.
[4]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