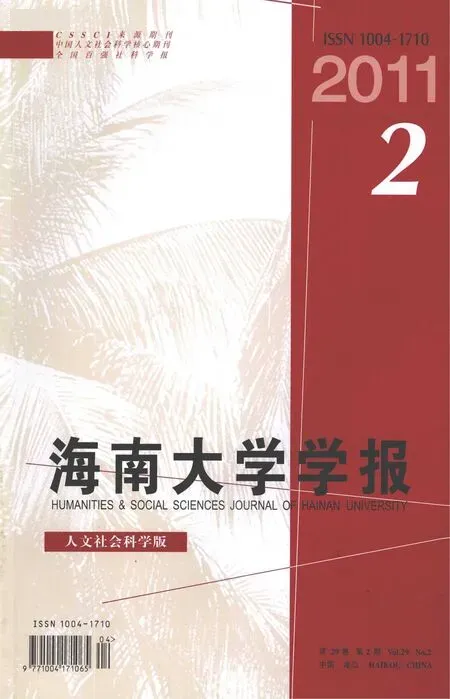论“二大”至“六大”期间中共对苏共党章的“移植”
2011-04-08何益忠
何益忠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上海 200062)
论“二大”至“六大”期间中共对苏共党章的“移植”
何益忠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上海 200062)
“二大”至“六大”期间,中共在制定党章的过程中移植了苏共党章中的很多内容。通过移植,中共很快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但这种移植也给后来的党内民主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
党章;移植;影响
“移植”原本是生物学、医学概念,后来被法学借用,指的是法律的跨国家 (地区)传播、流动,即一国(地区)对他国 (地区)法制思想、观念、原则、法律条文的学习、借鉴、吸收现象。其实,在人类交往史上,不仅有法律“移植”,而且存在政党规章“移植”案例。例如,“二大”至“六大”的中共党章就是移植苏共①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经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 (布),全联盟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 (布),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等。本文为行文方便,统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党章的结果。但是学界在中共党章史研究中,却很少关注这个问题②在现有论著中,学者们一般都很笼统地提到了建党后中共在制定、修改党章过程中受到了苏共党章的影响,但很少在微观层面进行具体探讨。相关论著包括范平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党章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年版;叶笃初:《中国共产党党章发展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肖芳林:《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发展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王金玲:《中国共产党党章发展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版;高放:《党章中某些传统规定探微》,《社会科学》1988年第 2期;张均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章演化过程的几个特点》,《北京党史》1999年第 5期;彭丽花:《党章中民主集中制理论的演进过程及启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 3期;张晓燕:《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修改的启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 1期;黄一兵:《中共二大到六大[党章 ]没有总纲的历史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 5期。。本文拟借用移植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二大”至“六大”期间中苏党章进行比较研究,关注移植过程中的矛盾及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祈望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并推动党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和成长起来的。在中共筹备召开“一大”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就曾来到中国。马林、尼克尔斯基还亲自参加了中共党的“一大”。中共正式建党以后,国内也经常出现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影。如参加过中共“三大”的马林、“四大”的维经斯基、“五大”的罗易。此外,共产国际还经常将中共党员接到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学习苏联革命的经验。因此,在中共建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中国革命间接领导者的角色,一些共产国际及苏共领导人成为中国革命不折不扣的导师。共产国际在中共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使它可以左右中共的方针政策,而且还能够影响中共党章的制定和修改,其结果之一就是“二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共党章与共产国际的核心成员——苏共党章③中共建党前后即开始党章“立法”实践,“一大”由于种种原因仅仅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没有制定真正意义的党章。“二大”终于通过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二大”章程经“三大”、“四大”修改,分别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1927年 6月,“五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又修订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8年 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制定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二部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章》。大致同一时期苏共党章包括 1919年 12月俄共 (布)“八大”通过的《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章程》、1922年 8月俄共 (布)“十二大”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以及 1925年 12月联共 (布)“十四大”通过的《全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党章》。另,本文中共党章内容引自选编组:《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 (从一大——十六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年版;苏共党章内容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 1982年版。以后不再一一注明。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移植”关系。
对比中苏党章,笔者发现中共党章的某些条文直接来自苏共党章。这说明中共党章的制定、修改者在制定、修改党章时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如关于党员资格,中共“二大”、“三大”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四大”党章仅仅将“宣言及章程”修改为“党纲及章程”。“五大”、“六大”《党章》增加的内容有二项:一是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二是党员必须缴纳党费。而同期苏共党章相关条款为:“凡承认党纲、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
在党的纪律方面,中共“五大”党章规定:如果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或有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 (解散组织)”,“对于党员个人,则加以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中共“六大”党章仅作细微的文字变动,即“对于团体是:指责,指定临时委员会,解散组织和党员重新登记;对于党员个人是:各种形式上的指责警告,公开的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开除党籍或予以相当时间的察看。”这些内容与苏共“十四大”党章的相关内容惊人相似:“凡不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和犯有党内公认为罪恶行为的其他过错,应给予处分。对于组织的处分是:指责,上级指定临时委员会,进行普遍的重新登记 (解散原组织);对于党员个人的处分是:党内指责,当众指责,暂时撤销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并将其过错通知行政和司法当局。”
关于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之间的关系。中共“五大”党章规定:“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而苏共“十四大”党章的相关条款表述为:“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委员会不得加以撤销,但须经党委员会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诸实施。”“遇有不同意见时,将问题提交联席会议。同本级党委员会不能取得协议时,将问题提交本级党的代表会议或上级监察委员会或党的代表大会解决。”两相比较,尽管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基本内容却一样。
这种“拿来主义”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党章条文中,而且体现在一些制度、原则中。这说明中共党章不仅“拿来”了苏共党章中的某些“因子”,而且“拿来”了苏共党章的基本“精神”。
首先,中共党章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源于苏共党章。民主集中制是列宁领导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是在俄国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06年,苏共“四大”党章首次明确提出“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1919年,苏共“八大”党章规定“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苏共党章要求“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选举党委员会”,“下级组织的成立必须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才为合法”,“党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而准确地执行”。
尽管学界对中共何时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于处理党内关系尚有争论,但从文本角度,中共“五大”党章即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六大”党章进一步将民主集中制原则界定为:各级党部由选举产生,各级党部应对选举自己的党员作定期报告,下级党部服从上级党部。此外,“六大”党章还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其次,中共党章中有关党员的候补 (预备)制度也来自苏共党章。苏共“八大”党章规定,党员候补(预备)制的“目的在于使预备党员切实了解党的纲领和策略,考察预备党员的个人品质”。苏共“十二大”、“十四大”党章要求“新党员是从受过初步政治教育并经过规定的预备期 (‘十四大’党章改为候补期,下同。引者注)的预备党员中接收。”苏共党章还针对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党员规定了不同的候补 (预备)期。如苏共“八大”党章规定:工人和农民至少须经过两个月的预备期,其他人至少须经过六个月的预备期。在中共建党前的政党章程中,少有对党员候补 (预备)期进行规定。中共建党后,“三大”党章首次出现了候补期的规定:“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五大”党章则缩短了党员的候补期,“劳动者 (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士兵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 (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
再次,中共党章中关于各级党组织的定期会议制度也来源于苏共党章。在中国政党史上,政党各级组织的定期会议并非始于中共④1912年 3月颁布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本会会期,分为全体大会、常会、临时会,皆由总理召集。全体大会每年开一次……常会每季开一次……临时会遇有重大事件方开,无定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后,《国民党规约》规定其党内会议包括每年一次的全体大会,临时大会,遇紧急重要事件不及召开临时大会时开全体职员会议,干事会等。除了全体大会以外,其他会议都无定期。而统一党则将其党内会议分为四种:全体大会、本部大会、全体职员会、评议会。其中全体大会每年一次,全体职员会每月一次,其他会议则无定期。参见章伯锋、荣孟源主编:《北洋军阀》(一),武汉出版社 1990年版,第 250、263、373页。,但就党的章程对各级各类会议的严格规定而论,通过对苏共党章的移植,中共实现了“超越”。苏共党章规定:各级组织的会议主要包括党员大会、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委员会会议。苏共“八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集一次,区域代表会议“六个月召集一次”,省代表会议“每三个月召集一次”,县代表会议“至少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乡的党员大会至少每月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按预先规定的每月召开两次”,区域委员会每月“在规定的日期召开两次会议”,省委员会每月召开两次会议。
在中共党章中,自“二大”党章始,就有了关于各级、各类会议定期召开的规定。如“二大”党章规定:各组每星期召集会议一次,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每月召集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召集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集一次。“六大”党章要求:城乡区委员会之常会“每半月至少一次”,县或市委的“全体会议的时间,可由县委员会自己决定,但至少须每月开会一次”,省委员会“决定自己开会的时期,但一个半月最少需开会一次”,中央委员会则“至少每三个月一次”;县或市代表大会“每三月召集一次”,省代表大会“每半年召集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
二
需要指出的是,移植并不等同于照抄、照搬,也不是简单“拿来”后即万事大吉,而是在“拿来”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即使在自己的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并没有简单地将苏共党章“搬迁”过来,照单全收,而是在“拿来”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再创造。这说明中苏两党党章存在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移植关系。对于中共制定、修改党章过程中的改造、再创造,学界已有关注。如一位美国学者在比较中共“二大”党章与苏共“八大”党章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者确实存在诸多一致的地方,但是“熟悉俄国共产党章程的某个起草者给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章程,而把我所不了解的中国党的特殊情况 (或许是历史上的情况)考虑在内了。”[1]大陆学者王金玲也认为,“二大”党章在充分学习和借鉴苏共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党章的同时,在结构确立与内容表述上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第一,党的各级组织只有四个层级;第二,在党的纪律中第一次提出了“下级执行上级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原则,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与气派;第三,对违反党纪的党员只规定了一种处理方式——开除党籍;第四,在“附则”中规定了党章的修改权、解释权[2]。
其实,对比中共“二大”党章与苏共“八大”党章,除了上述“再创造”以外,笔者还发现:中共“二大”党章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入党手续。苏共党章规定:“新党员由地方党委员会从预备党员中接收,并由该组织的最近一次全体大会批准。”具体履行这一职责的是乡级组织和党支部。而中共“二大”党章对新党员的批准手续则严格得多:在由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得到其许可后,还要“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中共“二大”党章之所以如此规定,一是因为建党初期党员较少,组织简单,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可以直接介入入党过程;二是建党初期,党对于发展党员相当审慎,希望以此严格控制党员规模。
中共“二大”党章在要求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同时,明确了下级组织的抗议权。至少从文本意义上注意到了上下级组织间的民主问题。关于上下级组织的关系,苏共“八大”党章仅仅规定:“一切党的地方组织对于地方性问题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党的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对不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的组织应给予纪律处分。但是中共“二大”党章在要求下级组织“完全服从上级机关之命令”的同时,还规定:“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不过,在未判决期间仍须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
中共根据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改变了关于党的最高机关的规定,使其更加符合中共的现实。关于党的最高机关,苏共党章规定:“每个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选举党委员会,党委员会是它们的执行机关,领导当地组织的一切日常工作。”中共“二大”党章则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的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在苏共党章中,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是各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委员会是执行机关。但是在中共党章中,却存在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等两个最高机关。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代表大会不可能经常召开,无法正常履行其最高领导机关的职权,必须赋予执行委员会最高机关的地位才能应付地下、非法生存环境的实际需要。
即使是受共产国际影响最大的中共“六大”党章,也在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再创造”。首先,“六大”党章改变了苏共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机构设置的相关规定,更为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苏共“十四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书记处——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为各负其责的平行机构。中共“六大”党章却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选举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按照各种工作部门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例如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农民运动委员等等。”显然,在中共党章中,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的领导机构,而组织部、宣传部等则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部门。其次,“六大”党章根据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情况弱化了监督机关的功能。在苏共“十四大”党章中,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党的监督机关,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党增强联共 (布)的团结和威信,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同党员违反联共(布)党纲和党章的现象作斗争,为了从各方面保证苏维埃机关的活动中贯彻党的路线,为了研究改善和简化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办法”。而中共“六大”党章仅用一款,寥寥数十字规定了党的监督机关——审查委员会:“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仅仅监督“财政会计”,其职权远不及苏共之监察委员会。再次,“六大”党章将开除党员的权力下放到支部,并明确被开除党员的申诉权。苏共“十四大”党章规定,开除党员的权限属乡 (区)党员大会,但需经上级党委员会批准。并没有规定被开除党员的申诉权。而中共“六大”党章则规定:开除党员由党支部党员大会通过,党的上级委员会批准,党员不服从开除决议时,“可以上诉至最高党的机关”。最后,“六大”党章之第十四章——“党团”几乎抄袭了苏共“十四”大党章之第十五章——“党外组织中的党团”的内容,但仍然有所保留,没有将苏共党章中“党外机关中党团不直接和下级机关的党团发生关系”的规定照搬过来。
三
建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使中共在制定、修改党章时或主动或被动地移植了苏共党章。但是,对苏共党章的移植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简单、顺利。相反,整个移植过程一直都表现得很复杂,充满着矛盾。据李达回忆,1921年年初,陈独秀曾起草过一个党章,强调党的集中和统一,党员应该服从纪律。李汉俊认为陈独秀是要求党员拥护他搞个人独裁,因此公开反对这一党章草案,并自己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实行地方分权,将中央设定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3]。另据蔡和森回忆,中共“二大”时,李汉俊还致信中央,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4]。
中共“二大”以后,党章制定、修改过程中的争论基本消失。但是在党章实施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却在党内出现。如党章文本要求党员承认党的宣言、纲领,强调入党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但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却规定“对于贫苦工农分子进党,条件要放松些,放低些。”[5]显然更为强调阶级身份的认同。一些地方党组织还将底层民众的结社仪式与入党仪式混同,“照洪家刊香盟誓的办法”接受民众入党[6]55。在党内生活中,“帮规”、“天条”之类的戒律也被带进党内。史料记载,一些地方“处罚同志打屁股是常事,察看与警戒更是家常便饭。”[7]有的地方“对于同志的制找 [裁 ]不 [按 ]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不干就算了,一干就是开除党籍或执行枪毙。”[6]34
党章移植过程中的争论、变异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中不仅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而且还需要将苏联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态中国化。中共成立以后,很快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于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迅速在中共党内传播,苏联党的组织形式也被运用到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共产国际支部组织中。但是,中国国情毕竟与俄国不一样,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具体论述并不一定适合中国,苏联党的组织形式也不一定与中国的组织文化传统相吻合。因此在中国革命中,不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等基本理论问题,而且需要将苏联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态中国化,建立适合中国传统的、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共在移植苏共党章过程中进行的“再创造”,实际上是力图建立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最初尝试。
“二大”至“六大”期间,中共既拿来了苏共党章的“形”,也拿来了苏共党章的“神”,还进行了“改造”、“再创造”,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移植”案例。但是,这种移植却给中共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通过移植苏共党章,中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从中央到基层的,严密的组织体系。高度的组织化不仅为大革命时期中共迅速壮大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且还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崛起提供了组织保证。但是另一方面,在移植苏共党章的过程中形成的集中统一取向,却给党内民主的正常发育带来了消极影响。中共建党前后,一些先进分子将布尔什维克视为“极集权的组织”[8]81,认为列宁“竭力主张党里的集权”[8]148。这使中共在移植苏共党章的过程中,更为关注其“集权”方面的内容,要求全党“有集权精神和铁似的[纪 ]律”[9]。对“集权”的强调尽管有助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却不利于执政时期的党内民主建设。
总之,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共产国际及其核心成员——苏共的影响,“二大”至“六大”期间对苏共党章的移植仅仅是表现之一。在移植苏共党章的过程中,尽管中共也曾考虑到自己的国情、党情,但移植过程仍然充满着矛盾,发生了诸多排斥和变异。对苏共党章的移植,使中共很快转变为一个高度组织化政党,但对于苏共“集权”组织模式的过度关注却给党内民主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
[1]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M].韦慕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1.
[2]王金玲.中国共产党党章发展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39.
[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9.
[4]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133.
[5]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编委会.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二辑[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1.
[6]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46.
[8]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 1集[G].沈阳:沈阳出版社,1981.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91.
[责任编辑:张文光 ]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2nd and the 6th CPC congresses,the CPC transplanted lots of content from the CPSU in formulating party constitution.The CPC quickly grew into a highly organized political party through transplantation,which also brought some negative impact to the inner-party democracy of the CPC.
Key words:party constitution;transplantation; impact
Research on Party Constitution Transplant ing from the CPSU to the CPC during the 2nd and the 6th Party Congresses
HE Yi-zh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eory,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62,China)
K 26
A
1004-1710(2011)02-0120-05
2010-12-03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11YS186)
何益忠 (1968-),男,重庆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